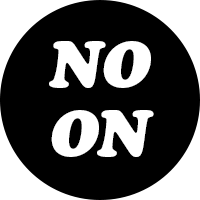口述 | David Ding
采写 | 李炯
今年春天,我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出差。出于好奇,我走访了国际SOS的应急医疗保障中心。在营地大院的东北角,有一栋外表普通的二层小楼,里面急诊室、留观室、化验室、职业卫生办公室一应俱全。意外的是,我碰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Ding大夫个头不高,圆圆的脑袋,声音洪亮,语速很快,外表年轻,但其实已经50岁。问他去过哪些国家?他犹豫了一下说,你该问我还有哪些国家没去过。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极端地区,见证过很多生死时刻。以下是他的经历和见闻。
1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英文名是David,在国际SOS,英文名比较方便员工沟通。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南京本地医院工作过6年。在来国际SOS工作之前,从未想过离开南京,更不用说出境工作。机缘巧合,2003年经朋友介绍,我加入国际SOS,成为一名国际医生,到现在都快22年了。
SOS是国际通用求救信号,而国际SOS是一家国际医疗风险管理公司的简称。1980年代,法国医生帕斯卡尔·瑞贺默被委派到法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他与好友银行家安努·韦西晔,于1985年在东南亚共同创建了一家专门提供国际标准的医疗保健和紧急医疗援助的公司——亚洲紧急救援中心(AEA)。1990年代,经过一系列内部调整和并购,公司业务扩展到全球,1998年正式更名为“国际SOS”。
2003年进入国际SOS救援中心后,我首先被派往扬子-巴斯夫石化工作,这个项目是中德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后来我被派往渤海和南中国海的多个海上石油平台,去过蒙古国奥云陶勒盖的力合力拓的金矿项目。在国内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中国澳大利亚合资金矿项目,我工作了两年多时间;之后又辗转非洲撒哈拉沙漠等多个石油项目,于2011年来到哈法亚油田。2015年回国在核电厂工作两年,2017年到马来西亚石油格拉夫公司以及鲁迈拉油田工作,2024年又回到伊拉克哈法亚油田。
20多年来,我的足迹遍及世界多地。从城市到乡野,从草原到荒漠,从平原到高原,从陆地到远海,工作环境里遇到多民族、多语言、多肤色的人,涉及的项目覆盖石油、矿山、汽车、钢铁厂、核电站、科研院所、超大型施工现场等场景。粗略算算,大约经历了六七十个项目。既有中石油海外项目保障长达6年,也有临时性的跟随勘探考察船深海考察;还有青藏铁路开通实验、翻越唐古拉山、巴彦克拉山、羌塘草原、可可西里无人区等地,这都需要高强度体能和身体素质。
2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跟随勘探科考船深海考察。刚上考察船时,什么都感觉新鲜,什么都很好奇。清徐的海风、和煦的阳光、节律的海浪拍击船体,一切都如诗和远方一样惬意。但这样的情绪并不能持续很久,渐渐海风变得粗粝,阳光变得灼热,海浪拍击船体的声音变得机械而烦躁。在相对简单和限缩的人际空间,心理压抑会与日俱增,深蓝的大海和跃动的鱼群不会再引起兴趣。在茫茫的大海上,孤独和无助才是最大的心理感受,万籁俱寂,只有海浪和发动机的轰鸣。这时候,市井的嘈杂才是人们最大的向往。
对我来说,海上工作只是短期的,通常也是轻松的。而对于常年航海的海员们,面对常年相似的场景和吃不完的海鲜,或多或少会出现一定的心理困难,略显木讷和少言寡语。
在特定环境,特定人群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当家庭或工作不顺,积累在一起就会爆发。我在海上平台遇到过此类心理突发事件,有些员工在突发的情绪波动下会做出出格举动,给本人、家庭、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在平台上遇到过一起惨烈的自杀事件。一名心理有问题的工人,在平台工作时间太久,处于抑郁状态,因为家庭情况想不开了。那天天气不好,海面上下着小雨,他的精神崩溃到边缘,悄悄躲到平台无人的一角,先是抹脖子自杀。一个人自杀不太容易,后来又割了手腕,估计是刀不锋利,一下死不了。痛苦挣扎后,他从十几米高的三层甲板上跳下去,当场摔死。我得到救援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只见他已摔得血肉模糊,脑袋都摔烂了,脖子断了,血管往外冒着血泡,也就没有救援的必要了。
这是我见到的最惨烈的一起自杀。
我们通常是驻点救助,随时待命,平时遇到紧急医疗事件不多,但也遇到过突发情况。有一次我在非洲一个石油管道项目做医疗保障。我跟随工作人员前往撒哈拉沙漠,踏勘管道线路。越野车在大沙漠里行进了很多天,因为根本没有路,每天都在绕行。当到达撒哈拉沙漠的腹地,发现那里居然有一些部落,多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沙漠贝都因人,他们在沙漠里过着游牧生活。
有一天,我们在途中露营。半夜里,一个来自部落的图阿雷格人骑着骆驼来找我们。他很焦急,我和他语言不通,交流半天,才弄明白是来找医生。大概是一个女的要生孩子,需要救助。
作为职业医生,什么情况都要救助。可我明白,当地环境比较差,艾滋病感染的人群众多,我又不是妇产科医生,生孩子难产会羊水破裂或者大出血,医生也有被感染的风险,所以我的心理负担还是比较重。我最担心的是救助不成功,对方很痛苦,我自己也会很遗憾。
在这种情况,防护设施不具备,又是夜里,天很黑。我随便找了一个矿灯戴在头上,匆匆忙忙跟他去了。所幸当时女子尚无明确临盆指征。经过周密安排后,以最快和最安全交通方式转送最近的医疗机构,后来母子平安。
在工作中,我还遇到过战乱,经历过生死关头。有一年去尼日尔执行任务,从国内出发,经迪拜转机到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始飞行都很正常,临近目的地,飞机开始降落时,我们看到地面四处有不明烟火。大约还有20分钟就快落地时,空姐在广播里通报,尼日尔发生军队哗变,军队与总统府卫队发生激战,飞机不能正常降落。
机舱里人们瞬间紧张起来,接着飞机又飞了起来。好在没过多久,机舱喇叭里传来空姐的声音,说通过联系,飞机将飞往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降落,但当时布基纳法索尚未和中国建交,我心里还是有不少忐忑。
又飞了一个多小时,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这个城市我们等候了3天,等到尼亚美局势平稳,机场通航,经过周密安保评估后,我们才又飞过去。
2011年,我第一次到伊拉克。经历多年战争后,伊拉克的安保形势极其严峻。除基地组织活跃外,当地部落之间的争斗也不时发生。尤其在巴格达或者巴士拉就更加紧张,偶发的火并猝不及防,极端情况下,能看到子弹在空中划出的弧线,听到连续的枪击声。我们也有项目员工被攻击导致车辆翻覆、人员受伤,甚至被劫持的情况。
3
有一年在非洲旅游,走在肯尼亚的大山里,我们搞不清楚要走多远才会遇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在山间峡谷里,我们遇到一幢木头搭建的小屋。进去一看,竟然是一名中国浙江青田人开的小超市。卖什么呢?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还有杂七杂八的食品和日用品。
在非洲的山谷里见到黄种人,一个做小生意的中国人,我觉得格外亲近。我问那人,怎么跑这里开超市?他说来非洲打工,参与的建筑工程还没完工,老板的公司就倒闭了,也拿不到工钱。没有办法,他只得来山里搞了个小超市,生意还不错。大山里经常有打猎的、勘探的、探险的人来光顾,到这个店里填加补给。店里东西卖完了,他就骑一辆破摩托车出山,到距离200公里的城镇去进货,一来一去,要跑两天。
为了帮他,我尽可能地多买了很多东西。这次相遇让人感慨,咱中国人真是勤奋,能吃苦。一个人连语言都不通,就能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片天地。有这样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中国不强大才怪呢!国家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策略,让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去,同时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偶尔休假回到南京,我也很忙碌。父母年事已高,白天我要陪他们,晚上要陪爱人和孩子。毕竟很长时间我不能照顾他们,对他们有亏欠的感觉。70后的我比较传统,照顾好家庭是第一位的。
这么多年在海外工作,我也习惯了这个行业。要问我何时回归祖国,我的回答是无奈和适应。《围城》有一句话,“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工作也是如此。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最终结果往往是各种外部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基于自身需要的主动选择。
——完——
作者李炯,喜欢旅行,探索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记录人间百态。
题图:Ding医生在非洲乘直升机执行任务,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