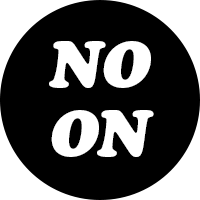文 | 谌程
夏日的一个夜晚,结束最后一单外卖配送,忙碌了一天的张赛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说到20多年的打工生活,他语气平静,谈到读书和写作时,他略显激动。“我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如此20年。”
嗜血的机器
张赛的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打工人,缺席了他的整个童年。他曾向小伙伴们炫耀着父亲从南方寄回来的邮票,也想和爸爸一样去打工。2003年夏天,他16岁时,父亲宣布:“从此你算家里的一个劳动力了。”于是,张赛从河南驻马店出发,搭上火车,转乘大巴,踏进福建晋江市陈埭镇一家卫生巾厂。
张赛的妈妈肯定不喜欢他这么年轻就去打工,但她太早离开了。妈妈曾说,自己没读过大学,就算捡垃圾也要送儿子去上大学。小学毕业的夏天,张赛到亲戚家过暑假,等妈妈接他回家,但一直没等到。那天他跟姨父到河边玩,竟然在水里发现了母亲的身体。“他们都没看出来,我第一个发现了她,挺残酷的。”
说起最初的打工生活,张赛说,“我第一天就被骂了。机器的轰鸣盖过人的声音,组长都很凶,老员工非常拽。他们有技术,你刚来,一个菜鸟,都不理你。”工厂生活和他想象的大不一样。读书时,周末放假要顶着烈日去除草、种植。他觉得农村生活太累,太阳太晒,受不了,只想要离开。打工应该会轻松得多吧。进厂他才发现,这里确实不晒,但环境太吵了,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危险。
卫生巾厂的生产线是一条嗜血的“钢铁巨兽”。张赛被安排到2号机台——一台高约两米、长约十米的机器。他站在轰鸣的“铜墙铁壁”前,眼前是一个个装满卫生巾的塑料筐,当筐子满溢,他就换上新的空筐。这是他的第一个岗位,由于站在小包膜附近,工厂里被称作“小包”,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这也是厂里职级最低的岗位。
“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我觉得小包就是包法利夫人,我就是小包。”张赛笑称。他很快领教了机器的威力:机台上方密布的刀具,稍有不慎就会“咬”住工人的皮肉。“这里没有工人不曾受伤,最常见的伤就是手被划伤。”张赛语气平静。出血不多的话,用无纺布缠一下,连创可贴都不用。止不住血才告诉组长,才会被送去医院包扎。某个夜班,张赛瞌睡了,直到机器突然卡停才醒,他发现自己的手被卷进了钢铁齿轮之间。从医院急诊室出来,没有手术,没有赔偿,只有两个月的基本工资带薪假。那根手指从此再也没能伸直。
后来,同一个位置,同一台机器,一个云南的女质检员手指也被卡了。“她之前还羡慕我工伤能带薪休假,结果轮到她时,工友都说她是故意的。”组长“刘德华”不小心将几根手指伸到机器里面,血从车间地面到医院走廊流了下来。最后,他的中指和无名指被切掉。
厂里的文艺青年
张赛年少时看过不少课外书,曾幻想会在未来遇见自己的林徽因和陆小曼,但是在卫生巾厂,他没有见过爱好文学的女青年。
刚进厂那阵,他把书带进生产车间。机器老出故障,在机修人员赶来之前,他可以偷偷看几页。有个女同事问他,看什么书?他说《羊脂球》,对方哈哈大笑。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有本小黄书叫《羊之球》。
那时候他经常走路去晋江图书馆,距离工厂五公里。当时厂里两班倒,下了夜班,他买上两个包子,边走边啃。在晋江图书馆借完书,走回厂里,倒头就睡。再醒来时,只要手能摸到书,就觉得安稳。有亲戚警告他,外出很危险,如果遇到有人查暂住证,会被罚50元(相当于一周的工资),还有可能遇上黑社会性质的抢劫。张赛笑着说:“一个人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但读了书就不一样,肚子里面好像有10万本书,10万个人陪伴你,有一种勇敢的气势。”
张赛生性腼腆,不喜欢说话,不出去玩,也不参加下班后的活动,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写日记、写诗。那时他喜欢看朱淑真、李清照、狄金森、伍尔夫……他最爱的是张爱玲,后来转行送快递,枕头边上有一本《小团圆》。一天赚了多少钱,他就翻到相应页码,看上几行。
习惯了工厂的噪音后,张赛找到了心中绝对的寂静。他记得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的一段话:“世界的寂静再也抑制不住贪婪,尤其是在它已经几乎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不过要记住:不要去想,只要去做。” 他也曾在机台上看西蒙娜·薇依的《工厂日记》,薇依在书中写道:“你必须以比思考更快的速度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这不仅禁止思考,还禁止做白日梦。你必须每天8小时站在机器面前,封锁自己的灵魂,关闭思想、感觉及所有一切。”
张赛说,人一旦做了工具人,就将做出疯狂的事情,螺丝刀会做出剪刀的事情。他从不自称“工人”,只说自己是“打工的”。他说,如果一个人认为工人顺从、听话、吃苦、耐劳、没有理想,那只是他缺乏对真实生活的观察及沟通。“一个工人,未必会朝着社会发出呐喊,他只是无声反抗、无声生活。”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涯中,他坚持记录、写作,偶尔投稿,总是失败。婚前,32开的日记本,张赛写了足足17本。
多年以来,他的行李一半是书,一半才是衣物。他曾以为,看书高人一等,后来发现,读书不能让他的技术变好,不能改善人际关系,还耽误赚钱。读书什么也带来不了,它像穿堂风一样,偶尔慰藉生命。有五年多时间,张赛不看书也不写字。最近,读完奥地利哲学家魏宁格的《性与性格》,他逐渐找回属于精神角落的自由。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张赛仍能背诵偶像周杰伦的《蜗牛》歌词,但他对蜗牛的坚韧精神有些疑惑。有几年他一年相亲几十次,希望可以结婚,找到一份有社保的工作。
工友温情的消失
张赛刚进厂时,本想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可以给爸爸寄一点,给姨寄一点,没想到厂里要多压一个月工资。第一次发工资也只有200多块。钱太少,没法寄。两年后他离职时,月薪涨到1000块。
二十年间,张赛打工足迹辗转十多家工厂,包括泉州、晋江、厦门和惠州等地,在卫生巾厂“三进三出”。他最后一次进厂,也是最长的一次停留,还是在卫生巾厂,一口气做了三年。
重复的劳作让他疲惫不堪:“每天说的话、吃的饭、穿的衣服、干的工作全部都是重复的。”厂里的老武离职时,留下一句话:“我和这个厂,缘分已尽。”这句话很快传遍工厂。但凡有人离开,张赛都视其为勇士,不是他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面对缠身绕体的庸常,他拥有惊天动地的勇气。
二十年间,工厂和机器也在不断进化。张赛记得,2013年,机器变得更智能,工厂从计时制转向计件制。“以前机器坏了,修个小毛病都要磨半天。改成计件后,大家舍不得让机器停。轴承快爆时有异响,我们马上打电话叫机修备零件,一点都不敢耽搁……这个制度很精妙,它激发你更爱上班,更想生产更多东西。”
自动化也瓦解了工厂秩序。以前组长、车间主任等岗位非常重要,他们对所有机器都门儿清,知道哪里容易坏,机器构造全部清清楚楚。他们也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对底下人十分严厉。工人们也都想着往上爬升。不过,当机器可以自主纠偏后,工人更独立,赚钱多少也就更靠个人能力。计件制之前,张赛的工资大概是3000多块,改为计件后,如果努力工作,工资单能多五百元。
除了更长时间的劳作,工厂的人际关系也开始瓦解。当工伤成为效率的绊脚石,工友间的温情也随之消亡。张赛说,以前工友关系十分亲密,下班后大家特别活泼,嘻嘻哈哈地笑闹。“以前工伤住院,即便那时的我孤僻、格格不入,工友都会带水果牛奶探望我。现在不会再有了。”张赛苦笑。“后来厂里的管理员的手被划伤,一个人都没去看他。这在我刚打工时不可想象。”
另一方面,工人的流动性也特别大。“看厂里效益好不好。如果工资不行,马上就走。”张赛记得,2008年,各大媒体大肆报道金融危机,他这样的打工人只知道“厂子效益不好”。工人们如候鸟般迁徙,“只要听说效益好了又回来,或者换一家厂。”另一个明显变化的年份是2020年,厂子效益奇差,每到星期天就自动放假。工作十多年,张赛第一次拥有星期天。
疫情让我看见周围
2020年1月23日,张赛在武汉,和同伴们一起穿梭在空荡的街道。除了一线防疫人员,只有一些外卖员还在持续奔走。
“大难临头才发现自己非常胆怯。”张赛回忆那时的体验,“不是瑟瑟发抖,而是整个人凝固了。大脑也凝固住了,整个人没有感情。每天就是送外卖,人都麻木了。”疫情之前,张赛自认为对生死豁达,当病毒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时,他第一次感到胆怯。
那个月送外卖,他的收入超过9000元。深夜回到出租屋,一个念头反复萦绕:“难道这辈子就这样嘎掉了?房贷没还完,文章没发表,什么都没做。”
亲历武汉疫情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将日记投给《单读》编辑部。这封邮件撞开了文学的大门,也撞碎了他过去“追求句子漂亮”的写作方式。“疫情让我看见周围的人,以前我都看不见。”张赛说,“以前写空洞的排比句,现在要写身边的人和事。”后来,他陆续写下自己的见闻,周遭的人及其精神世界。关于外卖员、保安、流水线工人的生存状态,当时是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随着围绕平台和系统的争议加剧,张赛的文字成为了解打工人生活的重要样本。
在最近出版的《在工厂梦不到工厂:如此工作二十年》中,他记录了自己打工多年的点滴,写下许多工友的故事。不过,书的编辑和出版过程充满挣扎。编辑指出,他书稿里的内容前后重复,他惊觉,重复的根源在于日记。“日记内容重复,是因为我的生活是重复的,我的感受也是重复的,但是我写日记的时候忘了。”工厂生活极度重复和单调,每天的足迹、生活、做事,甚至吃饭都是一样的,在不停地重复。
出书以后,张赛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但他更有动力写下去。未来,除了努力赚钱还房贷,写作上他还想挑战不可能,“想写一点自己没有写过的东西。”他写过诗,写过文章,曾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22年过去了,他说自己归来还是“蓬蒿人”。
“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如此20年。”他在书里曾写下一段自白:一直打工下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一天,下了班,洗了澡,刷不完的抖音,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你停下来,想了想。你想说说话,不是为了发出声音。你想辞职,不是因为劳累。你想大笑,不是因为天大的喜悦。只是因为,你有了一些想法,于是过去的生活重复不来,未来那样的生活里也再不会有你。以后,不是你在打工,只是你的肉体在打工。
家人活成“网友”
最近,张赛站在一席演讲台上。聚光灯下,他背诵着精心准备的讲稿。家里的双胞胎儿子对他的表现有些调侃:姿态不够放松,磕巴的毛病在镜头里一览无遗。视频下不乏批评,妻子也直言“动作不好看”。但此刻的张赛已学会自我和解——就像他的微信名“一棵树”,长在路边无人观赏,却自有存在的尊严。
张赛28岁成婚。双胞胎儿子出生后,他成了家庭的“网友”。最长的团聚是2020年疫情解封后——他辞去外卖工作回家摆摊,与孩子共处了珍贵的两个月。如今,他在武汉送外卖,家人在十堰,两地工资大概有一两千块的差距。“为这一两千,我不得不活成网友。”他在手机里写下:“还要吸入多少粉尘,还要扛住多少夜班,才能走完回家的路,奥德修斯,请回答。”张赛说,一家人从未完整地度过一个春天、一个夏天、一个秋天、一个冬天。和父亲一样,他再次缺席了孩子们的成长。
2025年2月25日深夜十点半,他在朋友圈写道:“重送外卖,万分惭愧,一切从零开始。”比起在厂里日复一日的劳作,张赛认为,送外卖有一种“假装的自由”:理论上能随时上下班,实际仍要每天奔跑十一小时。如果想要赚到更多钱,最好在雨天多跑单。日收入两三百元,月还房贷两千元,生活的重担依然沉重。
这些年来,张赛收入最高是在疫情前,赶上双11购物节,送快递工资拿过1万多元。
“最大的问题还是赚不到钱,有种无望。”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沉入夜色。当然,他仍牢记父亲常说的两句话:“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年轻时多吃一些苦,年老时多享一些甜。”
采访的间隙,张赛说起他在侨乡泉州发现的一个现象:红砖房都不贴瓷砖。“这事在我们老家不可想象,别人会笑话的。”后来他理解了,这是生活富足后的一种松弛。这种松弛,他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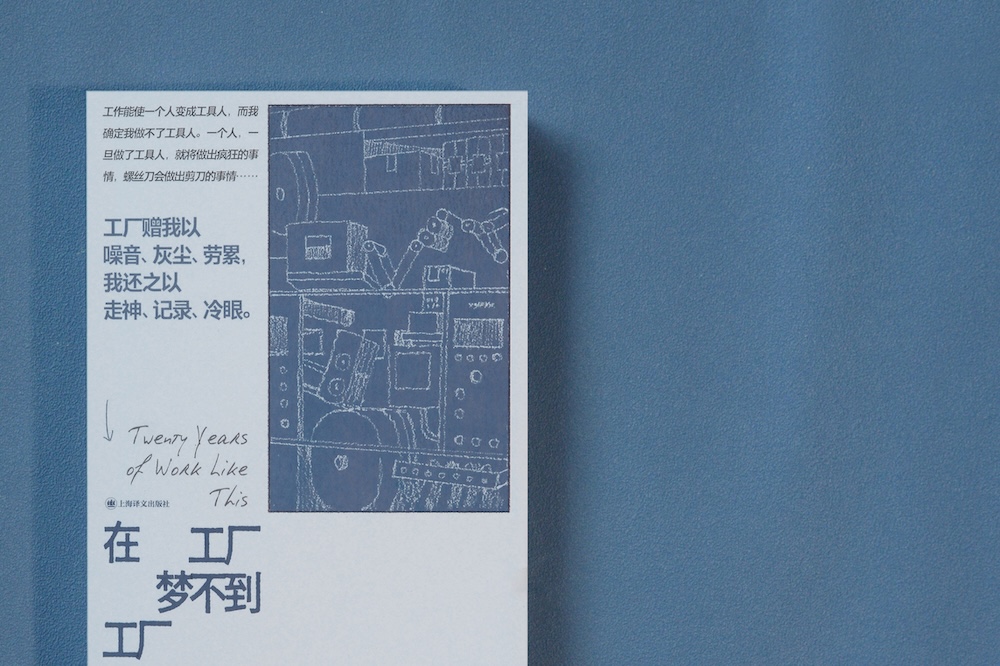
——完——
作者谌程,让我成为青年、森林和一首歌曲。
题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