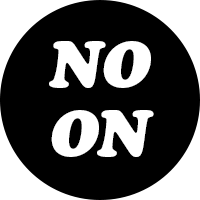采写|明亮
据2024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师队伍建设调查报告》,全国中小学教师离职率已连续五年上升,2023年达到5.6%。他们是主动离职还是被动淘汰?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稳定且待遇不低的职业?离开讲台后,他们都去哪了?
我们采访了几位离职的老师。在她们的叙述里,相似的困境反复出现:有人身兼教师、售票员与安全员;有些人的教案本被数据填报、迎检准备挤占,还要随时解决家校关系;有些人发现自己多年没有输入,只是在重复输出……离开教师岗位,既是对现实压力的被动回应,也是对职业价值的主动重构。此前积累的能力并未随离职消失,反而成了她们走向新生的底气。(以下人名皆为化名)
阿妙:“你一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
1995年出生的阿妙,师范专业毕业时心里藏着一股叛逆劲。“家里人总说,你性格适合当老师。越这么说,我越想逃。”2018年从韶关学院毕业后,她没像同学那样考编,反倒一头扎入旅游行业。她在广州某旅行社做策划、带团,在高铁与景区间辗转。工资比当老师高。不过,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带队,全年没几天能完整休息。
2019年,在旅游行业累到极限的阿妙辞职了,她决定去凉山做支教老师。早在大学时,她常在贴吧看一个徒步爱好者的帖子。那人带着小丑气球走中国,到凉山后却留了下来,联合上海的基金会办起支教点。“他说山里的孩子会把腊肉偷偷塞给老师,说这话时的认真劲,我记了很多年。”
凉山的培训持续了半个月,之后她被分到山顶学校教四年级。30多个孩子大多汉语生涩,“害羞得很,想跟你亲近,就往你手里塞烤土豆,或者把家里晒的玉米棒偷偷放在讲台下。”
最难忘的是某个雨天,山上下不来,四个支教老师断了粮。不知消息怎么传开的,傍晚时家长们踩着泥泞上山,用竹筐背来两筐土豆。“每个土豆都带着泥,我们洗了煮着吃,连续吃了一周。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放屁都带着土豆味’。”
原本她被分配教数学,后来因语文老师离职顶了上去。“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教他们用‘开心’造句,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觉得当老师没那么糟。”阿妙说。其实,凉山的生活很艰苦:没法洗澡时,只能用热毛巾擦身子,冬天烧热水总跳闸,旱厕离屁股只有十厘米。“那些日子让我知道,自己在哪都能活好。”
从凉山回来,阿妙在2020年加入广州某私立小学。这完全是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
私立学校的领导常把“家长是上帝”挂在嘴边。有次一个学生作业没完成,被留堂半小时,家长直接投诉到校长室。“校长没问原因,先把我叫去骂了一顿:要搞清楚谁给你发工资。”更让她难受的是校车任务——每天清晨六点到校接学生,傍晚送完最后一个孩子,已是晚上七点。“感觉自己既是老师,又是售票员,还是安全员。”那两年,她的工资能到八九千,但“心太累了,家长的要求永远在变,领导永远站在家长那边,我像个随时会被替换的零件。”
2022年,阿妙跳槽到广州一所公立学校做编外老师。这里的班级同样40多人,氛围却截然不同。有次课间,两个学生打架,家长冲到学校指责她“看管不力”。校长直接出面:“课间十分钟,老师不可能盯着每个孩子。您孩子先动手,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教他学会控制情绪。”在这里,她第一次体会到“被学校护住的感觉”。
公立学校更重班级管理,学生的心理状态、日常表现都要关注。她当班主任时,每天从早八忙到晚五,中间要盯着学生吃饭、午睡,下班后家长的电话还会追过来。甚至有家长在晚上11点打电话问,孩子在学校开心吗?如果不接,群里会有家长说“杨老师架子大”。
离职的念头在2023年底萌生,当时男朋友决定回海南发展。阿妙站在广州三号线早高峰的人潮里,突然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讨厌每天两小时的拥挤通勤,讨厌家长群里永远传不完的消息。更无法忍受的是,姐姐结婚时,学校以“疫情期间不得离穗”为由不让她请假回去。
但她还是坚持到了2024年暑假。“老师不能学期中途走,孩子们刚适应你,课程进度也不能断。”最后一个学期,学生总问她:“老师,你下学期还教我们吗?”她只能笑着说“到时候看呀”。最后一天散学礼,有个女生塞给她一张画,上面是一个老师牵着一群孩子,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杨老师,我们会想你的。”
2024年10月,阿妙在海南陵水的博物馆做起了讲解员。这里的工资到手五千,年终奖算下来也才五千多,相较老师的工资低了一截。但“每天朝九晚五,下了班手机不会再响,你终于属于自己了。”现在,阿妙喜欢上班的路,两边都是绿植,空气里有海的味道,开着小电驴像在旅游,根本不像去工作。
博物馆的讲解工作竟然与教师经历相通:都是靠嘴巴传递信息,以前讲课文,现在讲文物。她把给小学生讲课文的耐心,用到给游客讲黎族制陶技艺上。有次讲完公开课,教了几十年书的年级长拉着她说:“你真的很适合当老师,你一定要当一辈子的老师。”离开讲台,她更珍视那份认可的重量,也不再纠结六年教龄是否浪费。“当老师教会我的沟通能力、耐心,现在都用得上”。她知道,这是讲台岁月悄悄积累的底气。
尽管已经退出家长群,但许多家长和学生的微信她还留着。四川凉山的学生给她发消息:“杨老师,我考上县里的重点初中了,就是数学有点难。”“杨老师,我爸让我辍学打工,我不想去。”阿妙说,孩子的爱很纯粹,你骂过他们,他们还是会把你当亲人,这是当老师最珍贵的东西。
张佳:音乐课的尽头
2020年的一个午后,湖州一所初中的艺术楼,张佳站在音乐教室门口,听见里面嘈杂的喧闹声。那是午休后的第一节课,天气闷热,五十几个学生刚从主科解脱,把音乐课当成了释放压力的出口,异常吵闹。
“再吵的话,这节课就让给主科老师了。”她忍不住提高声音。一个男生小声说:“老师,我们在前面楼连厕所都要跑着去,好不容易来这儿……您别对我们太严了。”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她多年来对音乐教学的梦想。原来她的音乐课并没有给学生减负,反而成了另一种负担。这年她37岁,教龄刚满14年。
1983年出生的她,中小学偏科严重。中考时勉强踩过普高线,一想到高中还要面对数学和科学,她就满心抗拒。这时班主任递来一个信息:读艺术高中,高考理科不算分。像抓住救命稻草,她懵懵懂懂选了艺术类专业的高中。凭着远超艺术线的文科成绩,张佳考上了大学音乐学师范专业。2006年毕业时,她通过考编考试入职,成了一名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2008年进入湖州本地一所优质初中,一待就是12年。
在这里,她带舞蹈队、参加比赛,拿过不少好成绩。不过,她心里清楚,这些比赛、荣誉,不过是评职称的筹码,是学校考核的指标。音乐学科在学校里始终是“小学科”。排课总在下午第一节,学生昏昏欲睡;期中期末一到,音乐课常被主科占用。有次她去教务处争取课时,得到的回应是“孩子们听听歌放松下就行”。她认真备课,想带学生感受音乐的美好,可台下多数是茫然的眼神。这些被作业和考试填满的孩子,早已没有闲心去理解旋律里的美。她试着带学生听肖邦、贝多芬,可孩子们需要的不是古典和审美,只是片刻的喘息。
而且,她发现自己多年没有“输入”,只是在重复输出。优质课比赛更是让人窒息:抽签后24小时备课,教研员和团队围着她“磨课”,把她的教案改得面目全非,只剩技巧展示和流程设计。“很拧巴,我自己都不想上下去。”
某个下午,办公室同事都去上课了,她一个人趴在桌上,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一辈子都耗在这所学校,老了会不会后悔?“感觉人生被装在透明盒子里,一眼望得到头。”我真的喜欢当老师吗?撇开这份铁饭碗和编制,我还愿意做这份工作吗?
她绕着学校操场走了两天,决定要走。丈夫说,“想清楚就好。”2020年6月,她递交了辞职信。但她也没有完全“转身”,而是前往女儿所在的国际学校任教。一年后,她还是选择离开讲台。
她想“要活得比以前好”。这几年,她做过自媒体博主,卖过保险,现在和女儿一起做播客。2022年,她尝试高客单保险销售。从讲台到销售,她学着分析保单,拜访客户。第一次签下大额保单时,她在咖啡馆坐了一下午。不是因为兴奋,而是突然意识到:原来离开体制,自己也能站稳脚跟。
回顾过去,她发现教师这份工作的待遇其实很好。虽然工资不高,但有公积金和社保。离职后,她不仅要考虑生活开支从哪里来,还要独自处理社保等具体问题。但她从未后悔离职,现在的收入比当老师时高了不少。重要的是,她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用在午休后强打精神走进吵闹的教室,不用再为了优质课比赛硬背不属于自己的教案。
刘星:“体制就像个温水池”
2022年8月酷暑,刘星拿着入职通知书走进东莞一所公立学校。教学楼前的凤凰木开得正盛,她以为握住的是安稳的未来,却没料到里面藏着磨人的砂砾。
2021年,珠三角出现了教师招聘热潮。作为一名非师范专业的研究生,刘星被东莞“免笔试招研究生”的政策吸引。她是广东人,从香港读研归来,对体制内有着某种执念——家里几乎所有人都捧着编制饭碗。入职那天,校长拍着她的肩膀说:“我们学校是四大老校之一,你来了就是骨干。”
她很快发现“骨干”的份量。作为班主任,她要带45人的班级,教语文和道法,还要兼任道法教研组长。劳动课带学生种菜,心理课讲情绪管理,午休时站在走廊值日,放学要跟着家访。家长下班晚,家访总在暮色里进行。她骑着电动车穿梭在东莞的工业区,头盔里全是汗味。
第一年的试用期像漫长的集训。每周两天外出跟岗,剩下三天的课全排满,从早读到晚自习。一次,她连续上了六节课,嗓子哑得发不出声,只能让学生自习。“他们趴在桌上睡觉,我坐在讲台前发呆,觉得自己像台快没电的机器。”
那年冬天,同事指着她的额头说,“你长了根白头发”。回到宿舍,她对着镜子拔下来,忽然哭了。这样突然的流泪,在工作压力过大时也多次发生。编制带来的安全感,逐渐被琐碎的事务磨成枷锁。学校有十几个工作群,消息提示音从早响到晚。她养成了随时看手机的习惯,连午休都睡不踏实——班干部戴着电话手表,随时可能打来:“老师,某某打架了”“老师,有人把饭倒地上了”。
疫情后医院都停用了体温枪,学校还要求每天站在门口用坏了的体温枪给学生“扫一扫”。她举着发烫的体温枪,看着学生们机械地低头,觉得很荒诞。“他们好像不关心有没有用,只关心你有没有做。”
教研组长的工作成为压倒骆驼的稻草。有次校长让她三天内备一节参赛课,逐字稿要对应PPT,改稿就得改PPT,她熬了三个通宵,试课时却被全盘否定。“报告厅的灯亮到凌晨,我自己摆桌子、调设备,对着空教室试讲。”她记得那天结束时,天边已经泛白,她在走廊撞见清洁工。对方问:“老师又加班?”她点点头,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身体不断发出抗议。2023年体检,她查出身体问题,需要手术,医生说“和长期压力有关”。手术前一天,她还在群里处理学生纠纷;手术后第二天刚苏醒,就接过同事递来的手机,家长又在问孩子的作业情况。“没人说你先休息,好像老师就该是铁打的。”
2024年暑假,刘星跟校长说,想继续带高年级。“我性格不适合一年级”。但开学前一周,她收到调令,被安排去带一年级,还要提前两周返校培训。那天她正在广州逛街,接到消息,手心瞬间冒汗。她给老公打电话,对方看着她通红的眼睛说:“辞了吧,我们回广州。”挂了电话,她就给校长提出离职。说出口那瞬间,她觉得胸口的石头落了地。
同事们并不意外。这几年,学校里合同老师干满一年就走的越来越多。“外面赚得比这多,还不用应付这么多事”。而编制内的老师大多选择“摸鱼”:少接任务,少担责任。
离职后的六个月,刘星在美国欧洲转了一大圈。咽炎没再犯,心脏也不疼了。她终于能睡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看工作群,额头的痘痘慢慢消退,体重从80斤长回了正常水平。
偶尔她会收到学生的消息。有学生升了初中,会发来月考成绩;有家长给她寄东莞的荔枝,附言说“你在时孩子总说你好。”
“其实体制就像个温水池。”她说。刚开始觉得舒服,慢慢发现水在变烫,想跳出来又怕外面冷。真跳出来了才知道,新鲜空气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她也在思考,是否要重新回到讲台。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