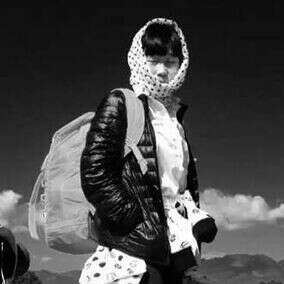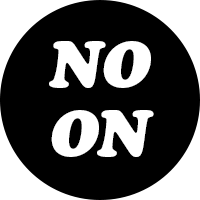图 口述|蔡山海
采访|李响
2023年,蔡山海关掉经营稳定的照相馆。此后的三百多个日子,他以独立摄影师的身份,穿行八万多公里,行走在中国的各个角落,用镜头创作出《逍遥三章》,其中的不少照片赢得粉丝和摄影师同行的热烈反馈。2025年他再次出发,这一次他驶向东北,一片“真正能代表中国普通县城生活”的土地。他曾深夜驱车在有猛虎出没的乡道;在老厂区里听退休工人讲述三线往事;在练歌房、小舞厅里体验当地人的消遣娱乐;和铁路旁排练的大学生乐手谈天说地……他在创建一份属于当代东北的影像档案——那里有魔幻的现实、流动的生命,更有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未来三到五年,他要把镜头一直对准东北,和东北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以下是他的口述。
从漠河的秋到丹东的秋
蔡山海这个名字,是我给自己改的,来自一句歌词“我依赖大海,并且信仰高山。”20岁时家人送了我一台卡片机当生日礼物,冥冥之中让我跟摄影产生了缘分。
我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北,九月这次是冲着东北的秋天去的。我走了三条线,丹东到绥芬河、哈尔滨到阿尔山、根河到漠河。我看到了漠河的秋天、阿尔山的秋天,丹东的秋天……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流转,我一直在看秋天,十一月初再出发就是去拍冬天了。
最近三年的春节,我都是在东北过的。今年春节,我在路上,好多人邀请我去他们家过春节。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待在东北,我的回答是,我在东北得到了强烈的情绪反馈。
东北人很直接,没有太多防备心。举个例子,我曾在长江边看到有人偷偷摸摸捕鱼,我就停车和他们聊天,问有没有鱼、捞什么鱼,对方回答“不知道、不清楚”。这种冷漠让我很尴尬,我明明看到他们戴着头灯、拿着渔具。在东北的同江市,人们给我的反馈完全不同,那些捕大马哈鱼的人不仅和我聊天,还问我要不要吃,完全不把我当外人,恨不得拉我去体验捕鱼生活。我在甘肃、山西走过,当地人也很热情,但还是比不过东北人。东北人甚至会说,“晚上住我家也没事,虽然条件简陋些,你只要不嫌弃就行”。
我在东北一次都没有被宰过,东北人永远都是热心肠。如果把东北比喻成一个异性,我想去东北,就像想去这个异性的家里。她永远热烈欢迎,你说什么她都有回应,这样的异性很难让人不喜欢。所以,我想说,我要和东北“谈三年、五年恋爱”。
熊与虎
我是江苏人,在我看来,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太过发达,无法代表中国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县域情况的,除了中原,就属东北了。东北的农业、工业、山脉河系,以及人口流失、生育率走低等特点,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东北的振兴大概要靠旅游业。最近我在大兴安岭采访了很多民宿老板。他们都说,没有哪年的九月像今年这样火爆,从一号到三十号,九月的根河一直人满为患。我想大概是因为小红书,人们看到大兴安岭的秋天如此美。这里的旅游业明后年只会更火。
东北的每个城市都有记忆点,我最喜欢的是抚远市。抚远在中国版图大公鸡的最东边,一个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城市。很多年轻人为了体验东极村的第一缕阳光来到抚远,那里还有处于中俄边界的黑瞎子岛。我是一个历史迷,黑瞎子岛在清朝时都是中国的,后来一半割给了苏联。很多游客来黑瞎子岛,除了眺望中俄边界,还来看熊。岛上有个动物园,养了200只熊,黑瞎子岛就是以此命名的,听说俄罗斯那边还有很多没被圈起来的野生熊。
抚远这个小县城既有文艺,又有旅游景点,还有我感兴趣的人文,三部分结合得很好。
大兴安岭的虎林市也让我印象深刻。虎林有个珍宝岛公园,是东北虎聚集生存的地区。我去那里,是为了跟拍一个从浙江回老家的年轻人。他和家人在珍宝岛公园不远处生活,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偏远村子,离最近的镇子开车也要五十分钟。我看他们在冰面上打洞捕鱼,还跟当地人一起捕林蛙。离开他们家时,他们叮嘱,附近有老虎出没,咬死了村子上五六户人家的看门狗,还给我看了之前发现的老虎脚印。当晚,路的两边是黑压压的树林,冬天路上还结了些冰,我不敢开太快。没多久,恍惚听到一阵低吼。为了辨清声音,我摇下车窗,那是我从未听过的声音。我很肯定,那大概率就是野生东北虎的叫声。那段路一点光亮都没有,车上就我一个人,我处于一种又紧张又刺激又兴奋的状态,甚至汗流浃背,就这样开了二十多分钟,才脱离了危险地带。对我这个来自平原的人来说,那次经历太魔幻了。
生来就为了离开东北
东北有很多带地方特色的“小舞厅”:三四十平的屋子,一个小舞台,想唱歌就上台唱,没人会管;舞台下的卡座可以点啤酒,卡座和舞台之间是“跳舞”的地方,也是当地人消遣、喝酒的空间。东北还有很多练歌房,从辽宁到黑龙江,我一路走来,发现整个东三省都有这样的练歌房。有一次我很好奇,想知道什么叫练歌房。我是下午进去的,看见一个穿着暴露的大姐。进去我就懂了,原来就是 KTV 嘛,我觉得南方是没有练歌房这三个字的。
东北老龄化特别严重,在小县城遇到年轻人的概率非常低,就像看见大熊猫一样。小地方的人口被更发达的城市吸走,一层又一层虹吸。每次遇到老人,我都会问:“您的子女现在生活在哪里?”问了有上百号人,大多数年轻人的去向是城市,或是南方,很少有大学毕业后回本地的。在黑河学院,我遇到了一帮搞音乐的年轻人,当时他们在铁路上排练。他们大部分是东三省的,提到未来的打算,大多表示想去南方,觉得那边机会多。所以我更加确信:东北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离开东北的。东北人就像候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南方,只有在春节时才回东北老家。
一个人在路上
我的童年比较自由,流动性也很大。2014年,家里托关系给我找了份工作,很安逸,安逸到让我害怕,一年后我辞职了。我用仅有的积蓄买了第二台相机,背起背包,走了一趟西北,去了一趟拉萨。这次旅程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自由。
2019年我大半年都在路上,去了中国很多县城,见识了各式各色的生活,拍摄习惯也发生改变,摄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走到哪就拍到哪。2021年开始,因为疫情我没法自由出行,就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照相馆,儿童、婚纱、婚礼、写真、活动,什么都拍。我的店运营得不错,一年能稳定收入二三十万,但是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大概是没人和我聊宇宙吧。
2024年,我关掉照相馆,开着我那辆老车再次出发,用“平推”的方式记录中国。我是个虚无主义者,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做的事是否有“意义”,直到我拍的那些照片陆续被人看到:把心事写满庭院的福清老人、在村里砌城堡的陈天明、在溶洞里翩翩起舞的守窖人……我在小红书上分享了很多“走地仙”的故事。当有人可以为这些影像和文字停留片刻时,我想,终于有人可以和我聊聊宇宙了。2025年初,我开始了东北的拍摄,继续看山,看海。
有人会问,这么长时间,一个人在路上,会不会有心理困境?2019 年确实是我的生命的低谷,但近 5 年的生命状态,可以用源源不断的正向来形容。一个人在路上,我是乐在其中。而且我不断有收入,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件内耗的事情。
我现在的收入来源很杂,自媒体账号占一半,其他占一半。我的社交平台粉丝量还可以,流量也不错,很多手机厂商找我合作,比如华为、OPPO 都会找我去拍摄手机样片。2023 年是最好的一年,很多手机厂商寄样机给我,我卖手机都卖了 20 多个。去年就只卖了十来个,今年只有三四个。我还有一些杂志约稿,时尚杂志委托拍摄的收入,也接一些私人拍摄。去年我在路上三百多天,总共花了十七万,还存了十三万。今年只有去年的一半。我对自己要求不高,能平掉支出就行。
有些摄影师不愿抛头露面,不经营自己的社交账号,自然无法获得社交账号带来的收益。我肯定是有商业思维的,而且执行力强。我是个长期主义者,不会脑子一热冲动做事,所有事情都是有条不紊地计划,觉得时机到了、准备充足了才会去做,做事也会比较持之以恒。只要定了目标,哪怕付出生命也一定要做到。
未来我不可能一直在路上,最近我决定搬去杭州生活。等我五六十岁了,或许还想去北京发展。我希望自己的生命状态一直都是有所期盼,有所变换的。我很担心自己的生活变得一成不变。































——完——
作者李响,界面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