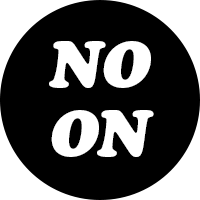采写 | 明亮
大部分城市人每天都会穿过小区的大门上下班,但有多少人曾停下脚步,留意过那位身着保安制服的大哥,或者大叔?他们每天都在忙什么?他们的主要任务真的是维护小区的安全吗?除了偶尔的停车纠纷,这些近在咫尺的陌生人和小区居民还有哪些交集?
这些疑问或许曾在你头脑里掠过,而真正的有心人则把保安当成严肃的社会学主题来研究。2016年,何袜皮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她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我几乎没有见过小区保安。中国的治安状况良好,而保安数量却不断上升,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这是为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何袜皮从2017年夏天开始在上海展开田野调查,一直持续到2018年。多年之后,她将自己2019年参加答辩的英文博士论文改写成一本中文图书《大门口的陌生人》,该书已于近日出版。
扮演“保安”
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是参与性观察,因此,何袜皮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田野调查道路——不仅要观察保安,还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首先来到一家物业公司实习,融入保安的过程并不顺利。她回忆说:“起初他们对我有些陌生和戒备。物业公司是甲方,保安是乙方。他们担心我是来监督他们的。我即便解释了我的研究目的,他们也并不完全理解,有些人以为我是记者。”
保安队长的更替,给何袜皮提供了突破机会。第一位队长不太配合,不愿交流,甚至有些抵触。他被调离后,接任的队长擅长社交,他允许并鼓励保安与何袜皮交流。
“下班后我常和他们一起吃饭,逐渐熟悉起来,他们也愿意分享,包括一些敏感话题。”制服里的大哥们逐渐展示出各自的性格,何袜皮慢慢能够描绘出他们的人生画像。作为社会的“蓄水池”,保安岗位容纳了各色各样的人。比如吴宇,过去曾是一名数学老师,身负债务,成为失信人后逃离家乡;比如方志,身负巨额高利贷债务;还有商人李云,落魄后不得已来到小区做保安,他梦想攒够钱回到兰州开一家烤鸭店。在一个笼统的保安称谓之下,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生。
让何袜皮意外的是,很少有人认同自己的职业是一名保安,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在都市空间里扮演“保安”的角色。李纳曾对其他保安说:“我就是一个农民,他是卖猪饲料的,你是一个厨师。”
除了这些特殊个案,何袜皮发现,构成这个行业的主流人群,是不善言辞的普通农民工,他们来自欠发达省份的农村或者县城。不过,在当下,因就业形势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失业白领也加入保安的行列。
温水煮青蛙的职业
“再不结婚就完蛋了!”2019年,“独生子”小亮对何袜皮说,再过两年就回老家结婚,但直到2024年,他辗转到另一个上海高端小区,仍然在做保安。
大多数年轻保安面对的最大焦虑之一,是家人的催婚。一过25岁,找对象就成了人生头等大事。小区保安作为一份职业,没有福利保障,工资低,社会地位低,没有发展前景,往往处于大城市婚恋市场鄙视链的底部。
此外,这个工作大部分情况下全年无休,没有任何周末或假期,一天13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导致保安们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城市空间寻觅爱情。一些人谈起了网恋,一些人回老家相亲,但大多都以失败告终。在城市里找不到对象,在家乡找不到工作,是他们的两难处境。
保安工作“最大的优点是不难,最大的缺点也是不难”,这句话令何袜皮印象深刻。保安的大部分时间是应付琐事,常规的有守门、巡逻、管理停车,偶尔也帮业主、物业或居委会干杂活,比如跑腿、搬重物、参与打击群租房等等。
有人曾以为保安只是暂时的选择,最后发现自己一旦做久了,就很难再胜任其他工作。杭静说,“这不就是温水煮青蛙嘛,等有一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来不及跳出锅了。”他曾坚定地告诉何袜皮,不打算继续做保安这个没有前途的工作,甚至主动辞去了保安班长的工作。不过,在带了未婚妻回到上海,找工作多个月无果后,他在另一个小区当起了保安。
何袜皮认为,当一份工作没有挑战也缺乏创新性,不需要太用脑,甚至不需要集中注意力,每天机械性地完成体力活,收入与个人绩效也脱钩时,人们很容易产生这种人生被消磨的无力感。这一感受也获得了更多群体的共鸣。
当然,这种感受也因人而异。有些中老年保安认为,这是最适合他们的工作,不用动脑、没有压力、体力活也不重。一位经营过烤鸭店的保安李云说:“以前当老板时压力大,许多事情要自己决策、承担后果,现在反倒心静了,可以想些自己的事。”而对于“想要拼搏的年轻人”,保安工作会让他们感到“浪费时间、学不到东西、缺乏成就感和收入增长”。
保安行业也与宏观经济脉搏紧密相连。何袜皮做田野调查是2017到2018年,当时经济形势不错,外卖行业蓬勃发展,年轻人更愿意去送外卖或快递。和做保安相比,收入更高,自由度也更大,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当时保安行业很难招到或者留住年轻保安”,何袜皮说,但这两年经济下行,外卖行业饱和,一些年轻人又回流到保安行业。
中产为何恐惧?
梳理历史,何袜皮发现,2010年是保安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当年实施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正式承认保安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1984年,深圳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保安公司,此后多年,保安公司名义上均由公安局承办和管理。而从2010年起,大量民营资本涌入保安市场。因为难以与国有保安公司竞争政府、银行等重要场所的业务,民营保安公司便转向小区和写字楼,“一方面接手原本由物业自行招聘的保安业务,另一方面开拓以往没有保安的小区”。
何袜皮最初的疑问是:为什么在犯罪率持续下降的中国,保安的数量却在上升?多年调查和研究后,她发现的答案是:伴随着中国房地产走入黄金时代,“安全”被包装成一种商品,变成业主,或者说中产的需求而被贩卖。
何袜皮认为,保安之所以成为中国都市小区的必备品,其症结在于恐惧。她引用相关研究指出,居住在越安全小区的人,反而越容易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一方面源于对经济地位下滑的担忧,他们要求更严格的安保和更封闭的小区环境,这些因素关乎自身房产的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恐惧源于对贫富落差的敏感,即使小区内部安全无虞,墙外那个可能存在贫困与失望的世界也让他们不安,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财产犯罪的“目标”。
在访谈中,我们的话题还从保安延伸到乌镇和阿那亚——两个精心设计、秩序井然、属于中产们的“楚门的世界”。何袜皮观察到,乌镇的民宿、餐饮甚至菜单都由一个总公司控制,实现了严格的品控。而在阿那亚,门票和高昂的住宿餐饮费,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辅以文化艺术活动,营造出一个封闭、纯净的社区环境,吸引了一批批的中产及“预备役中产”。它们都精准地捕捉并满足了一部分中产阶级对安全和秩序的需求。
城市里的小区大多都有保安,很多居民却避免与他们打交道,这是一种值得反思的现象。一些读者在新书发布会上告诉何袜皮,《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帮助他们实现了某种“看见”,增进了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和尊重。何袜皮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写保安,也在写中产、业主,写我们每一个人。她希望透过这些文字,能形成一种社会共同的认知,改善大家对保安群体的态度。
以下为正午与何袜皮的访谈,略有编辑。
正午:书中塑造了几类典型的保安形象,比如害怕让父亲丢脸的小亮、认为“干保安五年脑子会变钝”的中年保安,以及有前科的保安等,为什么选择这些人作为主要角色来呈现?
何袜皮:这些保安是其中比较有故事、性格较鲜明的个体。实际上,大多数保安是普通的农民工,从欠发达地区来到上海等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是中年人,不善言辞,人生经历相对平淡。这些保安构成了我观察和访谈的主体,但其个人经历可能没在书中具体展开。而那几个写了人生历史的保安,原本是论文最后一章的内容。改成中文书时,为了增强书籍的可读性,我将这些故事提到了前面。我认为,保安行业太过庞大,特别是一线城市的从业者各式各样,地域、背景各异,甚至现在也有大学生加入,很难说谁能代表谁。
正午:书中提到,保安群体缺乏年轻人。近年来,高学历者从事保安也不鲜见。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袜皮:我写作时的2017—2018年,经济尚好,保安行业面临招年轻人难的问题。年轻人更愿意去送外卖或快递,收入更高。我当时预测,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稀缺,保安行业招工将越来越难。没想到的是,经济下行时期工作难找,许多年轻人又考虑起保安这个行业。因为外卖行业内卷严重,收入不再明显高于保安,而保安工作相对轻闲。现在也有大学生因其他行业职位压缩而选择当保安。
正午:有位保安说,保安工作的“最大的优点是不难,最大的缺点也是不难”。这种低门槛、低成长性的职业,是许多人的就业困境吗?
何袜皮:保安工作的特殊性在于,它纯粹是对时间的消磨,大部分时间并未被有效利用。编辑将书中一段类似的话放在封面上,是因为它反映了许多职业的现状,即从事着看似无意义的重复性劳动。在一场分享会后,有位女读者对我说,她有同感,她是一名警察,觉得大部分工作都是琐事。这可能是一种普遍感受,尤其当工作缺乏创新性、任务比较机械、与个人绩效脱钩时,容易产生这种困感。
正午:你之前写过一本虚构作品《易碎品》。与之相比,《大门口的陌生人》在写作风格上有哪些调整?
何袜皮:《易碎品》是长篇小说,更注重悬念和情节的引人入胜,而《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非虚构的。在将英文论文改写为中文书时,我试图增强可读性,例如将故事性内容前置,每章以人物经历引出理论讨论,但总体上我还是追求真实、平实的叙述。我认为,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本身已足够吸引人,无需过多文学手法的修饰。
正午:为何中国的整体犯罪率在下降,保安数量却在上升?
何袜皮:小区保安的诞生最初与社会治安需求直接相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复杂,国家大力推动保安行业发展,将它作为对警力资源的重要补充。而后来,随着监控系统的普及、DNA 等刑侦技术的进步以及货币数字化的推进,犯罪率持续下降,保安行业的发展逻辑逐渐发生转变。在房地产行业蓬勃兴起与大量民营资本涌入的驱动下,小区保安演变为商业逻辑主导下的服务业产品,成为房地产项目提升附加值的重要配套。
中产业主为何对小区保安有这么强的诉求?主要源于两方面:
一方面,中产群体对贫富差距较为敏感,普遍担忧自身成为财产犯罪的目标。尽管这种担忧与实际治安状况可能存在偏差,有研究显示,居住在安全系数越高的小区,居民反而更容易产生恐惧心理。
另一方面,房产是城市中产家庭最核心的资产,房价对他们的经济地位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倾向于通过强调犯罪风险,主张更严格的安保措施和更封闭的小区,以此来维护房价,避免资产损失。
正午:这项研究对你后续的创作或研究方向有何影响?
何袜皮:我目前没有继续学术论文的打算,因为博士研究耗时较长,且这本书已是阶段性总结。我现在主要精力放在“没药花园”的文章和小说创作上。在虚构故事中,我也可能会借用当时观察到的保安这个职业的种种细节,塑造相关人物。
正午:你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保安或农民工群体吗?
何袜皮:他们不算是我这本书的预设目标读者,这本书也没有明确的读者限定,所有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读。它源自一篇学术论文,初衷是为学术界丰富知识体系,同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改编成书时,我弱化了枯燥的理论部分,降低了阅读门槛。内容上,它不只是写保安,还涵盖了中产、业主等多个群体,其实是关于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态。如果保安从业者愿意读,大概率能找到共鸣。我也希望不了解保安行业的读者,读完能对这个群体有个客观的认识,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完——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