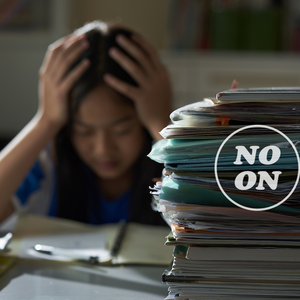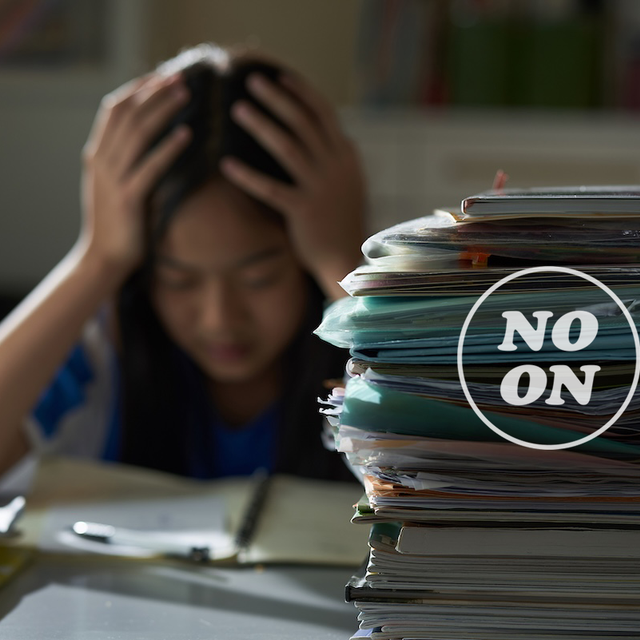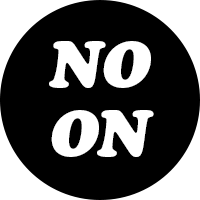采写 | 武冰聪
“我无法回应和触碰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作为一位母亲,梁鸿感到迷茫和困惑:为什么家长是爱孩子的,孩子不仅感受不到爱,却深陷痛苦?
梁鸿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她的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获得过多个图书奖项。过去三年,梁鸿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困住的少年——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以及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她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这些孩子来自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乡村,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却遭遇着相似的困境:无法进入常规教育系统中,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需要长期服药,他们与家长之间因为观念不和而纠缠、争吵。
在“梁庄三部曲”中,梁鸿展现了被时代变迁淹没的中国家庭和村庄,呈现过去30年间人们在“心理上的无家可归”。而这一次,她关注到了肉体在家里,心理上却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在她看来,在这个“成功”定义被极度窄化的社会,“升学至上”的氛围笼罩着一切,家长的爱与孩子的需求之间常常存在错位。
在采访中,梁鸿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学生。比如吴用,爱学习却受不了去学校,他反对妈妈给他设计的功利学习路径;比如敏敏,陷入游戏世界,拒绝上学;比如雅雅,家庭并不温馨,家长主动吃苦换取孩子的感动……针对不同孩子的经历和困惑,正午和梁鸿展开了以下对话。
吴用:不愿学习,还是不愿去学校?
海淀妈妈陈清画和她的孩子吴用之间发生了观念上的矛盾。
吴用得了严重焦虑、抑郁症,不愿意上学。陈清画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她知道吴用的痛苦,但她只能按照另一套规则要求孩子。因为社会现实告诉她,孩子不上学,就注定要失败。
陈清画每天早上小心翼翼地叫儿子起床,期待吴用这天能到学校,延续“清华北大”的可能性,又一次次为吴用的拒绝而流泪。
吴用喜欢数学,还提前钻研大学数学知识。按照陈清画的规划,吴用可以靠数学竞赛拿奖。他告诉妈妈:“我要的是学习,而不是上学。我只有在纯粹的学习状态中才能获取某种安宁,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我的整个生存是基于学习的热情存在的。但你觉得这违背了实际生存规则,那样没有未来。”
在一次和妈妈的长谈里,吴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人,大家各有各的轨迹,你非要认为有一种广泛的相同的社会规矩,这种观念会折磨你,折磨我,社会上每个人都在受折磨。”
正午:吴用喜欢的是思考,讨厌刷题和应试。书中另一位海淀少年提到,老师把更多的赞誉和关注给了前20%的孩子。你如何评价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梁鸿:当我们把自己看作制度中的一份子,就会有无力改变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系统和个人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老师和家长,是更耐心还是更严苛,能不能释放更多的善意?其实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把主动性抛掷掉,也就忽略了一个人的责任。哪怕是微小的一步,例如作业写到很晚时,家长说“咱们少做五分钟”,或者老师给一个平常不被关注的孩子多一个眼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教育部2017年就推出“双减”政策。如果把责任都推在别人身上、体制身上,那么我们的社会永远不会有任何松动。
正午:正午曾做过“学神”的选题,讨论了中国精英家庭如何再制精英。《要有光》中,有个孩子对妈妈的点评是:“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资源托底,所以,卷有卷的道理,否则会承担非常大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梁鸿:我们的贫富差异和阶层差异肯定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了三个地方,北京、滨海(化名)和丹县(化名),刚好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虽然孩子都出现不想上学、抑郁等情况,但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是不一样的。
在贫富差距的背景下,有些家长不得不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让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达成阶层的跃迁。但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顾及孩子,我们给他的压力过大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孩子他是个人,不是工具。
为什么大学生的抑郁比率也很高?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觉得,高中、初中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实现阶层跃迁,以后我们就轻松了。其实,人生永远没有绝对的轻松,因为我们在窄化成功的概念。
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能给周边人带来温暖。即便他在一个一般的公司,做一般的工作,难道就不好吗?难道就是失败的吗?我们为什么不对这样的存在给予积极的肯定。
娟娟:手机和游戏,出路还是陷阱?
在丹县,娟娟的妈妈面临两难:该让女儿继续上学,还是回到精神病院。开学才第二周,娟娟就起不来床,脾气越来越暴躁,不停向妈妈要手机玩,和哥哥冲突不断。她拒绝上学,说自己上课什么都听不懂,也不想听,作业都是抄的。
娟娟因为玩游戏的问题,和妈妈争吵。“你说话不算话,你说给我游戏充钱让我买皮肤,你最后又不给我。”
“我啥时候说过?我从来没答应过你,都是你自己想的。”
娟娟身高167厘米,体重超过140斤,不知道是不是吃药的原因,那一段时间她的体重增长很快。在省会精神病院的青少年心理治疗中心,娟娟被诊断为重度抑郁,表现症状为情绪低落、不稳定、狂躁,有自残倾向。
正午:今天的生活方式和2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外卖、游戏的普及,让孩子在家不无聊,可以不用出门社交。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这些因心理问题休学的孩子走出来?
梁鸿:如果整个社会没有创造一种多元的生活方式和多元的精神方式,你怎么可能要求孩子有多元的业余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从早晨六七点钟开始上课,再到放学之后写作业,很难有自己的时间去发呆、思考,这本身就造成了孩子生活模式的单调。当他有一点点机会放松下来,只有打游戏,这是最方便的方式,因为手机就在手边。孩子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他另外一个选项,比如自然是可爱的,麦苗和大树是吸引人的。
我们家长的生活方式也变得非常的单调,所以,我们给孩子创造的是一个极为单调的、枯燥的、唯一的环境,却反过来埋怨,孩子只知道打游戏。
当然,有些家长已经有意识地在培养孩子的多元兴趣。有钱的家长可以带孩子在全球范围内参观博物馆、美术馆,而孩子都是被拖着去的。为什么?因为回来以后,孩子需要写一篇游记,他也不想写。也有家长从小带孩子去学画画,但最终的目的是参加自主招生,考上好大学,这仍然是功利性的。
正午:如果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家长该怎么办?
梁鸿:在雅雅的案例中,她生病之后妈妈比她还崩溃,这对孩子的打击非常大。孩子最难的时候,在家庭内部,在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却得不到任何支撑。如果家长没有能量的话,小孩只能越陷越深。我认为,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家长去做一个有能力、有能量的家长。
正午:在书中,你提到了阿叔开办的教育机构。现在社会上开始有各种创新型学校,主张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也有“一出学社”等学习社区,面向休学学生开放。这些新的教育模式会对休学的孩子有帮助吗?
梁鸿: 孩子已经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了,那怎么办?他不能天天待在家里边,他也需要人群,需要社交。我们还是要寻找宽容的、崭新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并且我发现,有些机构是非常先进的,已经有心理咨询师、专业的医生都参与进去。
雅雅:“错位”的沟通
滨海女生雅雅16岁,皮肤微黑、娃娃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从小成绩优秀,是“别人家的孩子”。改变发生在考上重点高中之后,雅雅的成绩一度滑到中游。高一分科后,她即便考到班级第一,却更焦虑。课堂测试时,同桌翻面写字的声音都让她紧张得手心出汗。
雅雅开始抗拒上学,妈妈说她“叛逆”:“学校为什么不去,有老虎吗?”面对这样的情况,爸爸有时摔门而出,在街上散步,不肯回家;有时指责妻子的教育完全失败。雅雅被确诊为中度抑郁、中度焦虑。爸爸突然在她面前跪下磕头,叫喊:“你快点好,我们都受不了了。”妈妈哭得更厉害。为了陪雅雅,妈妈向单位请假,被领导批评后,她告诉女儿:“因为你,我的工作都快没了。”
雅雅吃了三个月药,状况没有好转。连续两三天,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雅雅在精神卫生中心住了20多天。出院后,她仍害怕考试。
正午:雅雅退学后,父母经常抱怨、争吵。在你看来,家长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和孩子沟通?
梁鸿: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孩子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不是一个笼统的问题来解决。家长只有在充分了解孩子的前提下,才能找到相应的对话方式。
家长需要学会倾听。很多时候家长是在自说自话,自以为对孩子好,但并不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倾听之后,家长就有可能改变认知和想法,从而改变对待孩子的方式。
在一个孩子未成年的时候,家庭是第一堡垒。如果父母都不能给孩子做一个基本的支撑,那么还能指望谁?现在不是家长推卸责任的时候,去抱怨自己也很辛苦,然后去打骂孩子,把自己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
父母在孩子面前应该展现出更高的主体性,更强大的勇气,成为孩子和社会之间的一道保护墙。
正午:雅雅的妈妈为了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空间,自己住在客厅采光不好的低矮沙发床上,让雅雅住进家里最大的房间。雅雅觉得,妈妈在营造出一种自己受苦、忍让的形象,让她在家里有不舒服的感觉。家长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梁鸿:我们的爱有可能是错位的,和孩子擦肩而过,并且还能给孩子造成某种伤害。家长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家长会在不经意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孩子施加某种冷暴力。
家长自以为付出了很多,但对于孩子而言,你给的爱是不是爱?孩子到底什么感受?我这本书记录的是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对话。父母不能老是在自说自话,自怜自爱。爱是相互的呼唤和应答,实现爱的方式就是倾听和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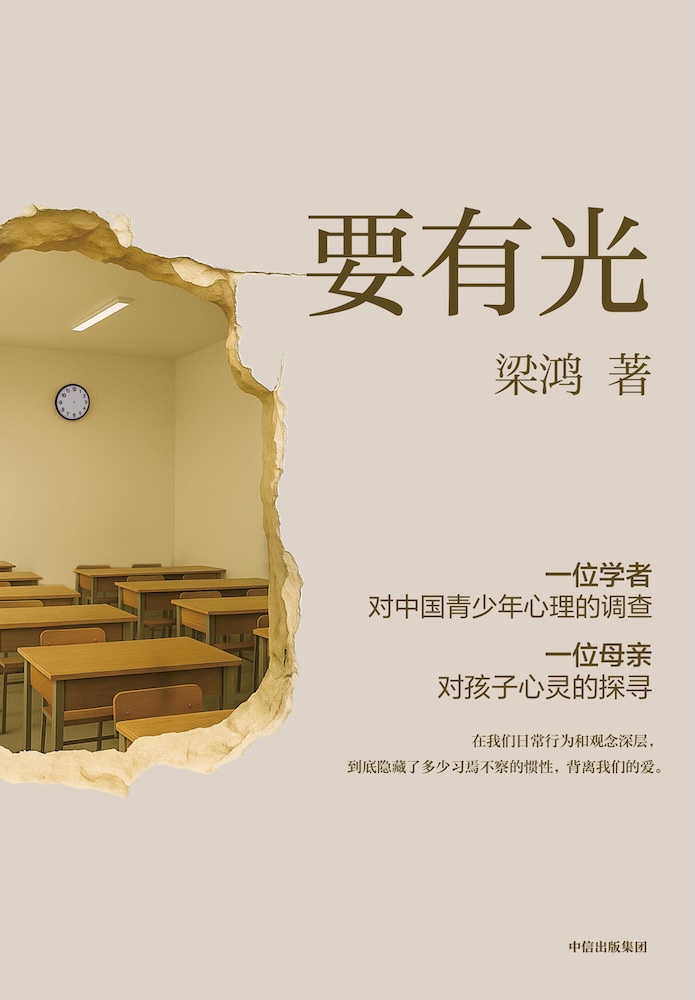
——完——
作者武冰聪,界面新闻记者。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