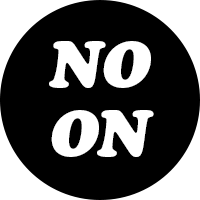采写 | 明亮
位于徽(州)杭(州)之间的“严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但它的故事比江南更动人。”杨斌说。
杨斌出生于浙江建德乾潭的小山村,19岁北上读大学,26岁跨越太平洋赴波士顿攻读博士,此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11年。他的学术研究一直聚焦中国-东南亚-印度洋三角关系,瘴气、张爱玲、海贝、南洋是他的学术关键词。
这位长期“向外看”的海洋史学者,在中年时却将目光收回家乡,以建德县(古严州府)为核心,探索其两千年变迁,写下30万字的《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从东汉严子陵的“高洁”到宋末谢翱赋予的“忠烈”,从南宋“京畿三辅”的高光时刻,到清代坌柏村汪吴氏等底层女性的坚韧……在杨斌的史料挖掘下,严州的历史如一副画卷,逐渐展现出丰富而动人的样貌。
很多人都不知道严州。严州府的湮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淹没淳安、遂安两县及狮城、贺城两座千年古城,形成千岛湖。1969年富春江大坝蓄水,淹没沿江村落如坌柏村(杨斌母系家族祖居地)。而严州府行政建制则在1958年被撤销。在地理变迁与记忆遗忘的双重湮没下,严州成了被忽略的“江南以南”。
近期,正午与历史学家杨斌深入对话,一起探寻严州被湮没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个离乡游子对家乡的复杂情愫。以下为访谈内容,略经编辑。
正午:您的学术研究一直聚焦云南史、海洋史,为何会转向家乡严州的地方史研究?
杨斌: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研究家乡史。我的博士论文做全球视野下的云南边疆,到新加坡后又做中国-东南亚-印度洋的三角互动,研究海贝、龙涎香,还有郁达夫这样的华人华侨,都是“向外看”的课题。从学术惯性来说,不会把目光放在浙西南的一个小府城。
转折是在2005年回国后。2006年我回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那段时间常回家。外婆、母亲和舅舅总会讲起小时候的事——外婆说我外公是徽州移民的后代,坌柏村的汪家过去靠砍柴烧炭过日子;舅舅说,20世纪60年代移民时,全村都眼泪汪汪不肯离开老家。我是学历史的,觉得这些人事不能就这么丢了,应该写下来。2006到2007年,我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两三万字的草稿,主要是外婆、母亲、舅舅讲的家族往事,那时候只是想留个纪念,没打算写成一本书。
真正决定写严州史,是在2017年。那年夏天我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到了澳门大学任教,或许是人到中年,突然下决心写一本不一样的家乡史。
此后我就开始系统看严州的地方志,从南宋的《严州图经》到清代的《光绪严州府志》,再到历代文人的严州诗文,越来越觉得严州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比如严州在南宋是“京畿三辅”,为杭州提供木材、木炭,还是皇族的封地;又比如严子陵钓台,从汉唐的“高洁”到宋后的“忠烈”,形象变迁里藏着时代的价值观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地方史课题。
简单说,这本书就是人到中年后的“回首”。不管走多远,总会想回到人生的起点,想弄清楚家乡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本质上是“中年离乡游子的思古之幽情”,有对家族、家乡和父老乡亲的情感。
正午:从2006年写家族草稿,到2021年完成书稿,前后跨度十几年,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杨斌:印象最深的是寻找史料的过程。严州的文献太稀缺了,太平天国战火把大部分地方文书、族谱、碑刻都毁了。左宗棠给清廷的奏折里写,战后严州“十不存一”,10个人里活下来的不到1个,人口尚且如此,文献更不用说。在相当有限的材料中挖掘出生动有趣的主题,讲述有血有肉的故事,同时彰显严州地理和文化上的独特形象,难度很大。
读者或可看出,我在全书的细节上有很多努力,如关于乾嘉年间坌柏村的汪吴氏一生的挣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我正在写汪吴氏那章。那时常用一个词“时空伴随者”。我突然想到,1793年11月马戛尔尼使团经过坌柏村江面时,汪吴氏正在村里为择嗣焦灼。他们相隔只有一箭之遥,却永远不会相见。一个是英国贵族,一个是中国山村寡妇,命运完全不同,但都生活在那个时代,曾经近在咫尺。我把这个想法写进书里,让汪吴氏的故事有了更广阔而又更鲜明的历史内衬。
正午:您在书中提出“严州是江南以南”,很多人认为浙江属于江南,您如何定义“江南”?
杨斌:“江南”是个动态的地理概念,是一个历史进程,秦汉到明清的所指一直在变。我这本书里的“江南”,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定义——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包括镇江、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杭州这七八个府,在浙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杭嘉湖平原”。这片区域是水乡、平原,经济富庶,文化发达,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
之所以说严州是“江南以南”,不是否认严州属于广义的江南,而是想突出它的独特性。它不在太湖流域的核心圈,是“江南的边缘”,“江南的延伸”。这种边缘性让它保留了很多不同于杭嘉湖的文化特征,比如徽州移民带来的习俗、山区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我在书中一再强调,严州在徽州和杭州之间,这个之间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空间上,而且也是经济上、文化上的。这些都是严州的魅力所在。
正午:南宋是严州的“高光时刻”,你在书中提到严州是“京畿三辅”“三位真主兴王之地”,这段历史对严州的文化塑造有哪些影响?
杨斌:南宋奠定了严州“名邦望郡”的地位,在明清以后严州逐渐衰落。南宋对严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政治地位的提升。北宋时,宋太宗没登基前遥领严州防御使;南宋高宗赵构当康王时,也遥领严州节度使;后来宋度宗登基前,同样遥领严州——严州成了“三位真主兴王之地”,对南宋政权的合法性非常重要。高宗南渡后,严州位于临安(杭州)西南,真正是“京畿三辅”,很多皇族被封到严州,科举时严州的赵姓进士特别多,就是皇族后代。
第二是经济角色的强化。杭州在南宋有几十万人口(马可·波罗说上百万,可能有夸大),但杭州没有煤炭,做饭、取暖全靠严州的木材和木炭。宋末元初的谢翱在严州,就是靠雇佣山民砍柴烧炭发家的。简单地说,严州是杭州的“能源基地”,这种经济联系让严州在南宋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第三是文化的积累。范仲淹知严州时,建了严子陵祠堂,还办了书院;陆游知严州时,也重视办学,严州的文气在南宋达到顶峰。南宋严州的进士数量,占整个严州历史进士总数的一半以上,还出了方逢辰这样的状元、黄蜕这样的榜眼、何梦桂这样的探花。科举的兴盛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比如严州刻本在南宋很有名,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严州刻版的,对严州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清。
正午:“湮没”是您这本书的文眼,既指地理上的淹没,也指记忆上的遗忘。这两种“湮没”有什么关联吗?
杨斌:地理湮没加速了记忆遗忘,记忆遗忘又让地理湮没的创伤更难修复。
先看地理湮没: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淳安、遂安两县大部分被淹,两座千年古城贺城、狮城沉底,30万人移民;1969年富春江大坝建成,建德北部的坌柏、张村等山村被淹,又有五万移民。这些移民被分散到江西、安徽、浙江其他地区,和故土的联系人为隔断。
地理湮没后,记忆遗忘就成了必然。1958年严州府建制被撤销,所辖六县划归杭州,“严州”这个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现在建德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严州”是什么,甚至以为建德一直属于杭州;千岛湖底的贺城、狮城,除了老一辈移民,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历史;坌柏村这样的小山村,只在民国县志里留了十几个字,具体位置很少有人能说清。
更严重的是,文献也跟着“湮没”了。移民时,很多家族的族谱、文书被遗弃;20世纪50年代后的运动中,剩下的碑刻、祠堂或被毁坏,或在江底。
这两种“湮没”造成的后果,是严州历史的“断裂”。年轻人不知道家乡的过去,移民后代找不到根,学术研究缺乏史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在地理湮没和记忆遗忘之间搭一座桥,让严州的历史能被看见、被记住。
正午:严子陵是严州最著名的历史人物,您在书中梳理了他从“高洁”到“忠烈”的形象变迁。这种变迁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价值观变化?
杨斌:严子陵的形象变迁,本质上是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历史符号。
汉唐时期,他的核心是“高洁”。《后汉书》里写他拒绝光武帝征召,“披羊裘钓泽中”,还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这时候的严子陵,是“不与官府合作”的隐士代表,推崇的是“自由自在、不慕权贵”的价值观。那时候的文人如谢灵运、孟浩然,写严子陵都是“望峰息心”洗涤尘虑,突出他的隐逸。
变化发生在宋末元初。宋遗民谢翱兵败后隐居严州,登上严子陵钓台哭祭文天祥,把严子陵的“不合作”解读为“忠诚于前朝”。谢翱哭文天祥拜严子陵,是忠于南宋。从这时候起,严子陵的形象开始加进“忠烈”的元素,并成为钓台的主流符号,成为遗民的精神寄托。
明末清初,这种“忠烈”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广东遗民屈大均来严州,登上钓台祭拜谢翱,写下《书西台石》,说“皋羽(谢翱)与予所遭,乃生民之至不幸”,把自己比作谢翱,把严子陵钓台当作抗清的象征。这时候的严子陵,已经不是简单的隐士了,他的“不合作”成了“忠诚于汉家天下”的符号。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严州知府李文瀛兵败后,选择投江于钓台来凸显对清朝的忠诚。
王朝更替、社会动荡时,文人需要一个“忠诚”的符号来寄托情感,严子陵的“不合作”恰好被改造为“忠于前朝”的“忠烈”。而在和平时期,文人更需要“高洁”的符号来表达对自由的追求。
正午:在书中你花了大量篇幅写女性,比如汪吴氏、杨太后,还有建德县志里的其他寡妇。为何关注这些被历史忽略的女性?
杨斌:一方面是受个人经历影响。我从小听外婆讲家族故事,女性的故事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是受我博士生导师柯临清的影响,她是最早把性别研究带到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虽然我的博士论文没做性别研究,但听她的课和她交流,让我注意到历史研究中的女性视角。
严州的女性史料特别少,除了杨太后这样的皇室女性,底层女性只有县志里零星的“节妇”记载,比如汪吴氏、陈葛氏、汪潘氏,都是“夫亡守节、捐田赡族”这样的简单描述。但这些女性都非常坚韧——汪吴氏28岁丧夫、35岁丧子,最后捐出40亩田地作为严州府学的膏火田。这一群女性的生平,哪里是“节妇”这两个字所能概括的。
在书写时,我会先理解她们的处境——不能用现代价值观评判她们的“守节”。在清代的语境里,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守节是她们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方式,汪吴氏捐田也是为了在家族中获得择嗣权,这是她们在有限空间里的“理性选择”,是对父权不屈不挠的抗争。
但我也不会放弃“史学审视”,比如分析汪吴氏捐田的动机,要结合清代的“旌表制度”——官府会表彰“节妇”,捐田能让她获得官方认可,从而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我也一一列举她捐田的明细,41丘田总共才40亩,最小的一丘田大约250平方米。田地之零碎,可见清代严州山区的生存压力。
简单说,就是“走进历史语境理解她们,跳出历史语境分析她们”。既不把她们当作“礼教的受害者”简单批判,也不把她们的“守节”美化成“道德高尚”,而是还原她们作为“人”,特别是作为“第二性”的女性之挣扎与智慧。
正午:新安江水电站和富春江大坝的修建,让严州的地理和文化发生了“两千年之变”。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杨斌:这两座大坝的修建,是严州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令人遗憾的一面。积极的是,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建造的水电站之一,为华东地区的电力供应做出了无法低估的贡献;富春江大坝也是如此。但对严州来说,负面影响也绝不容忽视。
首先是地理上的“割裂”: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新安江上游不再通航,严州和徽州的联系断了——过去徽商顺着新安江把物资运到严州,再转到杭州、上海,这种持续两千年的经济文化联系,一下子没了。1969年富春江大坝建成后,严州和杭州的水路也断了,严州不再是杭州的“能源基地”,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其次是行政上的“消失”:1958年严州府建制被撤销,其实和大坝带来的地理割裂有关——严州既没了与徽州的联系,也没了对杭州的经济价值,建制撤销成了“必然”。这直接导致严州的地方认同淡化,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严州”,只知道“建德属于杭州”。
文化传承上的影响更难修复:严州府前后有35万人口被迫迁徙,迁徙人数相当于严州府总人口的40%,影响之大,可想而知。移民分散后,严州的方言、风俗难以传承。淹没的古城、山村没有留下遗迹,严州的文献、文书在移民和运动中遗失。现在虽然有“严州古城”的修复,但很多是旅游“古迹”,虽然能够吸引游客,但无法还原历史。
这种变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文化传承——一座古城、一个村庄的价值,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记忆和认同的载体。严州的教训,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正午:写完《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后,你对“家乡”这个概念有了哪些新的理解?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杨斌:写完这本书后,我对“家乡”的理解更复杂了。家乡是每个人的“根”,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要去寻根。现在觉得,家乡是“被用来遗忘的”。遗忘中的家乡是最美好的,一旦回到现实,就会有落差。鲁迅的《故乡》和郁达夫的《还乡记》,就是充满了惆怅和焦虑:回去后发现闰土变了,杨二嫂并不可爱——家乡不是固定的,是活在记忆里的。
写完了这本书,感觉肩上和心底的压力一下子释放了,未来可能不会再进一步研究严州文化了。不是不关注,而是觉得该说的基本都说了。这本书不仅写了家乡,而且也尝试了地方史写作的新范式,再写也很难有新的突破。不过,严州当然会一直是我的“情感牵挂”。
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是澳门史。2017年我在新加坡发现了一幅乾隆时代的澳门山水长卷,后来到澳门后开始研究,去年已经完成了初稿。主要对比这幅中国画和同时期欧洲画家的澳门画作,分析乾隆时代澳门的社会状况,看两种文化如何在澳门互动。
正午:你希望读者从《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中读到什么?
杨斌:我希望读者能读到“被忽略的历史”——严州不是江南的附庸,它有自己的故事,有东汉的严子陵、南宋的杨太后、清代的汪吴氏,有跨国的联系,有底层的坚韧;也希望读者能读到“记忆的重要性”。一座城市、一个村庄的历史,不只是文献里的文字,更是人的记忆,一旦记忆消失,历史就真的“湮没”了。
我也希望读者能体会到,历史应该是公平的、民主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写自己的、家庭的、家乡的历史。200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的时候,给学生的作业便是写自己的家史,编自己的家谱。二十年后,我完成了自己的家史和家乡史,这也算是以身作则。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中年回首的一刹那,是对长辈的交代,也是对严州的乡情。

——完——
题图:浙江省建德市南峰塔东眺三江口,由出版方提供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