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吸引思宇的地方有很多,但最早的源头,可能是她初中时在机场书店买到的一本薄薄的福柯简介,其中一段福柯的话让她印象很深刻:
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关联,而不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
看了这段话,思宇决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当成艺术品来过。对她来说,福柯——这位法国的思想家——也成了个“神一样的存在”。所以,2006年,她高中毕业时,大家都以美国为“正途”,她却选了法国。
她先是在尼斯的一个语言学校进修。尼斯在地中海沿岸,气候宜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思宇在那里,半是学习,半是度假。她看到一家中餐馆,所有店员都穿旗袍,她想穿旗袍,就去了这家餐馆打工。在尼斯的滨海大道上,她认识了一位当地的消防员,两人成了恋人,她还跟着朋友一起,到阿尔卑斯山的林间露营,在山顶看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开摩托车到海湾里游泳,到山洞里跳水。
这段生活经历听起来精彩,不输给很多西方的年轻人。这和她的成长经历也有关。思宇生长在北京,从小,父母就希望她能自立,她举了个例子,三年级起自己就经常给家里人做饭。母亲是大学老师,一直支持她出国读书。不仅如此,1990年代,母亲就曾带着思宇到巴黎访学,对国外的生活,思宇已经不陌生了。
在尼斯待了半年,她通过了索邦大学的C1级语言考试,到索邦—巴黎第四大学去读书,专业是历史学。这所学校以文学和人文学科闻名,历史学更是声名在外。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思宇对历史不太感兴趣。但是要到法国读书,文科里,声望最高的学科,除了哲学,就是历史。这其中也有母亲的影响。母亲告诉思宇,在本科阶段,最好学一个基础学科。
在给巴黎四大的申请信里,思宇写了句“冠冕堂皇”的话:巴黎就像一本书,我只要把巴黎读懂了,我的历史就学成了。

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法国最大的魅力都在于文化。任瀚也是如此。来法国前,他在天津美术学院学了四年油画。他喜欢当代艺术,但四年的训练之后,他还是“没弄清楚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他想出国。纽约是当代艺术的明星城市,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看起来有创意又大胆。但他想去艺术传统深厚的欧洲。在欧洲,德国的绘画非常独到 ,但他不想再画画了,他想摆脱国内的学院派绘画训练留下的痕迹。那就到法国去吧,当代艺术的另一个明星。这也同中国美术史与法国的渊源有关。从徐悲鸿,到赵无极 ,再到严培明和王度,过去留法艺术家们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忽视的。
就艺术电影而言,更是如此。电影导演张凡夕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系。他喜欢学语言,读本科时学了法语。又看了很多法国电影 ,比如克里斯托夫·奥诺雷的《巴黎小情歌》。他想到法国去,拍这样的电影。2011年,他到了巴黎。2013年,他考上了著名的La FEMIS,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
二
思宇的性格很热情开朗,也很聪明。听说我要采访留学生,见面之前两天,她先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我讨论在巴黎的留学生活。采访时,又向我推荐了一些有特色和历史的咖啡馆。采访结束,她同我聊起别的留学生和我的工作,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她对他人的兴趣显而易见。
还在人大附小时,思宇就在学校里组织了漫画社,带着同学去找《北京卡通》的编辑交流;到了人大附中,她又成了学生会成员,带着同学们做事;学校之外,她还是某个知名游戏论坛的版主,交友甚广。思宇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充满信心,但是到了法国,她却感受到了冷漠。没有人想结识她,哪怕在主动自我介绍之后,也少有人表现出兴趣。
他们对她来自哪里不敢兴趣——一个亚洲小孩,可能是某个殖民地过来的,或许是越南,所以从事餐饮业;他们知道了她是中国人,也不感兴趣。尽管你跟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但在他们的眼里,你是局外人。还有人问思宇:“你们在中国还都穿长袍吗?” 礼貌自然还是有的,但冷漠从细节里透出来。
思宇想起在北京见到的农民工。她对他们当然是礼貌的,就像法国人对她一样。“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在法国的民工,”思宇说,“可能不到一个月我就明白这件事儿了,其实在北京的时候大家看民工的眼光是这么一种,会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方式。”
到巴黎四大之后,情形好了一些。思宇同其他国家来的留学生,还有法国外省的学生交了朋友。巴黎的朋友呢,也有一两个。她说,巴黎人有自己的社交圈,不需要这些外人。于是他们这些“局外人”,互助着解决自己的社交需求。再说,课业忙起来,她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社交。课程要求学习古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那时她的法语也没好到可以轻松应付课程。不上课的时候,她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是看国内的博客。那是2008年,博客方兴未艾。或者,打电话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一两年下来,原本“不乐意一个人呆很久”的她开始享受独处。
对原本就内向的任瀚来说,社交就没那么容易了。任瀚在法国生活的第一个城市是昂热。这是个意外。他申请学校时,时间有些晚了,没法申请公立大学的语言课程。中介帮他申请了一个私立商科学校的语言课程。到了那里,他发现语言班里全是中国学生,法语教师是个意大利人,经常迟到旷课。“其实是专门招中国学生挣钱的。”任瀚想重新申请学校,商校说,如果不把剩下一半学费给交了,就不帮他注册居留。 这意味着,他要打包回国,重新申请。
没办法,任瀚就这么在昂热住下了来,住在一个小镇上。他每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上课,爬上山坡,再经过一片麦田。他说,他可能是那个村子历史上第二个在那里居住过的中国人。房东是位老太太,一个退休的护士,和小镇上其他人一样友好。但任瀚内向。听到房东在客厅,就不敢开门。房东请他吃可丽饼。他听说是煎饼,想起家乡的煎饼果子,期待着。房东往他盘子里放了一块薄饼,上面什么也没有。任瀚尝了一口,说,这没有味道。房东说,是的,你可以抹些巧克力酱,或者撒点糖。
小镇人口不多,平时不太见得到人。任瀚大多数时候都呆在自己的小卧室里,看法语书,看电影,画一些手稿。刚搬过去时,房东家里甚至没有宽带。老太太不用网络,后来才专门为他装了宽带。每个周六,他都要先骑自行车到市中心的中国超市买一张电话卡,再回到镇上,在中心广场找一个电话亭,打电话回家。
到法国的第一个圣诞节,任瀚是同房东和她的家人一起过的。从早上10点起床,到晚上十一点多,菜一道接着一道地上来。吃到后来,他实在困得不行。平安夜就这样过完了。

三
刚到巴黎时,张凡夕的目标是像个法国人一样拍电影,抹去自己作品里的那些“中国”的痕迹,让别人看不出是哪个国家的导演拍的东西,像李安拍《断背山》一样。
为此他做了不少努力。还没到法国,他就开始尝试结交法国朋友。他在脸书上同一个法国女生聊天。法国女生说,杨丞琳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张凡夕不知该回复什么好。到了法国,他找学中文的法国人做语伴,努力结交那些对亚洲文化有些兴趣的法国年轻人,参加他们的party。每次的话题都差不多,“你是谁?你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得到的回复,不论来自哪个国家的人,都是“好有意思啊。”参加次数多了,所有的party都无聊了起来,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参加。就连搬家的时候,他也会考虑这位置是否方便同学来玩,“我是外国人,我要和他们交流”。这状态持续了三四年。
张凡夕确实结交了些法国朋友,也和法国人约会。不过他说,有时候当一个法国人对他表现出兴趣,他不知道那是对他本人的兴趣,还是对亚洲人这个人种的兴趣。
进入La FEMIS(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之后,他拍了几部全法语的短片。2015年,他的法语短片《原谅》在迈阿密同志电影节上映。刚到法国时的目标,他自认为达到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融入巴黎人的社交圈,并不值得付出那么多努力。“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有很多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他说,“从创作层面来说,找到自己最独特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转变发生在进入La FEMIS的第二年。他需要拍一部纪录片。但他自认不擅长拍纪录片,想着拍个简单的中国题材,降低难度。他拍了《笔仙》,一部记录他和朋友玩笔仙的短片。他喜欢鬼怪,选这题材只是好玩而已。拍出来,却成了一部探索留学生的挣扎和痛苦的片子。成片看着很像剧情片。观众看完,听说这是部纪录片,都非常惊讶。种种因素加起来,这部影片在法国观众中获得不少赞赏,比他之前的法语短片都要多。
“从此我意识到,创作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我要拍一部很法国的片子,或者我拍一部很中国的片子,”张凡夕说,“你只要有你自己想说的东西,就是特别的。这个特别不一定要通过‘我是中国人’来解决,而是找到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




四
跟意大利老师学了一年后,任瀚的法语课程就结束了。之后他通过了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艺术系的考试。艺术系的教育是五年制的,他考入四年级,四年级授课不多,要求学生们探索自己的方向。在天津美院,任瀚的专业是油画。他不想再画画了,他觉得画画不够当代,不够刺激。他想抹去自己作品中绘画技术的痕迹,尝试了原生艺术和其它很多种艺术形式。在尼斯的第一年,他尝试做了些其它媒体形式的作品,录像的,声音的,等等。
任瀚的法语依然不是很好,他害怕接触法国人,也不知道怎么约见导师。像在昂热时一样,他躲在家里做作品,探索之前没有尝试过的形式。这实际上并不专业,展厅和客厅的空间体量不一样,作品摆出来的效果不同。这些问题在半年后的实验画廊课上集中暴露了出来。
实验画廊课是模仿画廊,由同学们布展,向老师介绍作品。对任瀚的作品,老师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这个照片为什么放在桌子上?你这个画用夹子夹着,它的理由是什么?”任瀚回答,这还需要理由吗?老师继续提问,把所有细节都问了一遍,最后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走吧。”
这不是那天最不留情面的评价。老师对另一位画了朝鲜核爆素描的中国人说:“我觉得你不适合做艺术,你应该做政治。”
“当时只考虑内容了,只考虑内容和作品的形式这些,就是国内的教育嘛。在国内你会很关注思想内容,就觉得艺术要表达一个多么高深的思想,就好像教育人一样,但是在这边完全不是这回事,”任瀚说,“你的主题可以很无聊,关键是你怎么做。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在细节上,很多是我在国内完全忽略掉的细节。”
以前,他把一幅画画好,认为自己就完成了任务。但现在,他还要思考如何展示,思考画和空间的关系,和观看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去表达,在国内是不表达的,也不是说大家羞于表达吧,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说,艺术好像很难言说的。这边也是认为艺术很难言说,但是他们总有一套逻辑能够推着走。美院的五年,其实给你造了一个马达,这个马达可以带着自己走。”
当时的任瀚还没有想清楚这些,老师认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立方向,留他重读了一遍四年级。
五
我见到思宇时,她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她把采访地点选在拉丁区的一家南美餐厅,La rhumerie,列维·斯特劳斯与同僚谈论热带见闻的餐厅。思宇在巴黎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年,对这些有典故的地方,了解颇多。她留短发,穿黑色修身的上衣,坐下时,腰总是挺直的,无论是点菜还是聊天,都迅速而坚定。就着一杯加了朗姆和橙子利口酒以及奶油的咖啡,思宇谈起她的博士论文课题:高考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
从巴黎四大历史系毕业之后,思宇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修读硕士,研究方向是中世纪大学——现代大学的起源。对教育制度的研究兴趣,更准确地说,对考试制度的研究兴趣,来源于高中时的经历。高中时她是个”不学无术“的学生,“一直生活在校外”,在网吧和游戏厅刷夜,跟朋友打台球。同龄人在为了高考努力学习,她认为那没有意义,毕竟这些知识,在社会上毫无用处。高中毕业后的这十年,她一直在试图解答当时的疑惑:“他们到底现在干嘛?”这疑惑后来被总结成更具体的问题:“对教育系统的信仰是合理的吗?”
进入巴黎高师之后,思宇开始对比巴黎四大和巴黎高师之间的区别。巴黎四大的门槛低,没有选拔考试,法国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申请就读。她上课的课堂里时常乱哄哄的。但她说,这个制度“非常非常宝贵”,尽量迎接所有人,满足他们就读大学的基本权利,提供一套成体系的训练,给所有人接触和融入的机会。思宇就是在这些看起来有些乱的课堂里,学会了像一个匠人一样分析到手的史料,分析自己接触到的所有信息。
巴黎高师的招生人数极少,以门槛高著称,是所不折不扣的精英学校。里面的学生看起来,更聪明,仪态谈吐好,通俗点说,素质更高。很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曾在这里就读,福柯就是其中之一。但福柯带给它的光环,在思宇入学后没多久就消散了。“它(高师)其实对于学生的要求,对于学生的训练,完全不如(普通)大学,”思宇说,“它本身的价值不高,只不过是让这些已经在社会上有足够资源的人,去吸取更多的资源。它是一个让富人更富,让穷人更穷的制度。这就像布尔迪厄说的,精英学校就是教给鱼怎么游泳的地方。与此同时,(普通)大学是一个让穷人看到可能性的地方,无论他们最后有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资源。”
从欧洲古代的史料里探出头来,思宇把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精英群体的构建。写完论文,她把目光转回那时给自己带来疑惑的高考。她认为,高考没能打破或者削弱原有的阶级再生产。比如她的中学同学们,“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普通的职员,或者农民。”
“你认为自己是个既得利益者吗?”我问。
“我是,”思宇不假思索地说,“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最难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反对这个让你获得利益的制度。”于是,读了博士,思宇回到以前给她带来疑惑的那个环境,北京某重点中学,做田野调查,试图解构这个制度。
六
第二次四年级快结束的时候,任瀚的方向又回到了绘画上。
对他来说,同导师交流依然是件令人发怵的事。教学里,老师们多以批评和质疑来刺激学生创作,仿佛一个个严厉的亚洲家长。实际上,老师也期待学生的反驳和辩论。对语言不好的留学生来说,这种教学方式的压力尤其大。对任瀚来说,压力或许更大些。他看起来不像是个长于激烈辩论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坐在对面,你能感觉到,他在发出声音前,都要认真选择词语,排列它们,好让对方准确地接收信息,即使在说话时,他看起来也像是还在思考这事。
同任瀚交好的几位亚洲朋友,在他重读的那年,不是没通过考试被开除了,就是放弃学业回国了。任瀚也想放弃。有时,同学聚会,一位香港女孩会鼓励大家,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咬咬牙就好了。
转机发生在学年快结束时。一位美学老师给“后进生”们开小灶。每周,他们到学生工作室开小会,谈工作进展。本科毕业后,任瀚有好久没正儿八经地画画了,也就是时不时地画些草图。他尝试了各种方向,都是蜻蜓点水。压力上来,他就临摹弗朗西斯•培根的画来发泄。一次小会上,老师看见他临摹的《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中复活女神的头部,问,你是不是会画画啊?任瀚说,我以前学过画的。老师问,那你为什么不画?任瀚说,画画不够当代。老师说,你不能这么想,绘画其实是一种天赋,就这么放弃,有点可惜。不如试着画些素描,把别的想法先放下,放空一段,画几个星期的画。
于是任瀚又开始画画。到第二周,有些肯定的声音出现了。他硬着头皮去约素描老师,又得到肯定。他的方向就这么定了下来。期末将近,展示课上,他把自己的素描和装置一起展示出来。美学老师也教了他如何讲解自己的作品和展示。老师们惊讶,这么木讷的学生变了。他就这么通过四年级,进入五年级,最后获得优秀奖励毕业。
现在回看自己在国内接受的传统绘画教育,任瀚认为那反而给他带来了一些优势。那种包含了大量写实训练的美术教育,西欧已经不太强调,但在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在欧洲学生中,这反而成了少见的品质。因此他在做作品时,会考虑很多绘画方面的因素。曾经想摆脱的东西,竟成了优势。
在中国的经历还带来了什么影响?很难详细描述。任瀚长于自我表达,而非探讨政治、社会一类的议题,作品主题大多非常内向。这在年轻的艺术家中,似乎也是种趋势。上个世纪到欧美留学的艺术家中,很多都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使用中国元素的材料非常普遍。任瀚在做作品时,也不会刻意考虑这些因素。尽管,“在法国,你如果想作品放画廊里好卖,就要打中国牌。”任瀚说,“但我是觉得,我就要用他们的牌跟他们打,好像显得比较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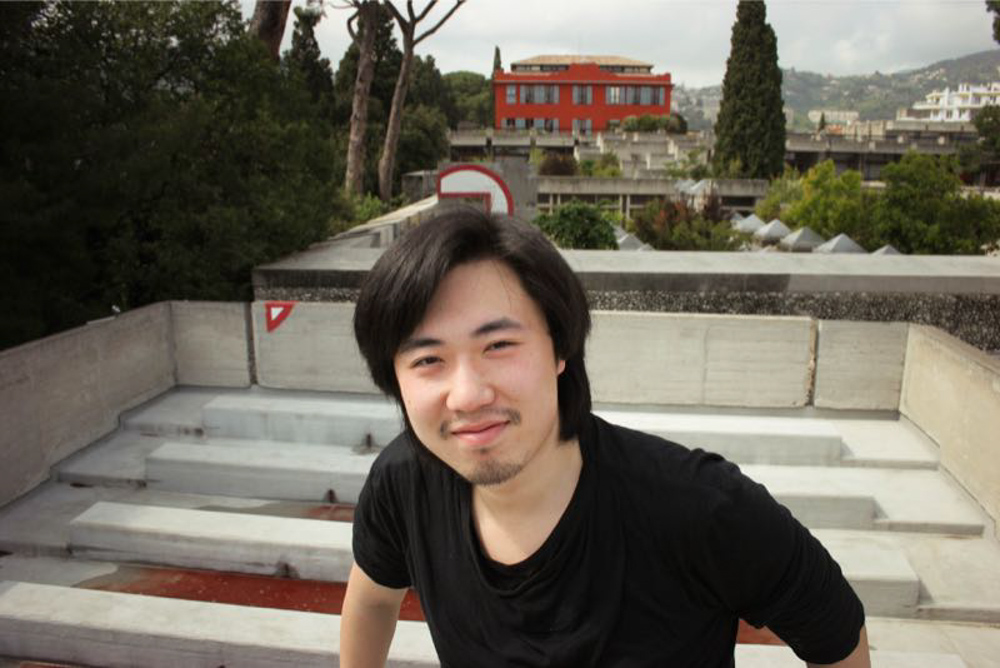






七
2018年的12月,几乎每个周末身穿黄色马甲的人都会聚集在巴黎的几个主要街道,高喊“马克龙下台”的口号。马克龙上台以来的种种改革引发的不满集中爆发。我见到张凡夕的前一天,那是周六,我们在爱丽舍宫附近的街道上看到“黄马甲”和警察的对峙。催泪弹的烟雾随风一阵阵地飘过来,高喊口号的人群散去。留下一些破碎的橱窗和被喷在墙上的标语。我们看见,一位身穿黄马甲的人在墙上喷出一行字:“工资制去死。”
第二天,这些街道又恢复了平静。行人在雨中撑着伞,无视墙上的标语,来来往往。周日营业的日本餐馆前都排着长队。张凡夕约我们见面的那家日式甜品店,却在周日休息。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到一家连锁咖啡馆去。张凡夕脱下沾着水珠的外套,里面是一条衬衫和一条马甲。他说话快而风趣,激动起来,就流汗,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整齐的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又整齐地放回去。
“黄马甲”的抗议爆发之后,张凡夕同朋友们的分歧,也小小地爆发了一次。
张凡夕的同学们在脸书上转一个警察要求学生靠着墙,手放头上,挨个检查的视频。他们说,支持学生,警察权力太大了,虐待学生,抗议。张凡夕发帖说,这事情后来查明,那50个人里只有一部分是高中生,其它的不知道是什么人。10个警察面对50个人,还可能有武器,不这么做,后果可能很严重。那条帖子下面,收到了很多反对的评论。
“太过政治化了。”张凡夕这么评价自己的同学们,在他看来,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对穷人的怜悯,但都是“没有经历世事的一帮年轻孩子,尤其是学艺术的,真的非常天真”。他觉得他们的狂热似曾相识。他警惕这种狂热,因此同一些朋友疏远了。而这是他刚到法国的那几年,曾经努力想融入的。
在张凡夕的职业规划中,巴黎依然是根据地。他对国内的街景越来越不习惯。街上的广告牌,建筑,城市规划,都没有美感,尤其是最近被强行统一的招牌。他习惯了巴黎的美感。他也习惯了法国人的直白。到一家咖啡馆,发现价格太高,会直接地说出“太贵了”,提议换地方。而在国内,或许是由于他的敏感,他感觉到不论去哪,服务员和路人打量你时,似乎都在打量你的经济状况。他不喜欢。但是,现在欧盟经济不景气,他拍电影,靠的大多还是中国来的投资。
2011年,任瀚从尼斯阿尔松别墅国立高等艺术学院获毕业并获得优秀奖励。第二年,他回到中国。比起中国,法国的艺术市场有些饱和。但是,在国内的艺术圈子工作,任瀚觉得有些混江湖的感觉。他不擅长社交,多少有些不适应。今年9月,他又回到巴黎。“在这边很安静,学术资源好,在这边做一些研究性的事情,做一些草图啊,小的东西,”他在北京的工作室还留着,“在国内会做一些发展,把作品更完整一些。”他正在申请艺术家签证,准备在巴黎和北京两地工作。
在北京的学校做田野调查的经历给思宇带来了一些压力。她发现,如果回国工作,处理学校内的人际关系对她来说,有些挑战,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学术领域,现在你只能全球找。”她说。
现在,对在巴黎的生活,她是享受的。2014年,思宇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交换读书,那时她每天要集中精力工作15到18个小时,学术工作成了体力上的挑战。但在巴黎写博士论文时,她每天全神贯注的工作时间,只有大约4到6个小时。她同周围的人交流,大家似乎都是这样。在巴黎,工作之外的生活非常重要。但未来的教职在哪个国家,还是个未知数。
—— 完——
题图为巴黎街景,来自视觉中国。文中其余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鸣谢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