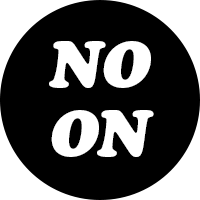文 | 日本《朝日新闻》采访组
编者按:经历过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代人,为什么还会“老后破产”,不工作就活不下去?工地周边指挥交通的保安员、办公楼里穿着制服的保洁员八成已过70岁,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越来越多地重回职场。与此同时,大公司里的中年人却失去立足之地,只能坐等退休。年轻人越来越难找到理想的职位,开始为几十年后的退休生活而焦虑……日本《朝日新闻》采访组直击日本社会面临的地狱级难度困局,其深度报道汇集成《无退休社会》一书。以下摘自该书的“迷失的一代的受难”一节。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许多业绩低迷、人员过剩的企业采取的措施不是裁员,而是最大程度缩减应届生招聘名额。在这段“二战”后最严重的“就业冰河期”从大学、专科学校或高中毕业的,正是20世纪70年代前期至8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们,包括全部团块次代。
经历“就业冰河期”的这代人常被唤作“冰河期世代”,用《朝日新闻》2007年专题连载的标题“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来称呼他们的人也不少。这代人相比其他世代,没有找到期望的工作,陷入不稳定就业泥潭的人格外多。这个称呼似乎很贴近他们的自我认知,也有很多人自称迷失的一代。
2000万人规模的迷失的一代现在正值三四十岁,他们当中不少人工作依然不稳定,靠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与父母同住,没有成家,对未来感到不安。媒体还给他们起了“四十危机族”“中年打工族”等新名字。
本以为是找到正式工作前的过渡
再过20年左右,这代人也将步入老年。面对自己的老去,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这里我想介绍一位采访中结识的男士。
这位41岁男士在一家公司当了将近20年的非正式员工。
他从关东地区的国立大学毕业那年,正值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六成的2001年,也是第一届小泉内阁成立,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那一年。
这位男士当时也没有想好毕业后做什么,求职季只参加了三四家公司的面试,所以没能找到工作。据说当年很多学生投递了一百多家公司也没有找到工作。他所在的大学情况也不乐观,毕业时已经拿到录用通知的人反而是少数。
大学毕业后,为赚取生活费,他开始在一家对公零售企业做临时工。他没有信息设备进货销售方面的经验,工作所需的技能全靠自学和钻研。很多兼职工和临时工干不了多久就会辞职,所以有时候他不在就忙不过来。他本以为这份工作只是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过渡”,没想到一干就是好几年。
“当时觉得能有活干就不错了,现在看来是我想得太简单了。起初时薪大约900日元,每月到手工资也就15万日元左右。虽然收入很低,但可以长期做,所以当时没有足够的危机感。”
开始工作后不久,店长认可他的工作表现,给他涨了时薪。因此,在连日加班的繁忙期,到手月工资有时也能超过25万日元。然而那位店长被调走后,接下来近十年他一直没有涨薪。他感觉到加薪与否全看领导的意思,与能力、经验完全不挂钩。
“我明明只是临时工,但只有我会干的工作却越来越多。正式工不了解一线的具体情况,和客户打交道时做不到临机应变。我原以为自己想走的时候可以随时走,但忙碌的工作挤掉了求职的时间。渐渐地,比我年轻的正式员工越来越多,现在连店长都比我年纪小。即便如此,对那些经验尚浅的正式员工,我还是会尽量照顾到他们的体面。“
根据客户情况调整订单需求并保证按期交货需要经验和细心。做这些通常由正式员工做的工作,让他很有成就感。
他被客户误认成正式工的次数也更多了。“咦,你是临时工啊。我还以为你是正式工呢。”然而,男士对公司的贡献没有得到认可,而且根据上面的方针,他还被禁止加班,到手月工资最多只有16万日元了。在男士看来,公司依靠临时工维持运转,却不改善他们的待遇,甚至把人当“成本”。
“客户都很信任我,可当我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向领导提建议时,领导却觉得我在批评他。工资低、待遇差已经够郁闷了,工作得不到认可对我的心理伤害更大,仿佛整个人都被否定了。”
责任该由谁来担
十八年间,这位男士并没有“躺平”。他一直在等待机会转正,也投递过其他公司,然而“应届生”门槛阻断了他的前程。简历的工作经历栏只能填“打工”,所以被当作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新人;参加其他公司的面试时,也总会被问及“为什么毕业时没有找到工作”。白发已经悄悄爬上头,而他现在还住在年过七十的父母家里。
“说到底还是太依赖父母了。我觉得40岁是一个分水岭,而我已经过了这个年纪。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虚度了半辈子。就这条件,我也不敢考虑结婚。照这样下去,晚年只会充满不安。”
这就是迷失的一代。这位男士自称“吃亏的一代”。即便如此,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还是后悔和自责。
“这些年我也并非没有努力,但最后还是没有正式工作,我觉得是自作自受。和求职季投了几百家公司的人相比,我还是不够努力。上大学时没能找到兴趣点,该拼的时候也没有拼出成绩。混成这样也有我自己的错,不能都怪就业冰河期。”
他把自己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讲给我。这些年他对待工作肯定也是这样真诚。听完他的讲述,我不认为这个责任在他自己。
永不消融的冰河
迷失的一代如今也到了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纪,而包括这位男士在内,他们依旧靠非正式工作和微薄的工资过活,没有摆脱“迷失”状态。这才是这代人的真实写照。
步入社会的时间仅相差短短几年,却给今后的人生带来难以逾越的差距。这一现实在统计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
对比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中2010年和2015年的工资金额,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35~39岁人群和40~44岁人群的工资相比大幅减少。也就是说,迷失的一代拿到的工资比大他们五岁的人在相同年纪时拿的还要少。得出这项结果的联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除工资以外,在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在职时间、20~29岁的能力发展乃至幸福感上,迷失的一代评价都很低。显然不论是否成为正式员工,这代人都“受到了亏欠”。
负责整理调查数据的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这样分析:“这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永不消融的冰河’,这代人到了中老年仍会面对严酷的现实。要想拯救冰河期世代,眼下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等他们到了50岁,再让他们从头来过也来不及了。”
智库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调查也揭露了迷失一代的具体困境。男性中从事非正式工作以及不工作也不求职的非劳动人口比例,比年长世代更高,该研究所认为这一现象与中老年“家里蹲”人数的增加有关。
迷失的一代的问题绝非这个群体自身的问题。这个群体现在受到关注,是因为庞大的人口群体处于不稳定状态,使日本社会整体受到沉重打击。
主角是女性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直面就业寒冬,被卷入非正式劳动力激增的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角”不是男性,而是女性。从事非正式工作的青年健康男性增多更吸引眼球,所以“男性非正式工”格外受媒体关注,但在此之前,女性就业早已出现大规模的非正式化。
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跌破60%的2000年前后,即便毕业于同一所一流大学,女生的求职之路也要比男生更加艰难。甚至有公司制定了“不招女生”的潜规则。在男生们陆续拿到录用通知的同时,很多女生投递了几十家公司仍没有找到工作,只能选择非正式岗位。
总务省2018年实施的劳动力调查显示,男性员工中非正式劳动力占22%,这一比例在女性中则高达56%。虽然该数字包括了结婚辞职后又出来做兼职的家庭主妇和老年女性,但女性从事非正式工作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以上。这一事实理应受到更多关注。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非正式工作的男性虽然也在增多,但派遣工、合同工、兼职工的主体依然是女性。
退休后钱会不会不够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三四十岁单身女性们对未来充满不安。身为派遣工或合同工,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支撑老年生活的养老金、储蓄和家人的援助都很微薄。“无退休”的不安已经蔓延到超高龄社会的主角——女性们的身边。
迷失的一代需要补贴
2019年秋天,我遇到了一位属于迷失的一代的43岁女士。拥有本科学历的她至今仍在从事非正式工作。
她哽咽着对我说:“我希望国家为迷失的一代提供补贴,就像育儿补贴那样。不要把错全推给时代,抛弃我们。”
“优秀职场人”是我对这位女士的第一印象。她因工作稍微迟到了一会儿,特意事先电话告知,见面后还非常郑重地向我道歉。她着装举止也无可挑剔,是一名通晓商务礼仪的职业女性。
就算她说自己是一流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我也不觉得奇怪。然而,现实中她却是东京一家公司的合同工,为了完成繁忙的工作争分夺秒,只有午饭时间可以离开工位。
像“昭和白领”那样在茶水间边聊天边品茶的生活,她根本不敢想。但即便全身心投入工作,年收入目前也只有280万日元左右。和十年前相比,时薪只涨了50日元。
这年9月,台风登陆关东地区导致首都铁路交通瘫痪的那一天,她花了四小时从家去公司上班。“如果同事们都不缺勤,我即便不情愿也不得不去。我是时薪制,而且休息了工作没人做,第二天还得加班。”
这位女士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我根据她的讲述整理了她这20年的经历。
她生长在一个昭和时代的“标准家庭”:父亲在大企业上班,母亲和父亲在同一家企业工作,结婚后离职做家庭主妇,生养了两个孩子。她从私立高中考入中等私立大学,毕业找工作的1999年正好是就业冰河期。她向一百多家公司寄出了索要招聘资料的明信片,获得面试机会的只有二成,并且都没有拿到录用通知。
最后,她经父亲的熟人介绍进入一家上市集团公司,正式走上社会。可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家公司只给女员工分派辅助性工作。早上擦桌子、整理报刊架也要女员工来干。
在昭和时代,女性通常通过“一般职位”进入公司,负责端茶倒水、复印资料;和公司里的20多岁男同事结婚后离职,回归家庭。这种企业文化被这家公司完完整整地继承下来。这位女士曾经提议用计算机提高工作效率,却被男领导拒绝了。
在这里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她想进一步提高职业能力,干了三年半后决定辞职。当时正是《年轻人为何三年就辞职》(城繁幸著,光文社新书)一书畅销的几年前。
“现在想来,如果当初在那家企业坚持干下来,或许已经等到机会了……”
辞职后,她换过多次工作,以派遣工和合同工为主。在默认应届生统一招聘的日本雇佣环境下,社会招聘的市场很小。每次换公司,待遇和劳动条件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越来越差。
其中一家是社长独裁的公司。那家公司类似于现在所说的“黑心企业”,两小时以内不算加班,也不准员工带薪休假。
她还在一家“共享服务”公司干过——企业集团为削减成本,把人事、会计等职能部门分割出来成立关联企业,以外包形式进行这些业务。这里的员工大多从一流企业的总部调动过来,实质上就是裁员。因此公司里充斥着自暴自弃的氛围。公司活多人少,她每天工作到深夜,赶末班车回家,到家倒头便睡。亲属过世请丧假时还挨了批评。
“周末两天也要上班。长时间劳动削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渐渐就会觉得,只要有地方愿意用我就知足了。”
即便如此,她仍然没有忘记提升自己。利用工作间隙学习,她考下了会计、计算机、托业和社会保险咨询师等资格证。但公司以年龄和缺乏实操经验为由,不给她转正。在她待过的几家公司里,连正式员工都疲惫不堪,甚至有人患上抑郁症。其中一家公司的40多岁单身女领导告诉她:“在这里,你会像我一样被工作榨干。我已经放弃结婚生子了,你如果还有这个打算,最好离开这里。”
“失去的二十年”,这个说法存在已久,而这位女士这些年的工作经历仿佛处在日本企业这二十年间的各种节流和裁员的第一线。她工作过的很多公司裁掉文职岗位,用非正式工替代,把一整个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公司来削减用人成本,强迫那里的员工长时间劳动。
据她说,这种公司的非正式岗位上总有许多迷失的一代的女性。她们学历高、能力强,工资微薄,还时刻担心公司拒绝续签劳动合同。恐怕没有比这更好利用的员工了。
想象不出安享晚年的自己
虽然女性被企业定义为廉价劳动力,但她们也有今后的人生。身处非正式岗位的单身女性经济基础薄弱,也很难得到家庭、储蓄、养老金等安全网的援助。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40年,女性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未婚率将从2015年的4.5%大幅提升到9.9%。按照目前趋势,靠养老金和储蓄不足以为生的女性老年人口或迅速增加。
记者结识的这位女士也对晚年感到不安,她说自己在日本年金机构的网站上计算过65岁以后能领到多少养老金。截至目前每月能领6万日元左右,如果今后继续工作,每月兴许能领到10万日元。为确保晚年有钱可用,最近她参加了“累积小额投资免税项目”(NISA)。
“只靠养老金生活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多干几年,但体力肯定会越来越差吧。父母那一代还能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但在我和朋友们生活的时代,努力根本得不到回报。”
女士完全想象不出自己安度晚年的未来。对“无退休时代”的不安使她产生了那个想法:“希望国家为迷失的一代提供补贴。我们这些没有孩子的人与育儿补贴和幼托免费政策无缘,却还要缴税。在劳务派遣公司工作的时候,很多工作内容是给休产假和育儿假的正式工补空缺。在世人讨论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会不会休陪产假的时候,希望大家也能理解一下没有孩子的人的心情。”
年轻一代也出现养老焦虑
年轻时的挫折会直接导致后半生的不安。即使努力维持眼下的生活,想到年老后还是很害怕。这样的年轻女性在逐渐增多。横滨市公益财团法人“男女平等促进协会”以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单身女性为对象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约83%的受访者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
“没有离职金也没有奖金。将来要想活下去只能申请低保。希望国家开设安乐死机构。”(35岁)
“退休后,光靠退休金连养老院都住不起。我大概会一个人死在家里吧。”(44岁)
“自己老了以后也没有个伴儿,身体或工作出问题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决。很不安。”(35岁)
负责这项调查的该协会职员白藤香织(50岁)在听到众多女性的心声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单身女性既没有家人,也没有住房。她们不清楚自己能工作到什么时候,需要多少存款维系老年生活。未来一片灰暗。她们觉得没有任何人关注到自己的处境,孤立感越来越强。她们是被社会遗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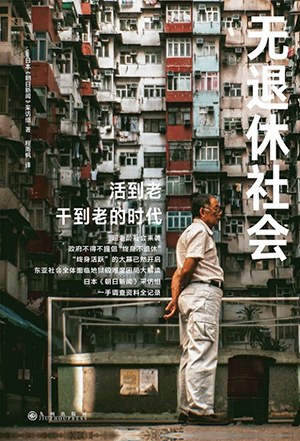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