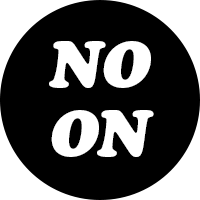文 | 顾闳中
在许多人眼中,青年旅馆往往跟背包客、间隔年联系在一起,公共活动空间让青年人有机会结识新朋友。2008年,我曾用两个月走过川藏线,一路都住青旅。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总能讲出旅途中的惊险故事或小众景点,能碰到那么多热情又同频的的旅伴真的很难得。怀着对青旅的美好念想,近期我在上海又住了一段时间的青旅。这次的经历让我发现,原来今天的“青旅”住客已是完全不同的人群。
我是因为一份新工作来上海入职的,离报到时间还有十几天,我也吃不准会在这个单位呆多久。周围的公寓房起码3个月起签,稍好一点每月要4K左右,思来想去,我决定暂时住青旅。
在上海这种超大城市,许多所谓的青旅,选址在写字楼周边的居民小区,由几个套房改装而成,其实只是一种提供低成本住宿“类青旅”形式,没有青旅通常都有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厨房。这类青旅里挤满了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多是文员、店员等劳动密集型职业,工作稳定性不高且收入有限。住在这种“改造型青旅”甚至成为在这个城市谋生的一种生活方式。
最后,我挑中一家位于张江高科的青旅。我挑了一个四人间,水电宽带全包,每天有人打扫,24小时热水,床位费80元一天。周末我一般回苏州,这样既能继续驻守苏州,也不耽误上海工作。四人间没有八人间那么嘈杂,住的人总是不满,因而有了足够的交谈空间。在这个四人间里,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她们都有各自的故事。
小敏,往返沪杭的单亲妈妈
小敏生于1980年,杭州人,在上海浦东一家药企做“成果转换”。她日常接触对象都是高知,精确说,即高校内持有专利的知识分子,她的职责就是推动专利进入投产渠道。
敏算是被工作绑在上海,但对上海并无过多留恋的人。敏在这家青旅住了很长时间,每周末回杭州和儿子团聚。她觉得,如果租房的话,有点浪费。而且张江这地方,虽然看着也挺乡下,但是租房价格并不便宜,这也可能和附近的几座大医院有关。在青旅住,她不得不忍受一些不便,比如不能做饭,干净程度也经不起精细打量。每周入住时,她都需重新铺上青旅给的三件套。
敏每天早7点会给在杭州的孩子叫滴滴上学,放学的时候再叫一次。听她和儿子的电话,每次说话都那么温柔和缓。十月中旬的一天,小敏提早收拾行李回杭。她跟我打招呼:因为父亲病了,需要她去照顾,这两周应该都不会来了。
我曾经问她,你那么关心儿子,找个杭州的药企很难吗?敏说杭州没法和上海比,所有大型知名药企几乎都聚集在上海。疫情最后一年,阴差阳错她去苏州工作了一年,苏州的药企机会都比杭州多一些,后来解封,她立马又回到上海工作。
敏告诉我,这个青旅的八人间、十人间经常供不应求,长租的人非常多,一部分是附近住院病人的家属,一部分是打工人。依我的粗略观察,隔壁那些多人间,总是住得很满,房间嘈杂,几乎都是刚出学校的稚嫩面孔。
敏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栖居青旅,她不得不做出一些生活质量上的让步。一边是建立经济基础的上海,一边是家人团聚的杭州,高铁让双城记变得便捷,每周往返奔波,我看到的是一个带娃中年女性的坚韧。
我自己每周往返苏沪,也觉得累。虽然高铁也就二十几分钟,但频繁进进出出仍然消耗人。每周一,早班高铁上清一色的年轻面孔涌出虹桥站,而我的意识还飘在苏州的梦乡。6点多坐头班高铁,9点到单位,还没开始工作,疲惫就占据身心。
四川阿姨的陪护难题
敏走了,来了一位四川阿姨。四川阿姨刚开始也悄无声息,回寝就安静地钻进床位,拉上床帘,很小声地看手机。对于公共场合主动关轻音量的人,我心生好感。有次就主动搭讪她,说着说着,阿姨的倾诉欲就上来了。
这个年纪住进青旅的不多见,阿姨来自四川农村,育有一儿一女,都已上班。她此前住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因为房租便宜。这个青旅还是女儿让她来的。她常住上海的原因很残酷:老公去年九月被车撞了,在附近的曙光医院医治一年多,情况不大乐观。
因为身体、脑部受到损伤,她老公长期卧床。有一段时间情况好转,又碰上肠梗阻,因为久卧,肠胃蠕动少,这些附属病都来了。肠梗阻治疗相对稳定后,又是肺炎,一不小心进了重症室。阿姨其实不希望他老公进重症,但进不进重症阿姨没有决定权。最近医生下了最后通牒,让他们做好料理后事的准备。
她的子女也请假轮流照看父亲,阿姨本人已退休,有农保退休金。她长期陪护,同时也请了护工。听阿姨讲话多了,我由衷感叹,这大概就是典型的中国妇女,吃苦耐劳、善良温情。
说起护工,阿姨感叹,有家人和没家人的病患,从护工那边得到的照料不可同日而语。对有家属的病患,护工会尽心一点;没有家属的,屎尿也不给你挤,甚至懒得给你翻身。即便有阿姨这种长期陪伴在病人身边的,如果不督促护工帮助病人排便,护工也不会主动去做,因为太脏。
他们家叫的是共用护工,即一个护工同时照顾三四个患者,一天人均200~150元。疫情那个时候,医院不让家属进去陪护,而院外护工可以,那段时间的护工都是日入2k。当然,这样的高回报,挣的确实是辛苦钱。
阿姨感叹,陪护病人比自己上班工作更累,每次来都得瘦几斤。中国家庭最怕的就是大病了,一人倒下,影响全家,花钱不说,还要匀出很多陪护时间。大医院旁边的房租贵,所以刚开始几个月,阿姨住在较远的乡下。虽然她老公是因公出事,住院有赔偿,但自己积攒的那几个钱,也经不起在大城市这么花,所以能省则省。
阿姨说,陪护的人也很煎熬。因为他老公有痰,夜里总咳,她就要起来帮助吸痰。这样根本休息不好,加上担心忧虑,所以她的精神状态不大好。她说,护士也会给吸痰,但每次戳管子的时候没有耐心,特别粗鲁,弄得患者很不舒服。她每次都尽量自己做,久而久之有了经验怎样让管子温柔地进入病人的喉咙。
有天阿姨整理东西,说要搬走了,因为儿子即将回去上班,她就可以长期住院陪护。祝愿阿姨身体健康,也愿他老公早日康复。
洁的婚姻围城
洁似乎是个i人,一看就不爱与人搭讪,平时避免和室友有眼光接触。没想到当我主动跟她打招呼,这姑娘打开话匣子就关不上了。洁只是路过短住两天,和上海没有更深的纠缠。
洁离婚一年了,至亲知道,亲戚不知道。因为不想被人问(怎么小两口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啊),所以2024年春节她没有回家。洁的老公是她的高中同学,从高中、大学到就业,共谈了7年恋爱,结婚也已满6年,算得上青梅竹马。婚后男方对她不似婚前那么宠爱,与她的心理预期有落差,或者说,两人都不是服务型配偶,最后不快积聚而致离婚,好在没有小孩。
但两人仍然十分迷恋之前两两相依的状态,所以离婚后又说上话,周末约着出去共度了几次,说起这些,她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开心。
我说,你那么在意以前那些不开心,为什么想要和他再婚?
她认真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感受,说起前夫近期对自己的百般殷勤,觉得生活似乎还有奔头。另外,也觉得已婚身份在老家人面前更“体面”。她真的没有办法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最后我们一致认同:她就是那种天生需要有亲密关系才觉得自己更完整的人。
琳,精打细算的河南姑娘
新入住了一个河南姑娘。本来各自吃着外卖,盯着屏幕,感觉八百年也不会对话。我主动挑起了话题,感觉不聊家常,空气实在太闷。
你是来这边工作的吗?话题一起,小姑娘的话就汩汩不断了。
她刚来上海,网上面试拿到了曙光医院的offer,做药物试验。每次新药出来,他们会辅助医生护士去推销新药。严格的说,他们是乙方身份。
因为国家医保新政出台以及经济下行,药企也经历了滑坡。当然,瘦死骆驼比马大,状况还不那么凄惨。他们这个岗位,以前是供小于求。只要你肯跳,只要你敢要,高薪不难。但现在显然是供大于求了。
我问她,河南没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吗?她说有,只是河南的薪水没有上海高,但是郑州的房租以及各方面开销却和张江齐平了。
出来打工,绕不开租房这个话题。姑娘虽然第一次来上海,才两天,已经在朋友的指引下,租好了房子。她在小区看的那种多人合租有独卫但共厨的房子,一月2100,已经签了合同,就等上家搬出来,她周末搬进去。我这才发现,我在附近看的都是单身公寓,显然2k的价格只能住得很憋屈,住得稍微舒坦点的要4k左右。
姑娘说,上海张江这边的小区更有性价比。她其实还看了另一个小区,配备更齐,家装也更新,价格更便宜。我问为什么条件更好还更便宜?她说,这边不比市中心,很多人买房就是为了租,目前租房市场供大于求,所以纷纷降价。她为什么不选择那种房子?因为怕新装修的有甲醛,所以宁可多个一两百,去住那种看起来旧旧的房子。我心想,这姑娘心思还挺密的。她还提到另一个原因:房租虽然便宜一点,但是水电上可能会超贵,房东可能在水电表上动心思,住进去你就发现每月费用特别高。
姑娘的各种信息源,听得我一愣一愣的。这姑娘外表看起来胖胖的很可爱,内心却是精打细算,做任何事情都有目标。
在青旅遇见很多人,不一样的地域,不一样的家庭故事,杂糅着不一样的生活智慧。拉上床帘,独对自己;打开床帘,就是世事万象。
——完——
作者顾闳中,资深平面设计师,曾长期供职于媒体。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