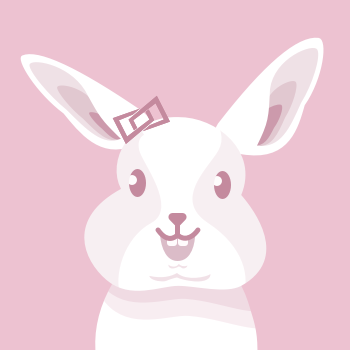采访 | 黄锫坚 王强
盛夏北京,我们与王笛约在CBD的一间星巴克采访。不料这家咖啡店周末休息,真不知是该叹息此地的人流过于稀疏,还是该赞赏此店在维护某种商业传统。无奈,我们只得穿过东三环,在烈日暴晒和暑气蒸腾中走了几百米,才找到一间冷气充足的咖啡馆。置身于林立的高楼中,抬眼望去,全是玻璃幕墙包裹的写字楼和商场。在感叹天气反常的同时,我们也抱怨CBD的城市规划对行人太不友善。在王笛看来,这种不人性的建筑规划,是权力和资本钟爱的“光辉城市”的样版。他更希望城市是有生命、有血脉的。人,而非建筑,才是城市文化的载体。相比北京,他更喜欢成都的聚会氛围。比如和老同学们约在一间绿树成荫的茶馆。在成都,你不用太守时,先来的人可以喝茶、吃瓜子、打牌或者麻将,等人聚齐后,再去附近的饭馆吃饭。
作为历史学家的王笛,其研究和访谈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涉及城市规划和街头文化时。说到北京的中轴线,他会想起晚清民国的天桥,那里如何成为外来者的容身之所。说到无人便利店,他会提及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如何方便,为左邻右舍提供热水和歇脚之地。说到北京的咖啡馆,他会想到成都的茶铺、茶馆和茶楼的区别,以及法国沙龙、美国酒吧和成都茶馆的异曲同工……
王笛本是在书斋和故纸堆里研究历史的人,过去几年却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视野。他在成都长大,80年代在四川大学求学和任教,1991年赴美读博,后在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2015年回到澳门大学教书。
说起自己和成都的关系,王笛自己都觉得很奇妙。2006年开始,他的著作《街头文化》《茶馆》《袍哥》陆续出版,这些书大多和成都历史有关,在学术界赢得了许多关注,但在成都并没有太大反响。那段时间,他回成都,大多是在四川大学开会或做讲座。这几年情况有所变化。回成都时,他往往在社区茶馆、图书馆和博物馆露面。当地商界政界人士都想要认识他。也许,随着各地为吸引投资和游客而绞尽脑汁时,茶馆逐渐成为成都最独特的文化名片,而王笛则当仁不让地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名人,有关部门甚至准备给他建一个文献中心。
和许多学者不同,年近70的王笛,没有微博、微信公众号,也不发朋友圈。他很奇怪,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和了解他的研究。在他看来,众多媒体的采访,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此功不可没。过去他的学术著作都在专业出版社出版,最近几年的大众类读物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销量可观。除了历史类读者,来自城市规划、建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读者,都喜欢读他的书。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成都的一位朋友看到这本书,决定做一个以茶铺为主题的展览。地点选在某一座修复后的老建筑,人们可以先去有名的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喝茶,然后移步50米便可以看展。展览参考了王笛在书中画的19幅插图,重新做了设计。王笛认为,如果他的学术研究能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为城市生活、城市规划提供一些参考,则功莫大焉。

拉黄包车的,在北京也可以享受相当的自由
正午:7月底,北京的中轴线正式入选世界遗产。一个帝都的城市中轴线,在不同时代意味着什么?除了政治秩序的传达,从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角度,可以怎么解读?
王笛:从钟鼓楼到永定门,这一条线包括天坛、故宫、天安门等十多个遗产。北京城的面貌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永定门就是后来重修的。北京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决定投降,很大一个出发点就是不愿北京城被战争毁掉。可悲的是,1953年讨论北京城往什么地方发展时,梁思成的想法被抛弃了。他曾明确提出规划——在北京城之外修建行政中心,但最后占统治地位的决定是采用苏联的建议。苏联还派来城市规划专家,方案就是在北京的中心建天安门广场,按照苏联的大广场、大建筑思路,后来还有50年代修的十大建筑,包括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等。到1958年左右,开始把一道道城门拆掉,让位于汽车交通和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在最高领导人的观念中,北京要变成一个工业城市,站在天安门广场可以看到烟囱林立,而古代城市怎样保护,没有考虑过。
在当时看来,北京也好,成都也好,都是封建的城。这些城墙实际上是阻碍现代化,阻碍交通的。大概十几个城门楼对当时北京的城市规划有妨碍,所以要拆除。现在保留下来的城楼非常少了。当时,包括历史学家吴晗都认为,梁思成的理念过时了,跟不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当时梁思成说过,你们要后悔的。现在看来,中轴线真的还算万幸,重修了很多建筑,勉强形成一个中轴线,它包容了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
中轴线申遗成功,说明北京留下了一些代表性的建筑。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更想思考的是,该怎样看待我们的过去,怎样看待老建筑。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在研究中一直主张,要走出帝王思想。我们都知道,北京城一直是都城,中央帝国的首都,从天安门、永定门到安定门,都是皇权的象征。很多老百姓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过去能修建出这么精美的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建筑、城楼。但我们在看故宫的时候,必须想到,在皇权的专制统治下,这些都是财富和权力的艺术,过去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享受,和广大普通民众没有关系。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老百姓都在旁边看着,甚至还哄抢。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当然,这些建筑保留下来了,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建筑经常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反思,历史到底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我们今天怎样去思考集权王朝体制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创伤。
第三,哪怕在皇城根下,你看那些老照片,在紫禁城外,在正阳门、永定门等大城楼下,在天坛的外面,就是天桥这样的世俗场景。天桥的面积很大。你去看清代北京的地图,天桥的规模几乎可以和天坛相比,而且是挨着的。天坛是皇帝祭祀的地方,怎么允许在皇帝眼皮底下有这么多的天桥杂耍、唱戏的、妓女,几百家商铺,各种公共空间,三教九流等场景。在清代帝都,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庙堂之下就有江湖,这在现代化以后是不允许的。
现代化其实是不断地强化权力的神圣性。20世纪初,特别是警察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天津在袁世凯当政时最早出现警察,然后各地开始设立警察,向日本、美国学习,包括北京。设立警察以后,政府不断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规范,包括交通怎么规划,哪里能够摆摊,直到现在为止,整个城管的理念就是在20世纪初形成的。
20世纪之前,你随便在哪个街头,都可以扯场子、卖打药。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大概1995年,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那里有专门的影像部。北京的老照片太多了,成千上万,上海也多,但是成都的老照片,我没有找到一张,这个例子也折射出研究内陆城市的困难。帝都是多么庄严的地方,但实际上却是两张皮。最低层的人也可以在帝都为生,像老舍写的骆驼祥子的故事。拉黄包车的,在北京街头都有着谋生的自由。为什么清朝一到灾荒,大量移民就进入到城市?就是如此。
今天我们喜欢干净的、整齐的、管理严密的城市,认为低层次人群和城市是矛盾的。其实北京、成都等地的建设和发展,绝大多数要靠所谓的低端人口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做建筑的,开商铺的,跑堂的,澡堂子搓澡的,三教九流都有。所谓的北京文化,宫廷文化其实是极少一部分,更大量的文化是在一般民众中形成的日常生活,包括语言、饮食、穿着,还有北京的街区,如四合院布局。作为帝国的首都,城市建设的布局肯定需要规划,但绝大多数的小街小巷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间形成的。
现在的城市也面临类似问题。哪怕是一个新建的小区,在规划下面也要允许有自然发展的空间。以前,一些小区由于生活不方便,开始穿墙打洞,把一楼空出来,开成小卖部、咖啡店、花店。各种日常设施,要做到走路就满足基本需求,比如购物、上小学和幼儿园、买早餐……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谈过很多这方面的需求和案例。
城市是有毛细血管的,不能只有几个大架子。而现在的高楼、单元楼,是最封闭的。人们即便住在隔壁,一般都不发生什么关系。而过去的好多文化是在邻里基础上出现的,比如小卖部、理发店、花店、杂货铺等。可是,现在人们都到超市去购物了。在超市,人与人之间没什么关系,越来越多地直接到机器上结算,无人商店甚至连看店的人都不需要了。
天桥与茶馆
正午:你对成都的茶馆有专门的研究,能否讲讲茶馆和天桥的区别?记得董玥的《民国北京城》选择了天桥作为样本来讲述民国北京的文化氛围,她关心的是精英知识分子、大众和地方文人的冲突。
王笛:我觉得天桥简直是一个研究的金矿。每个城市都有类似天桥这样的地方,上海有大世界,成都有华西坝,也叫扯谎坝。之所以叫扯谎坝,因为都是卖打药的、跑江湖的,都在那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谋生,所以叫“扯谎”,即四川话的“撒谎”。如果我来研究北京,会以人为中心来写天桥。
茶馆和天桥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天桥是一个大区域,你看北京的老地图,天桥挨着天坛,好大的街区,几百家店铺。而成都的茶馆分布在各个地方,每条街一两家。董玥写民国的天桥,用了回收(Recycle)这个概念,就是各种破烂都可以在垃圾里重新循环、再利用。所以,天桥是非常独特的地方。而茶馆不一样,空间更小,是专门喝茶的地方。
天桥有三教九流,比如说有秘密社会、乞丐、做生意的、跑江湖的、算命的、唱戏的。而小小的茶馆也可以容纳所有这些人群,所以,茶馆是个微观世界。
如果要研究微观史,可以写天桥。但茶馆更典型,就是从一个小的窗口去看一个大的世界。茶馆里有听评书的、看曲艺的,包括20世纪初电影的出现,最早都是在茶馆里。我在《消失的古城(增订版)》一书专门讲了电影怎样在成都出现。北京是先有戏园,后来才有电影院。成都刚好相反,所有戏园都是从茶馆演变过来的。大家在茶馆里不能干聊天,于是有人来演出,提供娱乐,戏园就这样渐渐发展起来的。
正午:关于民国北京,还有哪些著作值得推荐?
王笛:我有个师兄,叫程为坤,我们都是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学生,他比我高几届。我到美国读博的时候,他刚毕业,在找工作。非常可惜的是,一家人出车祸,他和他妻子都死了。他专门研究北京的下层妇女,他的书后来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出版后还得了奖。三联出了中译本,叫《劳作的女人》(City of Working Women: Life, Spa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我有个师弟,现在华盛顿大学当教授,叫马钊,写了一本书,叫《战时北京离家出走的妻子、城市犯罪与生存战略:1937-1949》(Runaway Wives),哈佛大学出版的。更早一些关于民国北京的研究,有一本是史谦德(David Strand)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这本书非常好,得了列文森奖,讲的是1920年代北京的劳工和劳工运动。
光辉城市、生态城市
正午:关于现代城市发展,大概有哪几种理念?
王笛: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版)》中有一个比较长的讨论。柯布西耶的理论对中国的城市规划有很大影响。柯布西耶是法国建筑学大师,对搞建筑的人来说,是要烧香拜佛的人物,绝对的权威。柯布西耶的理念叫“光辉城市”,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对“光辉城市”特别感兴趣,比如苏联、中国,还有南美的一些城市,全世界有好多范例。
建筑也是一种权力。我们的政府机构,哪怕一个县政府的大楼,也要走很多台阶才能上去。普通人要走上去的话,有一种心理压力,步履沉重,充分感悟到权力的威严。大道、大广场、高压迫感的建筑,都是光辉城市的展示。对一个从乡下来的人,在光辉城市,他无所适从,都不知道去哪里吃饭,哪里去歇脚,哪里去上卫生间。北京和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是如此。千篇一律的大广场、大道、高楼、购物中心、地铁……上个月刚去世的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对柯布西耶的理念有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他是大型的、机器时代、垂直等级的极端体现。为了强有力的视觉冲击,不考虑城市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以及城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种城市发展观念,来自美国的城市学家芒福德。芒福德说,城市要讲究生态,他的主要的观点是,城市是有生命的,有血脉的。城市应该是市民的城市,城市人要有尊严地享受自己的幸福生活。一定要讲究文化的底蕴。现在说的海绵城市,特别像芒福德的观点。他说,钢筋水泥把地下的水脉都切断了。现在许多城市,不管你挖多深,都没有水。过去成都向下挖1米就出水了,现在的城市地基挖太深,把水脉都抽掉了。到处是人为的景观,看不到自然。芒福德特别强调,城市是有机体,一定要把城市看作有生命的,也有从生到死的周期。而现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变成鬼城、死城,高楼林立,到晚上黑漆漆的一片,没有生机。
而我最赞同的城市理念还是J.雅各布斯的观点,她讲过波士顿北段的故事,那是一个贫民区,但犯罪率很低,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是当地最健康的社区。雅各布斯主张多样化和适合居住的社区。如果她的理念早40年在中国被接受,那么,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成都的铺面房就不会被拆。中轴线固然珍贵,我更可惜的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街道布局,传统的城市景观,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正午:在很多地方,申遗成功后,本来的老居民却可能被清退,当地又经历某种重建。
王笛:我们现在一搞开发,就把原来的居民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其实不管是中轴线,还是其他文化遗产,原来的居民、原汁原味的文化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人,文化的载体就是这些人一代代的传承。你把他们抽空了,变成冷冰冰的建筑,那还有什么文化?中国的理念必须要改,文化是由人来传承,一定不要用建筑来取代人。不能把原来的居民统统迁出,不能轻易把老建筑拆掉。比如北京,从申办奥运会成功开始,后来几年的大拆,对北京城市的伤害很大。按道理说,举办奥运会应该保护城市文化,但实际的效果却是相反。这次巴黎奥运会就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在国内却是一片的嘲笑之声,真的反映了我们与巴黎在城市认知上的差距。历史的大叙事,帝王的历史观,已经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根深蒂固,对宏大建筑、大广场、大道的崇拜,其实就是这种史学观影响的一种后果。
正午:巴黎奥运会好在哪呢?
王笛: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不是靠钱,而是靠文化和软实力。巴黎奥运会的好,就好在它是利用原来的空间和场馆来办运动会,奥运会和整个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开幕式,就在塞纳河上举行,完全是开放的,巴黎没有新建什么大建筑。其实,好多城市都办不起奥运会了,比如希腊,因为办奥运会而负债累累,当地居民都反对。巴黎创造了一个范例,就是利用原来的资源节俭办会。我觉得巴黎奥运会是一个转折,以后不应该有国家为了奥运会而大拆大建,影响城市本来的景观和文化。
开在庙里的茶馆
正午:记得你讲过一个案例,有个茶馆,就开在成都的一个庙里。
王笛:对,就是文博大茶园,就在大慈寺里边,我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一书里提到过。大慈寺是唐代的庙,后来遇过大火,明清重修过,后面是和尚街。我1997年在那里考察的时候,周边都是两层的铺面房,非常大一片。那时候成都已经在拆,但那个街区保留得非常好。大慈寺里边的茶馆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进去是三个大殿与三个大院,就是一个殿和一个院子交替,大殿和院子全开成茶馆,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由于大慈寺属于文博单位,他们就把大茶馆缩小了,现在茶馆的面积很小。
我的观点是,那个大茶馆的文化价值其实是超过那几个大殿的。为什么?因为那几个殿已不是当年的木结构,重修后我去看过,柱子都是水泥的了。作为一个古建筑,文物价值大打折扣。虽是文物单位,但大殿只剩下躯壳,我认为,当年的文博大茶园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价值其实已经超过了大殿。
我明年会出版我的茶馆考察笔记,书名叫《日常的史诗》,其中一部分就是写的文博大茶园。从1997年到2023年,我在成都多次考察。每次考察都有详细的笔记,记录我看到的故事。这不是学术专著,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录。
正午: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成都人的生活比较悠闲?
王笛:成都人的时间概念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清楚。如果你约上午十点碰面,成都人很难准时到。如果约在茶馆,你早去晚去都行,早到的先在那里喝茶、吃瓜子、打牌、打麻将,晚到两小时都没有关系。如果是要去吃饭,那还是要准时。要不你去了,别人都吃到一半了,不太好,是吧?喝茶就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聚会,尽量找那种有茶馆,附近也有饭馆的。许多成都人聚会时不是直接去吃饭,而是先在茶馆聚,先喝茶,再吃饭。像同学聚会,一般要搞一整天。也有在一个地方先喝茶聊天,午饭打麻将,晚上再吃,吃完再打麻将,甚至玩到深夜。
其实,成都在20世纪20年代就这样子。我在《那间街角的茶铺》里提到,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到成都,看到这么多茶馆里面座无虚席。他就说,你们要珍惜这种生活。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大家都是要向西方学习,很多人认为,这些茶馆早该消亡。而舒先生特别有前瞻。他说,我们在北京、上海,每天忙忙碌碌的疲于奔命,而你们成都是农国的生活,就是传统农业中国的生活,你们要珍惜。他担心宝成铁路修通后,成都生活就会被改变。
到2000年前后,成都其实都还在自卑中:打麻将、坐茶馆,怎么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龙头,成都的生活方式被很多人批评。这个样子,别人怎么可能到成都投资呢?到处都是打麻将的。真是时过境迁,现在人们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认知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没人再提这种批评了。
我想强调,休闲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和现代化并不是矛盾。过去我们觉得是对立的,你必须要改变,才能发展。其实成都的发展也并不慢。但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相当程度上还是保留下来了。当然,成都也在变,我们也得承认,但是不是朝着更适合于人们生活的方向发展,就取决于我们今天对城市的认知了。
——完——
作者黄锫坚、王强,界面新闻编辑。
题图摄影:黄锫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