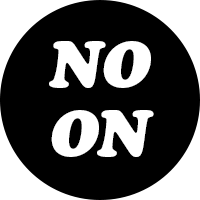文 | 赵景宜
2015年,我刚满21岁,第一次出国旅行。马来西亚是最后一站。从机场出来,巴士往市区驶去。望着窗外大片的棕榈树,想到了《阿飞正传》。阿飞,点解唔愿意畀阿妈睇你一眼?
太阳落山,车到了茨厂街,也就是中国城。我住在一个便宜的旅店里,一个西方嬉皮士开的,帮工是位孟加拉移工,他们都很年轻。除了在车流涌动、几乎没有人行道的都市漫步,我常在旅馆闲坐。某种氛围很吸引当时的我。没有空调的床位房,是最不受欢迎的。那几天,我的室友包括,一个经商的老年印度人,一位只住了一晚、连手机都没办理网络、早上很快离去的日本背包客(我分享了WIFI热点,他执意要我教他几句中文,为了要对我说:“谢。谢。赵。先。生。”)我感叹,哪怕旅行,日本人也好辛苦呀。大部分住客是西方人,有来东南亚过退休生活的,也有想要好好看看世界的年轻男女。
那时,一个舒适的带空调的单间,只需要人民币六十元。我期待有一天也来这里长住。在那个客厅,我们看电影,用YouTube分享喜欢的音乐,聊天,传递无法言说的烟,喝啤酒。我还能记住一些面孔,比如搬到吉隆坡的华人少女,她说新加坡太无聊了。我不敢和她说太多话,我能感觉到,因为我的出现,形成了小小的中文交流圈,这让她不太高兴。这也许是她想要逃离的原因。一个和蔼、外向的华人大叔,这旅店是他的安全屋。他说,他住在马来西亚的另一边,平日里照顾母亲太辛苦,就飞来吉隆坡散散心。
现在想想,我们这些完全不相干的人,甚至有些语言都不能互通,但还是开心地共度一个又一个下午。有天下午,我干脆躺在地板上,在半醒要睡的时候,有人提醒我,可以睡在沙发上。但我只是摇摇头,继续睡去,心里想着:管他呢,反正也是这样的旅馆了。从我的身上跳过去吧!
我真的就这么睡着了,睡的很深,像是忘掉了时间。
吉隆坡
我又要去吉隆坡了。2020年之后,我从没出过国。当我来到萧山机场,看到来自亚洲各国的运动员,流露出比赛后特有的松弛感,我感到一种不真实。对于海关、安检,我感到陌生和不确定。2020年春节前夕,我曾逗留在香港,无法决定回武汉,还是去北京过年。那时我很疑惑:真的只要买张机票,就可以想去哪就去哪吗?
抵达马来西亚,世界变得陌生。我费了很多功夫,才走到正确的地方,买到了一张去中央车站的票。一台很豪华的大巴车,冷气很足,里面闪烁着夜店般的射灯。抵达中央车站,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去往Pasar Seni的地铁线。
进入月台,我很奇怪,为什么英文都不认识了?过了一阵才发觉,字母是马来文。几天后我就不奇怪了。在国家博物馆,有些展品介绍也没有英文,只有马来文。中文标识?几乎是不存在的。
看黄锦树的小说,我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这片多雨的土地到处都是华人面孔。这几十年,整个马来西亚,包括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华人正变得越来越少。我还是住在茨厂街,能明显感觉到华人店主变成了少数。茨厂街与其说是唐人街,不如说是某种飞地。你能去往的地方,有进门要脱鞋的月树书店,书籍大多是华文女性作家。以及,彩虹骄傲的勋章。或者,某个庙宇,一家经营了很久的餐厅。
我从酒店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最左边是一家度假酒店的露天游泳池,游泳的人很少,往右看,是一条热闹的马路,能看到一家老牌茶餐厅。中午去时,茶餐厅坐满了人,我点了一碗冬菇鸡脚面。餐厅是一家三代在经营,年迈的阿嬷正在下面条,青涩的少年走来走去,为客人点单。他的阿公看起来很悠闲,他走出店门口,为街坊——几只跳来跳去的乌鸦——送来了鸡内脏。
同一条街,仙四爷庙的香火很旺。福建闽南的民间信仰深刻影响了海外华人。但也许妈祖、岳飞或保升大帝,都离他们太远。仙四爷是他们的地方神。他叫盛明利,出生在芙蓉。1860年,因为锡矿开采,盛明利带领当地华人与马来人爆发战事。尽管战事失利,领袖也阵亡,但人们认为他已升仙成神。另一位主供的四师爷钟炳,也与另一场1873年战事有关。我想,这些信仰为马来西亚华人带来了独特的国族认同。
那天深夜,我搭乘Grab,路途遥远就和司机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谈到了英文。司机问我,你知道吗?英文和马来语是很不同的,你也可以学一些马来语。“比如,英文是Malaysia,但我们只会说Malay。Malay。Malay。英文是Chinese ,我们会说cina,你可以试一试,cina。试着念一念?”
我还专程去了Kampung Baru,人们说,在首都,这里是最后一个马来传统的飞地。kampung,在马来语中是村庄的意思。很难想象,如此高度都市化的吉隆坡,离双子塔仅隔一个天桥的所在,保留着一处传统村落。最开始还有农田,现在变成了荒地和停车场。
在多年的抗争中,这里作为文化遗产被保存下来。我去的那天是一个礼拜日,分布在不同角落的广播,传来了布道的声音。那天几乎没有游客。偶尔,有穿着长袍的男人走过,他们是来度假的阿拉伯人。
在老城区,每到日落,不少人会拿着纸板,铺在骑楼下,开始过夜。巴生河的岸边,无人光顾的地带,也住着不少无家者。初次到访吉隆坡的人,也许会感到了危险。我想到了台北,也生活着数千名无家者。他们聚集在公园、车站,或者更隐蔽的淡水河边。当地NGO组织告诉我,有些无家者不愿被打扰,他们干脆远离人群,社会蒸发。
离开吉隆坡的最后一晚,午夜我去买汉堡。回来时看到一个赤脚的阿姨,正对着空旷的、只有车流的快速路,不停用马来语说着什么。她赤着脚,来回踱步,语气不满。我很不忍心。我拿着汉堡,走去了不远处的KK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奥利奥饼干,又返回她的领地。她还在踱步、呼告。我说,阿姨,你还好吗?她摇了摇头,不再说话。我问她需不需要水?她摇头。我用手示意,把水放在绿化带的围台上。我说,take care yourself。她没有和我眼神交流,只是点了点头。
我想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如同你无法穿过车流汹涌的一条街时,刚好看到了人行天桥,走上去后,却发现入口锁住了。如同,在吉隆坡散步,常常走着走着,就发现没有路了。










怡保
我坐上了期待已久的火车,从吉隆坡开往怡保。初中时,我在网上搜索东方快车,发现亚洲也有一趟。从曼谷出发,经过华欣、槟城、吉隆坡等地,最终到达新加坡。我想象,这会是一趟充满奇遇的梦幻旅途,沿路见到海、森林、异域风情的城市。
遗憾的是,窗外没有我想象的风景。马来西亚的铁路系统,看起来高效而便捷,车厢很舒适,没有人大声交谈,也没有人外放声音。两个多小时就到怡保了,火车站是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竣工于1917年。
走出火车站,步行就能到达老城区。怡保是个富有魅力的城市,霹雳州的首府,马来西亚第四大城市,共有65万居民。这个沿河城市,像一个迷你版的武汉。靠近车站的这一头,在近打河西岸,过去是一个采矿小镇。十九世纪,随着英国人到来,大力开发锡矿业,怡保慢慢成为了贸易中心。至今仍保留着众多老建筑——渣打银行、海峡贸易大厦,以及怡保大草场,殖民官员们打板球的地方。
1892年,怡保的“外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灾。在英国人一筹莫展时,出现了一位救星。灾后重建,也让怡保留下了深深的华人印记。面对大片废墟,英国殖民者认为必须开发河对岸的区域。可在当时,对岸近乎荒芜,无人愿意投资。一位名叫姚德胜的锡矿商人脱颖而出。
姚德胜出生在广东梅州,一个贫困的务农家庭。这位客家小伙,年仅19岁就来马来亚“过番”。经由新加坡,被水客介绍去了芙蓉的一家锡矿场当苦力。姚德胜用竹子制作了滑道,省了不少投放矿包的力,矿主将他提升为工头。后来他来到怡保,当起了“挑货郎”:从旧街场进货,挑着扁担卖去周围的乡村。极具语言天赋的他,很快学会了马来语、粤语,以及北方官话。他先是在怡保开了一家杂货店,后来用赚取的利润投资锡矿。还与当地富商合作,承办酒税、典当税。
姚德胜横跨多个产业,仅是矿山的雇工,最多时达三万余人。1892年大火之后的短短几年,姚德胜在河的右岸,建设了三百多家店屋,越来越多人搬了过来。他还捐献了一个地段,让英政府来开设人民巴刹,成为霹雳州第一间多层式商业中心。怡保慢慢具有了都市气息,电影院、邮政局、汽车、摩托车、公交车都出现了。
姚德胜对怡保的贡献巨大,英国国王封他为“和平爵士”。1900年,故乡遭遇大旱,姚德胜回到广东,组织各界人士赈灾。另一次山东黄河决堤,姚德胜在海外汇出了六万银元。光绪皇帝赐给他牌匾:乐善好施。孙中山也给他特颁过一等勋章,感谢他在革命时期,电汇过七万银元。
读到姚德胜的故事,我想到了同一时代在汉口创业的刘韵生。1899年,24岁的刘韵生成为汉口立新洋行的年轻买办。他在银行工作,利用低息贷款,开办私人钱庄。消息灵通的他也倒卖货物。上海当买办的朋友会给他发电报:各大洋行将会大量收购白芝麻。刘韵生就在湖北各地设点收购。他还嗅到地产的机会,短短几年,就买下了汉口租界外几乎所有的地皮,这些地多是湖泊和荒地。当英国人的租界不够用了,他们只好来找刘韵生……1906年,英租界将一条长约1600米的新马路命名为韵生路。很快这里成为了汉口的中心。花旗银行、日清银行、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等纷纷盖起大楼。
如今的汉口已失去当年的繁荣地位,但江汉路却热闹依旧。在怡保,有一条叫做Yau Tet Shin的路,很短的一条路。很少有人会好奇这背后的故事。如同汉口遗忘了刘韵生,怡保也遗忘了姚德胜。






度假屋
周末过后,怡保变得好安静。旅店老板告诉我,吉隆坡人喜欢来这儿过周末,逃离首都的拥挤。周末的旧街场很拥挤:何人可凉茶博物馆,要等号参观。沿路的餐厅,坐满了人,这里不仅有怡保传统美食,还有意大利菜、日本料理。
在马来西亚的旅行,我已经厌烦了“南洋咖啡”,它和越南咖啡一样的甜腻。喝了一杯之后,也不能消除身体的疲惫。在怡保,旧街场有许多咖啡店,正如上海、东京。在某栋历史建筑里,人们的交谈声、磨豆机的轰鸣,以及蒸汽冲煮后不易被察觉的水流声。阳光明媚,我看着透明的玻璃杯,冰块在晃动。我用手触摸着杯缘,感觉到水痕,现代生活真好。
旧街场有一种大理、清迈、峇里岛的松弛感。一种有别于都市,但又近乎于都市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你很难寻找一种地方性,至少它被隐藏了起来。我更喜欢,散步去河的另一头。新街场更开阔,由交错的骑楼组成,能感受到一种1930年代的旧日光景。这里还有马来人美食市集,1.5马币,就能喝到一杯鲜榨果汁。
在新街场,你能感到怡保作为传统商贸中心的气息。比如整条街都是金银首饰、当铺店,另一边只卖3C用品。远处有一家中药店,棕黄色的光晕下,陈列着一个又一个药柜。比邻的鹦鹉店,各种各样的笼子,以及叽叽喳喳叫的鸟儿。
漫步其中,店铺玲琅满目,大多前店后厂。有专门卖拉链、纽扣的,也有加工户外伞的工匠铺……好似回到了很久以前的广州。在怡保,你总能听到粤语。这里的华人大多是广东移民的后代。随处可见,小小的瓮,供奉着神明。来到河边,常有巨大的蜥蜴,如同鳄鱼一般,在水中游泳。岸边,摩托车穿梭而过,马来人在一旁放羊。缓慢、休闲,宜人。
我沿着河边走,太阳很晒,直到一大片住宅区出现在眼前。我很吃惊,在怡保,竟然出现了,像是废弃的战时监狱,或者是难民营的地方。土黄色墙上,写着字母编号:BLOCK B。细看,每个房子大约二十平米。它们共享着同一个很长很长的走廊,几乎延续了数百米。它们紧挨着宜人、自然的河滨公园。
那几天,我问了好几位怡保、太平的当地居民。对于首府的这片高密集建筑,他们都不了解。我只能查到一些或许有关的历史: 1945年,日军撤离后,马来群岛出现过两周的权力真空。很快,英国重新治理,为杜绝华人的革命,他们推出了一项“华人新村”居住计划,让散落各地的华人社群集中居住,便于监视与管理。
历史如快镜头闪过: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退到了泰国边境。1969年5月,华人在大选中取得胜利。三天后,马来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种族冲突,陷入长达两年的紧急状态……此后马来西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马来人优先”政策,包括取缔英文的官方地位,而代之以马来文等。
英国人推行的华人新村,参与了这些历史,却沉默不语。1957年,华人占总人口39%,共有244万人。60多年后的今天,华人占比下滑到了23.2%。学者估计,700万华人中,有超过八成来自华人新村。目前整个马来群岛共有607华人新村,仍有120万人居住。
这片住宅是否与此有关,有待考证。
最后一天,我又来此闲逛。我需要闭上眼睛,去想象一种曾经的热闹、喧嚣的生活。因为大多数人都搬走了,尤其是一楼,留下了空空的房屋。门口还留有主人的神瓮,以及神像的缺席。我看到一个喂猫的中年男子。他向我友善微笑。他的妈妈,还有几个阿姨,正坐在客厅里,若有若无地看着电视,有人读着中文报纸。门前摆有一个神瓮,供奉着仙四爷。阿姨看到我,疑惑地说了几句话。见我没听懂,她努力换成普通话:小弟,你也喜欢猫吗?门口的猫,你可以拿回去养。
走到出口,我看到了一块褪色的告示牌——華大偉區睦鄰計劃。我打开手机,想要做标记,但Google map只有一个英文名holiday home。几个小时后,我坐上了火车,离开了度假屋。








太平
在马来的最后几天,我感染了严重的感冒,身体乏力。我猜应该是第三次感染covid-19,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好在,太平离怡保很近,只需要五十分钟车程。这是一个更小的,也讲粤语的城市。
走出火车站,过天桥的时候,我问一个路人:雨下过了吗?他指着山的方向,笑了笑说:还没有。这是一个每年300天都在落雨的小城。下午四点多,到了旅馆,我就陷入了昏睡。
在高烧的昏睡中,我感到天渐渐暗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雨。每隔一段时间,外面的钟楼,会响起悠扬的报时声。在旅途生病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也变得更加敏感。在一个有数百年历史建筑里,我昏躺着,聆听到很细很细的声音。
我睡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醒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感到渴,但要等到天亮,才能去商店买瓶水。出去后,我买了一个面包,努力吃完。回来时,我又一次见到旅店的管家,她叫慧玲,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长得娇小,人很温柔。
慧玲很忧心,嘱咐我一定要去药房,去买Panadol,每六小时吃一颗,晚上就算睡着了,也要设好闹钟起来吃。她说,疫情的时候,这个药救了很多人的命。我问她,午饭吃什么好?她推荐我尝一尝肉骨茶。慧玲说,近来肉价上涨,肉骨茶也变得好贵。她从不做饭,如果买的话,会带回家分成两顿吃,这样划算。
我们的聊天,如同疾病的痊愈,总是断断续续。慧玲能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并为此骄傲。她爱读书,喜欢贾平凹、莫言,但没有读过黄锦树、黎紫书。她不知道怡保的度假屋,我给她看了照片,她摇了摇头,感叹住在那样的地方太吓人了。
那天上午,我躺了一会,决定去动物园。很近的路,但逛完后感到疲惫,只得叫一辆Grab回住处。茶室的小食摊关门了。我问老板,可不可以去别处买个面包,在这里配咖啡喝。老板说没问题。吃完后,我又问老板,有没有缓解感冒的凉茶?
她想了几秒钟,看着我,说,有自己的发明,不要钱。我记得,里面放了小柠檬、话梅。她做好后,盖上碟,称要等十五分钟。我喝完了一杯,想回去睡觉。但老板要我加热水,再喝一杯。我说,你怎么想到这款热茶的?她说,在无助的时候就想到了。
晚上,我去餐厅,点了两道菜。我想到了如今移居新加坡的妹妹。2015年,和她在兰卡威,那天晚上,她很开心,说这里有kangkung,很好吃。我记得那道热炒的蔬菜里,还放了下虾皮、海鲜酱。附近还有一家马来风格舞厅,响动着音乐。八年过去了,我又一次吃到了kangkung。吃着吃着才发觉,这就是空心菜呀。从少年时,爷爷奶奶和父母一起住,还有我和姐姐。奶奶,常会买竹叶菜,用香干、肉丝来炒。奶奶说,姐姐最喜欢吃竹叶菜了。吃得多了,我开始厌恶起它干巴巴的口感。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奶奶去世了。回想起来,这之后,我们家的餐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空心菜……竹叶菜,藤藤菜,空心菜。
离开的这天,我在旅馆的大厅休息,等候去往槟城的火车。这是一栋殖民地时期的独栋建筑,陈设非常温馨,响着吊扇运转的声音。我的室友也在等车,他三十多岁、皮肤黝黑,留着长头发,像个大男孩。性格很温和,在沙巴念的大学,毕业后在当地动物园工作过几年。现在住在吉隆坡,当Grab司机。他很怕热,在公寓独居,每月会花掉几百块电费。这一次,他开车回太平,是来给父母扫墓。他说,这几天在修车,就住在了这家旅店。他喜欢这里,能吃到很多熟悉的店,回想起漫长的中学时光。
要走的时候,我发现有东西落在了里面,就按了按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从吉隆坡过来度假的年轻女士。她有一种在写字楼的干练、开朗、独立。大多时候她就呆在旅店大厅看书。她说,有空的话也想去hiking。她看到我,笑了笑,说道:要给我钱(才开门)噢。
给你一百万。进门后,我向她抱怨,这几天都没喝过Espresso。她告诉我,正好出门带了挂耳包,要不要拿去?我耸耸肩,不只是黑咖啡,我不爱喝热的。反正要去槟城了,那里不愁咖啡喝。她建议我,下一次再来太平时,问一问慧玲,肯定能找到好的咖啡店。
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这里好像成为了某种家。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因为说着同一种语言,而共享着某种调皮和友谊。
槟城
比起太平,槟城是一个巨大的世界。1826年,英国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三个港口,整合为海峡殖民地。至今,它们也是马来半岛上程度不一的飞地。
如果说,从怡保的传统市场,能看出一种地方的中心性。那么,作为岛屿的槟城,与广阔的陆地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正因此,槟城有一种独特的国际化。这里有更多英文,也出现了中文路牌,马来语好似退场了一样。
我住的青旅,老板是一个华人,但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只讲英文。他的孙子刚学会走路,除了会喊“爷爷”,就不说任何中文了。北京大学宗教学博士吴小红是在马来西亚古晋市长大的。她告诉我,有少数华人更习惯讲英文,过去受雇于英殖民政府,之后让孩子读国际学校。
这里的华人大多来自福建闽南。1844年,福德正神庙,成为了重要的福建人社群。最早,人们以膜拜大伯公的名义,进行帮派活动。因为福建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三合会。乾隆五十一年后,在官府大力追捕下,天地会变成了不同分支:“洪门”、“添弟会”等。而三合会则成为了天地会盘踞在广东的势力。鸦片战争后,随着劳工的迁移,三合会传到了南洋、香港、美洲及澳洲等地。
1867年,槟城出现了暴动,人数处于劣势的三合会,与大伯公会展开了十天的大械斗,共牵涉了三万多华人。英殖民政府无法调停,从新加坡带来印度军队,才得以平息。从现代公司视角来看,三合会要更先进。他们的成员,不讲究原生宗族,也没有强烈共同宗教信仰,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权力规则。二战后,三合会成了国际性黑帮,从事烟酒、军火走私,经营色情业、赌博业,也投资电影,包括生产和销售盗版CD、DVD及色情光碟。
如今,人们认为,黑社会已经销声匿迹,成为了某种怀旧故事。我走入大伯公庙时,看到在中殿主祀的神农大帝。清宝殿,也是同庆社之所在。不远处,绘有一张壁画,在瀑布下,鸟雀与花丛中,一只幼虎,凝望着它的母亲。我看了良久,不禁好奇:当时的工匠,是按照记忆中、现已野外灭绝的华南虎所画,还是来自对于马来虎的观察?答案不得而知,也许并不重要。
我感觉,槟城很像是宋元时代的泉州。漫步在街头,总能看到小型庙宇,如同出现在泉州铺镜的那些不同的地方神。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华人道教、佛教,在很小的共同街区里,分别、共同礼拜。
在我住处附近,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道教庙宇,1800年所建的观音亭,为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庙宇。在型制上,观音亭和泉州关岳庙有些相似。而在泉州关岳庙不远处,就有迥然不同的清水寺。巧合的是,在槟城观音亭几米外,就有一个露天的、极小的印度教礼拜台。供奉的象神甘尼萨,能帮助人们克服障碍、带来幸福。这里相当热闹,白天,有摊贩专卖瓦玛拉花环,它用于婚礼,也用于奉神。晚上九点,我看到一位神职人员,神色凝重,穿着橙色长袍,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这些风景,在泉州很难再见。
旅途要结束了,最后几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位于泉州的日月太保宫。几个月前,我背着同一个书包,在门外等了很久。那也是旅行的最后一天。正值夏日午休,到了开门时间,还是没人来。最终,我没有见到两位南宋小皇帝……陆秀夫决定坚守,在广东崖山,不惜背着幼帝投海殉国。我总希望,故事会重新开场:他愿意带着幼帝,进行一次彻底的南渡。也许,跨过大海,消失在南洋的雨林里。
……
最后,让我们回到2015年,在吉隆坡的那个下午。醒来后,旅店很安静。我加入了电视旁,在看电影的观众。回想起来,故事很简单,一对爱恋的年轻男女,生了小孩后,却分开了。他们都很伤心,如同《毕业生》的氛围,没有控诉什么,只是一种“登大人”的破碎、迷惘。
离开的那晚,正好是斋月。我没有睡着,见到了可汗,那位孟加拉店员。我和他一起去了天台,看他准备日出之前的早饭。我们吃着食物,吉隆坡的天空一点点变亮。翻看照片,我也想到了其他人。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们没有共通的社交媒体,最后也失去了联系。
——完——
作者赵景宜,关心变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时代之中的具体处境。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