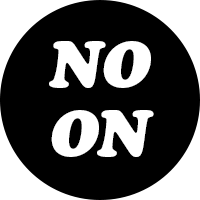采写 | 黄芩
高群书的微博昵称是“他回精神病院了”,这句俏皮话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在喧嚣的热搜背后,在动辄得咎的舆论场中,机灵的人们要么隐身,要么尽量圆滑,因此有人说,“娱乐圈‘活人’越来越少”。高群书是为数不多的“活人”之一,谈实事、怼恶评、聊电影……在与我们线下聊天时,戴着墨镜的高群书却锋芒尽敛,说起他熟悉的警察生活和破案细节,娓娓道来,就像一位喜欢讲故事的老前辈。
5月24日,高群书执导的电影《三叉戟》上映。该片改编自吕铮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三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突破重重阻碍终将犯罪分子缉拿归案的故事。电影的另一条线是,幕后黑手黄有发企图转移数十亿赃款,并雇佣老鬼、小青等黑道势力阻挠案件侦破。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为错综复杂的罪恶网络与人脉关系渐渐浮出水面。
警匪题材是高群书深耕已久且建树颇丰的领域。上个世纪90年代,他完成了《中国大案录》《命案十三宗》《征服》等纪实电视剧。《命案十三宗》被评为2000年北京十大热门电视剧之一,《征服》也火遍大江南北。2012年,高群书以真实案件为原型拍摄的电影《神探亨特张》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原创剧本奖。
新片《三叉戟》能否获得影迷的认可,仍有待验证。有人认为,档期一拖再拖,是这部电影的天然劣势。另外,在短短两个小时里,如何理解多线故事和多个人物的行为逻辑,这对观众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到电影与原著的区别时,高群书也承认,“尽管做了大量减法,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电影还是有些复杂了。”
在对电影的所有评价里,高群书最难接受的是不真实。“三叉戟作者,编剧之一是从警24年的现役警察,影片历经公安部门各部门上上下下十几次审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电影,我敢说,《三叉戟》无一处假。”电影上映后,高群书在微博上回应“拍的假”的质疑。
高群书之所以对“真假”如此在乎,或许也与他的职业生涯有关。与很多毕业于电影或戏剧学院的导演不同,高群书1986年从河北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曾进入石家庄广播电视局拍摄新闻专题片。即便日后成为影视剧导演,他仍然保持实地探访的习惯。在拍摄《中国大案录》《命案十三宗》期间,高群书走访看守所和警察局,在与罪犯、警察的交谈中取材,也重新认识了警察的不易和罪犯的挣扎。
在接受正午的采访中,高群书说,“我所有的作品,最根本的内核就是呈现中国犯罪史。”“生活本身就很丰富,所以你只要去挖掘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再稍加构思、升华,就足够精彩了。”在他看来,真实是好故事的基石,“去编织一个戏剧化的叙事过程但不破坏事情的真实属性,很考验编剧和导演的能力”。
把握每一个警种的特点
正午:为什么选择吕铮的小说《三叉戟》来改编,这本小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高群书:吕铮是从业24年的现役警察,没有哪个作家比他更熟悉警察这个职业,他对每一个警种都很了解。一名警察从事一个警种的时间长了,身上难免会带有这个警种不可磨灭的气质,吕铮能把握每一个警种的特点和他们的命运方式。
比如刑警,就总是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你,但当他信任你之后,就会和你掏心窝子。刑警相对来说比较直率,《三叉戟》里的“大棍子”就是这样。
经侦警察就和刑警不一样。经侦警察每天都在观察和动脑,因为他们面对的嫌疑人表面上可能都是好人。很多企业家“爆雷”之前,谁也想不到他们会是罪犯,但经侦警察很早就盯上他们并且开始判断了。经侦警察懂金融、懂市场、懂体制、懂经济规则,所以他们很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只是不知道犯罪的幕后黑手还有谁。
在《三叉戟》里也是如此,经侦警察并不只是直面犯罪嫌疑人,而要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交手。比如三个老警察要面对打手老鬼、小青,犯罪分子也可能利用家人、社会关系去削弱警察的战斗力。电影里,当警察们追到幕后黑手黄有发的时候,任务就简单了,因为正面交锋时,他就是个没有反抗能力的普通老头儿。他只有所谓的“外围能力”,“外围能力”来自于对有关部门的腐蚀,他们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被腐蚀的人都是通过表面上正当的方式来保护幕后的黑手。像魏晨饰演的警察楚东阳,用权力来施压,不让经侦支队行动,给犯罪嫌疑人争取时间转移资金。
《三叉戟》这个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得知黄有发的案件牵连甚广之后,警察组织内部不按常理出牌,而是派出三个将要退休、被边缘化的老警察,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作为老警察的经验去破案。貌似不指挥,实际上是充分信任这三个人。
《三叉戟》里的破案方式也很特别。现实生活中,这样大的金融案件通常都有整个专案组来侦破,专案组有专门的组长,下面还有资料组、追逃组等等。但《三叉戟》不一样,当警方面对一个复杂的强敌的时候,用强攻的手段可能行不通,就采用了一些巧招,从谋篇布局到主要办案人员的选择,都出人意料。
吕铮在《三叉戟》里塑造的三个老警察的组合,也是以往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里很少见的。以前也有退休老警察去侦办案件的小说、电影或电视剧,但他们办的案子都是杀人案,让要退休的老警察去办错综复杂、纠合了各方势力的金融案件,《三叉戟》是头一个。
正午:在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时,需要注意什么?电影的视角与小说有何不同?
高群书:我改编的核心点是高度尊重吕铮的原著。我不是第一个接触这本书的导演,我接手这个项目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个剧本了。但我觉得,原来的剧本和原著小说的差别比较大,原著小说里很多精彩的内容需要被尊重、被还原,包括对人性的把握和书写。
从情节上来说,电影《三叉戟》是一个复线情节,它的主线故事是破案,副线故事是复仇。既有“大背头”崔铁军为弟弟报仇,也有小青为父亲报仇。金融案件作为一个命运链,每个角色都挂在这根链条上,人物的重要性与在案件中的作用直接相关。比如小青是反派里最穷凶极恶的那个,他和他的团伙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肯定是最后一个要被攻克的堡垒。
正午:小说《三叉戟》也曾被改编为电视剧。同样的故事,电视剧和电影有哪些区别?
高群书:如果说拍电视剧是要种一片包罗万象的树林,那么,拍电影就是种好一棵树。电视剧有40多集,需要思考的是怎么在原著小说的基础上增加内容,把主线的情节从不同的节点展开。电影只有两个小时,需要做的是让故事凝练起来。我们保留了很多原著的台词和情节,但也做了大量减法,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电影还是有些复杂了。
我认为中国的犯罪可分为三类
正午:在《三叉戟》之前,你拍过《命案十三宗》《征服》《神探亨特张》等警匪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格外关注这类题材?
高群书:上个世纪90年代,我和公安部合作拍了《中国大案录》,那时候我采访了大量警察和罪犯,也刷新了我对警察和所谓犯罪嫌疑人的认知。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警察很威风,似乎无所不能,但真正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从90年代到现在,警察的生活一直都很苦。比如,每个警察都有一大摞没法报销的单据。这么多年来,我采访的每一个警察局局长都告诉我,“只要领导重视,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重视”意味着有经费、可以调动资源、有人配合,但不是每个案子都能得到“重视”。
再比如刑警,他们经常和犯罪团伙打交道,所以,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家人的安危。我认识很多警察,他们绝不会告诉你他们家住在哪里。即使你要给他们寄东西,你得到的地址也一定不会是他的家庭住址,他们在生活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
正午: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据你了解,今天的警察破案,与十年前、二十年前有怎样的不同?
高群书:我所有的作品,最根本的内核就是呈现中国犯罪史。我认为中国的犯罪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典型的黑恶势力犯罪,这种犯罪是主动的、有预谋的,犯罪分子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去组织犯罪。这种“梦想”有两种内涵,一是犯罪分子对社会不满,想要报复;另一种是他们想要通过诈骗等犯罪手段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类犯罪发展到一定程度,犯罪分子就会变得更有组织,手段也更隐蔽和“合法”。比如八十年代是控制沙土开采,九十年代是依附于房地产公司和某些基层组织去搞拆迁,2000年之后他们可能就开洗浴中心,自己做老板了……他们会通过勾结和利益置换来“洗白”,但发家过程有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我以前拍的《中国大案录》和《征服》,都是记录一个小人物怎么一步步发展成大毒瘤的。
第二类是激情犯罪,《命案十三宗》讲的就是激情犯罪。也正是为这些拍摄所做的采访,颠覆了我对死刑犯、杀人犯的认知。在此之前,我会觉得他们肯定十恶不赦,采访之后我才意识到,这类案件里的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可能是邻居、夫妻、亲戚等。犯罪分子只是某种情绪得不到宣泄,情绪慢慢积压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大地雷,然后会被一点点小事引爆。他们的杀人手段很简单,工具就是搬砖、擀面杖等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物件。
这么多年来,犯罪方式一直在演变,现在很少有黑社会,打打杀杀的事儿既费劲儿也赚不了钱。而且,到处都有监控,所以对于激情犯罪来说,侦破变得更容易了。当然,现在的犯罪手段依然五花八门,但侦破手段也在升级,所以,现在重要的不只是破案,更是追究犯罪动机。
第三类就是金融诈骗类的犯罪。对于犯罪分子来说,这类犯罪的危险系数更低,实施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他们操纵股市,或者把诈骗包装成一个正常的金融活动,他们的公司是合法注册的,获得资金的过程也是合法的。只是当钱到他们手中之后,用不合法的方式转移出去了。而生活改善之后,老百姓都想让手头的积蓄钱生钱。这些人就是抓住这种心理,用金融和理财的名义把老百姓的钱骗走。《三叉戟》里的黄有发就是这一类,当老百姓把钱投进去之后,就没可能再要回去了。
金融诈骗类犯罪的特点,是具有高度隐蔽性。破案的时候,需要层层“穿透”,要侦查到离岸公司,甚至是国外。这种犯罪很不好拍,因为你没法拍摄审计的过程,你只能呈现侦查的过程。
纪录片vs纪实风格的电影
正午:在成为导演之前,你曾是一名记者,你现在还保持采访的习惯吗?
高群书:必须保持采访的习惯,因为犯罪是千变万化的,每个案件有不同的侦办人和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采访才有可能足够了解要拍的人和事。很多东西无法光靠想象得出,这就是如今“现实主义”作品盛行的原因。生活本身就很丰富,所以你只要去挖掘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再稍加构思、升华,就足够精彩了。
正午:你的许多作品都改编自真实事件,例如《命案十三宗》《征服》《神探亨特张》。在你看来,真实事件以及纪实文学比虚构的小说更能打动观众吗?
高群书:真实肯定最能打动观众,但创作一个作品必然要进行戏剧化的提炼。还是那句老话,“戏剧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是“真实”的戏剧化,是把现实用更符合影视表现的方式进行再创造。
但再创造也是真实的,是把现实中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发酵的事件集中在两个小时之内。比如《命案十三宗》,里面的案件开始都是小事,无非是亲人之间拌了几句嘴、夫妻之间吵了架。但叙事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接下来一定会发生命案”的悬念。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戏剧化的过程,你只是在故事的开始就设置了一个悬念,而呈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去编织一个戏剧化的叙事过程,但不破坏事情的真实属性,这就是再创造,再创造很考验编剧和导演的能力。
正午:你的作品中,最受认可、得奖最多的《神探亨特张》也是纪实风格的作品。这部电影的演员全是素人。和职业演员相比,素人演员的优势是什么?你还会再用全素人的阵容拍摄电影吗?
高群书:条件允许的话,我会。我特别喜欢素人演员,因为选拔素人演员实质上是选择他们的个性,素人的个性是职业演员不具备的。职业演员的训练过程不可避免地消磨他们的个性,他们会去适应各种有套路可循的表演方式。
但每个素人都只有一种演法,就是演自己。“自己”对素人来说是天然存在的,导演要做的是激发他们的天性。并且14个素人有14种演法,但一万个职业演员最多只有1000种演法,这就是素人和演员的区别。
正午:“现实主义”是你作品的一大特征,纪录片和现实题材的电影到底有哪些区别?
高群书:对于我来说,我只能拍摄一个纪实风格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一方面,拍摄纪录片需要大量的时间;另一方面,拍摄纪录片需要很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细节和情节。但这些细节和情节往往是被拍摄对象竭力回避的。你拍摄不到的那些内容,恰恰是事件中最精彩的部分。
和影视作品不同,纪录片的画面必须是真实的。当然,现在有一种新的纪录片拍摄方式,就是制造矛盾,比如两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拍摄者不阻止,甚至去诱导矛盾往更激烈、更戏剧化的方向发展。但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太合适。
——完——
题图摄影: PJ.Wong
作者黄芩,刚从电影院出来,正在奔赴下一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