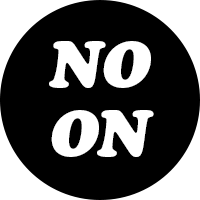采写 | 明亮
“那时候我没有狂妄地觉得自己能写一本书,这趟旅程太难,连能不能活着回来,我都不知道。”
冬日上海,街头弥漫着湿冷的空气。我与旅行作家姚璐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她穿着简单的羽绒服,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与兴奋。这次专访源于她最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看不见的中东》,这本书记录她从2016年到2020年的中东之旅。四年里,她用沙发客(Couchsurfing)的方式旅行,通过行走和记录,完成了一部跨越文明、性别与信仰的作品。她说,这不是一本旅行指南,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如何在战争和性别压迫中生存的故事。从和平的伊朗到战乱的叙利亚,姚璐始终聚焦于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女性的发声。
姚璐成长在一个性别相对平等的环境。她笑着说:“家里是我爸做饭,舅舅、姑父也做饭,朋友结婚后大多是老公掌勺。”这种日常在她看来稀松平常,走进中东,她才意识到它的特殊和珍贵。
我问她中东之旅的起点是什么。她停下来,回忆起2001年的“9·11”事件。“我那时候还小,觉得世界应该是和平的,突然看到现代社会发生这样的事,心灵受到很大冲击。”
那一天,学校突然停课,师生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目睹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震撼画面。“我记得老师们脸色苍白,同学们窃窃私语。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和平。”她说,“中国是个安全的国家。9·11事件让我开始好奇,新闻背后的世界到底是何模样。”多年后,她踏上中东的土地,实地探寻新闻之外的普通人的生活。

在枪炮声中喝咖啡、玩游戏
姚璐的写作计划最初并不明确。2016年出发时,她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当时旅行类的书大多是心灵鸡汤、攻略或爱情故事,我看不下去,想写点不一样的。”她笑起来,带着点自嘲地说:“但我没有狂妄地觉得自己能写一本书,这趟旅程太难,我连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知道。”
2016年7月,她第一次前往中东,目的地是伊朗。之所以选择伊朗是因为签证策略:“只能先去伊朗和黎巴嫩,再去以色列。如果反过来,以色列的签证会让你无法进入伊朗和黎巴嫩。”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她对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好奇。
与许多旅行作家不同,姚璐选择以沙发客的身份,进入当地人的家中,近距离与他们接触。“我之前没有尝试过沙发客,第一次就住进德黑兰的一个陌生人家,心里慌得要命,还用英语准备了一些新闻话题想跟人聊天,结果笨拙得像个学生。”
“我以前看新闻,觉得这些地方没法活。去了才知道,人总有办法。”到访伊朗时,姚璐发现,当地女性必须穿包裹住臀部的长款上衣并遮盖头发,但她发现有些女人对这一“规范”表达过不满。矛盾不断积压,2020年,一名女孩因反抗被捕后死在狱中,当地爆发“烧头巾”抗议。直到现在,规则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但她们还在继续反抗。
2017年,她从埃及回国,试着写了3万字,却很不满意。“那时候阅读量不够,文字很幼稚、浅薄,经历也不完整。”她把稿子扔在一边,继续中东之旅。2018年去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积累了更多素材。
到访叙利亚时正值2018年底,内战趋于平静,政府控制区相对稳定。在经历七年内战之后,当地人都对战争很疲惫,“不管谁执政,只要和平就好。”让姚璐没料到的是,2023年11月,阿萨德政权突然被推翻,政权在十天内实现更迭,举世震惊。当她联系叙利亚朋友时,对方也很茫然:“早该倒台时没倒,现在看似稳定,却突然崩溃,太魔幻了。”
在耶路撒冷古城,姚璐目睹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泾渭分明”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共享一座圣城,却像平行世界般互不打扰。这种表面的和平,反而让我预感到冲突的必然。”
在巴勒斯坦,伯利恒,她遇到一个曾在以色列监狱服刑三年的年轻人。他小时候跟父亲参与激进武装对抗犹太人,被关押三年。“我以为他会充满仇恨,但他很平静。他说监狱让他反思,仇恨无休止,没有意义。”出狱后,这位年轻人开始学希伯来语和英语,他想去以色列找一份新工作,过上好日子。“你得站在他面前,才会懂得一个人从激进到平和的转变。”
姚璐在巴格达遇到的人,几乎都有亲人死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那段时间。一个沙发主讲到他爸爸被炸死时,姚璐沉默了,不知道该作何回复。他却反过来拍拍姚璐的肩膀,安慰她说“生活总要继续下去”。他们对死亡看得很淡,见得多,反而更珍惜喝咖啡、聊天的日常。这些都是新闻里看不到的日常,看不见的中东。
2019年下半年,一家出版社找到姚璐,说她的选题有潜力。“当时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还没出版,旅行类非虚构作品是很稀缺的内容,他们让我试试。”
2020年1月,在新冠疫情大暴发的时期,她仍在前往沙特阿拉伯的路上,并辗转伦敦、土耳其等地,直到3月才搭上回上海的飞机。正是在这架飞机上,她读完了何伟的《江城》。这本书也成为写作的转折点。“我特别喜欢他的视角,”姚璐解释,“他住在一个地方,跟当地人‘混’在一起,用旁观者的目光观察,既幽默又有深度。我在飞机上突然明白了我想写成什么样。”
“他写涪陵小城,也让我学会如何观察自己的家乡。”姚璐在书中避免宏大叙事,采用平等的“旁观者视角”,记录教师、大学生、工程师等的故事。在新闻画面的“火药桶”背后,是无数人的坚韧生存。何伟曾说,“理解一个地方的最好方式,是承认自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姚璐同样拒绝坐在书桌前想象中东,而是亲眼去看黑袍下的笑容。非虚构的力量在于,它逼迫你承认世界的复杂。
她停下来,喝一口咖啡,看着远处说:“其实这本书不是为教人怎么旅行,是为让人们看到,那些地方的人怎么生活。”回到上海,她用八个月写出初稿,2022年10月基本定稿。因为某些原因,直到2024年底,《看不见的中东》才得以面世。
中东之行也对姚璐的生活态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她的很多朋友很绝望,但她知道,只要坚持,一切都会过去,总会看到希望。“我在叙利亚看到,人们在枪炮声旁喝咖啡、玩游戏,那是生存的本能。我相信,疫情也能熬过去的。”她笑着说,“我以前可能更脆弱,现在知道人有多坚韧。”

被看见的女性
作为女性作者,姚璐对性别议题格外敏感。在沙特阿拉伯,她买了一套黑袍和面纱试穿,店员教她面纱如何戴才“正宗”——眼睛露得越少越好,只能露一条缝,面纱紧贴睫毛根部。“这种感觉像刀片刮着眼睛,戴一会儿就头痛缺氧。”她愤怒于这种装扮的不合理,却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解读截然不同。
男沙发主们都说:“她们从小就习惯,没人强迫,是自愿选择,这样穿着会更安全。”但一个与她同龄的利雅得女孩却说:“这并非自愿,整个社会都在监督你,你不戴(面纱)会被指责不检点,连妈妈都会被责骂。我可以承受流言,但不想妈妈受牵连。”在沙特,男沙发主对姚璐独自旅行表达支持与赞赏,却对自家的妹妹或老婆持双重标准:“她们要在家里照顾家人。”姚璐感叹:“男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多想,因为跟他们无关。”
当然,姚璐也看到许多振奋人心的女性故事。在黎巴嫩贝鲁特,历经战乱的沙发主诺瓦来自叙利亚阿勒颇。她不喜欢做饭,厨房没什么使用痕迹,锅碗瓢盆用塑料袋装好。为了实现导演梦想,她一边打工,一边在学校里学习如何拍纪录片。她想通过影像告诉世界,家乡女性所经历的生活。她说“我才27岁,还有很多想做的事。”而她的勇气离不开父亲的支持,父亲从小鼓励她追求职业理想,有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将她束缚在家里。这种支持在保守社会如同奇迹。
“许多中东女性的困境,与中国小镇女孩并无不同,她们只是缺乏一双手将她们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姚璐说。在伊朗,沙发主帕瓦内拒绝传统婚姻和家庭生活,她不甘心当全职主妇,坚持去学校甚至免费的教育机构教书。每当站在讲台,她才不是别人的女儿和妻子,她是她自己。姚璐十分欣赏:“她们像春天的花,在极端环境下仍有生命力。”
姚璐的中东之旅也是一场双向的看见。她看见战乱下的日常、性别下的压迫与反抗,也被当地人看见。“出门很重要,你得站远一点,才能看清自己。我为什么敢表达?因为我被鼓励过。很多女孩不敢,也只是因为环境缺推她向外的那双手。”姚璐说。
八年时间,姚璐也感受到中国性别议题的变化。“2016年出发时,没有多少人讨论性别问题。2020年后,性别成热门话题,我写这些不再有焦虑,大家都愿意探讨。”她举例说,2018年她在公众号写过被伊拉克出租车司机性骚扰的经历,因不付车费被许多网友谩骂。“那时候观念很传统,觉得受害者有问题。现在不一样,大家会觉得骚扰者错。”
生理期的公开讨论是另一个变化。和许多热爱户外活动的女性一样,过去,女性在徒步时来月经,总是遭遇在哪里换卫生巾的困扰。大家在称呼月经时也总是代称“那个”“大姨妈”。姚璐曾在公众号中记录这些事情,有网友评论说其“不害臊”。而现在在户外时,女性越来越不避讳这个话题,越来越多女性会直接告诉领队“我来月经了,要去卫生间。”
这趟旅途不仅让姚璐看到中东,也让她看清自己。“去中东之前,我在自己的周围没见过一直在厨房忙碌的女人,男人都会做饭、做家务。写到这个,有人说我有优越感,可我真的没见过。”她反思,“上海的性别平等跟经济有关,早期有国企女工,女人有了收入,在家里就有地位。去中东后,这种反差让我更想了解不平等的根源。”
四年行走,中东冲突依然看不到尽头,而姚璐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了战火中的音乐会、面纱下的野心,以及女性之间无声的联盟。“世界不会因一本书改变,但若有一个女孩因我的书决定独自出发,一切就值得。”她说。

下面的九个问答,带我们与姚璐一起深入中东。
正午:你第一次独自旅行时害怕吗?家人怎么看?
姚璐:怕啊,尤其是2012年辞职去内蒙古那次,才24岁,没什么经验。去伊朗前更紧张,我还傻乎乎地准备新闻话题,思考跟沙发主聊什么。家人一开始反对,但慢慢也就习惯了。
正午:中东之行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姚璐:最感动的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对我的善意。在伊拉克旅行时,我的每个沙发主都会送我到汽车站,帮我谈好车的价格,嘱咐车上的其他乘客照顾好我,还会给我的下一个沙发主打电话,告知接我的时间地点。我就像被接力一样,被一个人交给另一个人。他们这种善意的帮助,让我得以安全地完成了旅行。
正午:有没有一刻,你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
姚璐:算是有吧。当我完成伊朗、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埃及的旅行后,我开始考虑是否去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时是2017年年中,叙利亚和伊拉克还处于内战之中,我很想去,但安全状况堪忧。我当时一度想过放弃,但好在观望了半年后,终于等到了一个出行的机会。
正午:行走中东四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姚璐:新冠最严重的时期,我发现上海朋友的绝望与叙利亚人的平静形成鲜明对比。中东教会我:动荡中人会本能地抓住日常,以此来维系生活的秩序。这种观察让我在混乱中保持冷静。
正午:旅行改变了你的性格吗?
姚璐:变得更坚韧吧。以前我可能有点脆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动荡的时代环境。去中东后,看到那么多人能在极端环境下找到活下去的办法,我觉得自己也能扛更多。比如新冠疫情时,我比朋友们淡定许多。
正午:有没有特别想念家乡的时候?
姚璐:没有,我好奇心旺盛,很喜欢旅途带来的新鲜感,也很容易适应当地的生活。在国外,我可以几个月不吃中国菜。
正午:当地人怎么看你这个独自旅行的中国女孩?
姚璐:好奇多过惊讶。土耳其有人问我“没信仰怎么活”,沙特有人说我这种不会做饭的女人“在我们这儿没人要”,但更多是友好。他们觉得,我一个人跑这么远很勇敢,有的还问我上海女人是不是都这样。
正午:评价一下近年中国性别议题的变化。
姚璐:能明显地感觉到2020年前后的巨大变化。2020年前,性别议题不太受关注,观念也比较陈旧,比如在性骚扰的新闻下面,很多人会抨击受害者。但2020年后,随着性别问题被热议,人们对婚姻、性骚扰等议题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苏敏阿姨自驾逃离婚姻被广泛关注、地铁性骚扰报案率上升,这些都是进步。
正午:你最想让读者从你的书里得到什么?
姚璐:我想让他们看到,世界很大,不同的人有不同活法。尤其是女孩,别被环境限制住。我希望她们读完能多一点勇气,去试试自己想做的事。

——完——
作者明亮,一个喜欢蹲下来看世界的人。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