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城市。我几乎认不出任何东西。”妈妈说,她瞪大眼睛,凝视着几十年的老电车和香港混乱的街道。 “我从没坐过叮叮车,它太慢了。”妈妈抱怨说。电车经过时,发出两声响铃以警示附近的行人—— “叮叮”就是这一声音的拟声词。“不过,这样也很好。你可以放慢脚步,好好欣赏一下周遭的风景。”
我妈妈离开香港、移居多伦多已经33年了,我回到香港也已经有四个多月。在母亲自己的家乡,我却成为了她的导游。
那些我所熟悉的拥挤街道,对她而言却很陌生。我带着她穿过现代化的地铁系统(那是母亲离开之后才建成的),帮她选择一条最好的巴士线路,去见她的老同学。我们一起步行穿过中环——香港最繁华的金融区,70多层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这些都是母亲从没见过的。我带她去了几家我发现的地道粤式餐馆,她却能用流利的粤语点着英文菜单上没有的菜。
说到底,我们还是香港人。
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专业点餐的成果,妈妈评论说,我的粤语水平提高了。此刻的我,享受这样的美食,积极学习粤语,与青少年时期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把小时候对母亲文化的冷淡,归咎于多伦多市郊白人社区的生活。当时,在300个人的小学里,只有三个华人小孩,我是其中之一。我只想和我的白人小伙伴们一样,拥有Wonder Bread的三明治,放学后去上芭蕾舞课。但现实是相反的,每周我都被迫去上讨厌的钢琴课,吃传统的中餐——蒸肉、炒青菜加一碗盛得太满的白米饭,在我看来味道简直淡极了。
一到周末,母亲就会把我送入中文学校,学习她的母语。我失去了周六上午的动画片时间不说,终日死记硬背那些复杂的汉字笔画,一度令我对这门语言非常厌倦。每当母亲对我讲广东话,虽然我完全可以听懂,但却只能用英文回答。
有一句广东俚语,形容我这样的人为“竹升”。竹升的意思是,竹子中间有结,因此水流无法从一端流到另一端。“你看竹子。它看起来像是空心的,实际上里面一节一节,是堵住的。”妈妈解释道,“就像你一样,你看起来像中国人,却又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你既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华文化。”这个词是个贬义词,而且它说得很对。每当我、我姐姐和表亲们拿错了筷子,或说着有口音的粤语时,妈妈和亲戚们就会拿这个来取笑我们。
对于母亲而言,目睹自己的孩子在两种文化之间拉扯,她也感到十分沮丧。她移民加拿大,又在西方的环境、西方价值观和信仰中把我们带大,但在教育的问题上,母亲其实没什么规律可循。唯一可以借鉴的只有她自己的童年经验。母亲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是家中六个子女的老二,她从小就被培养出了一种“弱肉强食”的思维逻辑。她曾亲眼见证了我祖父强烈的工作热情让他由一个基层的服装加工工人成长为工厂的领班,进而成为一名高级经理人。母亲上的是天主教修女严格管教下的女子高中,这无疑也影响到了她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喧嚣的城市生活、令人难以承受的学习、社会与经济压力,最终令母亲逃离了香港。
母亲离开时,是1976年,从那时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许多香港人都移民到了西方世界。我高中所在的城市,经常会出现香港来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那些孩子都成了我的高中同学。我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却始终没办法和他们交心,只能和他们、和母亲的家乡文化保持着远远的距离。在我注册成为大学生和更新护照信息的时候,我甚至在申请表上刻意地忽略了自己“太过中国“的中间名,心想这样就会令我不那么像中国人,而更像加拿大人。
离开这样的环境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份认同的割裂。大三的时候,我在国外待了一年,在哥本哈根读书,到欧洲各处旅行。我到了一些地方,在那里“移民”和“有色人种”的概念是闻所未闻的。一次,我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旧城区的一个酒吧里,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当地姑娘,她们正在一起庆祝某个人的18岁生日。也许是因为黄种人在东欧太过罕见,姑娘们好奇地围着我。“中国!你是从中国来吗?”一个女孩问我,语气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只是充满好奇。
“不是,”我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因这样的回答而感到羞愧,“其实,我从未去过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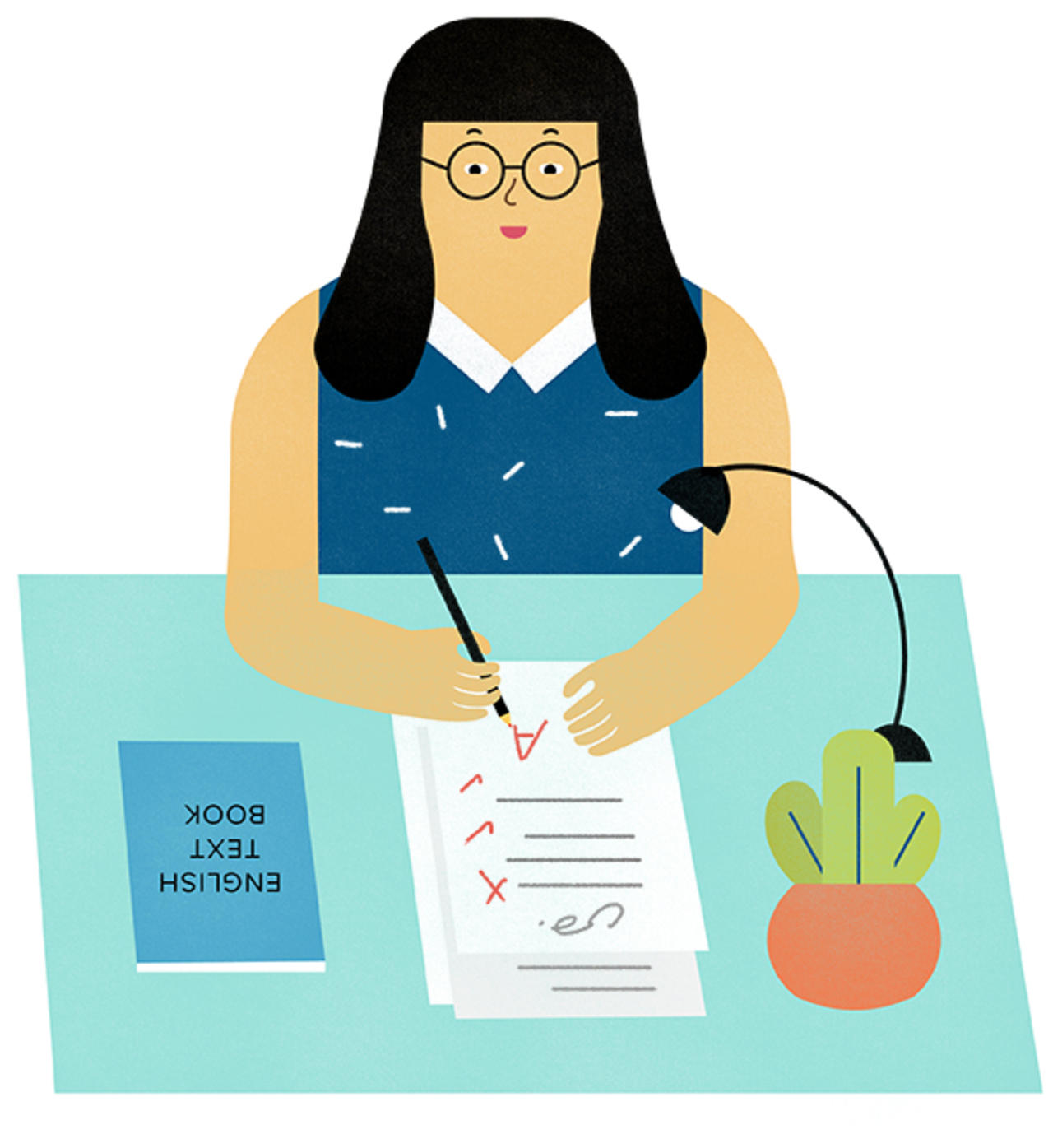
* * *
虽然从小和母亲及其他华裔移民生活在一起,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回到香港生活。大学毕业时,我赶上了经济危机,加拿大没什么好的工作机会,香港似乎成为了一个自然的选择。我很快在一所英语教学机构里找到了工作,并和其他60名外籍人员一起受训,他们多数都是来自于英国的白人。
那些曾经在青春期备受冷落的技能,如今却让我在一群新人中有了明显的优势。我说着有浓厚口音的广东话,甚至能和房东讲价,争取更便宜的租金。而我也开始乐于混杂在人群中,挤在服装店和杂货店里,直到蹩脚的粤语出卖了我“外国人”的身份。当新同事们在午餐时学着用筷子,并将狐疑的目光投向热气腾腾的竹篮——篮子里有咖喱鱿鱼、虾饺和馅料神秘的白馒头——我对这些菜就熟悉多了。
这些陌生人最终都成为了我的朋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社交圈从外籍英语教师扩展开去,我遇到越来越多与我经历相似的人——那些香港移民的儿女,出生和成长于西方世界,在西方接受教育,却选择到香港定居。如果回到青少年时期,我会尽量避开这些人,但在我们父母的土地上,我却找到了和他们的友情。
究竟有多少出生于西方国家的华裔如今生活在香港,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来自2013年香港太平洋人口普查的数字显示,香港居住着约30.1万外籍人士,他们占了本市人口的4.24%。与2009年的25.2万外籍人士相比,这一数字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港居住的华裔绝对不能被算作是本地人,但我们也不算是完完全全的“外籍人士”。我们带着对当地习俗、规范、语言和食物的不同认识,以“中间人”的态度游走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也保留了西式的价值观,尤其是自由和个人主义,会被以家庭为中心的香港人视为反叛的特质。
就英语老师的工作而言,我发现这种“中间状态”带来的更多是阻碍而不是帮助。在我任教的学校里,校方要给予学生一种“身临其境”的语言体验,这意味着以英语为母语的老师会更加吃香。我第二份教职的指导者帕梅拉·博威茨(Pamela Bovitz)就建议我,最好假装一句广东话也听不懂。
“她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孩子们会用母语说,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我会装出一副困惑的样子,忍住以广东话回应他们的冲动。我曾经在一家幼儿园工作,教这些小朋友学习英语。但是操场上的游戏、教室中的谈话,都在不经意间帮助我提升了自己的粤语。每天早上,我都能听到他们用粤语唱校歌,有一天我把这首歌唱给了我的母亲。她一边大笑,一边帮我进行翻译,让我理解了歌词是什么意思。
幼儿园里一共有七名英语老师,除了我,还有两个人也是外籍华裔。在过去十年里一直负责招聘外籍教师的博威茨说,每年她都能收到无数来自外籍华裔的简历——这种趋势最近几年越来越明显。
结束了幼儿园的教学工作后,我想换份工作,但没有打算离开香港。2010年,我修读了香港大学新闻系的硕士,在那里遇见了斯蒂芬妮·陈(Stephanie Chan)。她于2007年从多伦多移居香港,在香港的加拿大国际中学任教。在加拿大时,她接受了教师的培训,但是毕业之后,她一直在寻找海外的工作机会。“当时,我在师范学院的朋友们都在拼命找工作,”陈回忆说,“很多都无法在理想的地方找到一份永久教职。最后,有些人只能年复一年地做代课教师。”和我一样,陈几乎对香港一无所知,此前陈只来过一次香港。她的父母很小就移民加拿大了,他们一直生活在多伦多,和我母亲一样。
现在,陈在同一间香港国际学校教传媒研究与新闻学。她的丈夫也是一名来自于加拿大的华裔。他同样是被香港的就业环境吸引过来,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在美国公司的工作。
既不太像本地人,也不太像外国人,这对陈而言是一种积极的体验。“我已经能够在保持外籍人士身份的同时,欣赏中国的文化,”她说,“香港是一个外国人极易居住的地方,对于那些会讲中文的外国人而言,就更容易了。”
艾里斯·林(Iris Lam)虽然出生于香港,但她却在1980年代末就随全家移民加拿大了,那时她还是个孩子。2011年,她所在的香格里拉饭店给她升职,并把她派往了香港分部。林在那里工作了两年,而后又被派往了上海。2014年,她再一次回到香港,在文华东方酒店集团工作。
林曾经在上海和吉隆坡工作过,和这两座城市相比,她“外籍华裔”的身份在香港是最为显著的。“我发现香港人最习惯于接受 ‘外籍华裔’这个概念,”她解释道,“我从未感受到任何歧视,也没感觉到当地人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和我互动。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这样的人在香港社会中是很常见的。”
第二代移民的回流不只限于香港。在香港,我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了桑迪,当时她正在回首尔的路上。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桑迪的母亲和小姨离开首尔,移民纽约,在那里她们都做了收入更高的护理师。桑迪在2008年搬回了首尔,像我一样,她轻松地找到了英语教师的工作。后来她又成为了一名教科书作家,为一所私人学院编写教材。在与韩国上层阶级孩子的互动过程中,桑迪受到了启发,决定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韩国的国际学校高中生以及全球教育问题。从那之后,她三次回到首尔,目前正在该地展开长期的田野调查。
在首尔,桑迪和纽约的初、高中同学重新联系了起来。“有很多韩裔美国人都和我一样,因求职而回来。”她说。桑迪的同学们有在法律、金融、研究及餐饮领域工作的,但大多数人做的还是英语老师,而且就是桑迪刚开始的那间学校。“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高学历人士,在美国长大——最近都回到韩国了,因为在美国找不到什么工作。”

* * *
2009年,母亲结束了35年的护理生涯,在加拿大退休了。她渴望看看家乡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她也想来看我),于是,母亲在香港度过了一个长达七周的假期。上一次她回到这里的时候,还是1982年。
多年以来,母亲从来没有过度感伤于自己的成长经历。她曾经向我描述过童年的点点滴滴,但当她站在自己的故乡,时隔三十多年来又一次看到了记忆中的事物,过去的回忆还是像潮水一般涌来:周末父亲带着全家一起逛的那间百货商场;还有放学后她总会和同学们一起去吃的上海辣面条,以及摇摇晃晃的老电车所发出的那种“叮叮”声。
一天下午,我带母亲到香港历史博物馆参观。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包括一座战后重建时期的唐楼,它再现了战后香港恶劣的生存条件,日益增多的穷人就在那种环境下艰难谋生。
当我们转过拐角,唐楼映入眼帘,母亲的眼睛瞬时亮了起来。“这看起来真像我们的第一个房子!我曾经和你的大舅父和姨姨一起睡在上铺。”母亲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小型双层床。“我们不得不这样睡。”她补充道,两手相对,比出一个宽度,在床上比了三下,代表睡在那里的三个孩子。我想象着,当时母亲像沙丁鱼一般和兄弟姐妹们挤在一张床上,在一个因贫困而成为历史展品的房间里。
“你的婆婆(外祖母——编注)和舅父会睡在下铺,”她继续说道, “而你公公(外祖父——编注)会睡在行军床上。”一家六口共用厨房和浴室。我母亲一家人在那里住了五年之多,直到公公赚够钱,改善了住宿环境。最终,他们移民和定居在了加拿大。
母亲第一次回香港的时候,一直跟我在城市里观光,以及和几十年没见的老同学聚会。退休生活赋予了她自由,每年她都可以从加拿大飞回香港呆上几个月。她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安逸,这是由于养老金数目可观(这是在香港无法得到的),以及一辈子节俭的积蓄——“省钱”是华裔移民的一大标签特质,但现在的我很感激自己学到了这一点。
来到香港以后,母亲依旧带着一些西式的习惯。每当这个温暖的热带城市气温骤降,街上就会出现一堆穿着羽绒服、带着帽子和手套的人。但母亲已经被加拿大的冬天锻炼出来了,她还是会穿着短裤和T恤出门。在和侍者或店主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是说英语,然后才会蹦出广东话。母亲的朋友们总拿她爱吃甜食这一点说事,因为她已经习惯于餐后吃点甜食了——这是一个西餐中的准则,在中式餐宴中并不常见。“她们会叫我番鬼婆,因为我的所作所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白人女子。”
母亲当然知道她们是在开玩笑,就像当初,在年幼的我学不好广东话时,母亲会笑我是个“竹升”一样。但我知道母亲也有像“竹升”的部分。多伦多的生活令她养成了加拿大式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与她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交织在了一起。
四年的香港生活过后,如今我已经回到了多伦多。虽然我时常想象着,如果自己永久地定居在香港,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但我的心一直在多伦多。国外的生活更加简单——无论是在社交还是职业的层面。讽刺的是,我曾经一直努力地在多伦多广交朋友,试图找到立足点,最后却是在香港建立了成果丰富的写作事业,以及一帮无话不谈、年纪不等的好友。回到多伦多的一大好处当然是,我能够和家人在一起。我可以用日益熟练的粤语和叔叔阿姨们进行交谈,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还会煮菜给我的加拿大朋友们。学到语言和烹饪技巧,我当然深表感激,但最为重要的收获还是我在两种身份之间找到了认同。我曾因为自己夹在两种文化中而感到惭愧不已,但如今我很感谢这种际遇,因为它让我明白了维系自己生命的到底是什么。
* * *
Andrea Yu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她的更多作品可以在andreayu.ca找到。
Janny Ji是刚刚毕业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现在是一名插画家和平面设计师,定居于纽约。
这个故事由Narratively网站与《威尔逊季刊》合作共同发布。
翻译:徐徜徉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