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纳兹玛·罕(Nazma Khan)登上讲台,拥挤的房间瞬时安静了下来。一条色泽明艳的丝绸头巾裹在她的头部与颈部,使她优美的脸庞更加鲜明。我们都往前挤,以听清她柔和又充满活力的声音。
罕从11岁离开孟加拉来到美国讲起,当时她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戴hijab的人——一种遮住穆斯林女孩的头部和胸部的面纱(或头巾)。在初中及高中时期,纳兹玛·罕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他们朝她吐口水,大叫她的名字,质问她为什么要带着头巾。“9·11”之后,罕进入纽约市立大学读书,她受的折磨达到了顶峰。当时纽约人对穆斯林充满警惕,罕的头巾使她成为怀疑和嘲笑的对象。
“我觉得自己就像罪犯一样,”她说,“好像‘9·11’是我发动的,好像我应当向所有人道歉。”但是罕依然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忠诚,她将所有恶毒的评论与异样的眼光抛之脑后,依旧戴着头巾。
如今,罕已经30岁了,她正在纽约皇后区社区大学的穆斯林学生联合会上发言。教室里挤满了人,主要是慕名而来的穆斯林学生,其中很多人戴着头巾。罕的演讲引发了共鸣,人们不时点头以示同感。质疑的眼神,伤人的言语,这种滋味很多穆斯林学生和移民都曾经尝过。这是属于他们的“集体伤痕”,但也有共同的自豪感。演讲结束后,教室里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长期以来,许多人把充满宗教意味的头巾视为性别压迫及歧视的象征,那么,穆斯林女性到底为什么要戴头巾呢?其实,头巾已有悠久的历史,通常意味着谦逊,得体与尊严。2700多年前的《中亚述法典》中,曾经提及,不适当地戴面纱的妓女与女奴将会受到惩罚。相似的记载也曾出现于拜占庭帝国及古希腊、罗马帝国的史料中。
罕11岁开始佩戴头巾。当时她很渴望将自己包裹起来,希望自己可以和母亲、阿姨等周围的女性一样,看上去充满“女人味”。“当我戴上头巾,人们就不会评判我的外表,而会更多地关注到我的性格和智慧,” Nazma表示,“这是真正的解放。对我来说,这才是女性主义的体现。”
罕表示,佩戴头巾完全是她的个人选择。“在我的家中,很多女性成员会选择戴头巾,但也有很多选择不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选择,没有人逼我一定要戴它。”
她回忆道,第一次戴上头巾时,“我没有跟妈妈说什么,就直接把它戴上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头巾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就像很多居住在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女性一样,罕发现周围的人很难接受这种独特的打扮。
“初中时,班上的同学会叫我忍者或是蝙蝠侠。”很显然,这是一段痛苦的记忆,“他们会把口香糖粘在我的面纱上。” 罕在整个青春期一直为此而挣扎,要知道,哪怕是对最守规矩的孩子而言,青春期都是极为难熬的。罕选择了忠于自己的信仰,但她的妹妹却无法抵御同学的压力。“她(妹妹)有两年都没有戴头巾。”罕说。她理解和尊重妹妹的决定。至于她们的父母,“起初他们有些失望,但后来他们决定让她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父母依然无条件地爱和支持着妹妹,这一点不会改变。”而后,有一天,罕觉得,也许自己也应该不要戴头巾了。“有一天,我没有戴头巾出门,觉得自己像是没穿衣服。”仅仅一天的经历,就让罕意识到,其实她真的很想戴头巾。
“戴上头巾以后,我觉得自己完整了,内心很平静,”她说,“戴头巾让我觉得安全,受尊重,也很特别。我感到安宁,因为我遵从了创世者的旨意。在我看来,只有遵守创世者的旨意,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最终,罕的妹妹也自愿戴起了头巾。
罕在纽约市立大学读生物学与医学,但在毕业后,她决定走另一条职业之路。2010年,她创办了一家名为“神奇头巾”的公司,专门在线销售定制款头巾,公司的口号是:遮挡、包容、自信。她所销售的头巾非常时尚,颜色鲜艳,面料轻盈且缀有摩登的印花图案——与人们印象中的那些深色、厚重的传统头巾相去甚远。经营这家公司,罕的目标远不止销售数字增长那么简单:每销售一笔,她都会捐出一定比例,给当地穆斯林组织。“我向布朗克斯的穆斯林中心捐了钱,”罕说,“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帮助清真寺免于被抵押收回。”她耸耸肩说:“你不可能因馈赠而失去任何东西。”
在她公司的网站上,除了贩售实体物品,罕还增加了关于头巾的教育服务,有文章题为《时尚vs谦逊》、《我们不是在向男人屈服》以及《头巾对人类健康的好处》,后者谈到了头巾能够抵挡可能致癌的紫外线,既能保温又能御寒,同时,盖住头发也更加卫生。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罕开始收到其他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来信,她们会分享自己曾面临的歧视与非议,还有人担心自己会因头巾而找不到工作。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2010年,一个叫做哈尼·罕(Hani Khan)的穆斯林女孩因工作时不肯摘下头巾,而被加州圣马特奥市的一家服饰店开除。最近,法官对本案作出了裁决,判定这家公司有“职场歧视”。在美国,许多女性都曾因戴头巾而失去工作;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女性被禁止在公共场所、学校及政府机构戴头巾。
罕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对这些女性表示支持。因此,在2011年,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试图让非穆斯林女性感受一下佩戴头巾是什么样的。她创立了“国际头巾日”,邀请全世界的女性都在当天戴上头巾,亲自体验一下。2013年2月1日,全球首个“国际头巾日”正式举行。
“我在想,那些不理解我的人,如果能够戴上头巾,按我的生活方式活一天,也许能更好地理解我的选择,”罕说,“这样,他们下次遇到戴头巾的人,就不会再指指点点了。”
虽然罕对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她依然被第一届“世界头巾日”的盛况震惊到了。来自67个不同国家的11000名Facebook用户参加了“世界头巾日”的活动,全世界的非穆斯林女性将自己戴着头巾的照片传遍了网络。她们都表示,自己对穆斯林女性有了新的理解。她们乐于分享自己参与这项活动的初衷:
“为了更好地了解头巾,也为了更加尊重那些佩戴着头巾的女性……我住在犹他州,那里摩门教是主要的信仰。我想假如不止是我,我周围其他人也能了解真相,而不是道听途说,这样就太好了。”
--劳拉,美国,摩门教信仰者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向至少一个人解释清楚,世界上有很多妇女是自愿戴上头巾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极端主义者/恐怖分子。”
--埃斯特,美国,基督教信仰者
“那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罕说,“我从未像那天般如此开心。”这更坚定了她向世界传播“头巾”文化的信念。“在我死之前,我想给世界留下这项遗产。我不想出名,但我希望‘2月1号’这个日子为人所知。”
因此,2014年2月1日,罕设定了目标,希望召集百万人参与第二届“国际头巾节”,我也计划加入她们。我不是穆斯林,从未佩戴过任何宗教形式的头巾。我穿衣服也从不保守,有时也会露出乳沟,吸引别人注意。但我在一所招收穆斯林学生的大学工作,许多人会戴头巾,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义务了解不同的文化。
我喜欢“头巾令人谦逊”这个说法,我也发觉,头巾在有的女性身上很好看,尤其是罕,她能轻易地使头巾变成迷人的配饰。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被犹太教的父亲及天主教的母亲所养大的人,我对这两种宗教都有感情,但我并不倾向哪一种宗教,因此我也很难想象自己戴头巾的样子。在参加这次活动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有点紧张。我知道一定会有人盯着我看,无声地做出判断。我不清楚家人和朋友将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对我另眼相看。我还担心,如果当天在街上遇到了不够宽容、又不明白我为什么戴头巾的路人,我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我也担心一些细节,比如为了搭配头巾,我应该化个什么样的妆。我的棕色长发就是我的盾牌,让我可以安心地躲在后面。几年前,我剪了大约长达12英寸的头发,捐献给了一家公益组织。我还记得,当我坐上椅子,造型师准备开始剪了,我竟然哽咽了。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一项太突然也太剧烈的变化了。但当一切结束后,我带着一包头发走出美发沙龙,突然感觉到没有长发的自己是那么轻松又那么自由。那么,头发被完全包住,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感觉呢?
我做了一些准备,到“神奇头巾”的网站上阅读了《佩戴头巾小贴士》,其中有很多Facebook网友的贴文。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克服了最初的不适之后,大多数人都从佩戴头巾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很显然,很多留言的都是年轻女孩,希望能给予彼此支持:
一个名为希拉兹(Shiraz)的人写道:“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端庄而不失体面;高贵而不卑微;自由而不屈服;纯洁而不受玷污;独立而不受束缚;受到保护而不外露;理应受到尊重而非嘲笑;她们自信且从不缺乏安全感,她们顺从,不是罪人,她们是被小心翼翼呵护着的珍珠,不是荡妇。”
如果希拉兹和其他女性感到有必要在网上发文,支持那些考虑佩戴头巾的妇女,那么很显然,她们一定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反过来说,这令我感到,如果这些妇女们每天为了接近信仰而忍受那么多,那么,让我戴几个小时的头巾肯定没问题。
于是,我给罕打了个电话,和她约定在“国际头巾日”活动前碰面,这样我可以更加了解头巾的意义,以及如何穿戴它。当我到达她位于长岛的家中,她的热情令我感到宾至如归。她为我煮了印度茶,并奉上了一种好吃的名为kaju burfi的腰果糖。而后,我坐在她那颜色鲜艳的床单上,她开始准备包裹我了。我太紧张了,以至于坐得离镜子远远的。当她在房间里来回穿梭,收集着各种布料时,我发现自己的坐姿竟不禁变得端庄了起来,我双腿交叉,脚踝并拢,两手放在腿上,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等待被妈妈打扮的孩子一样。
在决定了使用哪种头巾之后——一件较沉的宝蓝色丝巾——她把所有用得上的布料都倒在了床上。罕令我将头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将一块白色的小方巾置于头顶,然后把它系在我的后颈。这种方巾能够固定头发,防止头巾移动。然后她将头巾放在我的头上,一边较长,并用别针将头巾和小方巾固定在了我脖子的后面。她轻轻地抓起头巾的长边,用它裹住了我的下巴和面部,并最终以别针将其固定于我脸部的另一侧。这之后,她又抓起了余下的布料,覆盖住了我的脖子和胸部。我已经尽量少地露出乳沟了,但是她用面纱覆盖我的胸部时说:“记住,谦逊不只意味着要遮住我们的头发。”
我脸红了。
在她完成之后,她向后退了几步,欣赏自己的杰作。“你看上去就像个洋娃娃一样!”我有点害羞地走到镜子前面。我不知道自己期待中的样子是什么,但却被镜中的自己震惊了——我看起来是如此不同。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形象是:修女。头发被盖住之后,我看起来比原先老得多,脸上的五官也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改变。
罕仍在兴奋地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我发现自己站得更直了。我似乎很自然地就站得很谦卑,双脚踏地,而不像往常那样斜着一条腿。我不知道两只胳臂该怎么办,于是让它们自然地垂于身体两侧。虽然头巾没有对我的行动造成任何束缚,但我绝对变得僵硬了。头被包起来,的确很有安全感,就像在茧当中。选择这一天来体验“头巾文化”是很完美的,因为天气很冷,又下着雪,我好像戴上了温暖的围巾和耳罩。柔软的面料也让我觉得很舒服,就像把孩子塞进了温暖的被窝一般。当我终于戴上头巾,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装饰物竟引发了如此多的争议。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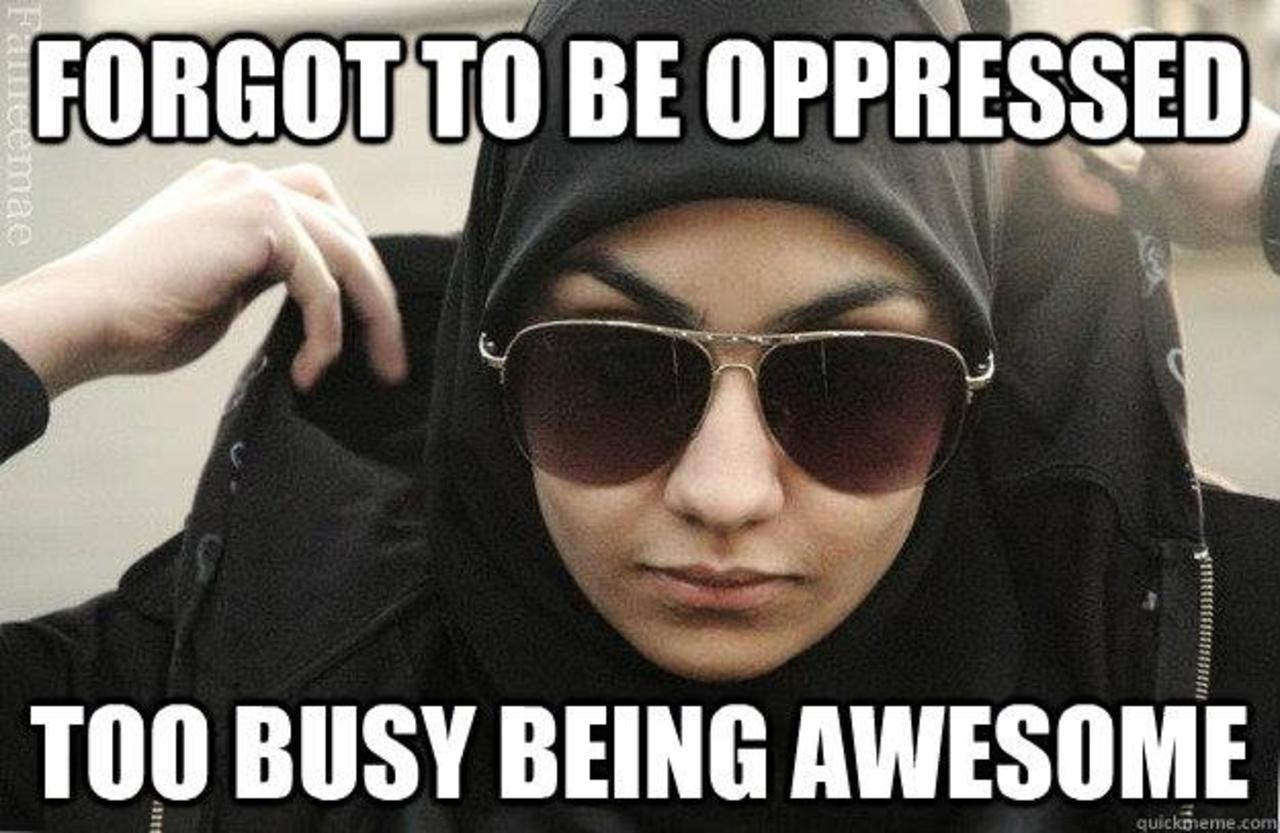



穆斯林妇女并不是唯一因宗教而遮住头发的群体。正统的犹太法典也规定,已婚犹太妇女在公开场合必须遮住头发。遮挡头发的不一定是头巾,你可以使用假发、围巾或发网——流行于中世纪的一种美发工具。基督教也有女教徒在教堂进行朝拜时“包头”的传统,基督徒精心设计出了特制的面纱、头巾,甚至还有帽子。《新约》中又这样一条:“不以面纱遮面而进行祷告或布道的女人,是在羞辱自己。”(哥林多前书11章:2-16)在很长时间里,这段话一直被基督教的信徒们奉为严格遵守的戒律,直到20世纪,许多教会才慢慢放弃了这一要求,但罗马天主教的修女们直到今天都还佩戴着一种类似穆斯林面纱的头巾。
在美国,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大部分男人和女人出门时还都会戴着帽子,这并非宗教习俗,而是出于社交礼仪。在当时,不戴帽子出门被认为是有失分寸的——那么戴帽子的美国人与戴面纱的穆斯林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
当然,很多反对“头巾”的人会拿出“性别平等”这个议题。依照伊斯兰教法,穆斯林女性在非直系亲属的成年男性面前必须将遮住头发,其目的是将私下的“自我”与公众空间内的“自我”剥离开。而且事实上,hijab(头巾)这个词在阿拉伯语里恰好是“分割”的意思。虽然教义中规定,穆斯林男性与女性都必须穿着得体,行事谦逊,但被要求隐藏其美貌的却只有女人。在许多非穆斯林人群看来,头巾无非是男性控制女性的一种手段,剥夺她们的自由,抑制她们的性生活。
在我了解头巾之前,我确实对戴头巾的女人们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认为她们是被逼如此,别无选择。但当我在Facebook上的“国际头巾日”主页上读到了这样一段来自穆斯林女性的发言,我开始改变主意了:
“我戴头巾,因为我选择如此。头巾反应了我的认同,也反映了一种谦和的人生态度。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要向这世界展示些什么,那么,我也可以选择我要对这世界隐藏什么,以及如何隐藏。”
和很多穆斯林妇女一样,罕并不喜欢拍照——这同样是穆斯林女性坚持践行伊斯兰教义中有关 “谦逊”的行为准则,她们希望外人不靠外表,而靠内涵来评判自己。在我与她碰面前,我曾询问她是否愿意拍摄一张正在为我包裹头巾的照片。她很抗拒。然而,当我来到她家,迎来了属于我的“头巾日”时,我惊喜地发现,她改变了主意。当她小心翼翼地帮我戴好头巾,我能感觉到她有多么开心。看到我所做的事情、更好地理解她的文化,这对她而言意义重大。
我告别了罕,开车回到位于皇后区的办公室,路上我一直没有摘下头巾。在罕家中,戴着头巾感觉已经很奇怪了,但是在自己如此熟悉的空间(比如我的车)内戴着头巾,这感觉更奇妙了。我禁不住好奇,当周围的人看到我时,到底会做何感想。但说实话,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在法拉盛市中心停车,在皇后区唐人街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这一地区,没有女性会戴着头巾。在那个瞬间,我很快就大致理解了穆斯林女性们的感受。那是一种仿佛你是异类的感觉,仿佛你并不为这个社会所容。人们是故意要避免与我进行眼神接触吗?还是我多想了?我很好奇当路人看到一个遮住头发的白人女孩时,他们的内心会冒出什么想法。他们会觉得这很奇怪吗?
当我把车开进大学后,我很想知道如果我戴着头巾走在校园里,将会发生什么。一些认识我的人奇怪地看着我,但大多数人都不会对我身上的服饰太过在意。
我停车的时候,取出了别针,拿下了头巾。我盯着车座上那团宝蓝色织物,陷入了沉思。戴着头巾的那几个小时并没有改变我自己,也没有改变我对自己的看法,更没有改变我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但是,我的确认识到,头巾就仅仅是头巾而已。虽然对于戴它的人,头巾意义重大,但对我而言,它不代表什么。如今,当我在校园里看到戴头巾的学生,戴圆顶小帽的学生,戴十字架的学生,甚至是穿毛衣背心的学生,我都会提醒自己,不要将焦点放在他们的装饰物上,要看到内在。



_____________
Marisa L. Berman是一位纽约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作家,她的新书于2015年初问世。这本书介绍了长岛游乐园——从康尼岛到蒙托克角。她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区社区大学的Harriet & Kenneth Kupferberg大屠杀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
Alison Brockhouse是一名活跃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艺术家与摄影师。
翻译:徐徜徉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