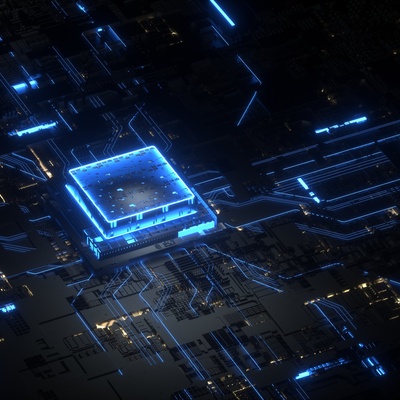1
2015年6月,李霄峰又找出了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这是一本他读了无数遍的书。翻开扉页,那句影响过千万文艺青年的名言扑面而来:“不要怕丢脸”。
几天后,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少女哪吒》将上映。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拍摄完成以后,我才真正学着做导演。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别人了。”
李霄峰的熟人会发现,他的微信朋友圈完全变了风格。在私人领地宣传自己的作品,过去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搞得跟安利似的,我还是安利的总头目。”以前,李霄峰的朋友圈是标准的高冷文青范儿:时不时甩一句令人费解的隽语,发个酷图片,心情波动时随机删,不经意间让世界感到此人骄傲……现在李霄峰每天平均发15条消息,每条都是《少女哪吒》的宣传。
6月24日深夜将近12点,李霄峰发了这天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为《哪吒》拉选票的小视频。贴完视频,他郑重地对766位好友打上一行字:“……请病毒传播这条视频,谢谢你们!”——“不要怕丢脸”,他对自己说。
李霄峰今年36岁。十几年前,他是著名的影评人,笔名LIAR,以文风犀利著称。后来合作过的许多导演和朋友当年都被他狠狠骂过。当了导演后,李霄峰翻出那些文章重读,“当年骂人家的这些缺点,好像现在我都有。”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某一天,他逛网偶得,黑泽明曾在1971年自杀过一次,未遂。那年黑泽明61岁。李霄峰觉得自己被黑泽明生生骗了一场,“你不是说不要怕丢脸吗?你那么大岁数了还自杀!”然后他慢慢想,慢慢明白,“其实,哪个导演不脆弱?”
李霄峰生就一副文艺青年命运多舛的样子。不高,一丝脂肪也没有的精干身材, 发型是极短的短寸;一副眼镜上框是黑色的,镜片直接融入脸色;笑时薄嘴唇扯开,嘴角羞涩,眼神狡黠,而眉头微倒挂,略显悲怆。头骨明明线条流畅,不知为何却让人觉得到处反骨。整体看上去,像是用密度极高的材料制成,放到水中便会直沉到底的一个人。
“那天我在想啊,从《哪吒》这个电影,我能看到我小时候,我难道是又把小时候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吗?”中学时因为“到处反骨”,李霄峰常被老师孤立,因为老师孤立,同学也就不敢理他。李霄峰父母都算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希望他大学别学文科,结果他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读“市场与广告”。上到大二,他退学,去了比利时学电影。在比利时上完两年基础课,他又跑了回来。
不止一个李霄峰的朋友这样形容他:“比较蹉跎……他是有点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劲头。”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迎来第一次互联网热潮。1998年左右,一个搞IT的程序员“边城浪子”建了网站“电影红茶坊”,李霄峰常去那里逛,聊天,看文章也写文章,结识了一批热爱电影的同龄人,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编剧顾小白以及《少女哪吒》的制片之一冯睿。后来李霄峰又摸到了新浪论坛,“像疯狗一样四处乱窜”,参加各种线下聚会。最后,这批人进驻当时规模最大的电影论坛“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
2001年,李霄峰出版了电影随笔集《天亮说晚安》,署名LIAR。

2002年年底,李霄峰进了陆川《可可西里》剧组,担任纪录片导演。这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专业电影训练,他自认从中获益良多。两年后,《可可西里》完工,李霄峰累坏了,他想不如找个工作,试试上班吧。
那一年,李霄峰用LIAR的笔名写了最后一篇影评,批评了顾长卫的《孔雀》。 当时LIAR撰写的影评可以拿到一个字一块钱的专栏稿费,出去行走江湖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李霄峰决定停止写影评,从此当一个真正的电影创作者。因为“不喜欢给自己留后路”,他还决定以后再不用“LIAR”这个名字。“那时候我很年轻,写的影评其实就是观后感,不属于评论范围。不写了,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呢?当想要抒发自己的时候,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吗?”
他给许多电影公司发了简历,把以前写影评写专栏的经历一概去掉,名字只署“李霄峰”。接到第一份OFFER,职位是策划,月薪1500。“我第一反应是受到了侮辱,后来再想,这是正常的,人家凭什么啊?我有什么经历呀,我不就是进一剧组,当了一个文学策划和纪录片导演吗?”后来他去了另一家电影公司作策划和发行,月薪3000。
2005年,当初被LIAR骂过的导演张元正在寻找年轻人一起合作。在带《看上去很美》奔赴威尼斯的航班上,他读了李霄峰的两个故事。从威尼斯回来,张元去找李霄峰,说:“下一部戏,我们合作”。当时李霄峰正百无聊赖,浑身力气没有使出的地方,又有杂志找他写影评,他刚有点心动,张元告诉他,霄峰你真的不能再写影评了,“这是俩方向”。
李霄峰觉得张元说得对。接下去,他开始查资料,实地考察,写剧本。一年多后,新剧本出来了,讲述某地一群不满18岁的少年团伙犯罪的故事,取材真人真事。李霄峰给剧本起名《无法无天》,也没想到应该改个名就送了审。审查意见发下来:“不批准拍摄”,有关部门认为这剧本“不适合张元”。李霄峰说,潜台词是“太适合张元,所以不许拍”。
李霄峰心灰意冷。他去工作室找张元,打算再喝一顿酒,就“拜拜”。张元穿着大拖鞋,大T恤,晃晃悠悠地进来,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李霄峰,说:“来一口”。
那天晚上张元和李霄峰喝着酒聊了一夜,又聊出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由李霄峰出演男主角的《达达》。
《达达》拍了50天。拍完之后,李霄峰有些厌倦几年来的电影生涯:“觉得没希望,对自己也绝望,这难道就是电影人的生活吗?就是每天聚在一起,胡吃海喝?跟那些商人打交道?拜这个大哥拜那个大姐?”对于电影,李霄峰的感触是编剧太没有掌控权,“做导演有掌控权吗?有,但也不多”。他想,不如自己开个公司算了。
李霄峰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是学广告的。管别人借了笔钱,他跑去上海,开了个广告公司。公司开完再次忽然想起来,这是盘生意,应该先做市场调研。调研了半年,结论是没有客户。
李霄峰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状态最差的一段时光。每天,他宿醉起来,到楼下的罗森超市买一小瓶芝华士,再上楼,喝到人事不省。直到2009年《达达》公映李霄峰搬回北京,那几年他说自己是“写什么剧本什么被毙,干什么项目什么黄”,除了写作,就是喝酒。希区柯克有篇小说叫《醉鬼》,讲一个人酒后杀了自己的老婆,自己却全然不知,“我那时候就那状态,喝完以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国贸桥上车开着,我把门一开,要跳下去。”
严重酗酒的问题困扰了李霄峰很久。“但有的时候,我突然一醒过来,会比清醒的人更清醒。我会清晰地看到世间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和身边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嘛。”2012年,他出版短文集《失败者之歌》,在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这共鸣让我不安,像久旱的土地掠过风”——导演贾樟柯在序言中说。
2015年,《少女哪吒》杀青后的那个春节,李霄峰彻底戒了酒。
《哪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李霄峰管母亲借的。“借给你拍电影,还不如买理财,你也不给我利息……”母亲唠叨几句把钱打了过来。李霄峰说,这些年他的生活还是要靠父母接济。“说白了,温室里的一代,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霄峰的父亲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干过活,一直漂着”。
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李霄峰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想改个名。“李霄峰这仨字儿特别冷,你说你本来有一山峰吧,跑到云霄里干嘛呀,能不能让人看得着啊?我觉得这名儿不平和,给人感觉特别傲慢。”父亲想了想,跟他说,别改了,“你就长这样,改也没用”。
2
1998年12月,卫西谛在BBS“西祠胡同”创建了“后窗看电影”版块。
卫西谛出生于1973年,比他在“后窗”结识的LIAR、顾小白、绿妖等人要大上一截。但是关于电影,他们的经验很相似:大都在小城市出生长大,大学里学理工科,观影经历是以录像厅中大量的港片为启蒙,经由好莱坞,来到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热爱电影的同时,他们都喜欢写作,渴望表达,但在现实中缺乏能够交流的同类。
回忆起在“后窗”的时光,顾小白说:“那是一个解渴的氛围,就像得到了源头。”顾小白2000年写的影评《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曾高悬于“后窗”首页很长时间,被无数网友满怀激情地阅读和转发。
2001年,在武汉上大学的绿妖即将毕业。武汉当时有电影爱好者自己组织的的观影活动,放阿巴斯、侯孝贤等导演的作品,放映地点一般是旧电影院或录像厅。那时候的周末,绿妖经常早上六点起床,坐七点钟的公共汽车从武昌到汉口去,刚好赶上九点钟的放映。
在公交车上,她会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头磕在玻璃上,又醒过来。
看完两部电影,绿妖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到学校,然后写文章,发到“后窗”。她记得,那时候的放映员偶尔去北京淘碟,带回从小西天、新街口淘来的VCD刻录碟片,都是用牛皮纸口袋装着,碟片上手写着片名。“那就是我们下一周的精神食粮,”绿妖说,“那时候的心情就像朝圣”。
毕业后没多久,绿妖来到了“圣地”北京。那一阵,“后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除了这批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一些就读或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专业人士也活跃其中,如史航,张献民,程青松和陆川……还有当时最出名的“饭局通知”版主、资深文青老六。顾小白记得,那时候北京的聚会频繁到几乎一周一次,一伙网上结识的朋友们吃喝、玩闹、聊天、淘碟,也赶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

2002年,“后窗”爆发了建版以来最大的一次论战。
当时,LIAR受《21世纪环球报道》之约采访贾樟柯,期间谈及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后来报纸被禁,LIAR将两万多字未删改的访谈原文贴到了“后窗”。“结果呢,”当时的LIAR、现在的李霄峰说,“就引起了一帮所谓的独立电影界人士的愤怒,还有学院派的愤怒——两边都得罪了。”
论战的起因,李霄峰回忆是“因为贾樟柯批了一句《安阳婴儿》,我原原本本把这话给写出来了,然后还附和了一句。他们就揪出我这一句话,上纲上线说我诋毁独立电影。” 不知为何,争论的点又迅速转移为“电影是否与政治有关”,一周内,每天都有数万字的长篇大论发布到论坛,各种注册小马甲出现,许多潜水ID浮出水面,更有人撕破ID以真身亮相,各种立场、利益、派别、关系错综复杂。
关于这场论战,不同的当事人说法各不相同。有说是电影理念之争,有说是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与学院派之争,整个过程,张献民曾评论:“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惊悚”。据说,那时候的网民还比较有要求,想人身攻击,也还先发一篇说理讲事的长贴,然后在下面用马甲开骂……LIAR就读的学校和原名很快被“人肉”出来贴上了网,李霄峰说“那是最早的人肉搜索”。绿妖则记得自己懵懵懂懂地被拉去帮战,听见顾小白在电话里问李霄峰:“你那边还需要多少人?”
现在回忆,顾小白把它总结为“长者和不愿意被束缚的年轻人”之间的论战。这场空前绝后的论战之后,LIAR及一批民间影评人出走,另辟版面,“后窗”步入式微。
2005年,“后窗”的精华文章结集出版为《后窗看电影》,内容简介中写着:“‘后窗看电影’成立的这六年,正是网络影评崛起、发展、成其规模的六年。而后窗网友这些文字,基本代表了这些年来的民间电影评论的正果。”
那个时候,BBS已盛况不再,曾活跃于论坛的民间影评人大多被吸纳入传统媒体。顾小白离开供职五年的铁道部机房,去《精品购物指南》当电影记者,同时写剧本。绿妖则早已开始更为严肃的纯文学创作。
除了《后窗看电影》,“后窗”的“遗产”还有老六编撰出版的《独立精神》、《家卫森林》等一批电影文化书籍。顾小白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也仍命名为《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
北京爆发“非典”那一年,“后窗看电影”的创始人卫西谛从京城回到了南京,养狗,写文章,过起独立撰稿人淡泊的生活。说起“后窗”,卫西谛说:“回头看我自己那时候写的,也就是认真而已。这是因为无知。大家知道的都很少,然后又很敢写。然后,更多的是那种交流的渴望。”
2013年5月开始,卫西谛和两三个年轻朋友合作,以南京为起点,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发起了每年一度的“后窗放映”项目——每个城市找一到两家电影院谈合作,放映一些小众的艺术影片,以国产作品为主。
卫西谛说,他厌倦了以前独立电影那种在咖啡馆和大学里放映的状态,“后窗放映”要的是标准的影院放映,“因为他们本身拍的就是电影”。北上广等大城市已存在所谓的艺术影院,电影节也不少见,“后窗放映”关注的多是二三线城市。项目做了几年,许多媒体都有过报道,发展势头比较稳定。“这算是我做的比较符合影评人身份的一点事情吧。”卫西谛淡淡地说。
卫西谛的家离高铁南京南站不远,是个幽静的小区,楼房旁边种着大丛竹子。他的书架上放着自出版的摄影集《Way Away》,那是2013年夏天他在美国66号公路14天旅程的影像日记。照片是用胶片相机拍摄的。
除了《Way Away》、“后窗放映”的小宣传册,卫西谛的书架上还有他历年来出版的电影文集:世界电影评论年鉴《电影+》系列丛书(2002年起)、《为希区柯克尖叫》、《未删的文档》、《华语电影2005》……也有《后窗看电影》。每年的“十大榜单”他仍然在做,但是他说,对写影评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中国电影吧,我没有太多评价欲望。但是一个中国影评人老写外国片,不太靠谱,在媒体和大众其实也没市场。还有,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也不像我们当时刚喜欢电影的那个时候,因为有好多大师没有看过,看到会刺激,会兴奋。电影的黄金时代差不多,2000年以后,我觉得看到的好电影越来越少。然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电影品味了吧?我觉得我越来越狭隘……每年我都会做一个小东西,就是年度十大,结果每年都很像,还是那几个导演的新作品。我觉很无聊了,写来写去总是那些…… 虽然我还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夏天过去后,卫西谛计划去欧洲,也许会再出一本影集,也许写一些小说一样的东西。 他没考虑过做导演,他说自己“进入一个圈子的那种想法一向就很弱。”
这些年来,卫西谛与李霄峰几乎没有联系。《失败者之歌》出版那年,他们在杭州正好碰上,两人都挺高兴。那之后,卫西谛去北京也会专门找李霄峰聊一聊。李霄峰最终当了导演在他看来是件挺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李霄峰要拍电影,是好多年了吧?
《少女哪吒》的原著是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作者绿妖。那个“剔骨还母,彻彻底底把自己再生育一回”的少女哪吒晓冰,是以绿妖少年时的一个伙伴为原型,“写完后,作为一个年少时拼命想要离开家乡的人,”绿妖说,“感觉自己无意中投射了情感”。和李霄峰一样,绿妖也出于“难道不借助别人的作品我就不能发光了”的质疑,逐渐脱离了影评写作。但是当导演,哪怕编剧,对于绿妖来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那太复杂了”。
2012年11月,李霄峰第一次读到《少女哪吒》原著。读完小说,他说:“我看到这俩少女,当场就已经活灵活现地戳在这儿了。再加上人物关系非常紧密,这种紧密是从内到外的,是在心灵深处建立的关系。这已经解决了一个电影最重要的问题。”他当即决定,放下手头已经改到第九版的另一个剧本,筹拍《少女哪吒》。
李霄峰找到绿妖购买五年的小说改编权时,绿妖问他:“你想好了?真的要拍?”
在一分钱投资都没有的情况下,李霄峰开始为《少女哪吒》看景。所有人都劝他说李霄峰你不要发神经病,你是不是疯了? 恰在此时,《哪吒》的第一稿梗概在上海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拿到了最具创意项目奖。“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可以做,没有什么退路了。”李霄峰说,“有一个瞬间,我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空气呀,正在向我聚拢。”
3
2002年,李霄峰从比利时逃学回到北京,一时不敢告诉家人,也就没地方住。他找到了在“电影红茶坊”结识的老朋友冯睿。当时冯睿住在东直门的回迁房,一个月房租1800。李霄峰就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有天晚上两人喝酒谈心,冯睿说:“李霄峰有一天你做导演,我来给你当制片人。”
那时候冯睿的工作是《新京报》的电影记者,为一篇调查报道,冯睿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底子摸了一遍,报道发表后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对真实的限度产生了质疑,冯睿后来离开《新京报》,彻底进入电影业,做宣发和制片,自己接一些项目。他说:“说是站着挣钱趴着挣钱还是躺着挣钱,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是撅着挣钱,挺痛苦的。”

2014年春节,《少女哪吒》的试拍、建组、谈演员都已经完成,李霄峰忽然发现,管母亲借的40万快花光了。就像刚从比利时回来那天一样,他又找到了冯睿。冯睿想了想,建议他“停,先止损”。
但是冯睿知道,李霄峰是一个嘴上答应“好的好的,对对对”,但是绝对不听建议的人。根据冯睿在电影业的经验,《少女哪吒》有融资的先天缺陷:不够商业,新导演,没有明星——李霄峰坚持用符合角色设定的新人主演。冯睿告诉他:“你弄这么一个东西目的一定要明确。第一次拍电影,你是想要作品成立还是想要卖大钱?口碑和票房你可能只能选一个,这个片子它先天不具备票房的潜质,那我们干脆就放弃,就一心来扑口碑。多少导演第一部拍完就籍籍无名了,与其这样不如用作品来把你抬出来。”
“这些都是我,一个制片人的嘴脸,”冯睿说,“制片人会比较功利,比较现实。”
实际上,冯睿当时手上正进行着一个自己的项目。考虑一周后,他决定卖掉手头的项目,将钱挪过来投进《少女哪吒》。“第一,李霄峰是我朋友,还是投友谊嘛;第二有个承诺在那儿摆着——虽然是酒后的。”2014年初,冯睿正式进了《少女哪吒》剧组。
之后,就是无数人的钱在滚来滚去,拆了东墙补西墙,“今天找这个借40万,明天找那个借30万,先把前面这个还上”。最惨的时候账上没钱,而冯睿卖项目的资金一时还没到,他觉得快完蛋了,“如果停机的话,李霄峰会损失,因为他前面自己垫了100多万,我要给他停掉的话,这100多万就打水漂了,怎么办呢?——我就哭。”哭完,又有朋友的钱刚好到账,然后冯睿项目的买主也通情达理地打来了尾款。《少女哪吒》就是这样在2014年5月18日杀了青。杀青后半年,所有资金才到位,投资方共计9名。
愉悦的创作过程告一段落之后,真正焦虑的阶段就在眼前。
作为独立制作的《少女哪吒》,9个出品方里面没有一个懂发行。2015年春节,李霄峰拿出家藏的好酒,专门请发行界大佬们来吃饭,取经。大佬听完情况,有的说:“霄峰,你这个片先搁一阵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什么什么片,拍完以后搁了三年,现在发,成了!”还有的说,你们走节展啊,“长了一副得奖相儿”。李霄峰急了,整个项目开始了两年,拍完都快一年了,“我必须得有个交代”。
在冯睿看来,饭等于白请,好酒也是浪费,“还不如给我喝了。”但他也承认,这情况正常。“李霄峰是用最难的办法,办了一件最难的事儿。”看过样片的大发行公司直接跟李霄峰说:“我觉得你这电影不错,你下一部戏想拍什么?我愿意跟进,剧本给我看啊,行,再见。”
最后,《少女哪吒》的发行交给了上海的“鑫岳”,一家小型发行公司,老板是冯睿的朋友。冯睿找到他的时候,他说:“发行了那么多恐怖片,也该为真正的电影还还债了。”
更改了无数次发行策略,走了无数弯路后,《少女哪吒》的上映日期最终定在2015年7月11日,正处于“国产片保护月”。冯睿预见到票房很可能不佳是在上映前的两个月,但是真正感觉“要完蛋”,是在7月6日。
7月2日到19日,冯睿与李霄峰正在跑全国的院线,一家一家影院考察环境,见排片经理谈排期。7月6日,冯睿在重庆见到了7月10号的排片:《小时代》48场,从早上10点排到晚上11点,7个电影院全部如此。“我就知道完蛋了。”
冯睿说,这与他两三年前做第一部电影发行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个时候你还能影响到影院经理的排片,那时候片源少,哪怕是暑期档也没这么多的大鲨鱼…… 现在是一个死结,最终话语权在影院。”
在合肥的左岸影城,李霄峰走进排片经理的办公室,亲眼见到了挂在墙上的大图表,每周、每月的票房清清楚楚写在上面,影院经理直接对票房负责,他们的收入和影院绩效也直接挂钩。“他们的压力很大,权力也很大——他愿意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权力就会大,如果不愿意,他就是正正常常的一个影院经理。”
这家影城的排片经理告诉李霄峰,他们特别向总部申请了《少女哪吒》,一天排一场,包括周末。“我觉得我们作为电影人,应该为电影做点什么。”听见经理这么说,李霄峰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什么情况?一个排片经理跟我说他是电影人?我当时惊诧莫名,特别感动。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都不把自己当电影人,一个经理说他是电影人,把自己看成整个电影行业里的一部分,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比自己高的一个东西。”
当然,李霄峰也知道,这样的人是沙里淘金,少之又少。他和冯睿都很清楚,跑院线,见经理,其实不会得到任何正式有效的承诺——哪怕得到了也没用。冯睿的目标和出发只是,让李霄峰从一个不想跟观众交流的人,变得能够将同样的话在一个晚上面对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影院说三遍。“我觉得他在成长。他知道和观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会看到只有三四个人的一个场,这也是影院给的。他会明白在终端,面临的生态是怎样残酷。”
在《小时代》和《栀子花开》的夹击下,《少女哪吒》公布的排片率是百分之0.12,据冯睿说,实际排片率更低。首映那天,《哪吒》排了104场,而发出的拷贝是2012份。
李霄峰说,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要研究市场,要尊重市场。“我不认为这是个健康的市场。把这些事儿都说透了,就是金钱可以操纵一切,可以蹂躏一切。”
《少女哪吒》的总投资超过900万,票房在100万左右,加上卖版权等收入,总共亏损20%-30%。李霄峰说,9个投资人对他的要求都是“别亏太多”——所以,还凑合。但这与冯睿“打平”的期许有差距。目前他们在操作第二轮放映,准备进大学校园,尽量让投资人“再少亏一些”。同时,李霄峰重新开始修改筹拍《哪吒》时放下的剧本,那将是一部接近类型片的犯罪电影,制片人仍是冯睿。开拍日期初步设定在明年4月,“这取决于资金”。
顾小白和卫西谛都表示,这样的结果已算是不错。“品相很好。”卫西谛这样评价《少女哪吒》。新晋导演的处女作往往是小制作艺术片,能够做到品相好,业内有口碑,下一部的资金压力相对就会减小,“之后,也许会逐渐融入一些类型片元素,慢慢探索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也是常见的情况”。
《少女哪吒》讲述了两个少女的故事。 在影片中,一个女孩妥协于世俗生活,另一个选择自毁,点题的话由这个十几岁的女孩说出:“这个世上只有一种活法,那就是诚实地活着。”
像当年的LIAR一样,许多看完《少女哪吒》的电影爱好者写了观后感。李霄峰收到很多邮件,有些人告诉他,被这部电影打动到落泪,也有人感到恐惧,还有人讨厌它,甚至表示仇恨。回想为这部电影经历的一切,李霄峰承认,有些时候,他会“轻微地厌恶自己”,也有些时候,“我在想,可能都是我当年骂过的,这事现在要报应在我们身上了,挺有意思的。”
在杭州的一次免费放映会上,李霄峰遇到了一名主动发言的女观众。她盯着李霄峰说:“你给我讲讲,白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这电影,我没看懂。”李霄峰回答,你看不懂正常。女观众很生气,站起来拎着包走了。
事后很多朋友批评李霄峰处理得不好,劝他以后别这么直接,“多讲讲你创作的艰辛”。李霄峰说:“我是很真诚的,我是真的觉得没看懂特别正常,为什么一定要看懂呢?”
几天后,《少女哪吒》的一名文学策划给李霄峰发来一条微信说:“你本身就拍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人,不要指望别人会接受你。”
“白马”这个意象来自于李霄峰的另一名文学策划。那个女孩本是山东胜利油田一个造油厂的会计,生活在东营一个县城中。她读了《失败者之歌》,给李霄峰写邮件,李霄峰被她的文笔和文学素养吓着了。有一天,这个女孩早上8点钟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班,县城的主干道上全是拉煤的大货车,尘土飞扬。骑着骑着,她突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匹白马,就栓在电线杆子上。她停下车,看了很长时间,然后骑着车又走了。回到办公室她给李霄峰写了封信,描述那匹白马,诉说心中的难过。她写:“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上前去把它放了。”李霄峰回信,告诉她:“你是看到了生活中的奇迹。”
“在普通平常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枯燥里,忽然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东西,而且还美,这不是奇迹吗?”李霄峰说,“所以很多人问我白马是什么东西,我说你管。你看到它,不就够了吗?还要怎么样,难道你非要看到它撒欢着跑才高兴吗?”
在《少女哪吒》的结尾,终于有一个女孩走上前,解开了那条缰绳。
————————————
所有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题图为《少女哪吒》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