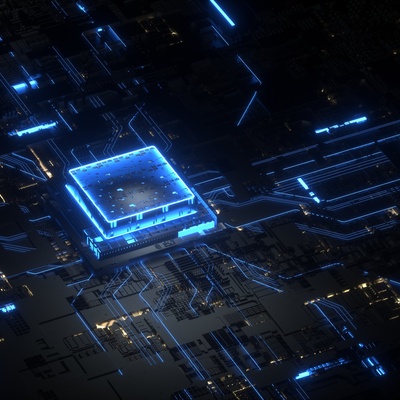采访:郭玉洁 吴筱燕
像很多人一样,欧宁曾拼命读书,想要离开令人绝望的家乡。那时他讨厌农村。他说,他所生长的粤西农村,基层干部腐败,民风剽悍,社会风气很坏。也像很多人一样,他终于考上大学,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年岁渐长,却有了“乡愁”。
2003年,欧宁开始做纪录片,他选定了城市里高密度、贫困人口多的社区,也就是“贫民窟”,分别是广州的三元里、北京的大栅栏。拍摄中,他看到许许多多人,他们无法在农村谋生,来到了城市。在他们的眼里,欧宁看到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父老乡亲,他们都是城市化进程中被抛弃的人,农村凋蔽的结果。
欧宁讲起自己的妹妹。初中毕业后,父母要妹妹放弃读书,在家帮忙干活,妹妹很愤怒,她跳上来村里招工的大巴,去了深圳宝安一家玩具厂。欧宁读大学时,妹妹在生产线上生产玩具。她每月工资450块,拿出250块给大哥。欧宁工作之后,给妹妹买了一个房子。但是他发现,即使妹妹有房子,有了不错的工作,农村出身还是让她自卑。在这个转型的社会中,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欧宁开始思考农村问题,他阅读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者的著作,他逐渐信服,城市化是导致今天中国种种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乡村建设是一条重要的道路。
那时,欧宁已经成为敏锐的艺术策展人、媒体人,他密切观察着中国社会,清晰地判断出时代的风潮。他去深圳读大学,因为当时深圳是中国开放的前沿;深圳没落时,他去了广州;2006年,他到北京,观察奥运会的筹备,做出了“大声展”、创办了《天南》杂志。然后,他又想搬到乡村。他说,他厌倦了当代艺术圈,有大量展览、大量资本,作品却和现实没有关系,更失去了曾经的批判品质。
碧山位于安徽黟县,它不如西递、宏村等地有名,原本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小村庄。欧宁决定搬回农村时,跑了很多地方,他觉得北方农村凋蔽萧瑟,污染严重,家乡粤西仍然令人绝望。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碧山,徽州一带纯朴温润,历史积淀深厚,他往返数次,买下一幢老房子,经过一番整理,他住了下来,并决定在碧山做一些事情,这些事他命名为“碧山计划”,而“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碧山共同体”。
在外界看来,“碧山计划”很像另一个欧宁的展览项目。美丽的徽州村落、古建筑的保护、“丰年祭”的形式、“共同体”的理念(它参考了世界各地的乌托邦实验)、欧宁的媒体网络,吸引了许多研究者、艺术家、记者,其中不少来自国外。
欧宁不这样认为,他说,“碧山计划”不是单纯的艺术项目,它是乡村建设,和全国各地乡建者的理念是一样的,只是他积累的资源都来自艺术界,所以只能从艺术开始,他希望随着“计划”的进行,有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人才加入,共同建设碧山。今年,好消息来了:南京先锋书店在一座徽州老宅里成立了“碧山书局”;一名大学生村官,在碧山村包了十八亩地,做有机农场。
困难仍然很多。2012年,第二届“丰年祭”被当地政府叫停。上一届村支部书记把他当作外来的有钱人,希望他出钱修路灯,包一条路的电费。有投资商买了两百亩地,想让欧宁做大型活动,这看似好消息,却有可能破坏“碧山计划”的初衷。外界的批评不断,说他不接地气。也有批评说,“碧山计划”吸引很多外来者去买老房子,抬高了房价,对于农村真正的问题,并未触及,反而加剧了。
对于这些声音,欧宁觉得,批评者不了解做乡村建设有多么困难。乡村建设的理念是让农村更像农村,注重生态、小农传统,这和当今城市化、资本化的政策和经济走向完全相反。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无法改变,乡村建设就举步维艰。碧山也是如此:土地污染严重,农民收入不高,只想卖地卖房子。这是整个乡建的困境,知识分子能做的极为有限。欧宁对此非常清楚。他说,梁漱溟和晏阳初同样面临不接地气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取得了胜利。知识分子在农村,不能把自己设想为拯救者,也不能神化农民,必须目标实际、行事谨慎,用行动说话。
欧宁的到来,毫无疑问搅动了碧山村。每个村民都知道欧宁老师的家——是村里唯一一家装空调的。但是他很少用,因为老房子四处漏风。他和妻子已经拿了居住证,儿子和母亲都接到了这里,这时他发现,徽州的房子真的是为家庭而建,有很大的公共空间。他家的大门敞开着,村民可以随意进入,有时他会为此苦恼,但他觉得为了融入农村生活,这是应该做的。他打算开始学习种田,并且改掉晚睡晚起的习惯,免得被村民瞧不起。
欧宁这样描述在碧山的生活:“在农村的生活非常好,每天去县城取个快件啊,买个菜啊,骑着我的摩托车,风吹着,两边是稻田,远远地看着山上飘着白云,山脚下有你自己的家。”

访谈:
一、
界面: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碧山计划”,你当时做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什么?
欧宁:首先,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是广东省湛江下面遂溪县一个小镇长大的。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考上遂溪县一中,一步一步从农村走出来,走到城市。我从小很讨厌农村,因为广东西部的农村,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基层干部很腐败,民风很剽悍,就算是今天,社会风气还很糟糕,吸白粉的人很多,每个村开赌场,村与村之间因为赌场的利益械斗……那个家乡令我很绝望,从小想离开,所以拼命读书,到了大学找到工作,慢慢在城市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年龄也差不多了,三十多岁了,开始出现乡愁了,过去事情的追念频繁起来,开始经常回老家。
到了2003年,我开始在城市里做纪录片。当时读了库哈斯的书,对城市研究感兴趣,选定的课题就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快速城市化形成的大城市里边高密度、贫困人口很多的社区,广州我选的三元里,北京我选的大栅栏。三元里本身就是个村,八十年代初广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起来,地不够,要向郊区扩展,把郊区的农地征作都市发展,保留了宅基地,结果农民盖了房子,把宅基地包起来,就成了都市村庄。实际上三元里跟农村破产有关,我的兴趣就从城市追到农村。我到北京拍大栅栏,很多在农村没办法谋生的人,他们来到首都,看了天安门之后,旁边有个很热闹的地方,就留下来了,那里也变成贫民窟一样。我在那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我的父老乡亲。
我是家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其中有一个妹妹,读到初中,广东开始流行香港电视,她就成天看电视,没怎么上学,考学不行。一个弟弟读到高中,看金庸小说,结果没考上大学。我在家像家长一样,负责安排弟弟妹妹,这两个就变成很大的难题。特别是我妹,我妹妹初中毕业之后,考上中专。我们家里从小就觉得女孩子不要读书了,在家里帮忙干活。她就很气愤,就反抗。结果有一天一辆大巴车到了我们家乡,来招工,她就“蹦”地一下,跳上车就走了,去了深圳宝安一个玩具厂工作。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妹妹工资才450块钱,她会把250块钱给我。等我毕业,找到工作之后,我买了一个房子给她,因为我觉得她对我帮助特别大。但是我发现即使有房子,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她还是很自卑,无法融入深圳的主流社会。我发现这个问题真的是……两个弟妹令我伤透脑筋。像我妹这样的农村少女多得是,她们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生产线。我妹还算不错了,她结了婚,在我给她的房子里住下来,可是她那种农村的根,没办法融入这个城市。我就觉得,哪怕是为了解决我家的问题,我得做点事情,帮他们建立自信,解决城乡差距。再加上我那时候看梁漱溟、晏阳初的书,就觉得这真是中国一条很重要的路,就做了。
还有一点,我自己不怕说,我这种知识分子的自觉还是很强的。我是八十年代成长的人,记得1987年,我第一次从湛江中学跑到上海,在外滩听着海关大楼的钟声,我就流泪了,我觉得我站在浦江边,跟三、四十年代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好像被钟声给接通了。这种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八十年代的后遗症。包括对结社的兴趣,包括所谓的历史感。为什么我做这些事情首先要了解民国的人,先找历史经验,梁漱溟、晏阳初的思想,这些都跟八十年代的成长经验有关系。
界面:那你为什么没有回到故乡去做这个事儿,而是选择了碧山?
欧宁:因为我现在对湛江的农村还是很失望。这两年还是经常回去,它还是没有变,当地基层政府基本上就烂掉了。“碧山计划”这种东西,在那个条件下,可能一下子就被浇灭了。另外就是,我们老家的民风很彪悍,粤西地区,跟韶关一样,是广东少数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所以农村人还在争夺生存空间,你要争夺生存空间就得很彪悍,所以民风没有碧山这边这么温和。其实我在这里有故乡认同感。我的“乡愁”不是针对具体地理的,我在台湾也有故乡认同。故乡认同不是一种过去的东西。
界面:所以到这儿是偶然的机会吗?
欧宁:不是偶然的,我从2005年开始选地方。我看过云南拉市海,那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在做艺术家驻留的地方,我去了江苏四川的农村,还去了兰考、定县、福建,去了好多地方。皖南农村我一直想来,但是没找到时间。2007年,我忙完“大声展”,想休息一下,顺便到这边看一下。结果一看就很喜欢,不断地来,一直到在这里找房子。
界面:这种喜欢是指你刚刚提到的民风吗?
欧宁:民风非常纯朴,另外徽州农村的历史资源,没有多少个地方能比。这里中国乡土的积淀非常深厚,可以挖掘的东西非常多。我也对研究很感兴趣,我觉得这边有很多课题可以做。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不是典型的中国农村,相对富裕了一点,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旅游业还可以,农业也没有凋蔽得很厉害,还有人在种地。再加上这边毕竟明清两代徽商文化影响,根还是很敦厚的。这是一个总体印象。至少我跟他们签协议,宅基地买卖本来不受法律保护,但是我也不怎么担心这里的人会毁约。我就是凭直觉吧,没有什么思辨支持。
界面:你去的其他地方都破坏得很严重吗?
欧宁:我去过河南,北方农村真的生存环境很恶劣,首先那个环境,风沙很大,绿化很少,经常都是灰尘,都是土路,卫生状况很糟糕,徽州农村你看还是很干净。中国农村千差万别,我们湛江老家很脏的,墟日,大家赶集完了之后,垃圾很多,很脏的。
艺术家见面再也不会彻夜长谈艺术,而是谈自己买了什么车,参加什么展览,作品拍卖多少钱,很没意思的。所以有点想逆着这个东西去做,所以到农村来。
二、
界面:那你是怎么想到用“碧山计划”来解决你的乡愁?
欧宁:“碧山计划”不是解决我的乡愁,我看了民国时期那些人的著作之后,像梁漱溟,实际上思考的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有些思路我觉得挺对的。中国的问题在农村。
做“碧山计划”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这是从民国那些人一直延续下来,包括温铁军,另外一个是当时我很厌倦我身处的当代艺术系统。我觉得当代艺术都在尝试各种展览,根据收藏家的趣味订制产品,跟现实没什么关系,而且2000年之后资本大量进入,艺术市场一下子起来,八十年代艺术的批判品质一下子消失了。艺术家见面再也不会彻夜长谈艺术,而是谈自己买了什么车,参加什么展览,作品拍卖多少钱,很没意思的,所以有点想逆着这个东西去做,所以到农村来。
在艺术这条线上,我做“碧山计划”的时候,还去了泰国清迈。两个艺术家在那里做了一个土地计划,在清迈郊区农村买一块地,大家都可以使用,请很多建筑师在那边盖房子,在艺术圈很有影响,等于把博物馆转移到田野上。这从反艺术建制的角度挺有创意的,但是从乡村建设的角度,它跟当地社区处于弱联系的状态,基本上有一点自己玩的感觉,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样。
界面:但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跟泰国、民国、台湾都不一样,你那时候应该也知道吧?
欧宁:我知道,完全知道。其实即便今天很多股力量在从事乡村建设,但是他们的高度都没有超过民国时期,因为有一个大的条件限制,民国时候,国民政府是支持的。梁漱溟说,他不依附政权,但是如果没有韩复渠,山东省主席,拿邹平一个县给他玩,他怎么可能?他的政治条件、空间是很大的,当代不可能。
但是,当代乡村建设一个好的地方是,我们的思想资源比以前多多了。说老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梁漱溟对农村的认识远远比不上温铁军,因为温铁军有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他把农村问题放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今天的思想资源,便利的互联网,让你的视野、学术工具,都比过去好得多,问题是你的政治条件比以前差。
界面:所以你才选择艺术这个方式来进行乡村建设吗?
欧宁:这个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和背景、资源,只有这个。假如我认识金融专家,生态专家,农村卫生,教育方面的,我不会去做艺术。这个过程得一步一步来,我原来的设想是先做文艺活动,慢慢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会有其他专业的人加入我的想法。但是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已经碰到政治瓶颈,所以这个想法就没那么完整的体现在现实中。
界面:政治瓶颈指的是什么?
欧宁:我们综观今天的乡建实践者,背后的理论都跟中央政府是背离的。乡建基本上是左派,主张社会公正,反对城镇化,反资本主义,这个和政府是矛盾的。还有就是,共产党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很清楚,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跟农民接触,那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话题有一点敏感。温铁军定县的实践是怎么失败的?很典型,跟当地政府搞不好。
还有一点,乡村主要的承担者是各级政府。基础建设、经济、农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还是靠各级政府。知识分子自发的这种行动,只能是一个补充。
今年过年,一帮无锡的中学生来我这儿,很有意思。他们关心社会,自己了解到碧山计划,就发起、组织了一个社团,来这边游学,做调查。他们提到一个问题,让我反省。他们说,你要真的想建设碧山村,为什么不去竞选村委书记?这个问题我一想,一个村委书记每天要干的那些事,我就觉得我干不来。首先,你必须得讲一些话吧,第二,修路,路灯,农业生产,养老保险,老百姓的娱乐生活,这个确实是干不来啊。
其实我们来这儿,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乡村治疗精英病。我很讨厌所谓的知识分子要拯救农村,也很讨厌把农民神化。
三、
界面:所谓“共同体”是你画的蓝图,并不是只有你来做的?
欧宁:对,共同体是一个愿景,是一个理论框架,但实际上在农村,建设主体还是农民,承担责任的也是政府。知识分子做的事情就是催化和点燃的作用。
界面:对于这一点,你这几年想法有变化吗?
欧宁:没有变化,其实我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农村建设的主体肯定是村民,知识分子从旁协助嘛,或者利用自己的资源,催化一下。共同体,理想来讲,外来的人和里边的人,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思想共同体是不可能的。
民国时期就算晏阳初、梁漱溟,都面临不接地气的问题。开始定县的人不是很喜欢晏阳初,晏阳初自己找贷款,影响了定县大概两百多家银号的生意,这些银号联合起来要把晏阳初赶出定县。定县和邹平开过两个乡村建设交流大会,座上没有一个农民,全是知识分子,梁漱溟就觉得很痛苦,都是知识分子呐喊,农民不动。农民为什么不动呢?因为梁漱溟说,要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做乡村建设,可是农民想减租,想要土地,你没有政治解决的能力,满足不了农民的根本需要,搔不到他的痒处啊。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做到了。毛泽东的方法就是革命,所以改良动员不了农民。你说可以分田地,农民马上跟着共产党走了。
界面:所以乡村建设是不是没有什么办法?
欧宁:不是,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目标设定得太高,就会陷入这样的困境。我觉得在农村做事情,就是从小处入手,目标定得小小的。但是我们有一种言说的癖好,行动背后需要一个理论依据,所以才会有“共同体”这样的计划。
今天面临的困境,不断重复民国时期的困境。在农村,我讲过嘛,农民和知识分子共处在农村的环境下,各有优缺点,不存在知识分子比村民高,也不存在村民比知识分子高。其实我们来这儿,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乡村治疗精英病,我需要农村,但是农民需不需要知识分子呢?要看知识分子能不能搔到他们的痒处。我很讨厌所谓的知识分子要拯救农村,也很讨厌把农民神化。
很多知识分子来农村的时候,把农民神化了,觉得农民很纯朴,其实不是的,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有毛病的。我们做各种事情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跟我们要钱,小到请村里的人表演,借一捆麦秆,都要收十块钱。当然这些要求也正常的。我想说的是,农民差异很大,有很纯朴的人,但也有一些很恶劣的东西,那种精明、趋利、狡猾,每个农村都有。
大家想像的农民,把农民神化了。关于碧山的争议里面,有个帖子特别可笑,说两个社会学家PK,谁更膜拜农民。其实农民的缺点真是挺多的,知识分子毛病也不少,就一个原则,都是人,就好了。
界面:你觉得跟农民打交道容易吗?
欧宁:我觉得挺容易的,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来这儿最大的感受是农民自尊心特别强,特别敏感,就像十年前我去新疆,汉维冲突没那么明显的时候,我感觉很放松,没有什么顾忌,但是前年去年再去,我就感觉自己不放松,总怕说话说错了。在农村也是一样的,农民很敏感,你在家里写邮件,农民走进来打招呼,你就要抬头跟他应付,晚一点,他都会觉得心里受伤。有时候来家里串门,你要送他走远了。你要是被他听到关门的声音,他会很敏感,是非常敏感的。
碧山村不是固化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村庄。所以我们来这里,是很谨慎的,警惕成为象牙塔。我家的门一直是开着的。
四、
界面:你已经决定在这里定居了吗?
欧宁:基本上定居了,我跟我老婆已经在这里拿了居住证,小孩在幼儿园,我把我弟弟的小孩也接过来了,刚上初中。我特别喜欢这里的生活,这个房子很舒服,公共空间很大,特别是把我妈、小孩接来,我才真正明白,徽派的房子为家庭设计的。在农村的生活非常好,每天去县城取个快件啊,买个菜啊,骑着我的摩托车,风吹着,两边是稻田,远远地看着山上飘着白云,山脚下有你自己的家,这种感觉。但就是来访的人太多了,时间很破碎。这里的饭局,应酬比北京还多,两个月的应酬超过北京半年。政府的,外来的,访问的,村民。推不掉。因为你的家在这里,所有人都知道。而且这里的交通、日常消费,都比北京贵。
我妈不喜欢这儿,跟我的想像完全相反。我以为她劳动大半辈子,在农村生活,会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她不喜欢。比如我说,妈你没事干,我给你找块地,我们一块种种菜吧。她说有没有搞错啊,我大半辈子我都在劳动,你还让我种地。另外她讲广东话,这里讲黟县话,交流有问题。这里买菜不方便,口味也不习惯,她从小海边生活,这里是山区,吃不到海鲜。我劝她去这边跳广场舞,去玩一下,她就不去。她做完家务就在家里待着,我妈很有意思的,她看《南方周末》。我妈是在村里的“毛泽东思想认字小组”学会的认字,所以她能看点书。有一次我们这边来了几个荷兰人,其中一个女孩是高罗佩的外孙女,我妈就很有兴趣,开始看高罗佩的书。
不是经常有人批评我们在这里开碧山书局,卖钱穆的书吗?但是农民难道就只配看《科学种田》吗?对不对?书店里经常有老人看一些很深的学术书,有个老人在看张柠研究乡村时间的书,还有老太太看《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我们对农民的想像太单一了。
界面:对于“碧山计划”,还有整个乡村建设的政治困境,你是怎么想的,能有什么对策吗?
欧宁:我对政治有些抱怨,但这是我来碧山必须要经历的。2012年我们的活动被取消,这种事情在这个国家是会发生的,这是一个现实,我不能因为这样跑掉。其实我有两次去美国的机会,我都没去。即便在深圳广州,我做的事情都碰到政治,我都没有抱怨,反而坚定了我的决心,不想离开中国。我觉得文化活动,是政府应该去做的,我们用民间力量做呢,它还查,这太没有道理了。
制度真的需要改善,但是我不主张用对抗的方式。我觉得在中国,你越对抗,你的空间就会越小,所以呢,我从来不对抗,我用建设的思路去做,在现在的政策条件下,拓展空间。所以,包括来碧山,政府取消活动我们也能理解,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照片反映中国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环境破坏,怵目惊心。但是这次碧山争议,我觉得外界的人没有看到我们的局限,没有看到我们在这边工作面临的约束,这种约束很多时候是政治上的。
乡村建设,那真是方方面面,不仅仅是文化。文化并不是农村急需的。最近几年我们也在解放思想,有时候自己的原则会约束自己,缺乏对现实灵活的应对。比如说,最近碧山村有人买了两百亩地,他们很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打算出钱让我们继续做大型活动,政府希望这个投资落地,就同意了。可是呢,我们因为有自己的原则,就有点不太敢用他的钱。因为那个地是农地,虽然后来改成建设用地,我们还是有点警惕,不知道这两百亩地要做什么。但是想想看,这种事情在中国农村到处都是。政府急于卖地,村民急于卖地,村民可是非常非常渴望大资本的进来,你拒绝这个发展商,会有另一个发展商,这个新的发展商说不定还不会跟我交流,至少这个投资人还听我们的意见。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能调整自己的原则,灵活对待这个现实,说不定后果比另外一个投资人来这儿要好一点儿。
碧山村不是固化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村庄。所以我们来这里,是很谨慎的,警惕成为象牙塔。我家的门一直是开着的。如果不是2012年政府取消了我们的活动,对我们公开活动的态度不明朗的话,过去两年会有大量和村民互动的活动出现,但是政府态度不明朗,所以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跟政府处理不好关系,可能你在这里住都不行。
艺术经常是扮演“士绅化”的帮凶和先驱。798,旧城改造,都是艺术家先过去,搞展览,资本进入,人口洗牌,这点我太清楚了。
五、
界面:回到和村民的关系。你毕竟是带着乡村建设的理念,想要发生影响,受到这么多限制,还能怎么行动呢?
欧宁:我觉得所谓融入当地文化,靠话语是不行的。我从来没跟村民说过大道理,一方面他们听不懂,他们也不感兴趣,在农村做事情,你想干什么,先做个样本出来,村民看着,亲身体验过,他觉得好,就会模仿,会跟风。所以农村工作,想发生影响,就多行动,做示范。就像老房子,农民不喜欢老房子,他们喜欢住新楼,我们来了之后,也没有说你们要做历史保护。我们把房子修好,欢迎他们来串门,他们一看,原来乱糟糟脏兮兮的房子,被我们整理成这样,也挺好。
还有,他们觉得城市里来的人都会善待老房子,观念就会有点变化。但是呢,这个他们也模仿不了,因为村民并没有那么多资本来修老房子,他们只是想用更高的价格卖掉。不过至少我们住下来,对老房子价值的认识,是产生了影响的。
另外,书店在这里,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书店就是让农民跟文化有相遇的机会,就凭这点,已经很有意义,至于影响能深入到什么程度,不是短时间产生的,这是细水长流的过程。
界面:你觉得你现在接地气了吗?
欧宁:我觉得我还是不够接地气,所以今年我开始想种地。还有就是生活作息方面,要起得更早一点。我刚来的时候,把北京的习惯带过来了,晚上工作,第二天起得很晚。这在农村被人瞧不起的。我还要尽快学会黟县话。我们深知,知识分子来农村最可怕的就是,变成自己的象牙塔,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警惕的,但是能不能做到,这可不是一两下子的,需要很长时间。
反正我们来了以后,没有破坏村庄,村民还能让我们住下去,我们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你看在丽江,很多地方,特别是艺术家社区,到农村盖工作室,他们去的时候,没想着处理跟当地村民的关系。我刚去过景德镇三堡村,一个艺术家搞了一个窑,在那儿住,那个村没什么村民,他面对的现实很简单,只要搞自己的艺术就行了。“碧山计划”可是从一开始就确定我们要处理跟2900多个村民的关系。
界面:种地可能满关键的,这是农民的知识,农民也会真正把你当自己人。
欧宁:是的。
界面:“碧山计划”传播得还是很广,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效应,让很多城里人,有乡愁情绪的人愿意回到村庄,觉得村里生活也挺好的?
欧宁:这个效应很大,但是这个效应也是我们担心的。可见我们担心的事情有多少。我不是老说一个词吗,“士绅化”,农民不喜欢老房子,外面的人喜欢,农民想要搬出去,外地人想要进来。最后,人口洗牌,这就叫士绅化,主体转化了。这个东西,在学理上我很警惕的,我很怕被人说是士绅化,但是士绅化是一个市场现实,农民特别欢迎外面人来买房子,出很高的价格,这样他们拿着钱可以到县城里买公寓,或者在本村盖新房子,一个愿意卖,一个愿意买,这是市场现实。所以士绅化、城市化是波及全国的现实。不仅在农村,在老的历史街区也这样,老的原住民冬天要排队到外面上厕所,七、八口人挤在很小的房子里面,一有火灾,消防车都开不进去,这些人拼命想离开。外面的人想买胡同的老房子,这就是双向的行为。所谓旧城改造,都是士绅化。艺术经常是扮演士绅化的帮凶和先驱。798啊,旧城改造,都是艺术家先过去,搞展览,资本进入,人口洗牌,这点我太清楚了。
新的一代对居住环境,怎么样舒适,和老一辈的想法不一样了。所以说保护,不是说我要保护老房子,而是把整个环境改变了。
界面: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吗?
欧宁:下一步我得找个工作。原来我在这儿编《天南》,拿固定工资,不用上班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现在搬回农村,门槛还是挺高的,如果你的工作是不自由的,你要上班,你就回不来。现在动员年轻人返乡,年轻人返乡干吗?你没有工作。我得找个事情干,因为积蓄很快就见底了。
界面:那碧山的事儿下一步是什么?
欧宁:现在做一些活动,日常化的,包括村民动员的活动。比如说7月我们做了村民的读书会,我觉得就挺好的。九零后的一个小孩,读《白虎通义》,讲乡射礼,我觉得特别好。在民国时,晏阳初也做啊,这个年轻人对经典的解读,太棒了。下一步我们请村里的知识分子,退休的老教师,做读书会,日常、小型的,教农民上网,在淘宝卖东西。
村里的老年人协会非常好,在村里还挺活跃的,村里的广场舞就是他们组织的,都是些退休的公务员、老师,跟民政局有关系,跟民政局申请了一点钱,买了个音响,现在变成每天都跳到十点钟,特别活跃。中间出现了一些风流韵事,挺有意思的。一个老先生出现了桃色新闻,可以写成小说,农村的生活真是非常有趣。我相信这个老先生突然变得这么浪漫和勇敢,跟我们来这里也有关系。这个老年人是我们早期进入这个村庄的一把钥匙。我们来了之后,他天天都穿西装,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室,镇委书记看他这么热衷文化,就给他买了个数码相机,每天都拍碧山村。他认识了一个妇女之后,就经常在那个妇女上山采茶的时候给她拍照去,这事情闹得很大,全村都知道。那个老年人威信扫地。
老年人协会比较容易打交道,他们就是当代意义的乡绅,而且比较热心村里的事,没有利益诉求。村委会不一样,全是利益,他们要修路灯,要我和左靖认捐(注:左靖,策展人,碧山计划的创始人之一)。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碧山村要修路灯了,希望左靖和欧宁一人负责一条路的电费,还不停游说我把村委会公共的一个房子买下来,因为他可以套现嘛。但现在刚完成选举换届,新的这个村支书比较好。
中国官场上的流动,有一点影响了中国的农村。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的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到农村来,基层历练变成一种生存选择,其实村官很难考的,很多村官是曲线的自我发展,不是真的喜欢农村工作,但是有个别真的很棒,我们就碰到了。这个村官是南屏村的,但是因为她在我们2011年、2012年活动的时候是志愿者,所以她就在碧山这边创业,办村官菜园,帮农民卖农产品,做得很好。我们帮她在碧山政府流转了十八亩地,她现在在做有机农场。她是屯溪人,一个女孩子,会讲当地话,跟村民交流特别好,村民特别信赖她。这个人,我们甚至希望她能当上村委书记,但是不太可能,因为那是行政系统决定的。现在的碧山村委书记,我对他还是挺有期待的,他是大专程度,也没有那么赤裸裸的,直接的逐利,对我们做的事情也能理解。我们很幸运,在这里碰到的基层干部,除了原来的碧山村委书记不太好,碧阳的书记,黟县县委书记,都非常出色,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问:上次和周韵吵架,对你有什么影响吗?(编者注:今年七月,哈佛博士生周韵在网上发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随后欧宁和她展开笔战。)
欧宁:对我的影响,就是来的人多得不得了。周韵她提的那些问题,是对我不了解,如果她有机会看一篇我关于农村的文章,她就知道她指出的那些问题我都有意识到。我最难忍受的就是她歪曲我的话,把我的话说成相反的,来支持她的质疑。我受不了这个。特别是路灯和星星那个,我是最关注路灯的,她居然给人的印象是我想看星星。但她这个争议导致了媒体的关注,是很好的。后来变成范围更广的关于乡村建设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我跟她的争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实际上关注乡村建设的人不算多,虽然已经挺热的了,但是关注的人还是不够多。
界面:好像乡村建设有自己的圈子,我看一些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我觉得已经写的很好了,很有说服力,但是对于外界,对整个社会来说,就好像另外一个世界。
欧宁:乡建这个圈子,内部的讨论很学术,公众层面的关注比较少。但是乡建这个题目是很牵动人心的,只要触及这个题目,都要抢占道德高地。
界面:为什么说是道德高地?
欧宁:关心农村啊,把农村想像为一个等待拯救的地区,社会良心的凝聚地,所以就出现社会学家PK谁更膜拜农民的笑话。
乡村建设也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实践者,其实很重要的是,力量要整合起来。做生态的也好,金融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教育的也好,应该整合力量。我们在视觉推广上面是有优点的,但我们也有缺点。
我认为“碧山计划”肯定是乡村建设,我一开始借用的思想资源全是这个。
——————————————————————————————————————
郭玉洁,记者,作家。她正在写的新书,是关于台湾社会运动和青年一代的观察。
吴筱燕,学者,就职于上海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