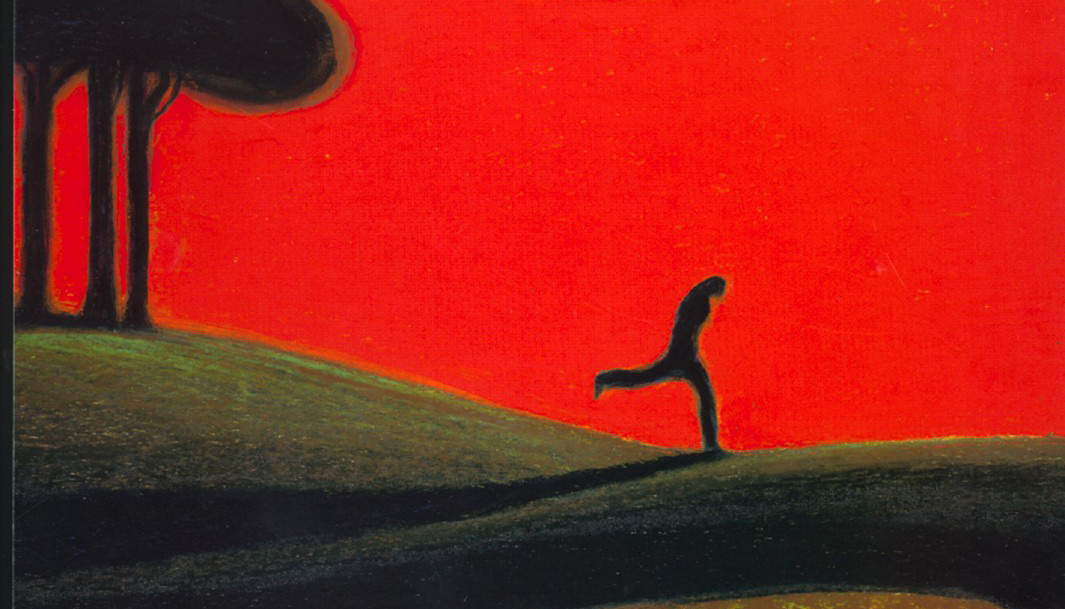因为打了一个哈欠,工厂的机器砸断了向阳的两根手指,没买保险,老板又不愿赔钱,向阳那次就找到我表弟,请我表弟想想办法。我表弟那时候在派出所做辅警,但派出所是我们那里的派出所,砸断向阳手指的工厂在杭州。我表弟就只好给我打来了电话。应该是从四岁开始,他就习惯了遇到问题找我想办法。但向阳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这事情我就忘了。两年过去,一天晚上,向阳的老婆没回家,电话打不通,向阳找了一圈找不到,最后又找到我表弟。我表弟把向阳老婆的身份证号码敲到电脑里,得到的结论是她已经到了隔壁县的一家宾馆。向阳和向阳的叔叔向阳的婶婶向阳的堂姐一起进了宾馆,我表弟停在外面抽烟。
开门的就是那个结巴,他就穿了一个裤衩,一看到向阳一家人,吓得站都站不住了,表弟说,向阳太老实了,就让那个结巴走了,揍也没揍,一家人领着老婆就回来了。
然后什么情况?我问。
就坐我车回来的,回来说饿了两个人就去喝豆腐脑了,表弟拿下巴指了指车窗外,就是这家,一下车就去喝了。
汽车放慢了速度,来到了路口,表弟拐弯,汽车驶进村子,掀起尘土,我关了车窗。秋天的村子是灰色的,路边尽是草垛,野狗身上的毛是炸开的,水坑里布满了绿色的水,好像那是几十年前的雨水。自从姥爷姥姥搬进城里,这村子十几年我没来过了。我妈妈我舅舅他们就在这里长大。表弟把车停在路边,往姥姥家的老房子走去。那房子也十几年没人进去了,钥匙是铜色的,表面光滑,像是一个什么纪念品。
我们把车停在老房子门口,门上的黑漆已经掉光了,表弟拧开锁,抽出生锈的门栓,推开门走进去。那房子是1988年建的,马上三十年了。八间房,当时是巨大的工程,早期只有一个院子,后来一分为二,中间上了一堵墙,那寓意是我的两个舅舅一人一半。一棵银杏树(我们那里称之为白果树)留在那里,地上满是落叶,看起来不止是今年的。院子里本来铺了水泥,也早就裂开了,房子黑乎乎的,我往里看,墙壁是黄色,满是蛛网,地上也尽是垃圾。我走到房间门口,没进去,望着院子,想起小时候过节来这里,一直觉得那院子太大了,几乎是广袤的。现在几步就能走到门口。
怎么样?表弟点起一根烟,看着我。他扬起头往空中吐烟。他不说话,等我下判断。他对我有一种服从感,似乎是小时形成的习惯。他自小是个没什么想法的人,似乎比普通的小孩更为天真,到了二十几岁仍然容易轻信他人。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就经常来找我拿意见——他并不去问他的父亲——和我们那里的大部分父亲一样,我舅舅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只有单纯的殴打。有一次因为成绩太差,班主任要求舅舅去学校,我表弟为了避免可预见的拳脚,不得不敲开了姥爷的抽屉,携带了一笔现金,自我们县的汽车站扬长而去。他盲目地登上了一辆大巴车,在列车到达浙江省金华市时,因为目光中暴露的胆怯和迷茫而被司机识破,将电话打回了我们县里。接回儿子,我的舅舅自那次终止了对我表弟的殴打,带他好好地吃了一顿。我也参与了那次吃席。你也算去过南方了。在饭桌上,我对表弟说。表弟应该是立即脸红了。
表弟把烟头扔到地上,拿前脚掌踩住,搓了几下。他不说话,等着我下结论。我为了体现作为一位表哥的判断力,沉吟了一会儿,环视了一下院子,说,走吧。
在那院子我完成了童年的回忆,并没其他什么看法。可以,锁门时,我向表弟补充了一句。
我们上了车,调转车头,开回村口的马路,来到乡里的卫生所,将钥匙送回舅妈那里。舅妈在卫生所门诊室唯一的医生,我每次见到她都见到她正在给发烧的小孩子扎针。那些小孩子扎着扎着针就长成了青年,结婚生下小孩子,小孩子发烧,就将他们抱到卫生所,继续交到我舅妈的手上。我舅妈就拿棉球沾了酒精,接着转身扬起了针管。
我们跟舅妈告别,出门上了马路。马路将村子一分为二,我们到了马路的另一边。进了医院的大楼,穿过楼梯,走上楼顶。虽然只是四层楼,但楼顶似乎比楼下更为昏黄。
表弟又点了一根烟。鸭厂真是赚钱,表弟指着远处说,那鸭子,你可不知道,一个月就长起来了,宰了就拔毛,去掉内脏,把脖子往肚子里一塞,接着就装塑料袋,一车一车往外送。
送哪去?我问。
卖出去,我也不知道卖去哪了,估计卖给南方了。一车一车往外卖,你不知道那个血水,那血水要是淌到河里,河肯定成红的了。
那它流到哪了?我问。
不知道,地底下吧。红旗肯定有办法。红旗太硬了,什么办法都有,你还记得海军吧,海军就是给他开车的。海军后来傻逼了,吸毒,吸完毒就揍人,有一回吸完了往街上跑,抱着人就啃,咬掉了半个耳朵,抓了,找了红旗,红旗也给他办出来了。上回我见他还是去年,他在家戒毒,他爸爸把他关在家里,狗一样关屋里,就留一个栅栏门,锁着,吃饭拉屎都在屋里,我去找他,他趴在门上,手里拿了个导航仪,说他到成都了,等回了山东再跟我说话,真傻逼。
他怎么到成都了?我没听懂。
关在屋里关疯了,他拿着导航仪说把全国都走了一遍,最远都走到云南了,真傻逼。表弟往半空吐烟圈。
我望着远处的空中,空中炊烟袅袅,炊烟下是黄褐色的农田,农田中间是一片白色的围墙,蓝色的厂房端坐在围墙当中,几块楼宇之间是一片空地,空地上布满卡车。一群人从一座楼里走出来,像一阵树叶北风刮走,刮进了另一座楼。这些人是下班了吗?我问。
下班吃饭,食堂和宿舍是一个楼,厂房是另一个楼。吃完还有夜班上。表弟说,那厂子工人得有几百个,南方来了一批,本地招了一批。向阳和向阳老婆都是那时候招工进去的,就那个结巴,结巴就是南方来的那批。
表弟将第二个烟头踩死在楼顶,走下楼。在楼梯里我们遇到了我的舅舅。你们吃饭了吗?我舅舅在走廊里问。自从我知道这个人是我舅舅他就在这个医院上班了,我舅舅推开办公室的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摆了洗脸盆的木架、一组黑色的沙发、一张中国地图、一个拖把、一个扫帚。除了中国地图,其他东西都在地上,它们都被白色的油漆画了线,围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新规定,规定什么东西放在什么位置,我舅舅说着往椅子上坐下去,鼓起两腮,在他的办公桌上吹了几下,才把两肘支上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
回来几天了,刚才去老房子看了看。
那里又什么好看的。我舅舅说。
那院子反正闲着,你看要是搞个机器,我说着,看了一眼我表弟,表弟用一半的脸笑着,另一半的脸不动神色。他并不看他的父亲。要是弄个机器,我接着看着我的舅舅,说,生产塑料袋,卖给那个鸭厂,你觉得行不行?
说完我又看了看我的表弟。我表弟正在看地面。当天中午本来我正在睡觉,他来找我,他说他昨晚喝酒时听说有一款机器,几万块,可以生产塑料袋,又跟我说起鸭厂的事情,他打听到鸭厂的塑料袋是从外地批发的,他想如果他在本地生产,供给鸭厂,一个袋子赚三分钱,一个月就能赚上万块。
生产塑料袋有污染,我舅舅又抬起胳膊,往他的桌面上吹了几口气,那生意要有那么容易,别人早干了。我舅舅退伍以后就在医院工作,但他的主业似乎是喝酒,十几年前也做过几次生意,但那些生意全是糊涂账,起初有人问他,问不出结果,后来也没人再问。他也从来不谈那些事情,他的肚子越来越大,现在常常就坐在他办公桌的椅子上。
我和表弟下了楼,开动汽车,驶出医院,沿马路向南开,路过了鸭厂,鸭厂的墙上贴着瓷砖,瓷砖上是烫金的招牌。
开进去看看,我说。
表弟将车头拐进工厂大门,我们沿着主干道往里走,左侧是一栋楼,没有阳台,窗户上挂满了衣服,花花绿绿。向阳是住这里吗?
是的,表弟说,他老婆也住这里,还有结巴也住这里。说完表弟笑着往外哼出一口气。
厂房里有微微的轰鸣,工人已经吃了晚饭继续上班了,表弟调转了车头,一个加速,我们开出了鸭厂,回到马路上,太阳已经没了,夜晚来了,空中开始隐隐出现黑色的颗粒。
汽车路过豆腐脑摊,火炉闪着光,火炉子上方的空气发生了弯曲。我和表弟下了车,要了两碗豆腐脑。豆腐脑支在火炉上一口黑色的缸里,摊主是个老妇女,她拿一个铁勺把白色的脑花撇上来,一块一块地,脑花堆在碗里,她又将粉条浇上去。隔着长桌,我和表弟面对面坐在马扎上,不时扬手驱赶空中的苍蝇。
有污染就算了,你再看看还有什么别的生意。我在黑暗里说。
好。表弟说着已经喝完了,他又点起一根烟。
等我也喝完了豆腐脑,我和表弟回了卫生所,告别了舅妈,调转车头往城里开。我姥姥家去城里的那条路是笔直的十公里,一直没有路灯。路的两侧是村落和农田,路上坑坑洼洼,表弟将他的车开得飞快,在一些地方汽车不免因此高低起伏。车灯照在黑色的空气里,空气里一片浑浊。
—— 完 ——
题图来自电影《L'Humanite》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