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正午的一封信
亲爱的正午:
六月底某个傍晚,我冒出了一个念头,打算离开北京。那时我们刚从西南地区回京,做了几场活动,精疲力尽。旅行的最后几日,我们留宿在贵州一座山上。那山名叫海龙囤,七百多年前是个土司的城堡,毁于明朝万历年间。山顶很安静,风景宜人,夜晚像睡在露天野地,我想一直睡在那儿,但谁都知道,那样的地方是睡不长久的。
在海龙囤,我认识了一个考古队长李飞。他跟我年纪相当,齐肩长发,由于常年田野,皮肤很黑,像个混了些时日的摇滚歌手。他讲了他经历的很多考古趣闻。其中一例,说的是十年前,红水河要修一座水电站,会淹没河两岸的荒地,包括一片布依族的坟场。他跟着考古队驻扎在坟地,大约有四五百座坟头。他们搭了帐篷,夜来无事,就在帐篷里打牌,输的人从身上拔一根毛,放在小瓶子里。考古队都是男人,方圆没有人烟。白天很热,他们就脱光了在河里游泳。夜里也讲鬼故事,旁边就是坟头,讲到大家害怕,晚上不敢上厕所,身子一歪,帐篷帆布掀起来,直接往外面尿。
饭桌上,李飞还讲了一些开棺古尸的故事,吓人,却比盗墓笔记真实。我知道,这么说容易让人把考古这件事浪漫化、冒险化。但李飞其实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学者。他带领考古队在这座山上扎了两年多,走遍了每个角落,如今这里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我答应朋友,要写写李飞的故事,但自从回到北京,它就搁置了。因为我冒出了那个离开北京的念头。
七月初的一天,我打开电脑上的地图,定位显示,我正在北京常营。
如果你选择卫星模式,再点击右下角的减号,世界开始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展开。你先看见楼群的一个个小阴影,西边没有绿色,有浮云遮盖,那是北京城。然后继续扩大,出现了山脉,渤海湾,土灰色的华北平原。拉动地图往南,中国越来越绿,在卫星模式下,这是一片没有地名的土地,你只能看见颜色的变化,偶尔会有湖泊、山峦的沟壑,不太清晰的黄河长江。你随意在上面标上一个大头针,地图告诉你,那是“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鲍沟镇”。你从未听说过那个镇子,你被它西边那个大湖泊吸引。距离613公里,开车7小时55分钟。你想试试,但瞬间又打消了念头,有什么好去的?可是,为什么不呢?
第二天上午,我打开电脑,几乎是无意识地,我再次点击了地图。这次我继续往南,颜色鲜绿,大约在长江以南的山区。大头针显示,那是“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汀溪乡”,1253公里,开车17小时。我想,如果去那里,我得带着我的狗,它可坐不了那么久的车,路上也没有旅馆给狗提供住宿。
接下来的事一发不可收拾。我查阅了中国哪些地方能让宠物入住。也许我该短租个房子,也许不用,我应该开着车,带着狗,一路往南。或者,我干脆消失算了。
某个念头一旦生根发芽,如果不及时除掉,很容易滋长。那天傍晚,我和朋友喝了一顿酒。朋友那时已辞职,无事可做,除了阅读便是喝酒。我们都为我的新念头感到惊喜,兴奋。“消失。听起来很牛逼。”他说。
“如果一个人彻底消失,就跟死了一样。”我说。
“海龙囤的故事你还写吗?”
“写。”我说,“会写的。”
拖稿的人都这么说。我们再喝了几瓶,散了。
回家路上,我用手机查了查银行存款,如果我足够节省,再活个两年应该没问题。然后再次无意识地,我又点开了地图。就是这样,生活的出轨总是先从脑子里开始的。
跟很多人比,我有先天的出逃条件。没结婚,没孩子,只有一条老狗。我也没什么事业心,虽说钱很重要,但不至于迷恋。在北京,我有一些朋友,但如果我离开这儿,几个月后,就只是个名字而已。朋友们可能不会这么想,但你最好对生活别抱太高期望。
接下来好几天,我都在做这场听起来很牛逼的“白日梦”,我把它叫做“地图上的旅行”:大头针指到哪里,就让思绪飘到哪里。我选了几个地方,详细计划了行车路线,甚至去一些租赁网站,找了找当地的出租屋。我列了个单子,写上我可能会带上路的东西:一条狗,几本书,一箱啤酒,笔记本电脑。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活着没那么多必需品。
工作照常进行,但不太顺利。大多数记者和我一样,都喜欢拖稿。我们从存稿里找了几篇出来,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比开天窗强。叶三那时正在进行一场真实的旅行,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晃荡采访。当她终于回到北京后,我告诉她,我打算离开这儿。
“离开?什么意思?”她说,“永远离开吗?”
我说是的,暂时不想回来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那你的房子还接着租吗?”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会的。”我最后说,“否则我那么多东西放哪里。”
* * *
我上次这么干,是2009年夏天。那次我们有三个人一起上路。我当时刚从一家杂志辞职,无所事事。忘了是谁提出来的,说我们可以租个车,从北京一直往西。也许去新疆,也许甘肃。艾伦是个美籍华裔摄影师,胖子,我们前一年在汶川大地震采访时认识。再加上我的朋友崔愤,她是我认识的最佳旅行拍档。
车是我租的。十年前还在重庆时我就考了驾照,但除了在驾校开过一辆破吉普,我压根儿就没摸过其他方向盘。不过,艾伦是美国人,轮胎上长大的。
我们找了个靠谱的租车行,看了一圈,挑了最便宜的,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艾伦说,选手动挡,这才是男人的乐趣。我没什么经验,事后看来这也许是我们犯下的第一个错。
临行前那个早晨,彭博社一个美国摄影师跳进了车里。我们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知道先去呼和浩特、包头,然后往南去榆林。那哥们打算在包头提前下车,打道回京。余下的路我们三个继续走,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一路往西。
第一天,两个摄影师轮换开车,我和崔愤坐在后座,大家都很兴奋。在呼和浩特,我们随便找了个宾馆歇了一夜,吃了顿烧烤大排档。艾伦吃着烤羊肉串,问我,明天你开车?
“什么?”我很紧张。
大家都很清楚,这一路不可能只有他一个司机。等彭博社那哥们一走,我迟早是要坐上驾驶位的。也许我隐隐有种期待,希望艾伦能渐渐明白,相对于他一个人疲劳驾驶,让我开车的风险可能更大。
第二天上午,我们前往包头。出发没多久,艾伦停在一个服务区,加满了油。然后他下了车,打开后座门,对我说,“该你了。”他建议我先在服务区熟悉熟悉。这里很宽敞,我开着车绕了几圈,似乎没什么问题。最后他跳上车,说,走吧。
刚驶出服务区没多久,我们就碰上了公路维修封锁,只留出一条车道。我小心翼翼开过维修路段,以很慢的速度缓缓前行。接着,我就撞上了右前方的一辆大卡车。
几年后回想那个时刻,我仍会脚抖。但那时年轻气盛,不明白这有多危险,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人。没有人受伤,已经很幸运。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打电话等待救援。天气很好,蓝天白云,太阳很烈。因为受到惊吓,所有人都不说话。几个人站在路边的栏杆处,抽着烟,守着那辆白色的桑塔纳,它看起来也像受到了惊吓。
现在回忆这次出行,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像一场没有目标的梦游。
救援车把桑塔纳拉到包头,直接送到了一个指定修理厂。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异的悖论:警察开不了责任认定书,因为必须先“车损物价鉴定”。鉴定人员说,修理厂可以直接定价。修理厂说,必须保险公司来定损。保险公司说,如果要定损,必须得在这个修理厂修车。但租车行的人在电话里明确表示:必须先拿到责任认定书,而且不能在这里修,得去4S店。
这个怪圈有点发晕。总之,那辆车就永远地停在了修理厂,无法取出,也无法修理。
我们在包头找了家连锁酒店,一天一天续费,不知何时到头。第三天,彭博社摄影师走了。我们开始在包头晃来晃去,每天失神地在街上漫走,坐在市区广场上聊天。到最后,我觉得生活似乎就该是这样。我们雄心勃勃要走遍西部,结果第二天就困在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里,我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干不了。什么都不用干,就那么晃着。
我已不记得那几天的生活细节,也许根本不重要。不过,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个内蒙古的六月,一切都很模糊,就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突然硬插了一段暧昧不清的经历。自此,包头对我来说,成了一个没有重力的城市,我总觉得自己是飘在那里的,而且我似乎很喜欢就那么飘着,虽然谁都知道,那样的状态不会长久。
几天后,北京的朋友帮我们在包头找了熟人,顺利解决了车的修理问题。我们和内蒙古人喝了一顿酒,大醉一场,醒来后回到现实世界,乘坐长途大巴返回北京。没过多久,艾伦回了美国。
三个月后,因为撰写一本旅行指南,我独自去了青海。那次旅行目标非常明确,我每天都在坐车,每天都要换个旅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青海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我爬了很多山,去了很多偏僻的小镇。可是,我再也没找回在包头的那种感觉。
* * *
进入八月,我的白日梦,我地图上的旅行,越来越令人迷恋。有时我开始出现幻觉,仿佛自己正在一个陌生的小城,漫无目的,活着或死了。
我喝酒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喝过的所有酒瓶,排列在阳台,就像一次次意志上的胜利。朋友说,得多喝,常喝,因为也许哪一天我就突然消失了。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说的是他认识的一个人。那人住在中国的某个小城,是个公务员,每到周末,他就去加油站,把油箱加满,然后开着车一路往西。他没有目的地,开到哪里算哪里,最远曾到过西安。在周一上班之前,他总是回到小城。周末就是他消失的时刻。
我没有周末。我周末就躲在家里,哪里也不想去。一到周末,到处都是人。年轻的夫妇推着婴儿车,蝗虫般挤满了商场。购物广场前面的空地上,永远都是老人与小孩。偶尔,我也会进一趟城。在下班高峰期,我走到常营地铁站,乘坐六号线。那时的地铁很空,所有人都在赶回家,你只需随便跳上一个反方向的列车。我在呼家楼换乘十号线,在亮马桥下车,然后沿着河边,一直往西。路的尽头有个酒吧,箭厂啤酒,那里适合约人聊天,也可以独自发呆,做做白日梦。
八月中旬,我还没有动笔写海龙囤的故事。仔细想想,写作其实也没那么重要。这个借口不错。格雷厄姆·格林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
噢,这有什么难的。只需随便跳上一辆车,就能逃避癫狂。
九月天气转凉,有风刮过,我找到了一条逃避之路。我们有三个人,轮流做主编。听起来有点可笑,是吧,因为没有谁喜欢在这个位置上停留太久。
我开始在深夜出门。有时凌晨两点,三点,我带上那条老狗,在常营散步。它已完全没有年轻时的活力,步履蹒跚,走一步,停一步,再看我一眼。我常碰到另外两个遛狗的年轻人。你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在午夜散步。我们偶尔打打招呼,很少说什么,每个夜行的人都像在梦游。
有时我能看见星星。一盏坏了的路灯,在黑夜中不停闪烁,路灯下有一把长椅。我喜欢带着狗坐在那里。世界很安静,我不再看手机,不再想工作。闭上眼睛,我在脑子里展开一幅地图,想象自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刻,让所有的写作都见鬼去。你只想逃走,逃到海底去。谜底就在那儿。
你最好带上一瓶酒,一饮而尽。
谢丁
2016.9.23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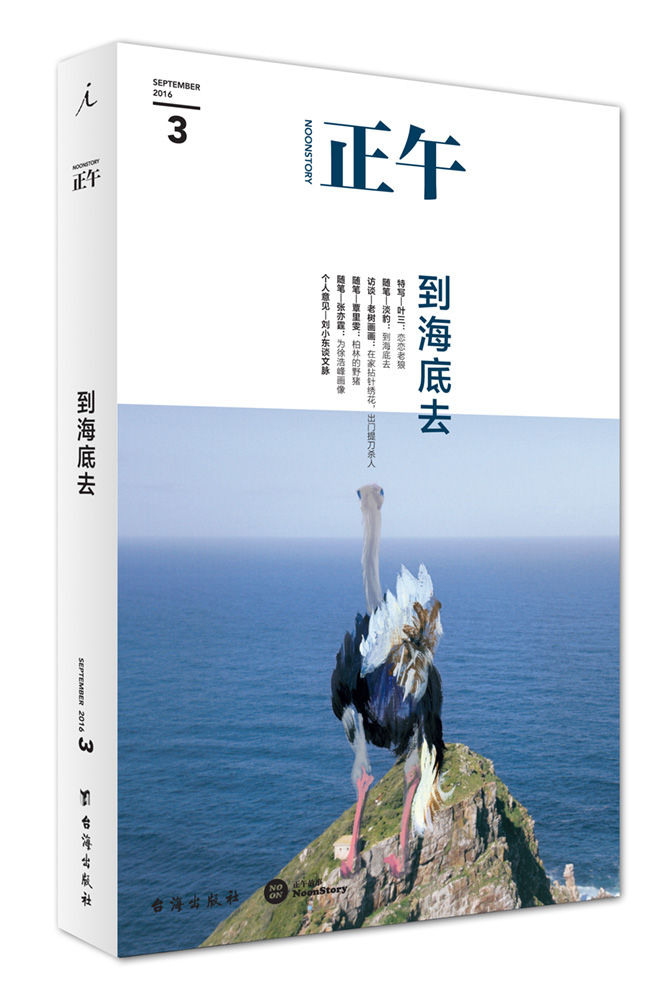
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