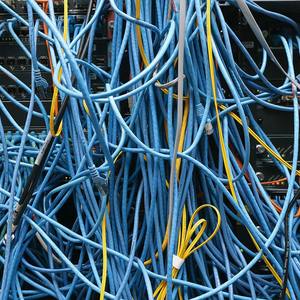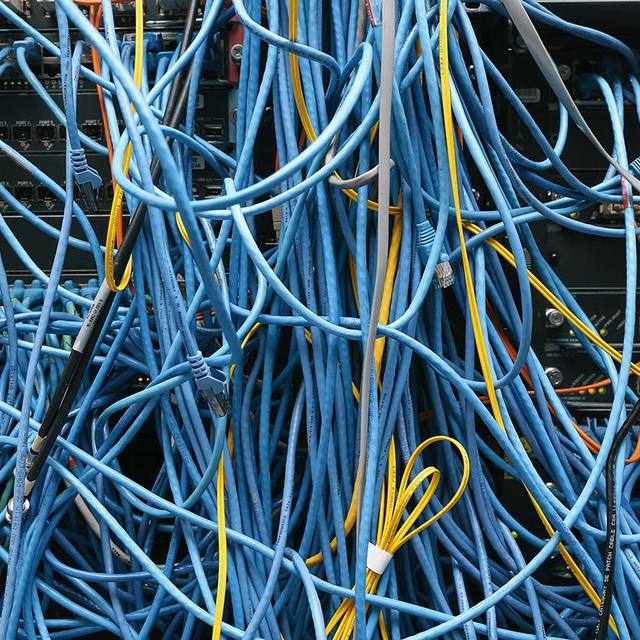中关村离北大很近。从北大南门再往南,跨过汹涌的四环,立刻就到了这个以电子产品闻名全国的地界。
在个人电脑刚刚兴起的时代,学生们前往黑风寨一般的电子商城里寻找一家看起来靠谱的商店,购买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那时电子信息化尚未普及,不是所有人都精于此道,所以这种采购之旅常常结伴而行,尽量降低风险。后来许多电子系的学生开起了自己的店,在南门外面租一个小房子,给师弟师妹修电脑、卖水货,当个中间商。这是当时的创业故事,大家还依赖于这种熟人关系、共同社区来寻找信任感。
后来,四环的这一侧发生了更多的变化。一度出现过一家体量惊人的第三极书店,整栋楼都在卖书,和其他书城展开价格战,让学生、老师们在此流连。结果一年之后就宣告这只是地产商抬高地价的策略,一个幻象。现在,昔日的第三极书店旁边已经正式被命名为创业街,书贩、书摊都成了创业者高谈阔论的咖啡厅。这是新的创业故事,也是新的花花世界。
用一个最时髦的词汇,中关村正在经历转型。经销商正在离开这里的商厦,想要卖电脑的人不再需要冲进去冒险,而是可以在网上购物,或者去苹果商店。在政府的规划中,这片具有指标意义的区域今后要改造成为新的互联网创业园区,它代表了我们正在进入的新的时代吗?我和吴靖教授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启。
吴靖,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美国爱荷华大学传媒研究系,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著有《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译有《媒体垄断》、《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研究领域包括传播与媒介技术的社会理论、批判媒体与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新媒介技术的社会使用与文化史、新媒体与创意产业等。

一
正午: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媒体转型、互联网时代,这个舆论的变化在您的课堂上是否也有反映?比如,前一段时间还有教育部鼓励学生休学创业的新闻。
吴靖:我自己感觉新闻和传播专业的学生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情绪,有一点沮丧。在课堂上交流现实社会中有争论的议题,他们的兴趣不是很大,我得到的回应不多,这也许和中国学生公共表达的习惯也有关系。其实学媒体的学生应该对社会充满了好奇心、热情和介入感,但他们大都是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为了完成学业才提供观点。
甚至是媒体行业的一些重大话题,大家对身份、职业的发展都有焦虑,可是在学生中就感受不到太大的热情。这也可能和我们的学生整体上的就业去向已经非常多样化有关系,大家毕业以后不再集中去媒体,媒体人的身份意识在我们的教育里已经非常淡了,多数人只是把学位当作一个阶梯。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学生们对新媒体、新技术是向往的,哪怕并没有太多认识,但非常好奇,被大的洪流裹挟。如果要实习的话,他们对互联网公司的兴趣也是很大的。
正午:这个变化是最近发生的吗?有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吴靖:之前也会有,但风气的确在变化。在任何时候,理想主义都是一个小的群体,但是这个小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今天,你感觉到这个小群体真的是一个很边缘的、自我坚持的群体,他们已经没有平台去表达这个群体的身份意识,而之前还是有的。
在这之前,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尽管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也是不平衡的,但理想主义的话语结构还是拥有它的表达渠道,但现在因为新媒体的碎片化,草根的、世俗的、虚无主义的观念完全通过新的媒体形式(微博、微信、视频等)来传播,理想主义的声音很少听到了。在前几个星期的本科课堂上,我讲到某个新闻事件,在学生中间的认知度非常低,我就顺便问了一下大家的媒介使用习惯,结果150人的通选课上,基本没有人使用新闻客户端,少数人订阅了澎湃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不读新闻了,这不仅仅是纸媒的问题。
正午: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一条结构性的线索来理解这种变化?前一段时间还有业界的声音认为学界给予的支持不够。
吴靖:我看到的主要是资本的影响,业界对此是基本无视的,他们看到的最大的阻力仍旧是权力。业界提到的许多例子反而是在资本的裹挟下,媒体主动寻求市场利益来损害新闻公信力,从而受到权力的惩罚。这些案例中的权力,是在代表社会对媒体行使规范权。
当然这种规范权的行使方式与程序存在争议,但在新闻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语境下,新闻活动天然的正义性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越来越多地在为特定的利益集团以及资本去服务,所以学术界从新闻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我觉得是在维护传统的新闻理想:为公共服务,生产公共领域。
今天,媒体不是超越其他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是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在媒体的持续渗透下,社会中各种各样利益都要通过媒体表现出来,其中影响最大就是资本,现在的政治权力也是通过资本的形式来对新闻媒体进行控制,它们之间是一种既博弈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在社会各方面的权力精英越来越统合的今天,媒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也并不意味着公众会成为附带受益者。
二
正午:在我们之前的一篇访谈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孟冰纯老师提到,新媒体的变革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
吴靖:互联网思维根本就是商业思维——资本在新的环境下如何寻找新的市场动力。一直以来,资本就把互联网定义为营销渠道、商业渠道,而不是公共领域。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公共领域是由新闻的内容和评论构成,而广告和公关的部分是由媒介伦理这样一种还算有一定强制性的规则给规范起来的,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两者之间的墙消失了。你会发现不是公共领域的逻辑左右了私人领域,而是逐利的逻辑左右了公共领域。
早期讨论的自媒体,乐观的人看到的是让更多普通人进入公共话语生产,好像是更加民主化的趋势,但他们没有看见的是,公共领域的言论生产是经过文化、制度的建设才形成,关于信息来源、真实性、客观中立这一套伦理不是被动的职业规范,而是一套社会伦理,也是一套公共表达的伦理,但是新媒体带来的新的言论表达空间和平台没有带来新的规范,所以就很天然地和资本所塑造的规范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广告和宣传。
公共领域的规范是去说服,去辩论,去充分地接收信息、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广告和营销是要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价值层面的讨论,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这套营销话语在新媒体领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需要购买媒体资源,现在不需要了,传统媒体之前那种权威的、高大上的公信力也就坍塌了,这种形象实际上是被广告支撑的,广告消失了尊严也就消失,其实一直是这样。
正午:所以当传统媒体遇到危机,很多人都快速转换成为一种公关公司的思维。
吴靖:我发现这是媒体主动追求的,传统媒体的反应是怎样适应这个市场,怎样为市场服务,而不是保存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回过头来想,之前到底存不存在这套价值体系是值得怀疑的。文化是很坚硬的东西,在新的语境下迅速用市场需求来描述媒体的变革,完全没有基于媒体公共性来思考媒体未来的发展,那么之前的信仰就可能是虚假的,没有坚实的内核。
正午:现实中的媒体人也是挣扎和纠结的,他们没有现实的经济基础,和他们分享信仰的人也越来越少。
吴靖:个人是很无力的,他们需要一套公共政策去推动和引导。我们现在设计的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政策,这就有很大的偏颇。互联网是一个平台,它应该有其他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卖东西,教育、新闻生产、实体产业和信息化怎么结合,都应该在政策中体现出来。我们的媒体政策完全看不出是要去建构一个公共领域,而仅仅是促进资本的发展,其实媒体本身在资本的影响下,已经全面市场化了。
实际上公共政策应该要去扶植市场看不到的文教、艺术和公共表达,这些东西的生产需要很长时间的投入、潜移默化的培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看不到盈利,这肯定是资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而恰恰是政府应该做的。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现在的公共政策是在为特定一部分人服务,而忽略了需要支持的另一部分,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媒体机构的空间就非常小。
正午:现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纷纷开始经营一些写作平台,但他们的努力也很难构成舆论的主流。
吴靖:资本也要为了自己的社会信誉、社会地位来买一些单,这种行为当然是很好的,有总比没有强。但它们也是有偏向的,不是完全的公共平台,现在中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多样化,社会分层也很严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权完全两极分化,有些群体在中国媒体上已经获得不了关注,他们没有引发全社会讨论的机会,他们是大的媒体资本不会关照到的群体。
正午:具体来说,是哪些群体?
吴靖:比如涉及留守儿童的一系列案件,这么大的丑闻,在中国当下充满抱怨和不满的舆论环境中,似乎应该引起对体制的批判才对。相比之前动车事件引发对国企的批判、吴英案对非法集资的讨论来说,这个持续了十几年、影响上亿人的问题,引发的报道却不多。当然我没有做定量的研究,但我没有看到特别热闹的讨论,媒体话语都很偏颇。我们的世界现在被单一、选择性地报道,尽管媒体渠道越来越多,但城市中产阶级所遭遇到的问题才是问题。
正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资本吗?比如说从北大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吴靖:这是一个系统,工作人员也不是被动的工具,他们是通过教育、社会化的过程,才成为有特定理念的群体。这么多年的市场化媒体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进入学校学习媒体技术,再进入到媒体,这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的环。就是说新一代的媒体从业人员都没有接触到城市中产阶级以外的事情,但传统上我们对于媒体的期待是打开世界的窗户,不仅是认识更广阔的世界,而是让不同的阶层互相认识相互了解。所以很难说这些工作人员直接受到资本的压力,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在结构上契合。
正午:所以现在来看,《南方周末》的时代,包括天涯、凯迪等网络社区的时代,所引起的舆论讨论的议题是相对更广阔的,这种怀旧成立吗?
吴靖:我觉得是成立的,因为那时的媒体人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他们经历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它的关怀是很下层的,关心民众关心底层疾苦,充满正义感,对公正有强烈诉求,这在上一代媒体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随着社会的变迁,包括教育对阶层的筛选,我们新生产出来的准中产阶级的这些知识分子,完全是精英主义的价值观,更多关心个人利益、自我实现,而不关心传统的家国天下和社会不公。他们的知识来源也是他们熟悉的城市中产阶级环境,在情感上也完全缺失了对另类文化的认同,没有同情心,要么是忽视,要么是猎奇、居高临下。
另外,他们的生活经验已经完全脱离了草根,上一代人多少是有底层经验的,这种切身的经验非常重要,对他的情感、语言体系都是很重要的塑造。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城市里,接受这种教育,接受全球流行文化的熏陶,阅读商业小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消费文化所建构。
我记得美国一位已经过世的教授曾经提到过,以前的记者很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可以深入社会,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这种情感和表达能力。现在新一代的记者依靠互联网搜集资料,坐在家里、办公室里,通过现代的通讯设备获取所有的信息,他是靠着已有的东西来生产新闻。
三
正午:在《中国语境中的技术变革与“互联网+”》那篇文章里,您提到了互联网技术在80年代进入中国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真空环境,一方面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激进革命在退潮。现在看来,那时候冲击才刚刚开始,现在似乎是全面失守的时刻。
吴靖:这就是悖论所在。我们通常认为80年代文化和理念争论的活跃,实际上背后依托的是那套公共服务的媒体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那几年的争论就无法生存。那时在争论中胜出的一派后来积极推进媒体市场化,现在自身的生存出现了问题,资本化和市场化把他们施展理想主义的平台挤压殆尽。
90年代初,还短暂地出现了一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以《读书》为中心,因为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从社会观念生产、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心被边缘化了,但是在那个讨论中,还是没有发现导致知识分子被边缘化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资本,还继续拥抱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政策。结果到了90年代后期,他们无力发起这样的讨论,因为可以发起讨论的平台已经沦陷了。
正午:后期的讨论把矛头更直接地指向体制,公共舆论也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
吴靖:实际上他们指向的体制和资本是一体的,但他们用一种符号层面的区隔来维系道义的高度。作为媒体,或者知识分子,在社会话语中如果不表现出一种批判的姿态,就会失去光环,因为媒体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抵抗强权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媒体是在和资本合作,它所批判的强权也在和资本合作,它们之间没有实质的差别。
正午:所以互联网思维并没有改变这种必然的后果?
吴靖:你很难说新技术是决定性的,它一定是在社会思潮中,以某种方式被发现被强化了。互联网在西方最初的设计中是军事性的,从军事发展到大学,成为一个发起讨论的平台,包括后来中国的网络发展也是这样,从大学的bbs开始,那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是非商业化的,逐渐辐射社会。互联网的文化基因应该是公开的、公共的分享,实际上是社区化的。互联网商业化是从90年代开始,和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相关,技术的小型化、消费化,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为个体消费者提供娱乐和消遣。这个趋势在个人电脑普及时已经出现了,硅谷新经济随后又强化了它。
正午:所以与其说是话语权的释放,不如说是消费能力的解放?现在所有的创业点子都是在寻找商业模式。
吴靖:是的,互联网越发达,实际上言论越少,消费行为越多,更多的欲望被发明。以前前所未闻的需求被包装成是生活里很核心的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是,前阵子很多媒体人辞职去互联网或者金融公司创业,他们都发表过一些言论,但张泉灵有一段话让我不能释怀。她提到“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而狗死了”,说的是出租车司机的电台节目收听率下降,不是因为有更好的节目来替代,而是司机都在用滴滴接单就不听广播了。对她来说,司机不听广播这件事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只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或者说市场的变化,聪明人要去抓住它,因为司机不听广播了,所以我不在这个行业了,我要到司机听的那个行业去。
她是一个著名的媒体人,但她的表述完全没有媒体的理想。如果媒体人都这么想,那么我们对媒体的话语生产还有什么期待?就只能任由资本去打造。资本会告诉你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读书或者听新闻,而是去玩更多更新的app,去双十一购物。
四
正午:那么如何看待权力?
吴靖:最近我才有一些这方面的思考,以前只是从单纯的旁观者、批判者的角色出发,希望通过提供批判性的思想来影响学生,他们以后会作为媒介管理者,成为社会的精英,甚至成为政策的制定者。但最近我觉得需要具体地影响政策,尽管实现起来很困难,也需要努力。
现在很多问题都集中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缺少公共性。北大的姚洋教授曾经对中国模式的成功中有一个重要的总结,他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中立的政府,既不亲资本也不亲劳工,是一个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斡旋的政府。
我认为这一点在十几年来的公共政策中已经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最初是一个反资本的政权,后面又经历了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90年代用亲资本的方式来培育市场,到今天又发展成为反劳工或者说忽视底层的利益,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与其抽象讨论宪政问题,不如讨论在现有的民主体制下有哪些漏洞,怎么执行。
因为在原有的制度设计中,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源就考虑到了各个阶层的代表性的,那么应该怎么把他实现出来?我们的委员和代表能不能真正的代表?他们怎样在政策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发出不同群体的声音?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比如媒体政策,就表现出严重的偏颇,我们的版权政策、对互联网版权的管理,都没有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印刷时代的版权制度是不是适用于互联网?多大程度适用?这些辩论应该体现在法律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但完全没有,只是很武断地把资本化的体系挪到互联网当中去。
据我了解,有些帮助政府部门制定互联网版权制度的人就是互联网公司的法务部门,他们像智库一样组织讨论、写政策性的论文,由他们提供的观念更多地左右了决策的方向,完全跨过了民意代表机构。
这不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它不在人大、立法机关的层面经过讨论,完全是执行部门和企业的法律,被封闭地完成了。所以我们学术和公众关注的方向,应该是权力的公共性问题。权力不是说你推翻它就好了,你要改造它,像姚洋教授说的,实现政府的中立性。
正午:现在更多的批评指向了审查机制的存在,而您认为应该从政策制定层面着手,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吴靖:只侧重前者会让问题变得简单化,监督变成了谩骂和指责,而审查也是粗暴的,两者没有什么建设性,就不能监督到具体的层面,不能有效地推进变化,而是一种对抗性的监督,陷入恶性循环。
当然,责任更大的应该是政府一方,它应该有意识地在组织更为成熟的讨论之后再去推进某个政策。而媒体作为推进政府进步的力量,应该更专业更深入去讨论,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这就涉及到记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没有能力去讨论到具体的政策层面,就只剩下立场了。
正午:这又回到了之前谈到的那个问题,记者的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
吴靖:现在的媒体上有太多的调侃,现在的批评更多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从一个点扩大成体制性的批评。戏谑只能制造一种虚无的心理状态,没有办法针对具体问题来引起讨论。媒体作为反对派,也应该是忠诚的反对派,不应该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五
正午:在您谈到的恶性循环中,互联网有没有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
吴靖:再观察吧,目前从政策的角度,我还没有发现在市场化以外的积极思路。
正午:有没有看到比较乐观的海外经验,比如BBC的公共服务模式,似乎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吴靖:其实欧洲有很多的媒体模式,说起互联网商业化不能只看美国,你会发现欧洲的互联网商业并不发达,现在著名的互联网企业不是美国的就是中国的,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模式。
某种意义上现在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比较相似,而欧洲不太一样。我觉得原因在于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商业化的,而中国媒体的公共服务文化不够深,就迅速被商业化的理念入侵。而欧洲有很强的公共媒体的传统,比如北欧有很多积极的公共政策,包括媒体派别的平衡、公共资金对少数族裔政策的支持,它的媒体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就崩溃了。再以英国为例,为了迎合国际资本的压力,英国也引入了更多的卫星频道、数字电视,BBC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但并没有压倒性的舆论要去私有化BBC,甚至有保守党明确反对这个议题。
这和每个国家的传统是有关系的,互联网的发展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而且我觉得中国仍有可能性,我们的媒体至少在法律上没有全部私有化。
正午: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对您的教学有什么影响?包括您在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反思或者自我反思?
吴靖:我到现在也没用微博发言,我认为不可能用140字说清楚一件事情。传播学效果研究中有一个规律,宣传或者传播要达到最大的效果,就要顺着社会的既有观念去表达,如果你去挑战它,只有在环境充沛的情况才有些微的效果——所谓环境充沛就是你要有充分表达的空间,还要在一个小群体的沟通中进行强化。在此之前,我认为课堂、教室就是这样的环境,可以传递一些挑战常识的观念,让大家反思自己的现状,微博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现在我会通过微信来发表一些言论,因为它基于电话本、朋友圈,影响的是周围的同学、同事、有共同想法和关注的人群,这是课堂的延伸。但我发现使用多了以后,效果也被冲淡了,发朋友圈这个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种姿态,是个人的建构,有时候也会觉得虚无。发的那些长文章,我不确定那些点赞的人是否真的看了。至今我看到好文章还是会转发,但会克制自己,我发现建构一个阅读和讨论的文化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完成。
这个经历让我强化了对技术的怀疑,技术本身不能达到你期待的结果,还是你的传播理念决定了如何使用技术。我现在也在和新技术相互摸索,尽管我对它并不太有兴趣。为什么只要是新的东西就去拥抱去服从,否则你就是过时的落后的,这本身就是很强大的意识形态,需要进行抵制。
正午:现在是不是必须通过微信来搜集研究样本?
吴靖:在一些研究领域是需要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媒介研究的很多领域都需要研究者深入的进入,比如流行文化、粉丝、真实电视、肥皂剧、游戏等,如果你要以民族志和人类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就需要成为一个深度使用者,比如我之前研究韩剧,也看了很长时间的电视。但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和反思能力,不能陷入消费的逻辑,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不能被它所控制。
不管是研究者也好,使用者也好,跟技术、媒体的关系应该是开放的,去感受,去体会,同时保持反思的距离、批判性的分析以及选择的能力。最高级的是生产内容的能力,最基础的是对媒体内容的选择能力,这又回到了媒介素养的话题。
所以老话题不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学术界应该去研究新的趋势、潮流,但也不要忘记那些“老的”东西,还是回到这些核心的议题:怎样进入和影响传播秩序,怎样提高公共言论的质量,怎样建构公共领域。
————
吴琦,《单读》主编,前《ACROSS穿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