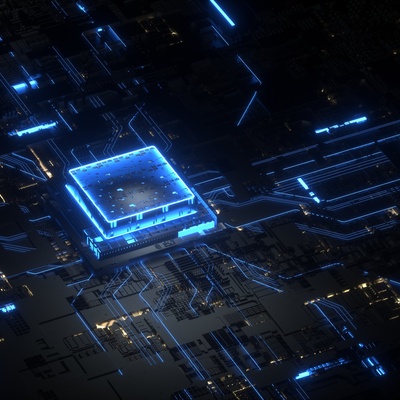一
一个月前,当了一年保姆的李桂敏终于攒齐了10874块钱的学费。经过体检、面试,她迈入了这所管家学校。
倒是不该这么叫——“保姆”——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说法。学校里的老师告诉她,正确的称呼应该叫管家服务师,是受管家管理的、从事家庭清洁工作的家政服务人员。去年六月,她从黑龙江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到北京找工作。第一份工作,待遇已算不错,包吃包住,每月净收入5000块钱,就是说出去不太体面:到别人家里做家政。她没什么开支,也没有时间去都市的繁华商区,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是手机。空闲的时候,她打电话给在乡下的母亲,母亲一直为女儿的工作发愁:一个大学生,怎么就去伺候人了呀。
在老家,李桂敏是个耀眼的姑娘。村里能念上高中的女孩为数不多,李桂敏是其中一个。她学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考到哈尔滨念大学,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李桂敏的父母都是农民,只念过小学,识得几个字,对大城市的生活是茫然无知的。当李桂敏告诉他们她在一个家庭里做家政,他们不免有些担忧女儿做了低等工作。但他们又非常信任她,觉得出色的女儿一定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
读大学的时候,李桂敏想做明星的私人助理。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天马行空。她上网搜私人助理,第一次搜到“管家”这个词汇,她心想,管家在中国好稀有啊。大学毕业,起初她按部就班找工作,但是她没有工作经验,学校也没什么名气,招聘单位只愿意给她3000块的月薪。在北京,这连基本的生活都没法保障。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自立。”李桂敏说。
她找了一个家政公司,被介绍进入一个五人的管家团队工作,其中有一名管家,两名幼儿成长师,一名厨师,还有一名保洁。雇主是一对海归夫妻,有两个小孩,房子是一栋五百多平的双层别墅,外加一个院落。李桂敏就是那名保洁员。
每天早上六点半,李桂敏换上工作制服,站在一层大厅等待管家分派工作。管家是一位30岁出头的男士,做事有一套标准流程。每天他拿着一叠表格,仔细记录家庭情况:今天家里添置了哪些物品;雇主从外面带回了哪些东西;家里有哪些物件损坏了,需要添置什么;用电量用水量;哪些衣物送洗衣房干洗了,哪些衣物被洗坏了,哪件衣服的纽扣脱落了;院落里的绿植生长情况;雇主今天穿了哪件衣服出门,带了哪些物品外出。
李桂敏的工作安排也被列在表格上。一般来说,她的清洁工作分为简单清洁、日常清洁和彻底清洁。管家制定了相应的清洁日计划、周计划和月计划。她从来不敢怠慢,管家的考核非常严苛,甚至连电视机后面的凹槽和螺丝钉都会检查。
刚去的时候,李桂敏不敢说话。每天说的话不超过10句,全部是询问:“这个杯子我应该放哪里?怎么放?”后来她学会了礼仪,雇主回来,她站在门口迎接,露出恰当的微笑:“您好,您回来了。”然后帮雇主挂外套,沏茶,端茶,这些都是从管家那儿学来的。
界限始终是分明的。她是管家团队最底端的那一层,没有资格直接和雇主说话,只有管家可以。雇主回来,管家向雇主汇报家里的情况,然后雇主向他征求意见:饮食上有哪些注意的地方,过段时间想要出门旅行,行程怎么安排,甚至,他们会聊起最近的时事政治,无论雇主抛出什么问题,这位管家总能优雅地接住。他微妙地拿捏着主人和仆人之间的落差感,把朋友和服务融为一体,即便是五星级酒店的客房服务也不能比他做得更得体了。所有这些都令李桂敏心生仰慕。
李桂敏一直在细心观察身边这位管家,暗暗留意他的言谈举止。他们平常不住在一起。管家单独住在一间大卧室,她和厨师住在一层的一个房间,按照规矩,没有管家许可她是不能上二层走动的。幼儿成长师一般和小孩睡在一起,因此也比她住得好。从前,这个家庭雇过菲佣,一般来说,菲佣和管家一样,会拥有自己的房间,菲佣的工资也比国内的家政高出一倍,区别在于:菲佣可以教小孩英语。
这就是北京一座别墅豪宅里的阶层分野,它也或多或少代表了很多中国宅院的生态。宅院的主人是不可抵达的生活在优渥天堂的人群,他们雇佣一个管家团队打理他们的日常起居,维持一所体面的宅院——没有什么比向客人展示卓越的服务团队更能彰显财富了。而管家是离财富最近的那个人。只有他有机会直接和主人交谈,也只有他有机会透过细枝末节,窥见一些浮光掠影的上流生活。如果他足够世故练达,灵巧得体,成为某个富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助手,他或许能够得到更多馈赠。在管家学校,这是一群稀有并令人向往的存在,他们完全不需要像李桂敏那样,为了学费辛苦打工,主人会亲自把他们送来培训——这代表了主人的器重和信任。
李桂敏的理想就是成为这样一 种人,一名被雇主持久依赖和欣赏的管家。
二
我第一次见到李桂敏,是在管家学校。那是一座封闭的四层红砖楼房,前几年刚刚翻新了一遍,在老旧的街道上十分显眼。四周都是低矮的平房,散落着各式饭馆、杂货铺,还有几家挂着破旧招牌的家政中介公司。学校被围墙包围,进出需要出示证件,门口的保安审视着每一位进出的人员,遇见生面孔,就会叫住询问来历。学校里,人们统一身穿制服,紫色翻领衬衣和过膝短裤,有时多了一顶白色方帽,有一点神秘的庄园气派。
我提出希望采访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学员,老师首先向我推荐了李桂敏。显然,在这所学校,老师对她青眼有加,并称她是这一期的学员代表。当她推门进来的时候,她首先向我们鞠躬,弯腰的幅度恰当地显示了礼节,又不会让人觉得过分。她化了淡妆,头发在脑后梳了个马尾,显得很精神。我们交谈的间隙,李桂敏会在杯中的水快要喝完的时候,走到身旁,及时添茶。不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旁边微笑地注视着你。
“我叫李桂敏,我是这期的学员。”这是李桂敏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她告诉我,经过这一个月的学习,她明白了怎么做事是规范的。她觉得,一个月太短,她想多学一点:红酒,茶艺,插花……每天的课程结束以后,她还在学英语,这是她从菲佣那儿受的启发:“你每提高一个技能,就是一个加薪的筹码。”
“培训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问她。
“我会去客户家里面做管家。”她说,她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家庭,有的雇主房子面积有一千多平,但只有两个人,有的雇主房屋面积没那么大,五六百平,但有老人有小孩,这些都是她考虑的因素。不过,她最在意的是雇主的态度:“有的暴发户等级观念很重,他觉得你就是比我低一档,我可以随便使唤你,你去给我干嘛干嘛,他用这种口吻安排我做事情,我是接受不了的。”她最理想的就是成为她之前遇到的管家那样的人:“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品质,管家和雇主能够像家人一样相处,这就是我期许的目标。”
在中国,这样的“管家”概念最近几年才兴起,主要来自英国。英式管家通常是男性,负责掌管整个家庭的日常运行,包括餐厅、酒窖、餐具室,有客人来则需要负责接待,举办宴会。一个资深的管家,在家里地位仅次于主人。如果主人的房子非常多,他甚至会参与处理一些房地产和金融事务。某种程度上,管家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阶层、观念的变化,欧美的管家急剧减少。有数据显示,到1980年代中期,英国的管家不过百人。此时,“管家”产业转向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中国。
进入中国之后,“管家”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在北京的这所管家学校,90%以上的学员都是女性,大多数男性是不屑于从事这份职业的。刘美妤2003年创办了这所管家学校,她说:“当时中国并没有管家行业,有的无非就是家政。家政公司非常不正规,没有正规的门面店,都是开在住宅或者很隐蔽的小办公楼里面,一两个房间一张桌子两部电话,都是老大爷老大妈没什么事儿干了,开始做家政,就是介绍保姆。”
管家行业的兴起和中国富裕阶层的出现密不可分。如果按照1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标准来计算,2003年,在中国达到这个数字的有23.6万人,而到2013年,已经超过了100万。仅在北京,拥有千万资产的家庭就有18.4万。按照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富裕阶层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平均拥有三辆车,四块表,每年平均出国2.8次,休闲时喜欢旅游、品茶,运动则喜欢游泳和高尔夫,1%有私人医生。
但是聘请管家团队,依然是一项非常奢侈的花销。一个正规的管家团队入户,每年大约需要四五十万。一年真正向刘美妤提出管家需求的客户只有十几个,她接过最大的一单,是雇主提出需要一个三十多人的管家团队入户,这笔费用每年高达500万。

三
在管家学校,我见到了很多和李桂敏一样穿着紫色制服的年轻女孩。她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好像第一次穿制服,帽子歪歪扭扭地套在头上,显得有些笨拙。管家学员和家政学员混杂在一起上课,并不是每个女孩都明确地想成为管家。老师们认为,管家是对家庭事务进行全方位策划、管理、监督的岗位,虽然入户以后,不用干具体的家务活,但管家应该知道每项工作的标准,在家政人员遇到问题的时候,管家能够做出正确的指导。“刚开始,班里的学员有些做基础家政,有些想做管家,但学完之后,都是从基层做起,一段时间以后,有的人才会显示出高于其他人的能力,慢慢走上来。”刘美妤说。
我试图寻找一位从管家学校毕业、并已经拥有一两年管家经验的学员。但是这异常困难,一旦进入客户家庭,管家几乎没有单独外出的机会。更忌讳的是,在工作时间给她们打电话是非常失礼的冒犯。
几天以后,经一位老师介绍,我见到了王姐。她做了两年的贴身管家,上一个雇主已经移民加拿大。几个月前,王姐位于北三环的家面临拆迁,但她对房地产商提供的赔偿方案不满意,正在做“钉子户”。她不敢再接客户,担心一不留神房子就被拆了。这样,她才有空和我见面。
王姐五十多岁,北京人,身量丰满,波浪卷发用一根发卡别在脑后,增添了几分风韵。她有一双王熙凤式的丹凤三角眼,说话慢慢悠悠,嗓音有些尖利,总体来说是个有气派的人。王姐不是一开始就做管家的,年轻的时候她在朝阳副食品公司卖过百货,也在五星级酒店做过配餐,后来当起了二手房中介。2007年,二手房市场低迷,工资也不见涨,挨了两年,她听说家政行业赚钱多,就转行了。
很少有北京人愿意干这行,她第一次去家政公司面试,老师一脸疑问:”北京人?你愿意干吗?你能干得了这个吗?”“我想的不是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事,我想的是这是一种服务,凭着自己的努力工作赚钱,不丢人。”她回答。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务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妻。老头几个月前生了一场病,需要人照顾。她第一次进老夫妻家,觉得真浪费,两个人住了一套三百多平米的房子,四室一厅,三间大卧室都带独立卫生间,还有中式西式两个厨房。老人吃饭不算讲究,每天早上她熬一锅粥,剥好蒜和花生米,放在两个碟子里,然后蒸两只从大连空运过来的海参,中午做些家常菜,晚上老人吃得极少或者干脆喝点酸奶。每天下午,她开着家里的白色奔驰,带着老两口出门转两个小时,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每周车号的限行日,就是她的休息日。对于一名家政人员来说,这样的工作算是极其舒适的。但两三个月以后,她就对当保姆这件事感到厌恶了。
老头开始频繁出入她的卧室,赖在房间里和她聊天,说着说着开始伸手摸她的手,然后他留了一张纸条:“我们约在XX饭店。”她向家政公司反映之后,离开了。临走前,她生气地把这件事告诉老太太:“老太太您得注意点儿!”老太太很无奈:“他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这次经历之后,王姐注意到工种的重要性。虽然同属家政行业,因工种不同,职位也有高低之分。服侍老人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份工作,老人脾气大,待遇也最低。幼儿成长师的待遇比一般的家政人员要高,因为需要早教的技巧和一定的学历,而在金字塔最顶尖的,则是管家,待遇高并受人尊重。王姐觉得,以她的能力,做管家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四
王姐报了高级管理班,并开始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
一个山西的煤老板曾约她谈生意。这位煤老板像刚发了横财,在顺义买了一套1000多平米的别墅。煤老板的意思是,希望王姐带一个五人组的管家团队替他打理别墅。王姐问:“开价多少?”“两万五,”煤老板接着强调,“五个人一共两万五。”这个价格让王姐吃了一惊,她转述当时的回答:“您都想提升您自己了,那么多人伺候您了,那提升还不得用钱来提升?您给两万五,我没办法给您找人。”
不久,一个女老板找到王姐,问她愿不愿意做她的贴身管家。贴身管家和管家团队入户不同,底下没有可供差遣的管家服务师。王姐同意了。
女老板租了两套公寓,楼下的一套用来招待客人,自己一般住楼上那套房子。她的丈夫在美国,儿子在加拿大读书,隔几个月回国才能见面。女老板经常出差,王姐就负责订机票或者火车票,开车接送。女老板有三辆车,一辆保时捷卡宴,一辆敞篷奔驰,王姐开那辆较次的车,奥迪A6。
女老板话不多,平时对待下属非常严厉,但对王姐,她很放心。王姐做事细心,懂得分寸。她一般只在楼下的那套房子活动,进入房间,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用的家居服,然后清点储藏间里的食物和酒水。女老板出行用的行李箱,王姐整理完毕以后,会用一根丝带在把手上打个结,以方便主人认领。逢年过节,她也会去商场替老板挑选礼品。
一次,有客人到家里做客。结束后,一位客人打算顺两瓶茅台酒回去,被她发现了。王姐告诉客人:“我是管这个家的,出现这种事情我不能轻易放你走。”此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丢东西的事情了。
和李桂敏对管家职业充满期待的神情不同,我在王姐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倦怠。女老板移民之后,陆续有好几位雇主找到她,其中有一户全家移民悉尼,希望把王姐接到悉尼帮忙管理家庭。王姐都拒绝了。一旦进入家庭,她就失去了私人时间,全部的心思都得放在别人的家庭上。她今年53岁了,2002年离婚之后,单身了十多年,她希望能找一个对象结婚,过过自在的生活。

五
李桂敏远没有到考虑这些的时候。在管家学校,四层的楼房被模拟成一栋家庭别墅,每个学员轮流做一天的管家。轮到李桂敏的那天,她总是忐忑又兴奋。她像个真正的管家,制定各式各样的表格:床品更换表,绿植养护表、出勤考核表,财务报表……早上六点,她开始分配工作,哪几个人做饭,每层楼的卫生由哪几个人负责。等到九点开早会,她进行考核。玻璃对角线的灰尘有没有擦干净,哪一盆绿植没有浇水,她一笔一笔记录在表格上……与其说她是管家,不如说她是一个认真的管理者。
李桂敏从管家学校毕业之后,我试着联系过她一次。电话拨通了,她的声音有些着急,说她已经在客户家里,很难抽出时间来见我,最近家里似乎在准备一场活动,她可能一个月都没办法休假。
”你外出给雇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能见面吗?”我问。
“那一定不行,这有可能侵犯到雇主的隐私。”她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联系上她。我想她可能已经换了号码,按照行规,管家都会备用两部手机,一部用于与外界联系,一部和雇主联系。无论何时,管家都要保持手机的畅通,以便在雇主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刻,及时提供服务。
李桂敏的努力和聪明才智,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清楚她是否实现了理想,成为一名被充分依赖和信任的管家,或者她还要再做一段时间的家政服务师?
在我们的对话中,她曾告诉我:“中国其实自古以来就有管家,你知道《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她就是个中国式管家。”
“她是你的偶像?”我问。
“可以这么说。” 李桂敏回答。
我想,假以时日,李桂敏一定会成她期待的那类人。
——————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