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变成一个救世主,又会感觉像一个暴露狂。我想没有一个写作者想让自己成为暴露狂或者救世主。我就开始思考,这样的写作还能持续多久?”来自台北的小说家刘梓洁日前在“2016上海—台北小说家工作坊”“文学虚构与现实”的主题对谈中这样说道。
“不是写了一部葬礼题材就是葬礼专家,写了诈骗题材就是诈骗专家”
刘梓洁出版的《父后七日》一书,是一本书写自己父亲去世的非虚构作品,而与她当日对谈的上海作家薛舒也曾创作过纪实作品《远去的人》,记录下自己父亲患阿尔兹海默病的经历。这两位作家都从非虚构转向虚构写作,在对谈中没有庆祝用小说获得了笔端的自由,却都认为,作家写的东西处处被人当真是尴尬的,处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是艰难的。

刘梓洁讲述自己因为写作非虚构散文而遭遇到的荒谬情形,“《父后七日》得奖后,在一些场合会有陌生的读者跑过来跟我分享他失去亲人的伤痛,我好像变成一个救世主,又会感觉像一个暴露狂。我想没有一个写作者想让自己成为暴露狂或者救世主。我就开始思考,这样的写作还能持续多久?”因为《父后七日》她还意外地收到台北殡葬局的邀请,“因为您在殡葬业学有专精,因此请您来担任台北市殡仪馆的殡葬顾问咨询委员。”
遭遇到这样状况的刘梓洁转向小说写作,以台湾诈骗的真实事件为原型写出了小说《真的》。她认为,将真实材料改造成小说的过程很艰难,不仅要求作者搜集调查信息的能力,还涉及剪裁材料是否道德的问题,“我有权力变形、转化真实材料,只写有趣的部分吗?我想真实不一定是事实或者是现实,而是小说家心里头的答案,那种真实。”刘梓洁的理想状态是,“带着真实事件,经历揣摩虚构和变形隧道和一连串冒险之后,看到的是未曾想象过的全新景象。”她认为小说家应该被更公允地评价,“小说家应该被关注怎么写,而不是写了什么,不是写了一部葬礼题材就是葬礼专家,写了诈骗题材就是诈骗专家。”
同样书写父亲的上海作家薛舒回应了刘梓洁的尴尬,“就像刘梓洁被当成殡葬专家,因为写《远去的人》父亲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散文,我也曾被当做阿尔兹海默专家。”因为父母和她对于“真实性”的定义不同,她以父母为原型写小说,也不敢让父母看到,怕他们会误解其中的故事与形象。“后来我妈妈还是在《收获》上翻到《远去的人》,看完后说,你把自己的妈妈写得很不堪。我只能哄她,这是小说,有虚构的成分。” 这件事让她想到,“可能很多人都像我母亲一样,不会反思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以为的自己有什么不同。个人应该对于有 ‘真实’有反思的自觉,不应该理所应当地认为什么是 ‘真实’。真实可能只是一个截面的真实,不是永远的、全面的真实。”

小说家可能会因为“真实”问题被读者和评论者误解,而反过来说,“真实”或“现实” 有时对小说家来说会成为创作的限制。在另外一场讨论“内省与蛮荒”的讨论中,上海作家任晓雯讨论书写“真实”的问题时认为,小说家要从对现实的模仿中、无聊的状态中跳脱出来,要书写苦难,反思死亡,而不是掉进厚重的历史中,成为永久的人质。“中国作家,特别是我,常常觉得要写一部很厚重的关于历史的小说,要写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到当下的一群人的面貌,一个清明上河图,一个历史卷轴,这种表述和思维方式有陷阱,好像要背负起书写民族历史这个责任,好像签了一张合同,必须为这个进行书写,我没有这个资格,我得先把我自己变成一个人。”

评论金理则认为,跟虚构作品一样,“非虚构”文类最重要的在于“文学”的表达而不是“非虚构”的手法,“在人类学和社会调查报告中,他们喜欢用 ‘地方感’,意思是基层民众在超乎现代知识的分类之后的、或者现代知识分类没有办法过滤掉的感受想象和表达,是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经验,但这不是文学最擅长的吗?梁鸿的《梁庄》打动我的是文学,而不是非虚构。”
“两地的时间差造成了对文学理解的不同”
在另外一场题为“内省和蛮荒”的讨论中, 来自台北的小说家黄丽群从这次来上海的感受说起,她比较了上海和台北两地在写作和理解上的不同,认为这是两地空间在不同时间环线上位置不同所造成的。“来之前,两地的同行们难免预期,我们基于使用同样的工具,基于同样的文化遗产,建筑的城邦内在的格局应该近似。来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商榷。两地的语言的壳是一样的,外延范围还有核心意义在某些时间有所不同,基于这个不同,两地的写作者语言折叠与展开的方式不同、节奏性不同、歧义、歧义造成的空间也不同。我说的不是线性的时间差别,应该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一种环状轨道,彼此在各自的环形轨道上走动。”

黄丽群以台湾作家李维菁的小说《生活是甜蜜》为例,小说里讲述一个女孩子下班乘地铁去相亲,这其中描述的地铁氛围和上海语境下的地铁环境并不相同,“台北的捷运有一个很奇怪的空间性格,和日式地铁的空间很相像。车厢里不是很拥挤,人流速度不是很快,转运站也不会走很远的距离。捷运覆盖尺度大概相当于上海的两三个区,集中在市中心的区,是非常白领非常都会化的空间。如果读一些台北写作者描述台北的捷运,这里不会被描述成三教九流拥挤或者很遥远的空间,它会被描述成清冷的现代化充满秩序的空间。”这样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对于文本和人物的理解。“台北现在有白领青年贫穷化的状况,这是经济由盛转衰会出现的状况,对比上海就不太一样。”
这个“时间”既在两地、上海与台北的比较之中,又在写作者与外界的关系之间。黄丽群说,在当代高铁一般的时间感下,如果小说家过于执着于内省,不管外界转瞬即逝的时间感,很可能就会自我边缘化、自我偏僻化。“文字这个介质在当代的 ‘时间感’遭受到很大的挑战。我经常有一个想象,有一个人左边的衣袖挂在慢车上,这是文字的文学的时间感,右边衣袖挂在高铁上,这是当代的时间感。这个人除非很有意识地跳到慢车上,去看慢车的风景,否则高铁一开,就一下子把人带走了。极端地沉溺在自我的实践和实验当中,会不会导致文学变成辟支佛?它只自度,不度人,只考虑自己,它没有办法产生意义,它会被时间感和自我偏僻化、边缘化。”
【其他对谈摘录】
黄丽群:小说一定要有用吗?
这几年常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作这件事情,尤其是写小说的本质是什么?对于当代的世界是否还具有必然要承担而且无可回避的意义?在一个大的场景下,小说原始的呼应人类本能说故事听故事的功能,其实已经有很多其他“效果”十倍百倍的产物承接。假设一个止痛药,其他药丸是三分钟生效,小说要三个小时甚至三天生效。放在小场景,同样在文学媒介,抒情诗可以提供更有效率更快速的审美体验。
这个时代被抒情诗以及被实时评论建筑起来,所以小说一定要有用吗?有些时候小说就是剥掉所用,还有一些什么说不上来的东西。如果我选择不将自己的写作方式和节奏迁入当代世界感和感官结构,会不会我只剩下极端个人的时间,这种极端个人的时间进入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不负责任?这是我没有办法回答我自己的。
金理:《梁庄》打动我的是文学,而不是非虚构
在大陆谈“非虚构”,指向具体的写作潮流,跟2010年前后《人民文学》推出的“非虚构”可能有关,我发现很多朋友在谈这样一个栏目,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在今天,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的文体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已经没有办法回应时代这个重大的主题了,这种情况下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或者借助非虚构的文体来重建文学的某种社会属性。
我想到了一篇文章,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一边》,如果有朋友是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他可能会对我所讲非虚构的潮流提出很多疑惑。当我们已经接受后现代,已经完成认同虚构性文学话语可以积极参与历史写作的时候,反过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要求文学具备一种非虚构性。第二,是不是在今天,非虚构具有优越性。第三,如果大家普遍觉得小说陷入危机,为什么不是积极的磨砺小说技艺,而是重新找一条另外的道路非虚构。

如果以我的阅读经历,又特别是在非虚构这样的具体的名义之下,取得比较广泛的声誉应该是梁鸿老师的《梁庄》。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反复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梁庄》这样非虚构的作品跟我们以前接触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报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读过一些论文,特别是人类学的研究,他们经常喜欢用一个词“地方性知识”,我觉得用知识描述基层民众的生活经验和资源,这当中已经有精英的处理、变形和想象,近些年他们喜欢用“地方感”,基层民众在超乎现代知识的分类之后的想象感受或表达,或者现代知识分类没有办法过滤掉的感受想象和表达,这是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经验,这不是文学最擅长的吗?《梁庄》打动我的是文学,而不是非虚构。
btr:一个故事只要有一个人相信,它就可以是真实的。
一个电影开头有一个字幕说,“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个声明并不是说里面的内容是虚构,反而是用这样的题材可以尽情地讲任何真的东西。
保罗·奥斯特说,一个故事只要有一个人相信,它就可以是真实的。他讲过一个故事,发生在圣诞节。有一个小偷跑到一个书店里偷钱逃走了,店主出去追他。追他过程中没有追到小偷,但是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有他的驾驶证,店主拿着皮夹子跟着驾驶证的地址找到他的家,开门是一个老奶奶,老奶奶一下子拥抱了这个店主,她说,孙子,你终于回来了。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这个奶奶是个盲人,这个盲人以为是孙子回来了。奶奶孙子长孙子短,你这么多年怎么没来看我。他就扮演这个孙子,奶奶拿东西给他吃。到一定时候,他说他要上洗手间,一看洗手间密密麻麻摆来偷来的赃物,他没有拆穿。就跟奶奶说我以后会来看你的,就走了。这个故事里面揭露出,日常生活中的扮演或日常生活中的虚构性,就像身份问题,当我们进入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在扮演另外一个自己。对于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分,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区分。
小说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你讲真实的东西,更真实的东西,或者更自由的讲真实的东西。非虚构,声称自己是真实的,却反而只能涉及到某一种真实或者某一个侧面的新闻报道。一直有这种感觉,好像一切都是虚构的,我们都是用文字在创作,任何东西最后是落实到文字上,一旦落实为文字,就不再有非常客观的非常绝对真实。就好比玛格丽特说这不是烟斗。连图象都做不到,我们文字就更做不到了。
孙甘露:艺术家拍的照片是虚构的,但是他达到的心理的真实的震撼
前两年在上海艺博会做过一个展览,既是照片展览,同时又是一个装饰。很好的解释了虚构、非虚构和真实,包括心理层面的真实。一个展厅,展板本来是一个凹字型,中间有一个展板分开,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你一生中见过的第一样东西”,另一部分,“你一生中见过最后一样东西”。每一个照片是一组两张,采访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一个盲人被问道,“你一生中见过最后一样东西是什么?”因为他是交通事故致盲的,所以说我见过最后一样东西是红色的公共汽车。艺术家就找到一辆公共汽车拍了一张照片,和这个盲人放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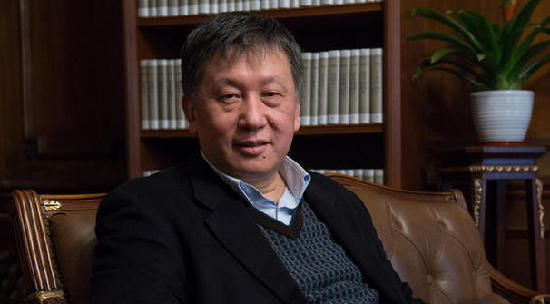
这是一个真实事件,艺术家拍的照片是虚构的,但是他达到的心理的真实的震撼,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个震撼不仅仅是当事人,实际上给读者观众造成真实感。
(该摘录未经发言本人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