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用这个笔名所写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于1992年。到2014年,这个名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赞誉,因为名字背后那位神秘的作家发表了广受赞誉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今年10月,意大利媒体《24小时太阳报( Il Sole 24 Ore)》记者Claudi Gatti似乎揭开了她一直小心隐藏着的匿名身份,这一新闻迅速登上全球各大报纸头条。费兰特的《Frantumaglia:一位作家的旅程(Frantumaglia: A Writer’s Journey)》收录了她的信件、采访和感悟,最近由Europa Editions出版社出版,本文即摘选自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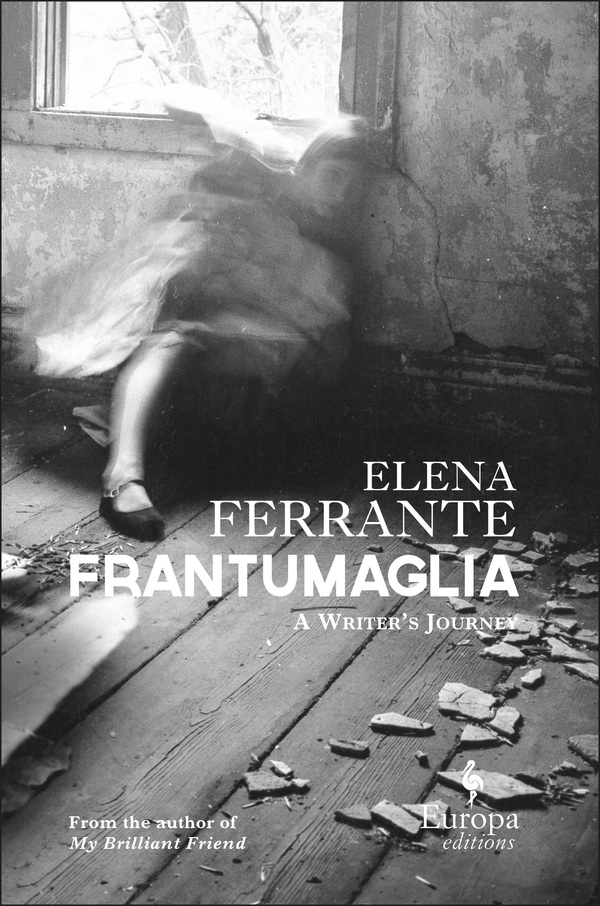
1991年9月21日的信
背景:她的第一部小说《险恶的爱情(Troubling Love)》在次年出版。其中,Edizioni E/O和Europa Editions的创办者Sandra Ozzola和Sandro Ferri是埃莱娜的出版人。
亲爱的Sandra,
最近和您以及您的丈夫的那次会面非常愉快,当时你问了我关于《险恶的爱情》的推广打算怎么做(还好你让我逐渐习惯叫它最终确定的这个名字)。你反问我这个问题,表情中带着困惑。彼时彼地,我没有勇气回答你:我以为我已经和Sandro说得很清楚了,他也说了绝对同意我的决定,我希望他不会又旧事重提,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要。现在我用文字回答,来避免出现尴尬的停顿、犹豫或者任何妥协的可能。
我不打算为《险恶的爱情》做任何宣传,任何可能需要我个人公开参与的活动,我都不会参加。对于这一长篇故事,我已经做了该做的:我写下了它。如果这本书能有一点价值,那就足够了。如果今后收到讨论和会议的相关邀请,我不会去参加。假如将来获评任何奖项,我也不会出席领奖。我永远不会宣传这本书,特别是在电视上,不管在意大利还是其他国家皆如此。我将只接受书面采访,但即便是书面采访,我更倾向于把它限制在最小数量,若非必要则不为之。在这方面,我对自己和家人做出绝对承诺。我希望今后不会被迫改变初衷。我理解,这样可能会给出版社造成一些困难。我非常尊重你们的工作,我在认识你们那一瞬间就喜欢上你们了,我也不想引起麻烦。如果你们不想再支持我,请立刻告诉我,我会理解的。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出版这本书。你知道的,原原本本解释我做出这种决定的原因并非易事。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和自己、和自己的信念下的一个小赌注。我相信,书本一旦写就,便不再需要它们的作者。如果它们有话想说,它们早晚会找到读者;如果没有,则不会有读者。之前有很多先例。我非常喜爱那些神秘书卷,古老的和现代的都喜欢,虽然没有确切的作者,但是它们本身一直以来并且还将继续拥有强健的生命力。在我看来,它们像是一种夜间奇迹,就像是贝法纳女巫的礼物 [贝法纳女巫是在主显节(1月6日)前夜给好孩子送来礼物的老妇人——就像圣诞老人],我曾在孩提时代等待着礼物的降临。我兴奋地上床睡觉,早上醒来时礼物就出现在那里,但是没有人见到过贝法纳。所谓真正的奇迹,它的创造者永远不会被人知道;它们可以是家中的神秘精灵这种很小的奇迹,或是能让我们确实感到震惊的伟大奇迹。不管是大是小,我始终有点孩子气地希望有奇迹出现。

因此,亲爱的Sandra,让我清楚地答复你:如果《险恶的爱情》自身没有足够的纺线来做编织,那就说明你和我都做错了;如果与之相反,它有一定的纺线,那就任其编织到所能及的地方吧,我们只需要感谢读者有耐心在最后选择了它。
再说,宣传推广的花费很贵不是吗?我将是出版社花钱最少的作者,我甚至给你省下了我的出席。
诚挚的,
埃莱娜

摄影:Chris Warde Jones/NYT
1994年9月写给Sandra Ozzola的信
背景:时值Edizioni E/O’s出版社15周年庆
亲爱的Sandra,
你做了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当我欣然同意为你的出版企业周年庆写点东西时,我发现按订单写作就像一个滑溜溜的斜坡,并且向下降落事实上是令人愉快的。接下来还会有什么?
既然你已经让我拔掉了塞子,水会通过管道全部流干吗?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可以接受写任何内容。
你会要求我祝贺你刚买的新车吗?我可以从大脑某处拉出第一次乘坐轿车的记忆,一行一行写下去,最后以祝贺你拥有新车结尾。你会要求我赞美你的猫咪刚生的一窝小猫吗?我可以回忆父亲曾经给我的那只猫,却因为恼怒于它的叫声,父亲后来把它拿走丢弃在去往Secondigliano的路上。你会要求我给你在做的关于今日那不勒斯的一本书,写一篇文章吗?我可以从自己过去因为害怕遇见爱管闲事的邻居而不敢出门那段时间说起,那个邻居之前曾被我母亲从家里扔出去,然后一句一句慢慢引出对于如今复又威胁我们的暴力的恐惧,但是已有的政治活动总是乔装粉饰自己,我们不知道到哪去找应该支持的新政。我应该主动提议回应女性诉求,写文章讨论要学会爱自己的母亲吗?我可以详细描述在我幼年时,妈妈是怎样在马路上抓紧我的手:我会从这件事说起——事实上想一想的话,我还真愿意写这个。我还模糊记得皮肤和皮肤相碰的触感,当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担心我会溜掉、在不平坦的危险马路上乱跑:我感觉到她的担忧,也害怕起来。然后我会找到办法引出我的主题,在中间举上Luce Irigaray(注1)和Luisa Muraro(注2)的例子。下笔如行云流水:对于任何主题,每个人总能写出或平庸或精美,或真诚或有趣的连贯篇章,不管那个主题是低是高,简单还是复杂,微小还是重大。
那么该如何是好,向我们喜爱并且信任的人们说不?这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写好了纪念性的几段内容,尝试传达真实的感受:对于这些年来你们一直奋斗、并且到了今天我觉得甚至更难胜出的这场崇高战斗,我充满敬佩。
这里就是我要传达的信息:美好祝愿。目前,我暂时打算以刺山柑开篇。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可以给你写很多回忆、感想还有普遍概括。这么做需要什么呢?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按要求用文字刻画今天的青少年群体,讨论对电视的厌恶,写Di Giacomo(注3),写Francesco Jovine(注4),叙述打呵欠的艺术,或者写一个烟灰缸。
契诃夫,就是那位伟大的作家契诃夫,在和一名想知道他的小说故事来源的记者聊天中,随手拿起碰到的第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烟灰缸——对他说:你看到这个了吗?明天你再过来,我给你看一篇题为《烟灰缸》的故事。一段绝妙的名人轶事。
但是写作的时机如何以及何时必然出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预示时机到来的因素开始显现时,写作亦有它压抑的一面。
即使是事实,也可能看起来像是虚构的。所以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会在页面边缘加上一句,不是刺山柑或者其他这类东西,不是文学写作,我的祝贺诚心诚意,发自肺腑。
下次再聊,
埃莱娜

我小时候住过的多所房子里,有一所房子的东边墙上四季长着刺山柑。那是一面粗糙光秃的石墙,上面有很多小洞,每一粒种子都可以找到一小撮泥土。尤其是那株刺山柑,骄傲地繁茂生长,虽然颜色很浅,它在我脑中印刻下有力和能量的形象。租给我们这所房子的农民每年把这些植物砍掉,但是全都徒劳。当他决定修补这面墙后,他给它涂上一层均匀的灰泥,然后刷成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蓝色。我坚信不疑地等了很长时间,等着刺山柑的根最后胜出,顷刻间打破那面墙的平静。
今天,当我寻找一种方式祝贺我的出版商时,我感觉它已经发生了。灰泥涂层裂开,刺山柑再次钻出地面,伸出第一条嫩枝。所以我希望 Edizioni E/O继续和灰泥涂层抗争,反对一切以消除创造和谐的行为。书本可能就像刺山柑的花,为了抗争顽强地一季又一季绽放。
注1:吕西·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1932-)是一位比利时女权主义者、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
注2:Luisa Muraro (1940-) 是一位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注3:萨尔瓦多雷·迪·贾科莫(Salvatore Di Giacomo ,1860-1934)是一位那不勒斯诗人、词作家和剧作家。
注4:F·约维内(Francesco Jovine ,1902-1950)是一位意大利小说家、记者和散文家。
————————————————————
1995年3月写给Sandra Ozzola的信
背景:“假定的简短采访”,回答记者 Annamaria Guadagni发来的关于《险恶的爱情》的提问。
亲爱的Sandra,
很抱歉我无法回答Annamaria Guadagni的问题。不是这些问题不好,事实上它们很有深度,问题在于我自己的限制。让我们听从内心,从现在起,避免承诺我不会接受的采访。也许最后我会受教,但是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最后不会有人会有采访我的念头,因此问题将在根源处得到解决。
事实是,每一个问题都让我想去收集观点,想要从最爱的书本中查找,使用说明,写上注释,偏题讨论,相互关联,坦诚分享,激烈辩论。都是我喜欢做的也是我实际在做的事情:它们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但是最后我意识到,我把材料组织起来不是为了一次采访,不是为了一篇报道( Guadagni同样礼貌性地如此提议),而是为了一篇故事。慢慢地我失去了信心。如果采访中的每个问题我都给出至少10页密密麻麻的答案,一份报纸会怎么处理呢?所以,基于我是个固执的人,我会把所有事情抛在一边,试着找到一些上乘的佳句,来明确表达出我在此期间积累的数页内容的意思。然而没过多久,这些句子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上乘,变得有时昏庸,有时自负,绝大多数时候是愚蠢。最终我只能随它去,非常压抑。
或许采访应该是这种形式:
问:认为《险恶的爱情》中的母亲角色是那不勒斯类型,这是不是错的呢?
答:我不这么认为。
问:你从那不勒斯逃离了出来?
答:是的。
问:对你来说,不完美是写作的真正维度吗?
答:对的。
问:一个人变得和自己的母亲混淆不清实际意味着丢失了一个人作为女性的身份,迷失了自我,是这样吗?
答:不是。
问:《险恶的爱情》是出于拥有母亲的需要吗?
答:是的。
问:是不是你扭曲的凝视,带给我们一种以不存在的身体在幻觉中旅行的印象?
答:我不知道。
问:你不觉得你的书一旦搬上荧屏,可能产生某种介乎神秘电影和恐怖电影之间的东西吗?
答:是的。
问:你曾在电影剧本上帮助导演Guadagni吗?
答:没有。
问:你会去看它吗?
答:会的。
但是 Annamaria Guadagni会怎么使用这种类型的采访稿呢?那么这就足够让我重新审视回答中的那些“是的”,“不是”以及“我不知道”,一切又从头开始。比如说,我回答中的那些“我不知道”,如果你挖的足够深,可能发现我知道很多或者甚至知道太多。还有一些“是的”,经过一番争论,可能会变成“我不知道”。换句话说,亲爱的Sandra,让我们放下它,以 Guadagni将会原谅我的方式拒绝这次采访,同时我要为了给你们的编辑生活添麻烦而向你和Sandro道歉。
下次再聊,
埃莱娜

2002年1月的信
背景: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被遗弃的日子(The Days of Abandonment)》在意大利出版,之后在2002至2003年间,她接受了三次采访。采访问题通过出版人发送给她。
亲爱的Sandro,
你说至少接受采访是必需的,这没问题,你说得对。告诉Fofi把问题发给我,我会回答的。我希望自己在这10年里已经长大了。但是,若为我个人立场辩言,我只会说:在这场与报纸的游戏中,被采访人最后总是会有谎言,其根源在于他想对公众展现一个最好的自己,他的想法要适合这一角色,他要打扮成符合我们想象的样子。
好吧,我一点也不讨厌谎言;生活中我发现它们非常好用,当我需要保护自己,隐藏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时,我会求助于谎言。但是在写书这件事上撒谎让我很难忍受;虚构文学在我看来,需要有意地一直陈述实情。
因此,我深切关心《被遗弃的日子》的实情。我不想温顺地讨论它,顺着采访者问题中的暗示说出他期望的答案。我理想的方式是通过简短回答得到和文学同样的效果,也就是精心编排谎言,借此完全讲述真相。换句话说,让我们看看我能够做的事情。我感觉自己状态不错,我打算说真实的谎言,即使我在写一条贺词。你一拿到问题,就发给我吧。
————————————————————
费兰特访谈选摘
背景:与 Paolo Di Stefano的这次采访在2011年11月20日刊发在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上,标题是 “Ferrante: Felice di non esserci”(费兰特:很高兴不出现),下面的介绍写着:《才华横溢的朋友( My Brilliant Friend)》与埃莱娜·费兰特之前的小说非常不同。它是一部极好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或者说两部,或者不止两部——故事讲的是一代人的朋友和敌人。费兰特的采访需要她的出版人Sandro Ferri和Sandra Ozzola从中协调。这些问题通过邮件询问,也通过邮件回答。
Di Stefano:埃莱娜·费兰特,你是如何从家庭心理小说(《险恶的爱情》和《被遗弃的日子》)转到现在这部小说的类型?据说这是三部曲或四部曲的第一部,它在情节和风格上如此漫谈,同时又如此聚焦。
费兰特:我不觉得这部小说和之前的那些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年前我就想讲一个打算消失的老人的故事——不是指死亡——不留下任何她存在过的痕迹。在故事里说明把自己从地球表面抹去,字面上地抹去,是多么困难的事,这一想法让我着迷。后来故事变得复杂。我加入了一个童年友人的角色,她们是对方生命中或大或小每一个事件的忠实见证者。最后我意识到引起自己兴趣的是,去深挖两个关系密切却又存在分歧的女性的生活。这也正是我所做的。当然,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为其中大约覆盖她们60年的故事。不过 Lila和Elena是用和其他小说同样的原料创作出来的。
Di Stefano:书里写了两个朋友的童年故事,Elena Greco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她的朋友和敌人Lila Cerullo与之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当她们看起来要分开长大时,她们的经历继续重叠着。这部小说是关于友情,以及一段邂逅如何决定一生的吗?也是关于反例的诱惑可以帮助发展个人身份吗?
费兰特:一般来说,一个人在坚持自己的人格时,会让另一个人变得迟钝。较强势、丰富的人格会模糊掉较弱势的那个,生活中是这样,可能在小说中更甚。但是,Elena和Lila的关系中,Elena是从属,但她在从属地位中得到了某种才华,这种才华让Lila感到迷惑,也让她为之目眩。这种活动很难形容,但也正是吸引我的原因。让我这么说吧:Lila和Elena生活中的很多事件将会展示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个人那里夺取优势。但是要注意:她们不仅仅在互帮互助,同时也在互相掠夺,窃取情感和智慧,让对方失去力量。
Di Stefano:(时间上的可能还有空间上的)记忆和距离如何影响了这本书的写作?
费兰特:我认为在经验和故事之间“加上距离”是某种陈旧的想法。对于作者来说,问题通常是相反的:要去连接这段距离,去切身感受所讲述的事情的影响,去走进我们所爱的人的过去,走进我们观察到的、听说到的生活。一个故事在成型之前,需要历经多重筛选。通常情况下,我们下笔太快,纸张还没有热起来。只有当我们感知到故事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细枝末节(有时需要花上数年),它才能够被写得很好。
Di Stefano:《才华横溢的朋友》也是一篇关于家庭中以及社会上的暴力的小说。这篇小说是要描写一个人如何设法在暴力中成长,或者不管暴力的存在而设法成长吗?
费兰特: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避开那些打击,这会回报给他们苦修后的宽宏大量。在《才华横溢的朋友》这个例子中,两个女孩长大的世界有一些明显的暴力特征,其他人背地里也是暴力的。尽管前面那种情况有很多,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后者。
Di Stefano:在书的130页有一句话写的很棒,是关于Lila的:“她考虑了这些事实,并且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让它们充满张力;当她把一切化简为文字时,她强化了事实。”然后在书的227页:“书写中的声音淹没了我……它完全清除掉了言谈中的废话。”这是在声明一种风格吗?
费兰特:让我们这么说吧,在我们用来赋予世界一个叙事顺序的众多方法中,我偏爱那种清晰而诚实的写作,当你去读这种方式所写的事件——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你会发现它们格外的令人信服。
Di Stefano:书中有一条更加偏社会学的线索:兴旺年间的意大利,与古老战争相对比的繁荣梦想。
费兰特:是的,并且那条线索延续到了现在。但是我把历史背景降到最低。我更喜欢把所有东西写进人物的行为中,外在的或者内心的。比如Lila,七八岁就已经想着要变得富有,并且拖着Elena一起,让她相信财富是一个急迫的目标。这一目的是如何在两个朋友间起作用的;它是如何被修正的,它如何指导或者迷惑了她们,这些都比标准的社会学让我更感兴趣。
Di Stefano:你很少向方言色彩让步:你使用了一些词,但你通常更愿意用这个短句“他/她用方言说道。”你从未想过用更具表现主义的渲染手法吗?
费兰特:作为一个孩子,作为一个青少年,我城市的方言让我感到害怕。我更乐意让它在意大利语中回响半刻,就好像在恐吓它。
Di Stefano:下一部作品完成了吗?
费兰特:是的,在非常初稿的状态。
“我们太不习惯于从作品出发,去寻找它们之中的一致和区别,以至于我们立刻迷惑了。”
Di Stefano:一个很明显但是又有必要问的问题:埃莱娜·费兰特的故事有多少是自传性的呢?在埃莱娜的文本中,你又放置了多少对文学的热情呢?
费兰特:如果这里的自传你是指用个人的经历来填充一个创作出来的故事,那么几乎全部是这样的。如果与之相反,你问的是我是否在诉说自己的个人故事,那就完全不是了。至于写书,是的,我总是引用喜爱的句子,引用影响了我的人物。比如,迦太基女王狄多,是我青少年时期一位重要的女性人物。

Di Stefano: “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这个笔名和作家Elsa Morante押了头韵,她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这是一个暗示吗?“Ferrante”和“Ferri”(你的出版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都只是我们想多了吗?
费兰特:是的,绝对是这样。
Di Stefano: 你从没后悔过选择匿名吗?评论更多在讨论费兰特的神秘身份,而不是关注在书本的品质上。换句话说,过分强调你的虚构身份,这种结果与你最初的期望是否背道而驰呢?
费兰特:不,我从未后悔。在我看来,把作者的人格从他的作品中抽出来,从他摆在舞台的角色中抽出来,从风景、物品,还有这种采访中抽离出来——简而言之,从他所写的语调中完全抽离出来——这是一种好的阅读方法。你所说的强调,如果是基于作品、基于词句力量的,那就是实在的强调。非常不同的是媒体的强调,让作者的形象支配了他的作品。在那种情况下,书的作用就像是流行明星汗湿的T恤,一件没有明星光环就毫无意义的衣服。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强调。
Di Stefano: 有人怀疑你的作品是多人之手一起写的,这让你困扰吗?
费兰特: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似乎是个有用的例子。我们习惯于从一位作者身上得出他的一系列作品的一致性,而不是从一部作品中找到这位作者的一致性。具体某位女作家或者男作家写出了这些书,这足够让我们把它们当做一段旅程的元素了。我们会很确定地说起这位作家早期的成功作品以及其他不那么成功的作品。我们会说他立刻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说他尝试了不同的类型和风格,我们会追溯重复出现的主题、场景、一次进步或退步。让我们换种说法,我们有可以找到的House of Liars和Aracoeli,但是找不到一个名叫Elsa Morante的作家。我们太不习惯于从作品出发,去寻找它们之中的一致和区别,以至于我们立刻迷惑了。我们太过习惯于作家在前,而当作家不在那里或被移除时,我们最后不仅会从一本书到下一本之间的发展中看到不同的手笔,甚至会从上一页到下一页之间看到差异。
Di Stefano: 那么你会告诉我们你是谁吗?
费兰特:我在20年中出版了六本书,这还不够充分吗?
埃莱娜·费兰特:小说里的一生

《险恶的爱情(Troubling Love)》 (1992)
费兰特的小说处女作,书中主角Delia在母亲意外身亡后,探寻她的家人在那不勒斯的秘密往事,揭开其中的真相。《纽约时报》评论道:“作者愤怒而饱受折磨的声音是颇为少见的。”1995年,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Mario Martone)将原著改编成电影,并在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展映。
《被遗弃的日子(The Days of Abandonment)》 (2002)
费兰特的第二部作品于十年后出版,讲述一个叫Olga的女人被丈夫抛弃,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的故事。《卫报》的 Meghan O’Rourke写道,这本书具有“神话一般,有时会让人想起美国诗人Sylvia Plath富有画面感的诗句”。
《丢失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 )》(2006)
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离婚的大学老师发现自己病态地迷恋上了在海滩上看到的一家人,作品预示了那不勒斯系列小说的很多主题,包括女性友情、母亲身份和社会阶级。 《波士顿环球报》评论道:“这篇小说笔锋尖锐,没有那么容易从记忆中移除。”
《才华横溢的朋友(My Brilliant Friend )》(2011)
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小说系列的第一作,为我们介绍生活在那不勒斯一个贫困社区的两个女孩Lila Cerullo和Elena Greco。出版人Adam Freudenheim在《卫报》中写道:“这些女性小说是我在文学界遇到过最好的刻画女性友情的现代作品。”
《新姓氏的故事(The Story of a New Name)》(2012)
Lila和Elena在越来越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与之对比的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之间逐渐拉开的文化和经济差距这一背景。《纽约客》形容此书是“充满艺术的笔触,引人入胜”。
《逃走的人和留下来的人的故事(Those Who Leave and Those Who Stay)》(2013)
虽然Elena在地理上和情感上与Lila和那不勒斯相距甚远,她们之间的联系依然存在。《纽约时报》的Amy Rowland在书评中写道:“也许你读过埃莱娜·费兰特之前的全部作品,而这本书中的暴行让你毫无防备。她的每一部那不勒斯系列小说新作,都会再一次地让你宛如初见。
《失去的孩子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Lost Child )》(2014)
四重奏的最后一章,双重教育小说的完结,延展开60年里最好的部分。《卫报》的Alex Clark写道:“我不确定自己之前读过比它更加吓人的对友情的描写,或是更加冷静的对于利用他人的观察,还是在相互依恋的关系中。”
(翻译: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