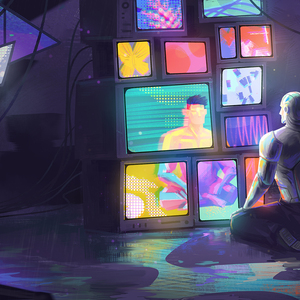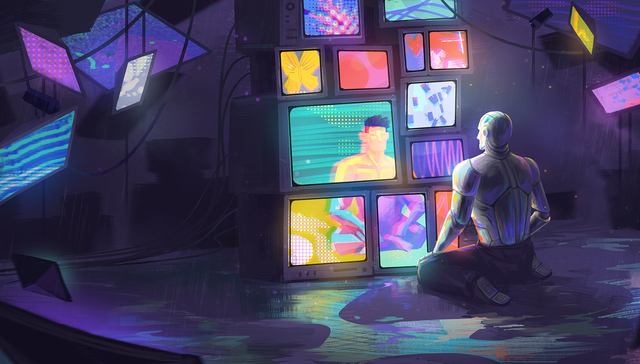撰文 | 汪星宇
编辑 | 黄月 姜妍
打开Midjourney的界面,随机进入一个聊天室,在聊天框内输入“/imagine”(想象)的命令,会弹出一个带有“prompt”(提示语)字样的方框,在方框内输入关于图像的文字描述,按下回车,等待十数秒,聊天页面里便加载出四张与文字相呼应的图像。这是使用AI图像生成工具时典型的操作体验,简单、直接、高效。
在AI的帮助下,无数没有艺术技法训练的用户,通过自然语言的交互,被赋予了图像创作的能力。即使这项能力目前看起来还不够精确与稳定,但就大众对于艺术的想象而言——用户通过自己的描述产出了“独一无二”的、“精美”的作品——似乎也足够令人满意了。

在近期一波又一波的AI浪潮里,类似的图像生成工具(包括Dall ,Midjourney、Disco Diffusion、Deep Dream、Stable Diffusion、文心一格等)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使用,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艺术家。当视觉表达的门槛骤然降低,“提示词成为了生产力”,我们该如何去定义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又该画在哪里——以及最终艺术是否会因AI而终结?
01 艺术如何成为了艺术?
艺术终结的论调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终结”并非指向艺术本身,更多是关于一套艺术叙事方式(narrative)因不合时宜而被淘汰。正如哲学教授、艺术研究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中所澄清的,“并不是说不再有艺术……而是未来的艺术将不再享有目前这套妥帖的叙事方式。终结的是这套叙事本身,而非叙事背后的物。”探讨艺术终结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挑战传统或者颠覆某一学科,而是像美国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在论述现代主义的本质时提到的,“为了使其在其能力范围内更加牢固地扎根”。那么,“艺术”是如何成为今天意义上的“艺术”的呢?

在西方古典时期,“艺术”(希腊语, tekhne; 拉丁语, ars)指的是遵循一定规则、可以通过教育习得的活动。按照这种解释,依托灵感与直觉的音乐与诗歌不算艺术,只有在音高与诗学的规则辖制下才能被纳入艺术的范畴。绘画在当时则更多被认为是一种手工的“技艺”,而非智识性的创造。

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创作出符合透视、自然和真实历史的场景,画家必须精通几何、解剖和文学知识,绘画变得需要学习、强调规则,开始跻身“艺术”(liberal art)行列。与此同时,如乔尔乔·瓦萨里在《艺苑名人传》中所展示的,个性、情感与直觉的要素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被放大,艺术定义的外延被扩展,绘画逐渐摆脱了纯粹的工艺性与实用性,开始有限地关注美学价值和视觉表达。
进入十七世纪下半叶,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的出现与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艺术”与“科学”之间有什么不同?在学科高度分化的当下,这近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回到达芬奇的时代,孕养他的是一个强调通识的、艺术与科学未做区分的大环境。法国学者夏尔·巴托在《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1746)中将艺术划分成七种形式(建筑、舞蹈、音乐、演说、绘画、诗歌、雕塑),并认为统一这七种艺术形式的核心要素在于“通过对于自然选择性的模仿来传递一种美(beautiful)”,而这是科学所不具备的。这种对于纯艺术(fine art)的认知被广泛认可,并延续至今,即使对“模仿”的阐释与对“美”的定义多有争议,“艺术”仍获得了独属的轮廓。

这套关于“再现”与“美”的叙事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摄影术发明的冲击,再现的意义被削弱,个体情感表达与平面性回归成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内核。强调形式分析的风格化叙事一度占据主导,随后又被观念驱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浪潮裹挟与抛弃。
从这个意义上讲,AI生成图像在形式与内容上似乎从未突破(后)现代艺术的范畴,巨量生成图像只是对已有艺术风格的践行或重复,甚至我们在撰写提示词时,仍然在借用传统的、风格化的术语。但AI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并不在于它生成的图像本身,它本身便是一个极度挑衅的艺术品。它的出现,就像乔托的圣母子像、马奈的妓女、杜尚的小便池一样,拓展了我们对于艺术边界的认知,撼动了(或者即将改变)艺术的生产关系与创作方式。
02 我们与AI的关系是委托创作吗?
在使用AI图像生成工具时,直白的交互机制不禁让人想到艺术史上长期存在的艺术委托传统。建筑家Iktinos和Kallikrates便受雅典城邦的委托主导了帕特农神庙的营建,达芬奇受贵族Lisa del Giocondo委托创作《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西斯廷天顶画》背后有美第奇家族的支持。后来,商业元素渗入,十七世纪的荷兰小画派与市民阶层开始连接;进入十九世纪,以印象派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与古典的学院/沙龙传统决裂,艺术进入了画廊、咖啡馆与日常的生活;二十世纪的两次战争使得西方艺术的中心从巴黎转向纽约,艺术相关的商业活动愈发兴盛。但艺术委托或者艺术消费中间仍旧存在着委托人/消费者与艺术家/创作者的两级,而在AI图像生成的语境中,这样的角色分界似乎正在被打破。

乍看上去,我们与AI的关系就像委托人要求艺术家按需创作,这种创作更加直接、廉价且高效。但其成立的前提在于将AI看作一个独立且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我们之间存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与平等关系,否则它只是一款机器、一个工具,或者某种意义上人类意识的集合。事实也是如此,我们面对的,更多是一个接受需求,给出反馈的界面,背后是尚且无法完全解释的黑箱式流程,是建构模型(如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输入代码、监督机器学习的科技公司,是训练AI的大型语料库和图像库,也是承载这些数据库的物质基础设施。
无论如何浪漫化这一过程,我们与AI的互动基本还是停留在接受指令与反馈指令的任务本身,所谓“智能”更多是产品体验上的想象。AI之于用户的价值,就好像画笔与颜料之于艺术家的价值,根源上还是工具性的、物质性的连接,只不过其中物质的循环在高算力的媒介中被急剧地加速——我们所提供的文本与图像,既是创作的要求,也成为了创作的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AI图像生成的语境中,我们既是委托者也是创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在艺术史中从未出现过的角色在当今的艺术生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科技公司。数字艺术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科技公司提供的软件工具,这些新的媒介限定了电子图像的控制参数与改造空间,将展示的界面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从实物载体转移到电子呈像,为艺术家的视觉表达创造了充分的可能。但我们也需要警惕,这些科技公司通过所谓非功利的图像收集和对于AI中性化的工具塑造,试图掩盖对于视觉艺术家作品的版权侵犯,对于艺术家传统工作方式的颠覆性破坏,以及对于大量不可见的廉价数据劳工(包括我们)的剥削。当我们沉浸在使用AI自由创作的快感时,也需要意识到这中间存在的大量尚未解决的道德争议。

03 怎样的“调教”有怎样的图像?
当用户在各种平台上讨论AI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语是“调教”。这当然是一个有些戏谑意味的表达,说明用户希望通过有效的控制得到精确的产出,但其中也影射着我们对于AI理解的微妙处——对AI的控制是有技巧的,但又没有固定程式。其中核心的控制步骤便是撰写提示语,不同的表述会直接影响画面的最终效果,而这与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也不无联系。
在写提示语时,我们需要确定画什么,画人、画物、画建筑、画空间或者画特定的母题,就像古典时期的艺术家会在正式创作前绘制大量的草图,明确画面的主题对象、构图方式、或者做一些技法的练笔。其次便是怎么表现这些对象,在提示语的表述案例中,大多的输入都是笼统的、关键词式的、风格化的,但对于艺术家(排除action painting等特定风格)而言,这些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手与材料真实接触后的技法实现。
最终,我们怀揣着不确定的忐忑迎来了AI的答卷,在其中找寻对自己诉求的回应,又常常因为某些意料之外的呈现而感到惊喜;但对于古典时期的艺术家来说,一幅画的创作尾声常常只是对于细节的填充与修补,总体的效果在构思时便已经由反复的斟酌而确定。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目前的AI制图带有一种强烈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赋予了作品妙手偶得般的创造力与易逝感——就好像同样的提示语不会反馈出同样的图像,但同时也使得作品缺乏作者性和人与材料的互动,使其与创作者生命体验的连接过于微弱。如此的创作过程是疏离的、旁观的、缺乏表达的,文本与图像的互文,知觉与视觉的通感,在一种不可控的被动的视觉接收中被理想化地达成;而用户所感受到的满足,大约或多或少源自一种言出法随般的赋权,以及审美与创造力平均化后的自负,而并非一种真实的投入性的创作体验。

但AI图像生成的随机性并非一成不变的,如同控制论思维(cybernetics)是整个机器语言的底层逻辑一样,这项技术必然向着愈加可控的方向发展。一开始可能是文本表述的精确度不断提高,形成一套标准的、明确的形式分析术语与范式,使得AI能更可控地输出预想的效果(ChatGPT的AIPRM插件中有辅助Midjourney提示词撰写的功能;Midjourney也可以通过“/describe”的命令将图像转化为精准的提示语,从图像与文本的两端来学习如何与AI沟通)。或者AI的文本阅读能力能够得到提升,我们可以输入更大段、更细腻的文字,AI也能够更“共情”、更定制化地给出回应。之后也许我们将不再依赖于文本,大脑中的画面得以直接视觉化地呈现,或者我们能够在虚拟的感知空间内更自由地对视觉元素进行创造与调整。
控制与混乱,精确与随机,是AI图像生成技术需要平衡的两个端点,我们对AI的期待不再只是一种依附于使用者本身的静态精确,但可能也不是如今这样难以进入的旁观。它也许是商业实践中保质保量的图像生产,也许是对于个体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也许在更集体的层面,只是一种对于文明的温习。
04 尾声:是终结,也是新的开始
艺术是否会因AI而终结?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当下现代主义的、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叙事,已经无法有效阐释AI带来的有关艺术生产关系与创作方式的变化。
但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的答案,终结意味着将迎来一套新的艺术叙事。而整个艺术史的演进本身就是在内外力胁迫的绝境中自我突破的过程:当马奈毫不掩饰地展示颜料的粗糙肌理时,当杜尚将现成的小便池送入艺术展览时,当观念艺术家们抛弃掉对形式本身的执着、追求纯粹意义的表达时,时人也一定在追问与怀疑艺术的去向。艺术史又在此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从装饰性、再现性到表现性、观念性——直到今天,在一个图像泛滥、AI兴起的视觉时代,我们再次来审视艺术的终结。
如果说形式导向的艺术支流经过漫长的跋涉汇入了一片汪洋,观念导向的艺术流脉也因为表达话语权的平均化而枯竭,未来的艺术叙事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疑问句,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肯定句。或许艺术将更加依赖经验的感知,或许艺术将变成纯然的想象,或许艺术会依托元语言的泛感官表达——至少我们能够肯定,一种新的艺术生命体正在成为现实,而AI将是它的重要注脚。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艺术史论学士,纽约大学媒体、文化与传播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