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为人父母者几乎都经历过以下的场景,尤其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忙碌了一整天以后,你在傍晚回到家里开始准备晚饭,但这与企图在一场暴风雪中做饭无异。孩子哭闹不止,炉子上的意面已经快要溢出来了,面试后很久都没有音讯的雇方忽然打来了电话,门铃响声大作,而你则是家里唯一的一名成年人。
不妨想象一下,在你手忙脚乱、应接不暇之际,某个人来到你面前说:“嗨,我这里有些巧克力。我可以现在给你这些巧克力外加5美元,如果你愿意再等半小时,那你在巧克力之外还可以得到10美元。”你一面试图把刚学会走路不久、紧抱你的小腿不放的孩子打发走,一面伸手去关掉炉灶,并回答说:“把巧克力和5美元放在台子上,赶紧走。”迅速做出此决定,意味着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就此少了一件——且厨房里也会少一个人。你并没有时间做出看起来更优的选择,即得到同样多的巧克力以及两倍的钱,而条件不过是稍候片刻。
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有助于减轻些许负担的支持系统(support system)。传感器在检测到沸水即将溢出时,便会关掉炉子的火。一个数字助理在响铃三声后会接听电话并回答:“抱歉,我有几分钟没空——请在五分钟后再来电。” 门廊里的传感器会播放语气严厉的录音(可能还配有高亢、渐强的狗吠声作为背景噪音):“闲人免进”。至于小孩……好吧,目前还没有对付他们的技术。但如果有数字助手(digital supporters)来帮你分担这类琐事,你就有空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了:稍后再拿巧克力,以及获得双倍的钱。
手忙脚乱的父母们并非有望凭借这些小工具(gadgets)来缓和精神压力的唯一群体。一项研究要求飞行员在飞行模拟过程中每听到一次表示有危险的警报时就按下某个按钮。在超过三分之一的情形当中,志愿者飞行员并没有记下声音,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警惕。从事此调查的研究者还在这些场景中扫描下了飞行员的脑电图(EEGs)。扫描结果显示,任务密集的飞行场景所提出的要求在大脑中造成了认知瓶颈,甚至于紧急的听觉警报也无法突破它。

神经人机工程学家目前正在研究应做些什么来打破这一混乱局面。他们追踪了我们在注意力、执行功能、情感与心绪均游移不定时的身体变化。他们甚至还推测了我们的各种生理反应之间是如何协调与同步的。
这一领域的学者试图改善某些活动的安全性,例如飞行,现实世界中的相关悲剧可能就源自人类的失误。他们运用神经科学方法来理解大脑的运作,以及为什么大脑有的时候会酿成灾难性的错误或疏忽,如没有记下大声且不间断的警报等。一旦这些模式得到了认识,那我们就能运用各种机器来予以探测,并与它们的人类“伙伴”一同合作,以减轻负担,防止不利后果。

我们需要协助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资源有限。人脑绝不是有如永动机一般的信息处理器。它的有机结构和一棵橡树或一只企鹅没有太大区别;它的能力是有限的,所能利用的能量数目也是有限的。我们的认知工作量就等于我们运用这些资源来做出决定或完成任务的能力之总和。
这一情形中的慎思系统(deliberative system)处在大脑的前部,即前额叶皮层。压力下的过载在N-back任务当中体现得很明显,这一任务会对工作记忆施压。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是我们分析信息来实现即时回忆的“场所”,例如记下我们正打算加入的视频会议的密码。在N-back任务中,测试的参与者需要记下某一序列中的项目是否是之前已经看过的。一开始的难度很低,序列里只有一两项,随着项目量的提升,前额叶皮层会抵达其极限,效率随之下降。一项研究表明,当这个“n”或者序列里的项目数达到7,前额叶皮层就会“举手投降”并表示放弃了。结果便是决策能力的崩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脑过载的时候会做出更多冲动性的决定,因为我们没有按照意愿来运用慎思能力的余地了。我们都经历过那种认知过载的感觉。注意力、记忆以及执行功能的需求量若是太大,我们的空间就会耗尽,进而就会开始忘事、把计划搞砸以及犯下一些很严重的过失。

今天,我们的过载频率已经远超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过载。你甚至必须处在特定的年代才能记下诸如“(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结束于周五下午五点,且在下周一早上之前一般都不会重启”这种时间。但那也已经是过去式。如今拜电子邮件、短信和社交媒体所赐,我们的同事可以全年无休地进入我们的个人空间以及口袋里——还不只是工作上涉及到的人。世界各地的人也总是处在我们的空间里,随之而来的就是智能手机上的多重信息流,导致大脑被淹没,继而产生信息过载。
从神经人机工程学的视角看,我们可以开始探索一些减轻此负担的办法了,无论是运用模拟、数字还是有机的小用具。哪怕小用具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过载的始作俑者,它们还是能成为缓和现代世界需求激增的必要解决方案。
小工具令人们无需手工追踪时间的流逝,解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
诸如此类的小工具可能与钻木取火的历史一样悠久。迄今所知的最古老日历显示了一万年前的人追踪月运周期的方式,他们不只依赖自己的记忆,还参照月相的形态精心挖掘了许多的坑洞。这一土制日历2013年在苏格兰重见天日,上面甚至还标出了冬至的日期。
古希腊人在几千年前就开始运用一种名为安提基特拉机械(Antikythera Mechanism)的复杂机器,使计时水准再上了一个台阶,它有时也被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计算器。据推测,其用途包括追踪月运周期、行星位置甚至于奥运会等赛事的周期。从算盘问世到电子计算器的普及,这些小工具令人们无需手工追踪时间的流逝,解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甚至还能执行相对简单的数学运算,尽管可靠性有高有低,而今天我们对它们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

虽然现代的研究用来精确测定脑电波变化模式或心率上升的小工具要相对复杂一些,一般而言,我们也仍不需要技术来告诉我们自己的大脑何时才需要使用神经人机工程学支持伴侣。
这一伴侣不一定非得是机器。有研究提出,在情感、职业或教育方面共度过一段时间的人,其脑电波已开始显示出同步性,彼此间会及时产生共鸣。一项于2021年慕尼黑神经人机工程学大会上宣读的研究指出,这种同步超越了脑电波。据作者们的报告,与在不同课室上课的学生相比,在同一个课室上课的学生的心率和表皮反应都有同步现象。他们的结论是,这些措施可用于显示学生何时对课程丧失了注意力。这一研究结果还表明,当心灵汇聚在一个知识共同体中,同步就有望发生,负担的分摊可为集体创造出更多的决策及问题解决空间。
集体心灵的概念意味着,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种群当中,原初的设定并不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心灵独揽所有工作,而是多个心灵在进化的影响下协同运作——这一观念不算新颖。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2017年即推出了合著的《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独立思考》一书。他与另两位作者近来又提出,个人在使用自己的大脑时也得依赖来自其他人大脑的“部件”,他们称此为“知识共同体”(community of knowledge)。
他们所阐发的观点之一,是我们在解决问题、做出决定乃至于运用记忆时,彼此都是相互依赖的。这一依赖性的意义是,我们经常会把自己的信息外包,凭借我们与他人的联系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而非闭门造车。如他们所注意到的,我们经常会与他人的大脑相连接,不仅是附近的大脑,还能跨越时间与空间(比如你与我现在就处于连接状态),从其他心灵处获取信息,并将其整合进自己的知识库。只要有世代相传的古老记录,我们甚至可以从数千年前已经逝世的人那里摄取观念。

[美]史蒂文·斯洛曼/[美] 菲利普 ·费恩巴赫 著 祝常悦 译
中信出版社 2018-1
当我们将他人收集来的信息加以组织,使之形成一种可相互确认的社会模式时,我们就有了文化。文化既是助力,也是负担。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理论生命科学高级研究员塞西莉娅·海耶斯(Cecilia Heyes)就著有《认知工具:文化进化心理学》一书。她主张,对于一些在我们看来具有社会性的行为而言,人类并不是生来就有与此对应的内在本能,但我们的确是生来就装备了诸如记忆、注意力以及模式识别能力之类的工具,以学习这些实践。进化提供了基本的工具包,但让这些工具在社会上得到锤炼、继而发展出相应技能的则是文化,每一种文化在做这件事时都有其专门的、独特的方式。
海耶斯以一系列达尔文式的术语来形容此过程,某些形式的实践在特定环境中幸存了下来,另一些则消逝了。存续下来的实践可通过“社会学习”来传给后人。
较少的负担容许我们把更多时间用在慢思考上,运用我们最优越的问题解决工具
她将这一我们社会地而非先天地运用的装置称为“认知工具”。按她的论证,有了先天的工具,我们就能造出具有社会性用途的“小工具”,例如可以模仿其他人,一般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此类小工具可以是某种形式的神经人机工程学捷径,有了它我们就不用每次遇到别人都重新学习微笑的意义——这种现象的自动化性质为其它流程省下了大脑空间。
在我们一同参加活动时——不论是散步、烹饪还是用餐,我们也会和他人的心灵打交道,而且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彼此分享心中之所想。有了这种相互性(reciprocity),我们就能分享问题、梦想与欢乐,这种分享如果采取较健康的形式,那我们就能得到支持、洞见或是他人发自内心的欢乐这类回馈。在这一人际系统中,我们卸下了一些认知负担,邀请其它大脑加进来解决问题,提供有用的经验来帮助理解问题,或只是分享情绪,暂时忘却一下负担。
海耶斯主张,假如她所谓的“小工具理论”是正确的,那下一步的推论就是,我们文化实践中的现实小工具可以“令我们的心智能力产生迅猛的文化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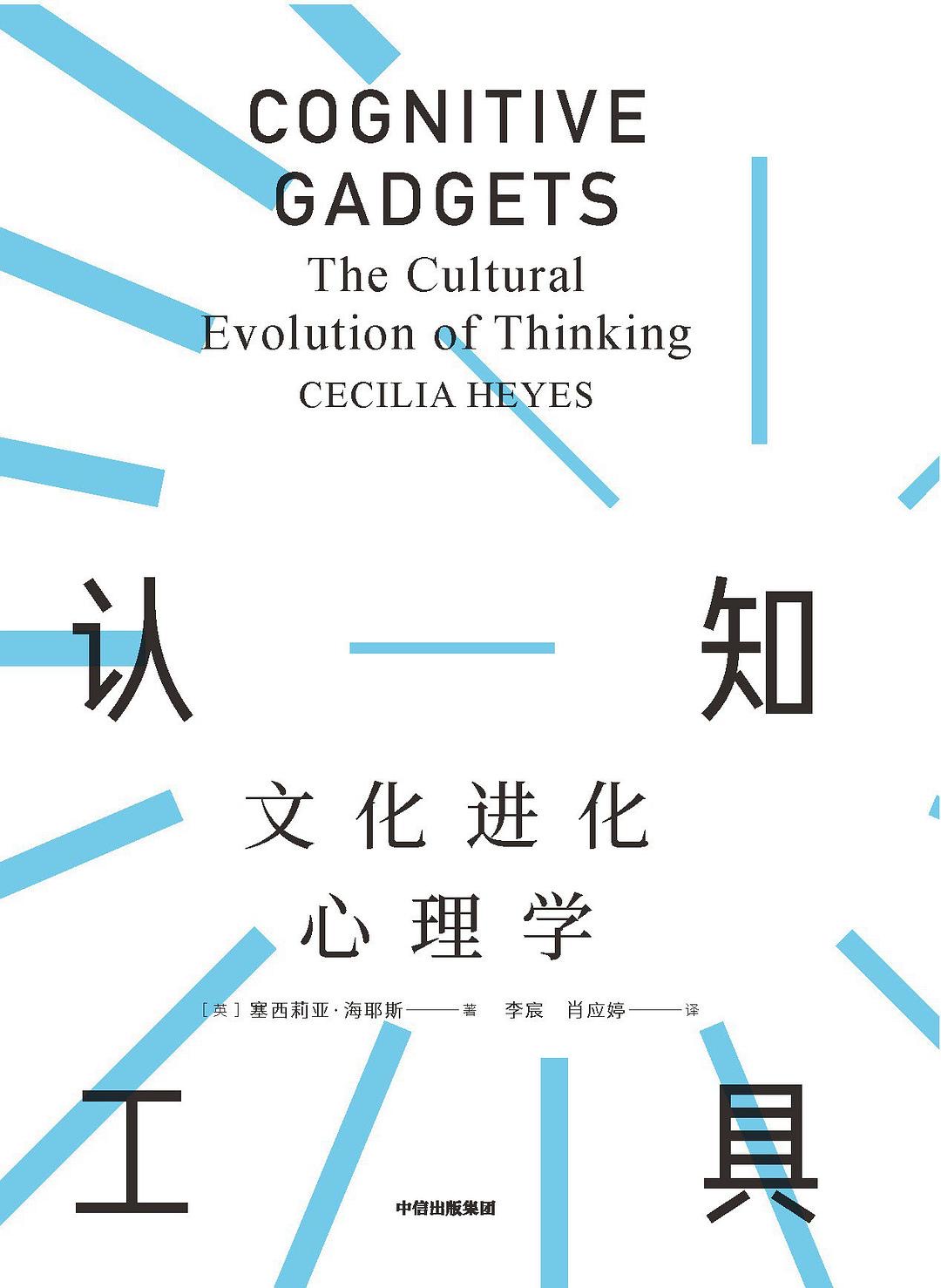
[英]塞西莉亚·海耶斯 著 李宸/肖应婷 译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2021-4
这一预测似乎也是成立的,若干现代技术已经帮助我们显著提升了认知测试的成绩。许多人认为的确有智商这回事,甚至于它在人的一生当中也是大致不变的,我(指本文作者Emily Willingham)在2021年的《量身定制的大脑》(The Tailored Brain)一书里对以上两大主张都表示了质疑。智商已经被证明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极度不稳定的一项指标,它受到被试者的动机、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差距及学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变化的典型范例之一,或许就是“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它似乎印证了有关认知小用具足以促成“心智能力”之巨变这一预期。
弗林效应乃是新西兰智商研究学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新近记下的现代社会一大变化。他发现,仅在20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里,许多国家国民的智商得分就有实质性的增长,以至于如今都可归为“天赋过人”的行列。弗林认为,现代社会里教育渠道的更新,催生了日益增长的问题解决需求,而这也许能解释智商测试成绩在同代或代际间的提高。在成长过程里,我们的先天工具会受到现实世界中认知工具的种种磨砺,二者会产生相互作用,这逐渐成了一项全球性的重要特征。
技术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释放我们的认知空间(除非你每天刷5000次以上社交媒体)。例如,我们不再需要把天生的工作记忆用在电话号码、方位甚至日程表上。较少的负担容许我们把更多时间用在慢思考上,运用我们最优越的问题解决工具,使我们可以少犯错误。
一些研究提出,与智商测试分数较低者相比,成绩更好的人群能够容纳更大的认知负载。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智商与更高的处理效率有关,而更高的效率意味着事半功倍。如果我们的技术小工具能以同样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效率,为我们留下更多的认知库存,那大部分人就已经属于人机系统里的一部分了。未来已经降临。
事实上,这些技术小工具是无处不在的。在一些环境中,人们易于犯下严重且代价高昂的错误,此时的关键就是维持注意力以及防止走神。有研究表明,在丧失必需的注意力之际,我们前额叶皮层的使用率也会下滑,而这里是人类大脑中一切成熟而深远的思虑之所在。专家指出,有三种保持该区域活动、防止其停摆的方式:一是改变人们参与任务的方式或者调整“用户界面”,二是调整任务本身并降低它的认知要求,三是在人们的决策能力濒临崩溃时予以警告,以便其采取反制措施。

无论科技含量高低,数字小工具都当下地发挥着减轻此类负担的功效。日历的提醒功能可以让你在特别繁忙的日子里免于记忆池过载之忧。我会为一项活动设定三次提醒——两天前、一天前、半小时前——这使我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至于忘记重要会议。
不过,与未能听见警报声的飞行员类似,这些电子邮件提醒迟早也会淡出我的脑海,为此我又加了一道保险:我会把最新的邮件提醒放到收件箱顶部,标为未读,这样它的标题就是加粗的。虽然已经和电子邮件打了三十多年交道,“未读”邮件还是能抓住我的全部注意力。在会议真正开始前,我一直能看到这封粗体的“未读”邮件并保持警觉。至少对我来说,这一神经人机工程学策略可以把我从某些精神状态中拉出来(如走神或者专注工作以至于忘记了时间),激发我的神经活动,继而提升我的表现——以及不要错过会议。用研究术语来说,就是我已经“调整了用户界面”。
我们也可以对日常任务进行微调,以减小它们所施加的认知负载。将高要求的活动简化为机械重复的工作就是一种策略,例如每天中午都吃一样的东西。另一种策略是限制必须一次性完成的高要求活动的数量,例如在前一天晚上就定好第二天的穿着,而不必一面催孩子出门上学一面想怎么搭配衣服。我们能够诉诸的最为直接的神经人机工程学调适方法之一,就是把任务安排到相对不那么拥挤的时间窗口里,这样它们就不会短时间内堆积如山。如果星期天下午恰好有空而可以一次性把下周的餐食准备好,进而省掉五个“在厨房里不知所措”的傍晚,那这个调整就是相当值得的。
最大的风险与大脑被“劫持”有关,此时现实世界的小工具遭到了坏人的利用
在设置这些个性化、体面且节省脑力的支持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尝试扩展自己心灵中的空间。体育活动就是一种绝大部分人都易于诉诸的方法。新近发表于2021年神经人机工程学大会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年轻男性群体中,单腿的踏板运动可以提高前额叶吸收氧气的能力,继而使执行功能测试的成绩得到提高。这些发现与另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年轻男性及老年群体的研究的结论一致,其中绝大部分都提到了血液流动与氧气输送这两点,另有部分证据显示某种分子的增殖可帮助神经元之间产生新的连接。这些效应都指向更高效的认知处理过程,使人对认知负载的感受不那么强烈。
我们甚至可以针对自己来做神经人机工程学研究,以打开一扇内在的窗户,洞察我们自己在认知过载时究竟是什么状况。目前它尚且无法告诉我们是否已处于决策能力崩溃的边缘,但我们距离那一刻也已经不远了。
“可穿戴设备”——智能手表、健身手环等——已经可以监测你的心率及其变化态势,这两项指标都会随认知负担而波动。与预期一致,你在认知过载的时候心跳也会加速。最近我自驾旅行时在冰天雪地里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当时手环提醒我每分钟心跳已经快了若干下,且这一增加一直维持到这次紧张不安的旅程结束。有研究就指出,心率的变化区间在过载状态下会变窄,这反映出人针对输入的波动进行弹性化调整的能力变差了。这种反馈在消费级应用方面目前还不算成熟,但我们正在大步前进,迟早可以求助于手腕上的小工具来洞察自己的内在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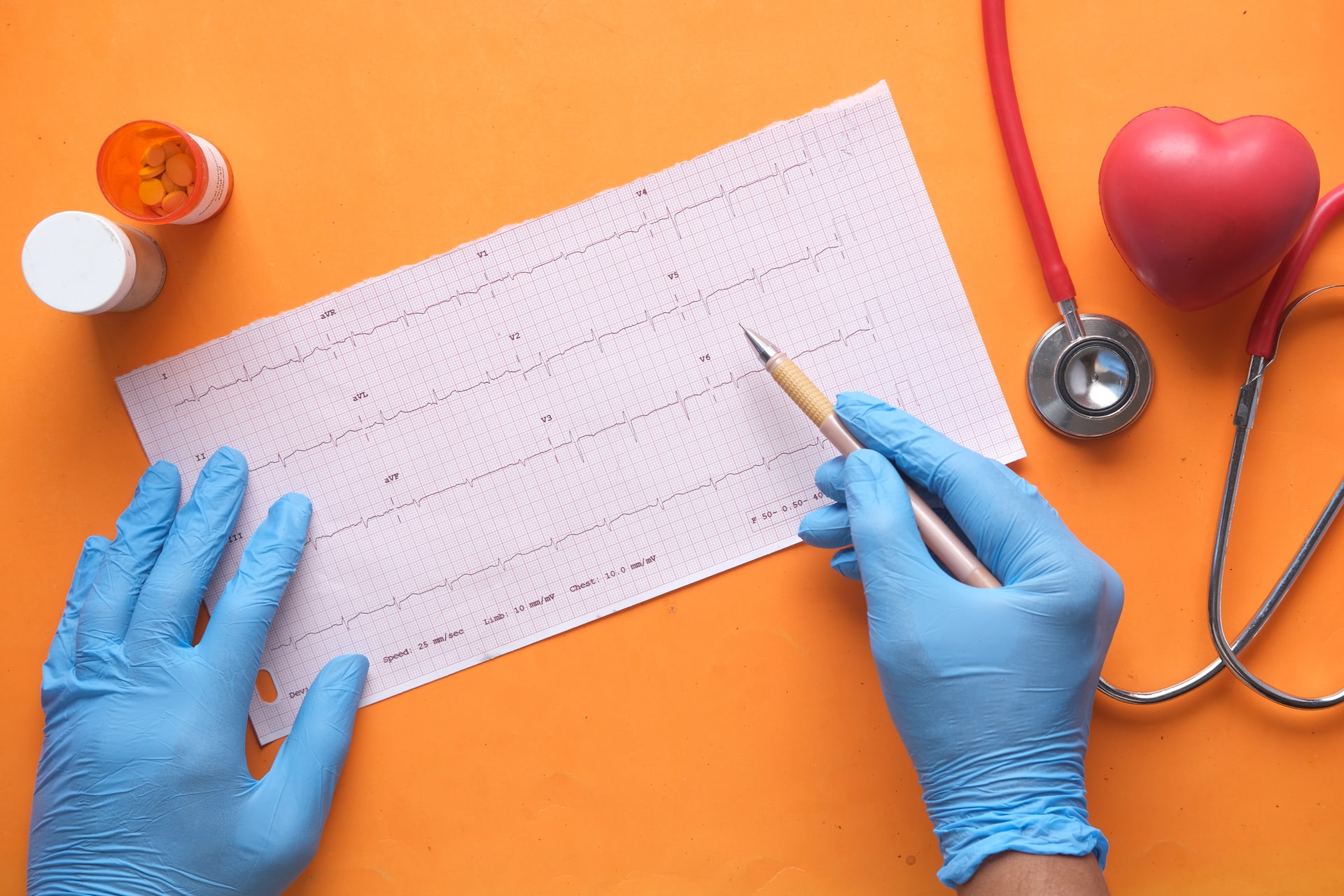
上述以及其它一些措施已能应用于更大的舞台以及更严格的任务要求。研究者评估了NASA控制室里的人员在火星任务期间使用这些设备的状况。负责任务控制的人员必须在存在26分钟信号延迟的状况下与火星车互动。在最初的90个太阳日里(火星的一天为24小时40分钟),依照常规安排,负责向火星车发令及下载其信息的工作人员每天要不定期轮班。火星与地球在一天时长上的出入,意味着每一班次的开始时间都不同:某周某天早上8点的工作,到下周同一天可能就晚了5个小时。此类巨大变化可能会让地球人的大脑产生紊乱。在间歇期里,团队必须计划好下一次通讯时要向火星车指派哪些任务,一张清单上可能会有数百条命令等待运行。据一项估计,哪怕只有一条命令出错也会造成高达4亿美元的损失。
这些任务当中有一部分是可以自动化并且交给机器的,但并非全部。鉴于此,监测控制室人员的生理状态,估计其认知疲劳的发生时间以避开错误的高发期,可谓事关重大。
怀着有朝一日开发出此种监测手段的期望,研究者们列出了一张包含28个“工作负载指标”的表,可用于识别一些与易犯错状态相关的模式。这些指标包括心率的变化态势、眨眼、言语模式、瞳孔扩张与脑电图记录。这里的考量是,我们可以通过算法来获取这些信息,进而调整“人-机”团队中人类的工作负载要求,不过这些模型目前似乎都还处于开发过程中。
个人并不是NASA,但我们也许有能力处理研究者提出的指标当中的某一部分。某团队正在开发适用于学生与教师的可穿戴设备,它们可以探测体温、心率以及“皮肤电活动”(electrodermal activity),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意识到”学习习惯以及追踪相应的趋势,以做出调整来缓和过载状况……对于教育者而言则可预测学生在某项活动中的参与度以及专注度。
有了周全的准备(我懂,疫情当前要摆出善于做“计划”的姿态),我们就可以强调一下人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某些接口的好处。设想一下,未来的机器可以将我们的认知小工具与人际间的记忆连接起来。 我们也许能以这种方式来填补小工具上的差距,或体验并真正地感受到成为另一个人有何滋味。在记忆开始消退或需要检查其准确性之时,依靠外部存储以及将记忆传给另一个大脑,很可能会成为保存记忆的良方。这将是一种保存祖先回忆以及连接先人大脑的全新方式。
毫无疑问,这些计划里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元素。在构想一个脑机接口与人机合作办公的世界时,担忧总是少不了的。最大的风险与大脑被“劫持”有关,此时现实世界的小工具遭到了坏人的利用,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脆弱时刻并恶意使用了信息。此外,在使用者是谁、其目的是好是坏、谁更容易受到不利影响以及谁可以借之来谋取利益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可能会导致鸿沟的不公。
如哈耶斯所指出的,我们或许可以用先天工具来开发、调试及更新认知小工具,但真正需要我们关注及警惕的,也正是我们视之有用但同时又有其阴暗面的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反复重演的一幕,就是先开发技术,后考虑如何限制其滥用与剥削性使用,哪怕我们具有足够的集体智慧来防患于未然。面对我们将如何使用如此巨大的力量这一问题,乐观态度是很难有的。但我们也必须牢记,人类的乐观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尽管它也得像我们所用的其它工具一样接受锤炼与打磨。
本文作者Emily Willingham系美国作家,著有《阳具:来自动物阴茎的生命课》 (Phallacy:Life Lessons from the Animal Penis)以及《量身定做的大脑:论氯胺酮、酮类与伴侣关系,教你如何获得更好的感觉以及更敏捷的思维》,现居旧金山湾区。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