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找到一个新词来形容人们在封城结束后滋生的那种希望与警觉相交织的奇特心态。温布利球场和温布尔顿中心球场近乎满座的场景令人无比欣慰。但人们真的有必要把距离拉到如此之近吗?用得着如此兴奋地载歌载舞吗?他们真的需要在得分以后把别人的头挟在怀里来表示友善吗?好吧,答案是肯定的——体育赛事上的粉丝行为就是如此。生活逐渐恢复开放,但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如何和自己不熟悉的人打交道。眼下必须重拾这些礼节。我们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以前那样,怀着平常心与陌生人闲聊?握手已经不时兴了吗?“口罩政治”已经让人们变得相当不耐烦了,但随着商店、巴士和火车的人满为患,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而言已经颇为沉重,而新冠疫情则让情况雪上加霜。近来有调查表明,社会信任已呈现滑坡之势,人们对移民、难民及其他被视为外来者的人群的态度更趋强硬。边境墙在各国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边界管控措施与移民政策日益收紧,冷战后资本主义宣扬的“没有国界的世界”已经沦为了泡影。而我们败坏的政治与文化战争则意味着,陌生人之间讨论争议性话题经常容易滋生怨恨并引发骂战。
把大部分生活转移到网络上是无济于事的。社交媒体及其过度分享(oversharing)的文化,加上其古怪而混杂的公-私话语基调,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将陌生人聚集在了一起——潜水、偷窥和随意插入他人对话。其后果之一,便是一项令人哭笑不得的预设,即人们可以公然闯入陌生人的生活,然后指责对方是如何的愚蠢与错误。另一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是,仅凭主观认定他人有不当之举,便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拍摄他人,继而将照片发布到公共空间,以求让对方“出道”。在网络上,我们忘记了陌生人也和自己一样有缺点、脆弱性与复杂性。相反,我们围绕着自己的生活,惹出一堆相互关联、没完没了的事端,陌生人则是这些故事里令人恼怒的虚构角色。
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就会接触到更多的陌生人。最近有一批新书专门探讨了如何更好地与陌生人相处,对我们不无帮助。乔治·马卡里(George Makari)的《论恐惧与陌生人》(Of Fear and Strangers)以及汤姆·卢茨(Tom Lutz)的《陌生人的好意》(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将于今秋上市。威尔·白金汉(Will Bucking-ham)的《你好陌生人:我们如何在一个断联的世界里找回连接》(Hello Stranger: How We Find Connection in a Disconnected World)与乔伊·基欧汉(Joe Keohane)的《陌生人的力量:在一个充满怀疑的世界里连接有何益处》(The Power of Strangers: The Benefits of Connecting in a Suspicious World)7月之内即会出版。这两本书的文风和方法迥然不同,但正如其标题所言,它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一样的。

基欧汉在书中援引了丰富的社会心理学前沿研究成果,其结论表明,与陌生人建立连接有助于消解党派思维与僵化判断,提高社会团结度并使我们更加投入自己的生活、对生活抱有更大的希望。白金汉的解释更加个人化。2016年时,白金汉的伴侣因癌症去世,巨大的悲痛一度令他麻木,而路边的种种邂逅则帮他找到了安慰。与一名咖啡师交谈片刻,或者在火车延误后与同行的乘客闲聊几句,皆让他坚定了如下的信念:世界还有转机,生活仍将继续。“陌生人与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没有干系,”他写道,“而这一缺失恰能减轻我们自己的负担。”
在古代,对陌生人热情好客乃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基欧汉引用考古学证据指出,这一义务诞生于一万年前,在第一个定居下来的人类社群里便已经存在了。陌生的旅人之所以获得重视,是因为他们能带来贸易、新闻和八卦。以礼待客的义务还根植于人类对自身脆弱性的深切体会——即意识到在一个没有安全网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可能漂泊无依和陷入窘境。

古希腊人在生活中有一套严格的对待异乡人的礼节(code of xenia),这个词大致可以翻译为“与客人的友谊(guest friendship)”。如今我们使用的排外心态(xenophobia)一词的字根即来自希腊词xenos,它兼有“陌生人”与“朋友”的含义。这套礼节规定,主人有义务为陌生人提供最好的座位、食物和床榻,临别还要赠送礼物及提供交通工具。在从特洛伊返回伊塔卡的旅途中,如果奥德修斯遇见的村民没有遵循这套礼节,他就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漫长的旅程。如今,面对从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乘小舢板远道而来的难民,希腊岛民为之提供饮食和住所,也体现出对这一古老契约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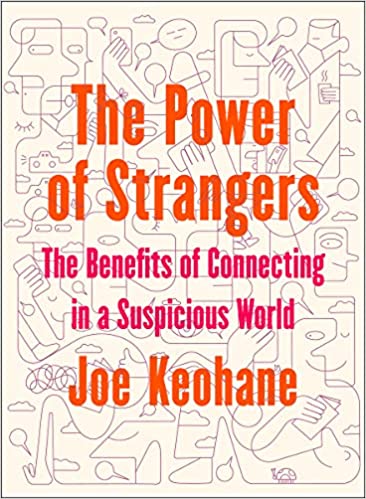
许多神话和民间故事里都有看似低贱的陌生人实际上是贵族、王公或是圣者的桥段。宙斯假扮成四处讨饭的乞丐,奖赏欢迎他的人并惩罚亏待他的人。在《圣经》里,人们接待陌生流浪者并为其提供食物,后来发现其真实身份是天使。在日本的民间传说里,异人(ijin)或者说“不同的人”通常表面上是肮脏的乞丐或穷苦的游民,实则是王子、祭司或是神祗。隐瞒身份的陌生人对我们来说构成了一种人性测试——如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大概都通不过这项测试。
白金汉和基欧汉在书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令人羡慕的外向性格,街边偶遇即能让他们兴奋不已。基欧汉的书里有一条叙事线索,讲述他向专家学习与陌生人交谈的技巧,但却发现自己并不太需要这种帮助。他举了一些教人如何开始谈话的模板,但每一个都是我这种胆小鬼不敢用的。(例如:“不好意思,我明白在火车上不该和人搭话,但我确实很喜欢你这件衣服。”)白金汉的视野则源自他在教区牧师之家长大的经历,这里既是一家人的住处,又是社区里的活动中心。他是那种会让陌生人睡在自家沙发上,然后一时兴起去保加利亚或者缅甸旅行的人,更能很快和当地人交上朋友,藉此找到免费的食宿,临走时还能得到新朋友赠送的去往下一目的地的汽车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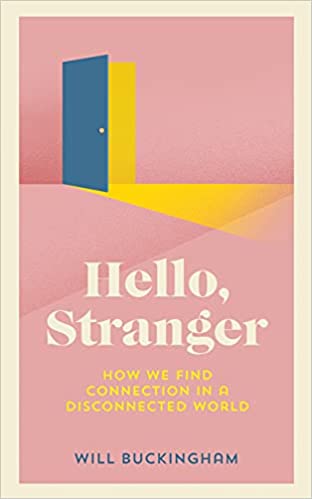
好在这两本书都没有苦口婆心地鼓动我们也变成两位作者的样子。白金汉十分清楚“我们对陌生人的反应总是有两面性——有一种混杂着焦虑、可能性、激动与恐惧的颤栗”。客人(guest)、主人(host)、好客(hospitality)、敌意(hostility)、人质(hostage)这些源于同一字根的词,皆内在地反映着某种矛盾心态。拉丁语的hostis一词兼有客人、陌生人和敌人这三层涵义。
正如尼采所言,“好客的目的在于化解陌生人的一切不友好感受。”希腊人对待异乡人的方式,是以恩惠来缓和担忧,但这种做法也极有可能滑向侮辱与冒犯。《奥德赛》里就有很多不称职的主人和宾客。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不但没有向奥德修斯及其属下提供食物,反而声称自己不惧怕陌生人的保护者宙斯,还吃掉了好几名属下。奥德修斯回到故乡伊塔卡之后杀掉了一群滥用主人好意、擅自占据他人住所的人。
对陌生人有防备心是很自然的。婴儿成长到8个月以后便会体验到“陌生人焦虑”,面对不熟悉的人时会回避眼神接触以及哭泣。深切的依系构成了我们的感情生活的核心。在新著《朋友》(Friends)里,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人们能真正予以关切的人有一个数目上限。平均而言,我们会有5个密友和150个普通朋友,这和一个狩猎-采集部落或中世纪英国村落的规模是一致的。此限制发端于我们的认知能力,以及在维系友谊上所能投入的精力和时间。邓巴还有一句逆耳忠言,那就是“关于朋友很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在天灾击倒你之前就与他们结交”。好朋友向你伸出援手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好心的路人。

拥有密友和友善对待陌生人并非截然对立。邓巴认为,牢固的友谊“有助于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笃定,使我们更信任自己生活其中的更广大社群”。而基欧汉也提到了一些强调“最小社会互动(minimal social interations)”之价值的前沿研究,这些研究主张,此类互动并不是亲密关系的替代品,而是与之相辅相成。陌生人带来的人类连接具有新鲜感,且不会怀有太高的期望。陌生人有时还能一眼看透你的底细,洞悉你的深层自我的微妙变化以及无意识举动,而长期以来已经与你建立了默契的朋友是注意不到这些的。
中世纪以降,陌生人关系经历了变迁。前现代的生活更偏向公共,陌生人经常会在社群里的长桌上一同用餐,由于空间而非性的缘故同床共枕,大小便也都在彼此的眼皮底下。进入16世纪,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称的“文明化进程(civilising process)”在全欧洲范围内推展开来。在埃利亚斯看来,其关键在于民族国家的勃兴及其对垄断暴力运用的主张。社会生活从此变得更加安全,与陌生人打交道也更少以纠纷和争斗告终。公共场所的行为准则变得更趋严格,对自我克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人们在生人面前受到了更周全的护卫。
现代城市的兴起则将以上所有因素熔冶于一炉,将所有陌生人置于一种物理上亲近但情感上疏远的境地。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其1903年的经典短论《大城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中提到,在这种限制之下,城市居民无视邻居,以空洞无神的眼光打量着巴士与火车上的其他人。但西美尔也认为,要是没有这种从城市的固有特质中衍生而来的限制,城里人将会“陷入一种无法想象的精神紊乱状态”——被陌生人看见,于无声处受其评价,乃是现代大都市的宿命,“冷眼看人”乃是重要的自我防卫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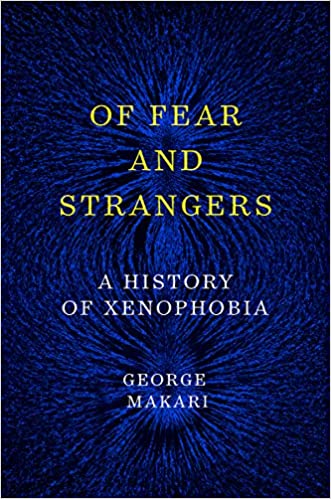
城市的匿名性可能导致异化,但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陌生人之间仅凭良性的冷淡即可保持相安无事。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了“礼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这一术语,用以形容我们在公共场所认可他人之存在的一系列礼节性做法,如点头示意和快速打量。戈夫曼还揭示了与陌生人交谈的合适时机以及恰当内容等一系列潜规则。他发现,根本的原则是不要说任何可能让你自己显得缺乏基本理智的话。不要问陌生人今天是几月几号,此话一出即等于公开宣布你是困惑与混乱的制造者。
如今,在当代生活的诸多非-场所(non-places)里——连锁酒店、机场、设有自助收银机的超市——我们几乎完全不需要和陌生人交谈了。非面对面的导引(将你的卡放进插槽,准备好你的登机牌,输入你的密码)取代了人类的互动。消费者的交易活动也趋向于由APP和算法来接手。它们关心的唯有你的密码和信用卡数字。
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进一步加速了这些趋势。我们所依赖的许多事物,如食品和娱乐等,如今似乎是从某个不确定的、无可联系的别处匿名而来的,如透过触摸屏或鼠标点击。居于“别处”的人群,则是由快递司机、超市搬运工、仓库拣货员以及其他做着不安全、收入低的零工的人们所组成的静默大军。“被技术过滤得不可见以后,”基欧汉写道,“为我们的需求服务的陌生人军团变得和实用工具没什么两样了,被困在一种永恒的陌生人状态当中。”
许多低薪工作的不可见性进一步强化了“自由主义的悖论”。提出该术语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霍利菲尔德(James Hollifield)认为,这一悖论198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与欧洲政治文化的一项关键特征。自由市场想要廉价、可流动、灵活性强的劳动力;选民想要更少的移民。政府则力求让双方都满意。在英国退欧公投前夕,其悖论性表现得尤其突出。大卫·卡梅隆政府一面试图削减福利以及其它一些欧盟公民所享有的公民权,一面又想继续依赖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在通过消费主义的地面时,我们依靠陌生人来缓解运动中的摩擦力,但又希望他们不要对我们提任何要求。

然而,我们不可能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永远不接触别人。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一书中,文化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主张,鉴于脆弱性(vulnerability)人皆有之,我们和其他人类紧密相连,包括那些我们只是偶尔碰面乃至于根本没有见过的人。我们倾向于视自己为拥有主权的、自给自足的实体,但每个自我都是有缝隙的,也都可以被渗透。柔软、可延展并且终有一死的躯体已足以令我们动荡不安。我们的皮肤是多孔的,我们的呼吸道是敞开的,我们的感觉也是敏锐的。这不仅让他人身上的病原体有机可乘,也迫使我们直面他人的欲望、暴力、困苦与目光。我们无可避免地是社会性的存在,他人简简单单的一瞥都可能让我们受伤或是狂喜。“我们让彼此重归不完整(undone),”巴特勒写道,“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错失了一些东西。”
一个陌生人把一根针扎进你的上臂,你努力把宽慰和感激的眼泪憋了回去。何以如此?我想这部分地在于那根针可能救了你的命,帮助你回到了某种正常状态。但也有可能是它令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变得更具可见性(并伴有短暂的疼痛):相互的关心和共同的命运这条无形的绳索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纵然有千般不是,社交媒体仍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启迪我们。许多你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认识的人在你的时间线上无穷无尽地滚动着,庆祝着他们的成功,分享着他们的晚餐照片,对某个以前你从未想到过的东西发泄怒火,或是对潜在的听者倾诉自己的悲伤和失落。读这些东西无疑是劳神费力的。但这样做也可能让你醍醐灌顶,促使你直面自己的偏见和特权。用超现实的眼光看,一个陌生人的心智与你判然有别。每个用户头像的背后都是另一种生活,都是另一颗忙于处理其独特现实的鲜活头脑。基欧汉提出,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乃是“满载着未知货物的宝船,整个宇宙的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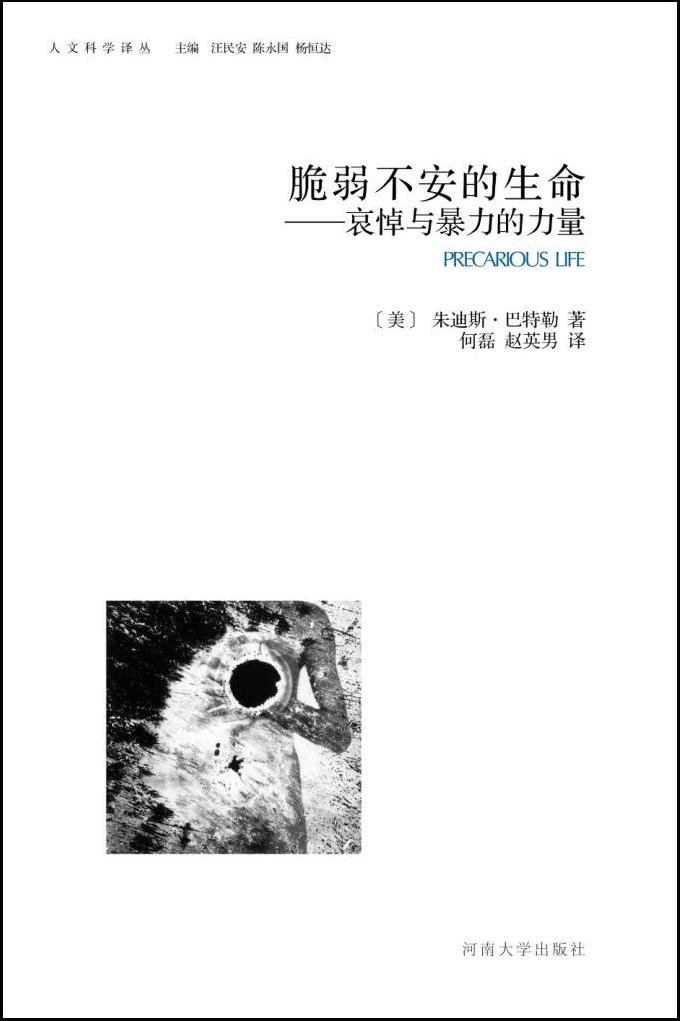
[美国]朱迪斯·巴特勒 著 何磊/赵英男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3
我们是讲故事的动物(storytelling animals)。每个陌生人都保存着一个我们未曾听闻的小故事。奥德修斯用以回报主人好意的唯一礼物是:讲故事。在讲给我们听的故事中,陌生人不再是我们自身故事里的劲敌、漫画化的角色或者跑龙套的。他们乃是自成一体的角色。他们的故事使我们想起了顽固的他性(otherness)以及他人生活的多姿多彩。这种提醒并不总是舒适的,但它或许能帮助我们领会一条复杂的、为人们所共享的真理,其丰富性归根结底远超眼中只有自己的虚构故事。
技术把我们和陌生人割裂开,但它也将我们与陌生人相连接。例如有帮助你在自家空闲卧室安置过夜的背包客的APP,或者你可以和世界另一边的人来一首卡拉OK合唱,又或者你可以匹配到一个来自战乱频仍之地的出租车司机,而他会在10分钟的车程里与你讲述他们的旅途见闻。现代生活也不是非得冷淡和不好客。如今,限制逐渐放开,许多人仍旧举棋不定——渴望在拥挤的室内以及座无虚席的厅堂里来一场狂欢,但又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一条鼓舞人心的经验是,这种谨慎和开放之间的张力在人类历史中随处可见。我们一般都能想出解决办法。
伴侣去世后不久,白金汉就走出了家门,开始接触附近的陌生人。某种本能告诉他这将会有帮助。“(我)邀请周围的人来用餐……家中变得吵闹、热络和嘈杂……我通过这种方式将原本支离破碎的世界重新缝合了起来。”他还有个类似的直觉,那就是疫情之下“我们正好也最需要抵制那种让我们的生活格局变小的冲动”。与陌生人的每一次偶遇都是一次信仰之跃。另外,白金汉也体会到,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继续往前走——我们的祖先以前就是这么做的,而事实也证明他们做对了。这里的洞见是:陌生的人们秉持慷慨和好奇的心态走到一起时,必将有好事发生。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