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金被公认为是继T.S.艾略特之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诗人。在20世纪现代主义风潮盛行时,他一反庞德与艾略特以来晦涩、“学问化”的现代主义路径,主张坚守“英国精神”,回归英诗的格律传统,以一种散文般质朴、晓畅的语言抒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战后英国居民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拉金最常涉及的主题,当时成长于战前与战后断层中的一代人面临着社会的束缚和宗教信仰的丧失,而拉金作品中的冷静、忧郁、幽默与讽刺,恰恰刻画出这一代英国人的精神肖像。
1943年,拉金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毕业生能够找到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由于视力不合格,拉金没有被征召入伍,他曾两次尝试当公务员,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找到了一份在什罗普郡做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小说《吉尔》《冬天里的女孩》以及第一部诗集《向北之船》。与其他职业作家不同,拉金毕生都没有靠写作谋生,他先后工作于威灵顿公共图书馆,以及莱斯特、贝尔法斯特、赫尔等大学图书馆。1974年出版的诗集《高窗》被认为是拉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但自此之后,他几乎不再写诗,对曾经爱好的爵士乐也失去了兴趣,每天只是大量喝酒,写些散文,记录下他对死亡的恐惧。
在公众眼中,拉金是一个严肃、孤独的英国人。他一生没有结婚,过着独来独往的简单生活,极少参与文学圈的活动或接受采访,对出国旅行也毫无兴趣。他认为,旅行只对小说家有用,因为小说家需要新的场景、新的人物、新的主题,但“诗人真正需要专心做的事是重新创造熟悉的事物,他没有义务去介绍陌生的东西。”对于作家所取得的任何名声,拉金都持谨慎态度,他尤其反对作家靠领津贴或官方资助来写作。1984年秋天,就在拉金逝世的前一年,他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但他拒绝了这一荣誉。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他明确指出,桂冠诗人的身份和职责在今天的英国并不明朗,它带来的知名度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非常有害。
近日,拉金的随笔集《应邀之作》推出中文版,收录了他应报刊、杂志等媒体约稿发表的五十余篇随笔、评论、访谈等,可以说浓缩了他一生的主要审美理想和艺术观点。下文是拉金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的部分对话,亦收录在《应邀之作》一书中。拉金难得侃侃而谈,与采访者分享了他的个人生活、职业发展、诗歌创作上的观念和经验等,是对人生的一次全面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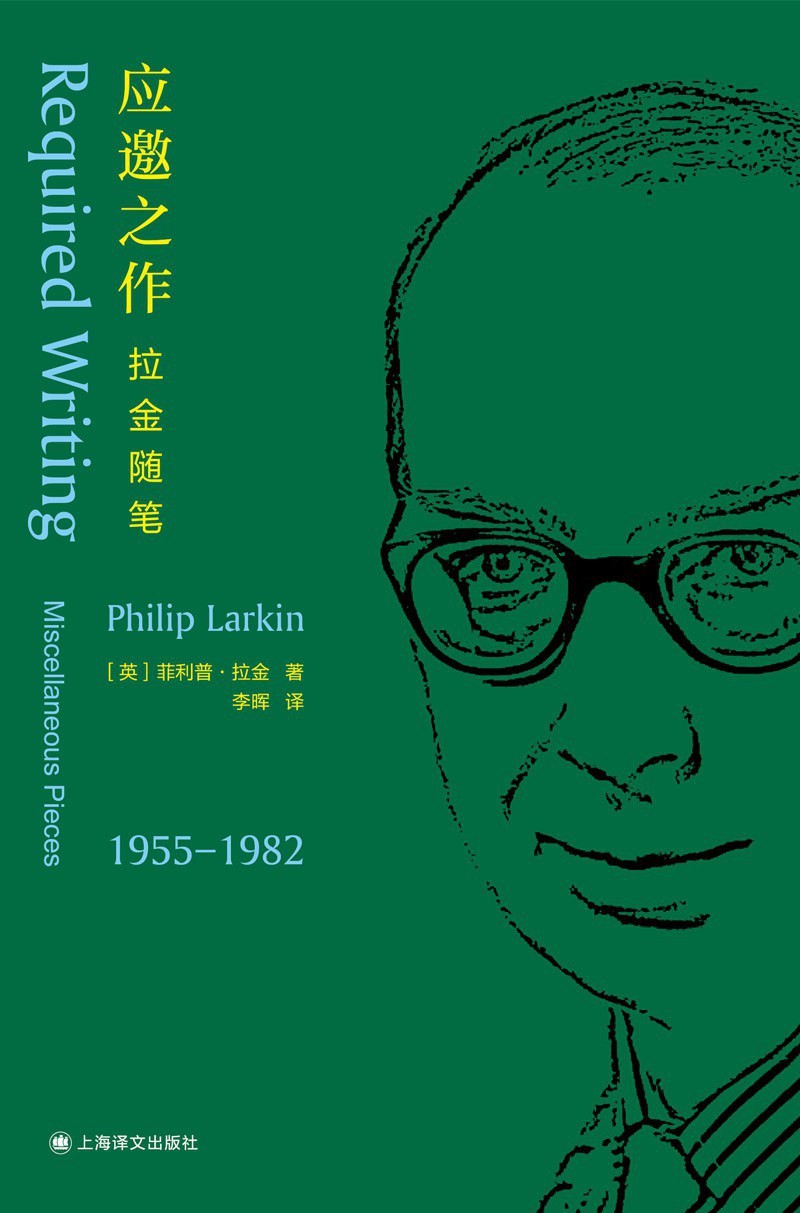
[英] 菲利普·拉金 著 李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06
《菲利普·拉金对话<巴黎评论>》
采访 | 罗伯特·菲利普斯

您可以描述一下在赫尔的生活吗?您是住在公寓里,还是有一座独栋住宅?
我是1955年来赫尔的。十八个月过后,我搬进了大学里的一间公寓,然后在那里住了将近十八年。那是一座独栋建筑的顶层,因为在战争期间作为美国领馆办公地而闻名。《降灵节婚礼》(1964)的大部分,以及《高窗》(1974)的全部诗作,都是在那里完成。如果不是因为赫尔大学决定把房子卖掉的话,我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搬出来。搬家真是一段可怕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房子已经很不好找了。最后有朋友通知我说有一栋大学附近的房子,于是我在1974年把它买了下来。我现在还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您每天的作息规律是怎样?
我尽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工作一整天,然后做饭、吃饭、洗东西、打电话、写付费文章、晚上喝酒看电视。我几乎从不出门。我想每个人都在试图忽略时间的消逝:有的人通过做很多事情,在加利福尼亚住一年,下一年再去日本;或者是通过我这种方法——让每一天、每一年都过得一模一样。很可能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
您刚才没提到写作的安排……
关于写诗,我说的任何东西,都只能算是一种回顾。因为自从搬进这个房子以来,我其实写的很少……但我真正动笔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在晚上。下班以后,清洗工作结束后(抱歉啊:你可能会说是“收拾碗筷”)。这跟其他事情一样属于日常惯例。而且这样真的有效果:我不认为一个人写诗的时间可以连续超过两小时。收工后你就按照循环往复的程序来处理。把它先放在一边,过二十四个小时再看,效果会好得多。因为到那时,你的潜意识或什么的已经打通那个障碍,你可以继续写下去了。
您为什么要写作,为了谁而写?
以前我们总读到奥登的这句话:“提出难回答的问题很简单。”简短的回答是:因为不得不写,所以你才写作。如果要加以理性表述,似乎可以这样说:你看到这个景象,体会到这种感觉,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景,然后必须要寻找一种语词组合,通过触发他人相同体验的形式,使之得以留存。你需要向最初的体验负责。它并不像是自我表达,尽管可能看起来相似。至于你要为谁而写,这个嘛,你为所有人而写。或是为所有愿意聆听的人。

您是怎样成为图书管理员的?您对教书不感兴趣吗?您父亲的职业是什么?
我的天哪,这都可以写一堆自传了。我父亲是市政府的财务长,一位财政官员。我在上中学以前丝毫没有想要“成为”什么。等我去牛津的时候,战争还没结束。除了当兵、当教师或者做公务员,并没有其他可以“成为”的什么。1943年我大学毕业时,知道自己做不了第一种,因为我被评为“不合格”(我估计是视力原因);也成不了第二种,因为我口吃;然后我又被公务员部门拒绝过两回。我想,好吧,这可让我解脱了,然后我就蹲在家里写《吉尔》。不过在那个年代,政府当然还有权力送你去挖煤或种地或进工厂,而且他们也写了一封非常礼貌的信件,问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翻看了当天的日报。我看到什罗普郡的一个小城市正在发广告招聘图书管理员,然后就应聘,然后被录用,再把情况汇报给政府。这个结果似乎让他们挺满意。
当然,我那时不算是真正的图书管理员,更像是看门打杂的——那是一个人管理的图书馆——我不能假装说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先前的管理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年左右。我担心自己也会在这地方度过余生。这让我开始完善自己的职业资质,只是为了以后能离开这里。我是1946年走的。那时我已经写完了《吉尔》,还有《向北之船》,还有《冬天里的女孩》。这可能是我生命里最“紧张激烈”的时光。
您认为学术界作为一种工作环境,对创意写作者来说是否合适——具体而言,他们教书上课适合吗?
学术界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话说回来,我又不是教师。我没办法当教师。我会觉得,咽嚼别人做过的工作(我指的是学术写作),肯定乏味得要命。它会让你对整个文学事业感到厌烦。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没有那种心智,概念式的,或推论式的,管它什么名称呢。如果我必须要像这样考虑文学,比如说这首诗为什么要比另一首“更好”,诸如此类,我会死掉的。
我们听说您从来不朗读自己的诗作。在美国,这样做已经成为诗人们的正经事了。您喜欢参加别人的朗读会吗?
我不会做朗读会,不会的。尽管我录制过诗集里的三篇内容,但那只是为了表明我会怎样读它们。听一首诗跟看文字相反,它意味着你会遗失很多东西——形状、标点、斜体,甚至包括你意识到还剩多少内容。纸上读诗,意味着你能按照自己的速度,恰当地吸收它;听一首诗,意味着你被朗诵者自己的步伐频率拽着往前跑,沿途之间丢失各种东西,而不是加以吸收,还会混淆“那里”和“他们”的具体所指,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朗诵者会把自己的个性横亘在你与诗歌之间,不管效果好坏。这种情况,在听众身上也会发生。我不喜欢在公众场合听东西,甚至是听音乐。其实我想,诗歌朗读的发展,是建立在与音乐的错误类比之上:文本就是“乐谱”,它只有在“演奏”过后才能“恢复生机”。这种类比的错误之处在于,人们可以阅读语词,却无法阅读音乐。当你写下一首诗的时候,你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置入其间:读者可以清楚地“听到”它,好像你在房间里对他亲口说出来一样。当然这种诗歌朗读的时尚已经导致了某一类诗歌的产生,你一接触就能够理解的诗歌:简单的韵律、简单的情感、简单的句法。我认为它在纸页上无法站立。
您觉得作家如果有经济保障,算是一种有利条件吗?
整个战后的英国社会都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认为经济保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条件。我当然愿意经济上有保障。但是,你问的其实不是工作的事吗?整个问题是,作家,尤其是诗人,其实是怎样挣钱的对不对?
从一方面来说,现在你不能像一百年或七十五年前那样,当个“文人”就能轻易谋生了。那时候还有许多杂志和报纸,等待着人们去充实版面。现在的作家收入,就像作家自身一样,几乎已经降到勉强维生的水平以下了。另一方面,你又能够通过“成为作家”,或“成为诗人”而谋生。如果说你打算加入文化娱乐行业,再从艺术理事会里领点儿救济补贴(现在这些机构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然后成为一名“驻校诗人”,诸如此类。我想我原本可能会说——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我原本可以找个代理人,然后说,看,我一年里可以有六个月时间来做任何事,只要我能在剩下六个月里随便写东西就行。有些人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办法对他们管用。但是我的成长经历却导致我认为:你得有份工作,然后在业余时间里写作,就像特罗洛普那样。等你开始通过写作而挣到足够金钱的时候,再逐步退出那份工作。可是,在我还没能“通过写作而谋生”之前,就已经五十多岁了——后来只是因为我编写了一部庞大的诗歌选集(注:指拉金负责选编的《牛津20世纪英国诗歌集》),才达到“写作谋生”的状态——那时候你就会想,得了,我还是等着拿退休金吧,既然我已经等到这个地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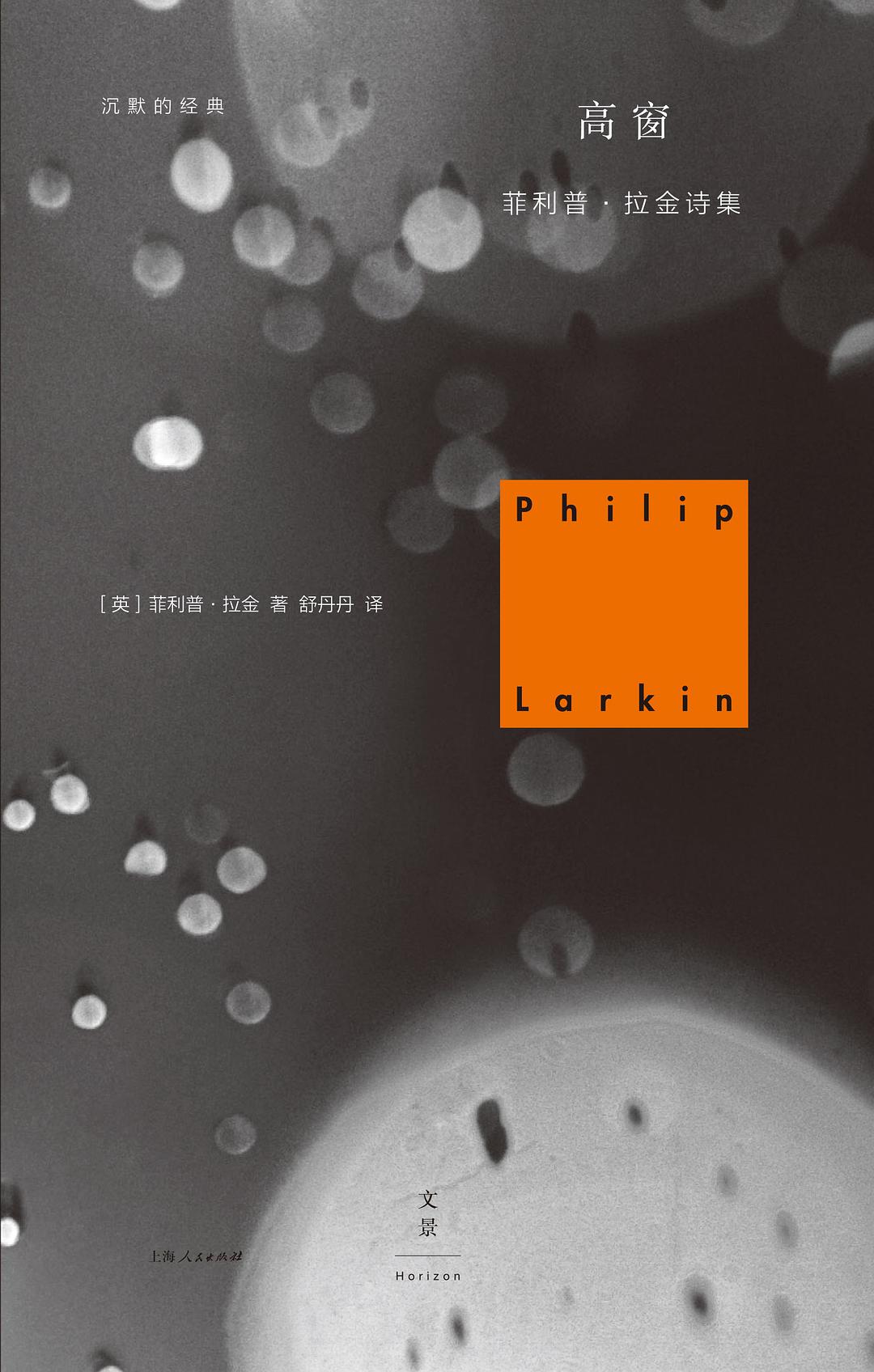
[英] 菲利普·拉金 著 舒丹丹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01
您能描述一下自己和当代文学群体之间的关系吗?
我多少有些回避您所谓的“当代文学群体”。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我不靠写作谋生,所以不必为了挣钱而跟文学编辑、出版商和电视界的人保持联系;第二,我不住伦敦。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跟这个群体的关系相当友善。
作为一名单身汉,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局外人吗?或者,就像您诗歌《参加的理由》、《多克雷父子》和《自我即人》里的讲述者那样,您享受单身状态、保持单身状态,是因为您喜欢这样,并且宁愿以这种方式生活?
很难说。是的,我自己选择保持单身,而且没有喜欢过其他选择。不过,多数人确实会结婚,这是自然,另外也会离婚。所以我估计我就是您说的那种局外人吧。当然,我时不时也会为这件事发愁,但解释原因的话又太费功夫。塞缪尔·巴特勒说过,生命不是以这种就是另一种方式被糟蹋掉。
您觉得幸福快乐在这个世界是无法实现的吗?
这个,我想如果你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在可预知的未来没有任何烦恼,那就是一个人能够指望达到的最大限度了。但是,那种持续情感高潮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嘛,不存在的。因为你知道,哪怕只要想到自己将来会死,你爱的人会死。
您在《向北之船》第二版的序言里,提到了奥登、托马斯、叶芝和哈代对您早期的影响。您在研究这四位作家的时候具体学到了什么?
噢,我的天哪,诗人可不是让人研究的!你读到他们,然后就想:这太神奇了,这是怎么办到的,我能不能做到?这是你学习的方法。归根到底,你不能说:这里是叶芝,这里是奥登,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他们就像拆散了的脚手架。托马斯是一条死胡同。有哪些影响?叶芝和奥登嘛,是对诗行的驾驭,是情感的形式化疏离。哈代……让我不怕使用浅显之语。所有那些关于诗歌的美妙警句:“诗人应该通过显示自己的内心而触碰到我们的内心”,“诗人只关注他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所有时代的情感,以及他个人的思想”——哈代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
奥登赞美过您的形式。但是您曾经表明,您对形式几乎不感兴趣——内容是一切。您可以就此评论几句吗?
恐怕这是比较蠢的一句话,尤其是现在来说,人们已经这样不讲究形式了。我读诗时就会想,没错,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想法,但他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首诗呢?为什么不让它变得让人难以忘怀呢?仅仅把它写下来的话,并没有什么用!在所有重要的层面,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我所说的内容是指诗歌里留存的经验,那种流传下来的东西。我这么说,肯定是因为看过了太多纯粹由词藻堆砌的诗歌。
如果有一种诗,它基于多数人会轻易错过的某个意象。您可以描述一下这种诗的源起和制作完成过程吗?(邻里之间的洁净小路,城市车流里的一辆救护车?)
如果我可以回答这类问题的话,我早就是一名教授而不是图书管理员了……我记得以前说过一回:我无法理解这些奔波于美国各大校园、向人们解释自己是怎样写诗的伙计们:这就像到处向人解释你怎么跟自己老婆睡觉一样。所有跟我聊过这件事的人都说,如果他们的经纪人能够敲定这个睡觉题目,他们也会照谈不误。

作为一名作家,您具体有哪些写作怪癖?您觉得自己是否具有某些明显或隐秘的写作瑕疵?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用五步抑扬格用得比较多:有些人觉得这样写有压迫感,所以会尽量远离它。我的隐秘瑕疵只是水平不算太好,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从来不说教,从来不勉强用诗歌去做事情,从来不积极主动地寻觅诗歌。我等着它来找我,随便它以什么样的躯壳形式。
您觉得自己归属于某种具体的英国文人传统吗?
我记得好像乔治·弗莱泽说过,诗歌或是“远占眼光”(他是苏格兰人,说话有口音),或是“道德话语”。我属于第二种,而第一种更好。一位著名的出版商问过我,诗歌是怎样标点断句的。我说,跟散文一样。他好像被吓了一楞。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现在写作,或以前写作,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在没有变成楞头青之前,还是通过普通方式来运用词汇和句法,描述可以辨识的经验,尽量让人难以忘怀。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传统。其他东西,那种不着四六的东西,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偏离。
您对桂冠诗人的职责有什么看法?它是否发挥了某种有效功能?
诗歌与王权都是非常原始的东西。我赞成它们以这种方式结合,我是指在英国。从另一方面看,桂冠诗人是什么,他要做什么,这一点还不明朗。在某种程度上,是刻意如此:它并不算一份工作。没有任何义务,没有薪水。它甚至不算是多大的荣誉,或者说,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我确信,它最糟糕的方面,尤其在今天,就是它带来的知名度,在公众层面与诗歌相牵涉的压力。这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肯定非常有害。
当年丁尼生可以发表一首十四行诗来告知格累斯顿应该怎样安排外交政策,而这种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有趣的是吉卜林这个人。他被多数民众认为是堪比国家发言人的诗人,却从来没成为桂冠诗人。他在布里奇斯(注:指罗伯特·西摩·布里奇斯,1913-1930年的英国桂冠诗人)被任命的那一次就应该是了。但他并没有,很典型的情况——这个位置并不是如此考虑安排的。它的恳切意图是为了荣耀某人。然而任何有关王室的事情在今天都能引发如此狂热的关注,它确实更像是一种真正的磨难,而不是荣誉了。
作为一个不喜欢接受采访的人,还回答了我们的所有问题,您真慷慨。
我恐怕没说什么很有意思的话。您必须要认识到我对诗歌从来没什么“想法”。对于我来说,它始终是在各种需求的综合压力下,一种个人化、几近于生理释放或解决方法的东西——想要创造,想要合理化,想要赞扬、解释或进行外化。根据具体情况,不一而足。我对别人的诗歌一向不太感兴趣——当然,动手写作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没有人写过你想读到的东西。
也许我的诗歌观念很简单。曾经有个时候,我答应帮忙去做诗歌竞赛的评委——您知道那种竞赛,他们有3万5千个入选作品,你要看其中最好的那几千首。看了一会儿我就说,那些情诗都到哪里去了?还有自然诗呢?他们说,噢,那些都被我们扔掉了。我现在估计,它们应该都是我喜欢的那些诗。
1982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应邀之作:拉金随笔》一书,较原文有删减,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