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英国最大的文学小说部门出版商之一Vintage宣布了今年将主力推广的五位新小说家:梅根·诺兰、皮普·威廉姆斯、艾尔莎·麦克法兰、乔·哈姆亚和维拉·库里安。
她们五人都是女性。但你可以原谅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在2021年,以女性作家为主的名单太普遍了。在过去的12个月里,几乎所有的小说评论都是围绕着年轻女性展开的:帕特里夏·洛克伍德、雅·加西、雷文·蕾拉妮、阿夫尼·多希、劳伦·奥伊勒。如果问任何性别的小说家最近正在阅读谁的作品,他们几乎肯定会提到雷切尔·库斯克、奥特萨·莫什费格、雷切尔·库什纳、格温多林·莱利、莫尼克·罗菲或玛丽亚·斯捷潘诺娃中的一个。或者他们会在安妮塔·布鲁克纳、佐拉·尼尔·赫斯顿、娜塔丽亚·金兹伯格、奥克塔维亚·巴特勒、艾维·康普顿-伯内特身上找到新的共鸣。出版界的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这种能量与女性有关。
媒体的报道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五年里,《观察者报》的年度新人小说家专题展示了44位作家,其中33位是女性。你会发现奖项入围名单也是类似的比例。日前公布的科斯塔处女作小说奖提名名单中没有男性,该奖项过去五年的提名作家中也有75%是女性。今年的拉斯伯恩斯奖的八个入围作家中只有一名男性。迪伦·托马斯奖的入围名单上有一名男性(以及一名非二元性别者)。作家俱乐部的最佳新人小说奖也是如此,评委主席露西·波佩斯库说,“很高兴看到女性在入围名单中占主导地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出版业人士都能理性看待这个情况。“为什么说‘很高兴看到’?”一位男性出版商在名单公布后不久给我发来邮件。“你能想像性别互换的情况吗?一份由五名男性和一名女性组成的入围名单,主席说,‘很高兴看到男性在入围名单中占主导地位?’”

一代人之前,入围名单均由男性主导,比如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巨头:英国的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威廉·博伊德、石黑一雄,美国的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和索尔·贝娄。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小说家都是男性。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虽然出版界几乎普遍认为目前女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积极的,考虑到持续了6000年左右的男性文化霸权,这既是早该到来的,也是必要的。但出版商、代理商和作家中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觉得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正被一个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的行业拒之门外。
那位男性出版商不厌其烦地指出,是的,“现在令人兴奋的写作都来自于女性,”他自己也出版了更多女性作品——这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男性作家,他们已经无法被注意到了”。

许多女性可能本能地对男性说他们需要更多曝光度抱有否定态度。当女孩在高考中比男孩表现更好时,当女性能够与男性平等竞争时,都会出现类似的担忧。当然,当你向出版界的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你往往会收到一个白眼,也许随后是一句“等等!去年的布克奖获得者不是男的吗?”。那些不相信存在问题的人,会把《夏奇·贝恩》的作者道格拉斯·斯图尔特获奖作为男性优越性的证据,却往往很难说出其他进入奖项名单或畅销书排行榜的年轻男性作家。有马克斯·波特......萨姆·拜尔斯......几个美国作家,如本·勒纳和布兰登·泰勒。然而,这些人中很少有人算得上家喻户晓,也没有人有萨莉·鲁尼那样的文化热度。
这是为什么呢?那位男性出版商特别指出,Vintage的编辑几乎都是女性。(Vintage的19位文学编辑中,只有4位是男性。)他认为,这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团队,而是整个行业的性别平衡现状。(英国出版商协会2月份发布的一项多样性调查显示,64%的出版业员工是女性,女性占编辑部的78%,市场部的83%,宣传部的92%)。
“每当我把小说发给编辑时,看到的都是女性名字,”一位男性经纪人说。和出版商一样,他担心被视为“某种男权活动家”,只愿匿名发言。这个话题是一个马蜂窝,我接触过的图书行业的几乎所有男性都拒绝公开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反感。
“多年来,每次我参加出版界的晚宴都会抱怨这个问题,我得到的答复是让我闭嘴,”这位经纪人说。但他坚持认为,困扰他的不是性别构成,而是普遍的群体思维:对男性小说家缺乏兴趣,以及普遍认为男性声音是有问题的。
“有一天,我正和又一位28岁的女性开会,”他继续说,“我总是问编辑,‘你在找什么样的小说,’而她正好说,‘我想要的是一部代际家庭小说。’我说,‘哦,类似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吗?’说实话,她的反应好像我说的是《我的奋斗》似的。她说,‘不!绝对不是那样的作品!。’我心想,‘但你刚刚描述的就是这本书啊!’”

文学品牌Serpent’s Tail的出版商汉娜·韦斯特兰说,她并不总是相信年轻人写的小说会有市场。“如果一个男性作家的好小说落在我的桌子上,我确实会真心实意地对自己说,这更难出版。”她认为,男性作家“通往成功的道路”更窄,因为向男性开放的奖项更少,愿意报道男性作家的杂志更少,愿意支持他们的媒体人物也更少。比如,多莉·奥尔德顿和潘多拉·赛克斯会在她们的播客中专门支持女性作家。
根据《书商》的数据,2020年的1000部畅销小说中,629部由女性撰写(其他27部是男女合著,3部由非二元作家撰写,剩下341部由男性撰写)。在“大众和文学小说”类别中,75%的作品由女性作者创作,75%的女性和25%的男性似乎是当代出版业的一个黄金比例。普遍的共识是,年轻男性作家已经放弃了文学小说。他们认为叙事性非虚构作品(尤其是罗伯特·麦克法兰风格的游记和自然写作)或类型小说(尤其是犯罪和科幻小说)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们较少受到文化和推特讨论的影响。
夏曼恩·洛夫格罗夫是Dialogue Books的创始人,她创建这个品牌是为了关注那些被排除在主流出版之外的边缘作家。洛夫格罗夫一直在寻找更多的年轻男性作家。她最近的成功是出版了保罗·门德斯的首部小说《彩虹牛奶》(Rainbow Milk),讲述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耶和华见证人的成长经历。
“真正有趣的是,如果我出版的是一个黑人同性恋作家的作品,就更有可能通过他们的故事获得曝光度,因为这样的故事被认为具有原创性,而且符合#多样化声音#的要求。”她说,“而如果我出版的是一个白人、工人阶级的男性作家,似乎就很难取得突破了。”她引用了31岁的亚历克斯·艾利森的《身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Body),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脑瘫患者和他的年轻女护理员的小说。“有人问,‘男性应该书写女性吗?’,你会想,‘作家怎么能只写一个性别?你怎么能不写一个女性角色呢?’”她认为,出版业已经成为一种单一的文化,由 “白人、中产阶级、顺性别、异性恋的女性”所主导,她们自认为是受害者。“因为这一切都是关于瓦解父权制的,所以男性没有机会。”
北爱尔兰作家达兰·安德森同意“阶级是出版业的肮脏秘密”这一说法。他说:“工人阶级男性作家,几十年来基本上被中产阶级男性文学机构挡在了写作之外。而现在,我们却被期望为一个不属于我们的过去做出回答。”他认为对著名男性作家的攻击,反而由他这一代工人阶级男性作家承担着。“而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办法去承担马丁·艾米斯或约翰·厄普代克欠下的债。”
但无论阶级如何,男性,或者至少是男性读者,是否真的想要获得这样的机会?每当我与男性交谈时,无论他们是20岁、30岁还是40岁,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他们根本不在乎小说,尤其是文学小说。他们有游戏、油管、非虚构、播客、杂志和网飞。梅根·诺兰的处女作《绝望的行为》(Acts of Desperation)是今年名气最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她说:“我认识的主动寻找和阅读小说的男性,都是在文学领域工作的。我觉得我认识的大多数男性,每两年都读不了一本小说。”

诺兰想知道现在做男性小说家是否“本质上已经不那么酷了”,并认为男性在小说中错过了一场可以与八九十年代的“酷、性感、轻松”相媲美的运动。“现在让一个男性小说家作为令人向往的文化人物,登上非文学杂志的封面,几乎不可能了,”她说。
诺兰同意,这种文化转变与“年轻女性大量涌入”相吻合。但这是因为“只是在最近,女性才可以开始写关于性等私密话题的小说,并被归类为文学小说”。
她的小说讲述了一个20多岁的女性与一位男性的控制性性关系,因其对女性欲望的诚实真挚描述而受到赞扬。她是否认为目前比起男性,女性在描写性时不那么拘束了?“我觉得如果我处于男人的地位,我就不会那么谨慎。我也许会对我的写作方式更加小心翼翼。我虽然还是会受到一些攻击,但并不是人身攻击,只是有点尴尬。”
男性作家肯定对性问题感到更退缩。十多年前,克埃尔·西哈在《纽约观察家》发文称,他那一代的男性小说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约书亚·弗里斯、戴夫·艾格斯)已经衰落了。他们是“畸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没成熟的男性作家”,对性和争议敬而远之,连邮件都不愿发。
快进到2020年的夏天,小说家卢克·布朗去年出版了《盗窃》(Theft)——一部关于性阶级战争的风俗喜剧,他认为只有女性才有自由以 “真实和复杂”的方式呈现性关系(他特别提到了萨莉·鲁尼、格温多林·莱利和莉萨·哈利迪)。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写道,直男把欲望与权力的滥用联系得过于紧密,以至于“没有一个明智的人敢于”诚实地写出他们与女性的爱情经历中的痛苦。
布朗认为唯一的例外是爱尔兰作家罗布·道尔,他的第二部小说《门槛》(Threshold),根据他自己的描述,是对“我自己受损的男性心理和男性气质本身诚恳但混乱的探索”。但多尔认为,作为一名男性小说家,诚实地书写性,“会有点被鄙视。这感觉就像我得了某种奇怪的传染病,进城的时候,就会自动响起铃铛,周围的人们都会离开。”

他同情那些选择远离男性小说的读者,部分原因是“整个20世纪是对男性性欲的一个相当近距离的审视”,但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如今的男性作家“害怕”且正在“迎合”他们认为女性想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为了被允许占有一席之地,他们需要有正确的观点,成为所谓的好男人。他们这样做,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没有阅读价值。”
并非所有的年轻男作家都认为当下是男性写小说的严峻时期。萨姆·拜尔斯在3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小说《加入我们的疾病》(Come Join Our Disease),他42岁,正在现代出版界大展身手。他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别肥沃的文学时代,主要得益于女性打破了传统。他称赞蕾切尔·卡斯克的自传实验,艾米尔·麦克布莱德的现代主义新方法,以及埃莱娜·费兰特的“大型、跨越历史的国情小说”,人们过去只将这些特征与著名男性小说家联系起来。
“只要有一位黑人女性获得布克奖,对某些人来说就是文化的终结,”拜尔斯说,“几十年来,女性和黑人在小说中一直缺乏曝光度,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但现在,人们嗅到了男性曝光度减少的一点气息,哪怕只有短短一年,我们就迫切地要对此做些什么。这是一种真正的关切,还是主导文化在感受到威胁时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虽然出版界正开始解决有色人种女性小说的糟糕纪录,近年来有坎迪丝·卡蒂-威廉斯、凯利·里德、英格丽·佩尔索德和奥伊因坎·布雷斯韦特等作家高调亮相,但许多有色人种男性作家认为他们依然缺乏曝光度。由黑人中学教师转行写小说的阿什利·希克森-罗文斯认为出版业仍然是一个“白人女性的世界”。当他在写第一本书《392》时,统计数字称2016年只有一部英国黑人男性的处女作出版。“这个数字太可怜了。如果我是个年轻的黑人男孩,看到这个数字,我会觉得成为一名作家比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更难,而且收入还少得多。”最后有七八个经纪人与他接触,但他指出,所有人都是白人女性。他现在正在创作第二部小说《你的表演》(Your Show)。“这是一本实验性的文学抒情小说,但它是关于足球的。”他说他的女经纪人最初并不热衷于这个想法——在Faber出版商一位男编辑的热情帮助下,这个想法得到了挽救。

Curtis Brown公司的经纪人卡罗琳娜·萨顿惊讶于男性感到被排斥在小说之外。她强调说,女性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在出版界获得自信:“当女性被排斥时,为什么没有在媒体引起骚动?”她问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女性开始书写自己的声音,而我们不知道这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
她坚持认为,现在有很多成功的年轻男性作家,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从主导视角来写作,也没有像罗斯和阿米斯在80年代或90年代那样的自信。不过,她还是承认,人们对新人男性小说家的期望比过去要高。“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要想获得25万英镑的预付款,标准真的很高。他们必须写出非常杰出的作品。而女性更容易获得更高的预付款。”
必须要追溯到12年前,即罗斯·赖辛和乔·邓索恩的处女作,才能看到获得大额预付款的男性作家。尽管于今年2月出版的凯莱布·阿祖马·纳尔逊的《开放水域》(Open Water),据说在经过9次竞标后获得了“可观的”预付款,但许多经纪人和编辑都告诉我这是多么罕见。萨顿认为这是因为“现在是属于女性的文化时刻”,她们的故事“似乎感觉更新鲜”。
但与我交谈的匿名男性出版商认为,我们应该对男性目前没有创作“新鲜”小说的说法保持警惕。“这也有一个反面。难道我们能说,15年前黑人女性没有写出过好书吗?”
显然,在出版界出现了一种霸权,洛夫格罗夫称之为“白人女权主义”。这种霸权有可能使小说变得陈旧和可预测,并疏远潜在的年轻男性读者。既有趣又令人沮丧的是,与我交谈的出版界人士似乎都认为他们的典型读者是在英国白金汉郡或牛津郡长大的28岁白人女性。牙买加小说家马龙·詹姆斯在2015年获得布克奖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对他来说,“白人女性的原型”是长期受苦的中年郊区读者。他认为,由于这类女性占据大部分小说购买市场,有色人种作者被逼着去“迎合”她们。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警惕对女性的羞辱,因为是她们的热情、激情和投入使整个出版行业得以持续发展。还有一个问题是,尽管女性的知名度很高,但她们是否得到了与男性小说家相同的文化尊重?有一种危险是,小说从此被当作一种女性化的形式而被否定。特别是鉴于小说的历史,从其18世纪的起源开始,就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它是提供给那些没有接受过科学或政治方面正规教育的富裕女性的轻浮文学。正是像塞缪尔·理查森这样的男性作家以及一代男性批评家,被认为使小说写作专业化。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许多女性对“男性作家都去哪儿了?”这个话题经常与“小说死了吗?”这个问题相伴而生感到怀疑。拜尔斯说,在他的职业中,作为男性当然有一种权威。在采访和谈话中,他经常被邀请讨论政治或小说技法,而他的女性同行则不会。他说,很多时候,女性被要求书写和讨论她们的个人生活。
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出版品牌之一4th Estate的编辑主任基沙尼·维德亚拉特娜坚持认为男性并没有受到歧视。然而,她确实认为“在出版业的各个层面上,白人、中产阶级的顺性别女性占主导地位”。维德亚拉特娜认为,某些“公认的观念”的确需要受到挑战,特别是对“比较标题”的依赖,即出版商通过与其他类似书籍进行比较来考虑提交的作品。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萨莉·鲁尼现象:每个出版商都急于寻找年轻的女作家来填补所谓的“鲁尼型”缺口。
“对这种思维模式的依赖导致出版商总是在复制已经存在的东西,”维德亚拉特娜说,“这让出版商无法进行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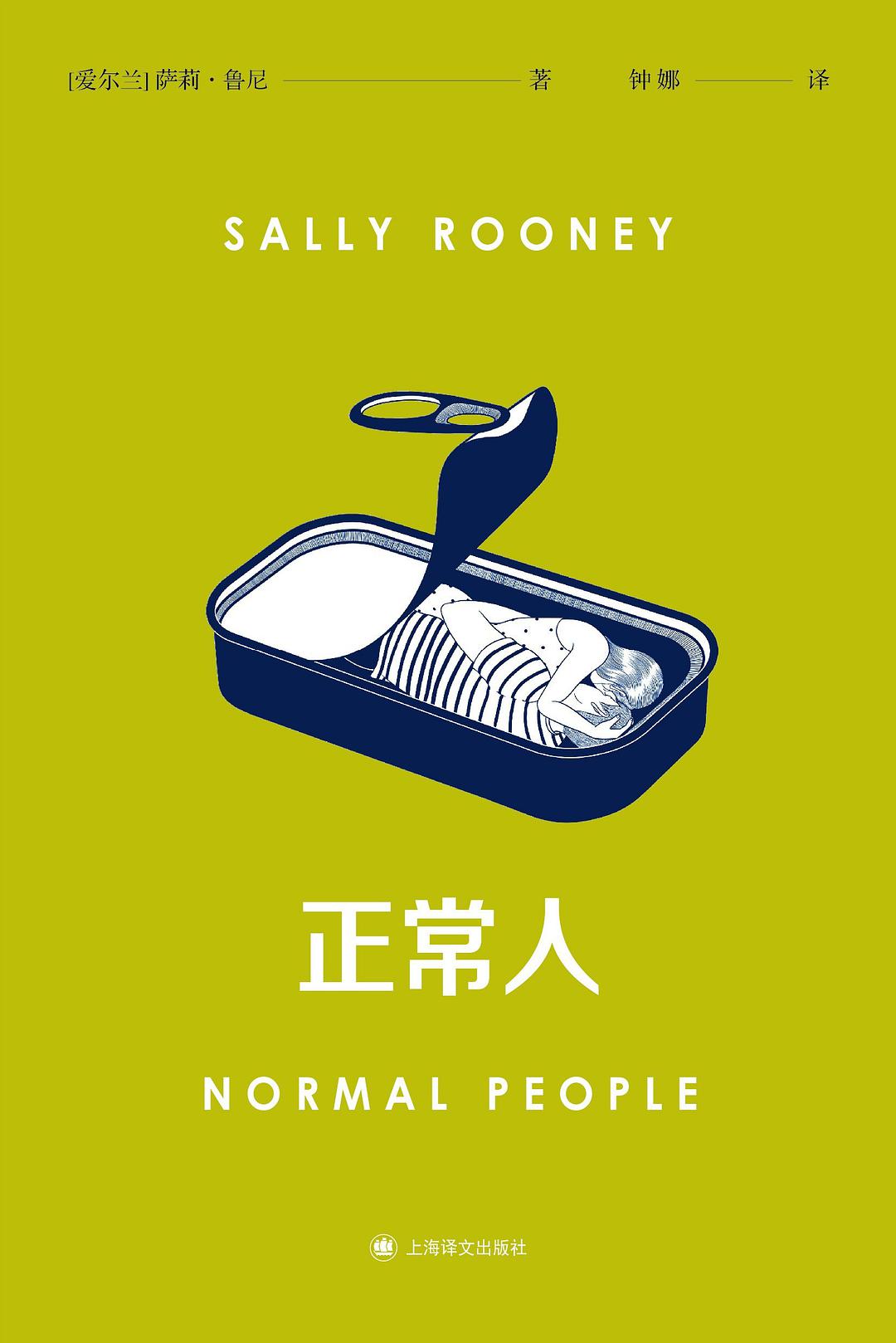
[爱尔兰]萨莉·鲁尼 著 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群岛图书 2020-6
对洛夫格罗夫来说,改变不可能很快到来。“出版界的人说‘我不读男性作家’,好像这是一种荣誉。这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也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丈夫同床共枕,有些人有儿子。拒绝让那些与你分享生活、同样拥有希望和梦想的人发出声音,这种想法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洛夫格罗夫觉得这个行业“没有完成我们为整个社会出版的使命”。她担心男性会抑郁和脱离社会,并认为如果把男性排除在外,就会产生“一种后坐力”。
但罗布·道尔建议,也许局外人的地位并不是一件坏事。“我认为,历史上真正优秀的写作和伟大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来自荣耀和胜利,而是来自排斥和反对。”
如果我们不再期待2020年代的重要男性小说家就像是1980年代著名男性小说家的翻版,那么有迹象表明,年轻男性作家的小说将进入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时代。今年春天,凯莱布·阿祖马·纳尔逊的《开放水域》出版了,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加布里埃尔·克劳泽、桑杰夫·萨霍塔和克里斯·鲍尔的书都受到了好评。耐克什·舒克拉、卢克·肯纳德、詹姆斯·斯库达莫尔和迈克尔·唐科等作家正在大展拳脚,加斯·格林威尔、布兰登·泰勒、布赖恩·华盛顿和保罗·门德斯正在创作有关同性恋欲望的杰出小说。还有萨姆·里维埃和威尔·伯恩斯等诗人,他们的首部小说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在2022年,4th Estate推出的重磅处女作是卡西姆·阿里的《好意》(Good Intentions),是该出版品牌与作者签下的六位数合约中的两本书之一。
萨顿认为人们一直都在阅读男性的文学作品,这一点不会改变。但“彻底改变”的是他们占据的文学空间,他们的地位不再是主导性的。“他们的挑战是用新的视角给读者带来惊喜,”她说,“这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因为文学和文化不会停滞不前。”
(翻译:李思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