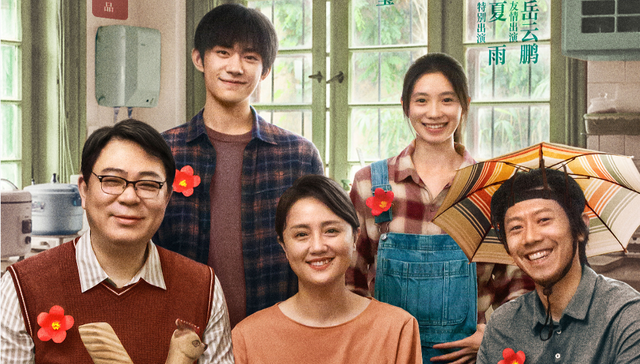记者 |
编辑 | 黄月
“坚持就是胜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是癌症患者经常听到的话,也是他们会对自己和同伴说的话。在最近上映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这些句子反复出现,有时候是主人公叛逆的调侃嘲讽,有时候是病友聚会上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句子?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胜利”,癌症患者为何用“孤岛”来隐喻自我?
如果我们循着两位身患脑癌的电影主人公的故事来思考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出以下答案:癌症的不确定性根本性地改变了患者对未来的预期和计划,他们害怕伸出手后又扑空,因而给自己裹上“生人勿扰”的刺,就像男主人公韦一航所做的那样,而这种“丧”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坚持”意味着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胜利”许诺了心态改造后的甜蜜。
但在这样的讲述中,我们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缺失了,因而为电影中亲情和爱情流下的泪水变得有些索然寡味。诚然,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心态”,一个人的心态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有巨大影响,但心态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完全受个体主观调控的,身体失控、吃喝拉撒等基础行为失调、家庭社会角色转变等问题都是影响癌症患者心态的重要因素。面对如此身心磨难,能鼓舞人保持乐观、不要被击垮固然可喜,但我们理应先检视癌症是否真的可以被战胜、癌症患者的真实经验为何,否则“坚持就是胜利”将会沦为一句口号。

现代医学所能完全攻克的癌症种类有限,大多数患者被现代医学拽离了死亡的边缘,生活于健康与疾病王国中间的“缓和地带”。癌症这样的慢性病让带病生存成为时代的常态,比起如何征服疾病,人如何与疾病共生是更需要被认识和讨论的问题。《送你一朵小红花》对医疗资源紧张、癌症污名化、因病致贫等问题进行了去政治化处理,但用“丧-乐观”的两极对立来理解癌症,用小红花消灭丧,本身就透露出“正能量”至上的政治主张。
电影中的马小远积极乐观收获了观众的泪水和赞美,而在现实中真正乐观抗癌的女孩松饼君却遭受网暴,至其离世,仍有人恶毒地留言“完结撒花”。癌症从来不是简单的生病治病,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共同塑造的复杂疾痛经验。

01 抛开“丧”和“乐观”,我们如何理解癌症?
“你好,我叫韦一航,你要看我的脑部肿瘤切片吗?”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男主人公韦一航是一名年轻的脑癌患者,他的自我介绍总是充满挑衅意味,想要用“脑部肿瘤”吓退对方。但面对同样身为脑癌患者的女主角马小远,他第一次遭遇了挫折。马小远不但没有表现出震惊,还用轻松的口吻说,自己五岁的时候脑部肿瘤就有二级了。
与乐观外向的马小远相比,韦一航显得乖戾孤僻。他不善与人交往,常常独自缩在沙发上打游戏,偶尔参加一次病友会,也用愤世嫉俗的发言把场面弄得十分尴尬。“正常人”是他心中的一道魔障,他反复质问,自己想当一个正常人有什么错,为什么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也没办法成为正常人。对观众而言,不把癌症挂在嘴边的马小远似乎“正常”得多,她做网络直播,组织线下活动,每天笑容满面。在这样的对比下,观众很容易把韦一航的困境归结为他个人的性格、思想问题,马小远也批评韦一航浑身是刺、自怜自艾的样子只会让他更苦闷。但一个人患癌后的表现,是由其原来的性情决定的吗?
在现实中,许多癌症患者表现出的孤僻、忧郁和愤怒,都和他们患病与治疗的经历密切相关,与其说性格态度决定抗癌命运,不如说癌症改变了他们的一切。从2014年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涂炯及其研究团队在一家专门治疗肿瘤的三甲医院进行了长达5年的田野调查,他们访谈了数位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对病人从检查、入院到出院以及回家后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涂炯据此写成《癌症患者的疾痛故事》一书。书里记录的一位食管癌患者J伯便在病情反复后性情大变。他第一次手术返家后不久,因为蹲着刷牙,胃液和食物反流并漏进肺部,造成脖子处伤口震裂,再度入院。科室的医护人员发觉,二次入院的J伯不再如从前那般温文尔雅、宽容豁达,而是“斤斤计较”、处处发火。人们通常这种变化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看到身上插满管子的病人,明白他“难受”“有火气”“需要发泄”,认为等病好了这些都会过去。然而,癌症对患者的纠缠远比我们想的更深远复杂。

就手术治疗来说,患者感受到的恐怕不只是一个“难受”的身体,而是失去控制的身体。在健康状态下,人很难察觉身体的存在,吃喝拉撒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从身体被异物侵入的那一刻起,这具熟悉而陌生的躯体开始引发一波又一波的精神震颤。即使患者在术中处于全麻状态,他在术前也必然明白,手术台上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也不再完整,它是可供切割的模块,没有人能从这样的想法中免于恐慌。一些脑部肿瘤手术还会在中途唤醒被麻醉的病人,以观察其大脑神经状况,许多被唤醒的人后来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电影中易烊千玺所扮演的韦一航似乎正是如此)。术后插管的束缚和疼痛自不必说,更令人难过的是,许多癌症患者盼望着早点恢复自由身,拔管后却发现这具身体连基本的动作都无法完成。涂炯观察到,食管癌患者术后需要重新学习吞咽、咳嗽等动作,因为食管切除变短后,胃部位置上提,从前的动作习惯不再适用。书中一名军人患者几十年来都大口喝水,他在抬起水杯准备快速喝下时被护士及时制止,才没造成严重后果。食管癌患者必须重新探索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吃、一次吃多少、吃什么都需要一点点摸索,并在不断的练习中与新身体磨合。
如果说缺乏切身经验让我们不足够理解癌症患者之痛,那么现代医学仅仅专注于“治愈”则加深了这种误解。首先,“治愈”在很多时候仅仅指向身体疾病,也即是医学人类学奠基人凯博文所说的disease,但患病并不只是病理层面上的问题,它还涉及患者的切身感受:病人如何解释、看待疾病,疾病如何改变了他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关系等等,凯博文将这些更宽泛的、非权威的经历归纳到“疾痛”(illness)概念。在如今的医院治疗中,癌细胞、肿瘤是本位的,患者的精神苦痛和身体苦痛一样被视为暂时的,是为了“治愈”而不得不暂且忍耐的临时状态,许多人相信,只要能在医学上宣布“治愈”,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以食管癌为例,患者接受治疗后生存期超过五年,医学上便可称为“治愈”,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学系荣誉退休教授亚瑟·弗兰克认为,从疾痛角度来看,患者只是进入了一个“缓和地带”。一位术后生存多年的癌症患者曾向涂炯坦言,担心癌症复发,觉得身体“背着一个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何时就会爆发。”癌症迫使幸存者在做人生决定时必须将生命长度和质量的不确定性纳入考虑,涂炯总结道,癌症带来的是一个“受限的身体和受限的未来”,患者需要随时依病情及预期来改变生活和未来计划,他们的心态也随之起伏。这就是为什么韦一航会执着于“正常人”与自己之间的区别,而再怎么积极的马小远也会因癌症复发而悲观地倒下。“丧”和“乐观”的两极分化,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癌症患者的经历。

涂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5
02 从“与疾病斗争”到“与疾病共存”
“治愈”一词折射的是从患病到痊愈的单向线性历程,这种理解显然不适用于癌症这样的现代慢性病。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对这类疾病另有比喻:“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要不得不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疾病不是在生命的前路上等待我们,自生命降诞之时,疾病便与之同在。健康与疾病具有共时性,没有人能完全属于健康王国,而不涉足疾病的王国。
弗兰克进一步发展了这个隐喻。他认为,两个王国之间存在一个慢性病的“缓和地带”,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进出两个王国使用的不是公民护照,而是需要定期更新的签证,医学的发展将越来越多本会死去的人留在了这个缓和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癌症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疾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医师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中认为,现代人的长寿是20世纪早期癌症普遍出现的重要因素,在古代,许多人在细胞癌变以前就因肺结核、霍乱、天花等疾病死去,当文明克服了其他疾病之后,癌症王国曝露在外。
据美国癌症学会发布的《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报告,2018年全球有大约1810万癌症新发病例和960万癌症死亡病例,中国分别占380.4万例和229.6万例,是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癌症已成为中国人口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带病生存”已为常态,小到颈椎问题,大到癌症,现代人的生活与慢性疾病纠缠在一起,绝对的健康似乎才是一种例外状态。治愈不是抗癌的终点,如何学习与疾病共处,让生活得以继续,才是更大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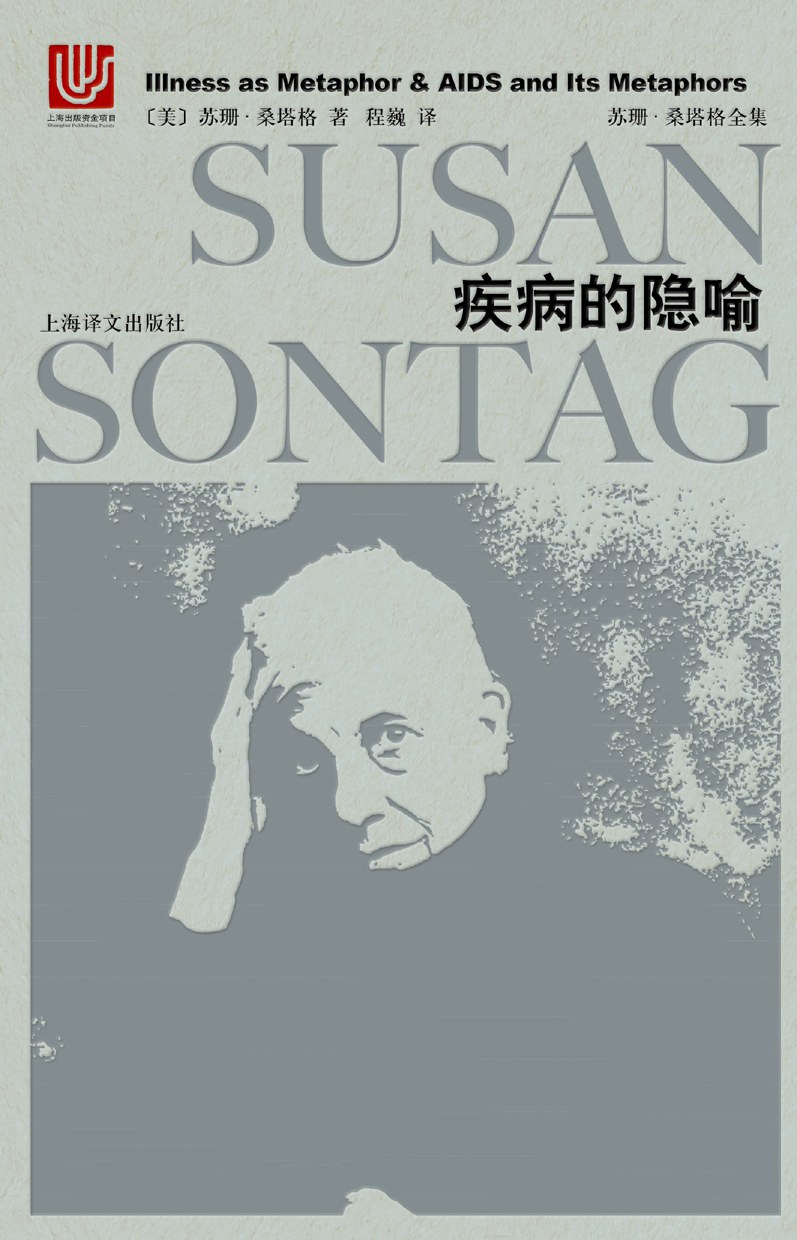
[美] 苏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4
“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患者,患者也会以此自我砥砺。但是“胜利”意味着什么?旁观者与癌症患者所说的“坚持”和“胜利”是否存在差异?涂炯注意到,癌症治疗中充满大量“战斗”隐喻,疾病被看作外来的侵入势力,病人需要化身“战士”,为生命而战。然而,那些攻击人类的癌细胞恰恰来自人体内部,它们在扩张一事上做得比人类更成功,可能无法彻底根除,一直存在复发风险。对一些患者来说,明天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是生是死,永远无法知晓。美国索诺马州立大学社会学系荣誉退休教授凯西·查默兹提出,“与疾病作斗争”同“与疾病共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不愿意承认疾病是生命固有的一面,力主将之排除,“为自我而斗争”;后者则试图让患者接受疾病所带来的新现实,在此基础之上去追求生活,“与自我斗争”。
食管癌患者L伯在术后常说“坚持就是胜利”,但涂炯发现,L伯所说的“胜利”不是指“治愈”,而是“坚持治疗和锻炼”。在医院5年,他遇见过不少像L伯一样的癌症患者,他们在疾病中思考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在废墟之上重建生活——B伯出院几年后一有空就要干点农活,还被镇上返聘回去指导工作;H伯种田养鸡;L伯和两个孙子住在一起……乍看之下是正常老人的晚年生活图景,但其背后却是他们与家人日复一日的努力和隐忍。B伯随身携带抑制胃酸反流的药物,H伯克服了打营养液堵管、注射器折断、吞咽苦难等一些列问题才摸索出新的生活模式,L伯则要小心避免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免得自己“惹人嫌弃”。
普通人可以用“坚持就是胜利”来表达支持和关心,但我们是否有资格敦促癌症患者去做斗士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借同样身为脑癌患者的马小远之口来批评韦一航的“丧”,巧妙地避开了其中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不过在“正能量”时代,身处其中的我们无法逃避这一拷问。患者有战斗的权利,也应拥有“投降”的权利。查默兹认为,投降(surrender)不等于放弃(give up),放弃是任由疾痛吞没自己,而投降意味着开启自我转变的可能。人们常对癌症病患说的另一句话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说这句话前,首先尝试理解何为“孤岛”,才有陪伴孤岛的能力,惟其如此,“坚持就是胜利”才能成为鼓励,而非绑架。

[美]悉达多·穆克吉 著 李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2
03 癌症疾痛故事背后的政治性
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这个角色或多或少地呈现了癌症患者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割裂、身体失控、与社会脱节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于“丧”,而“丧”需要接受“积极”改造,这一过程经由与乐观女孩马小远的恋爱完成。“丧”被消灭了,昂扬向上才是正确的。马小远这个角色博得了不少观众的同情和喜爱,但在现实当中,癌症患者的积极进取却招来了恶毒的网络暴力。
前段时间,不到26岁的抗癌女孩松饼君不幸离世,有人在她的微博留言区和B站视频上留言“完结撒花”。2019年,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松饼君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治疗期间,她坚持健身、旅行、完成学业,并决定拍摄vlog讲述自己的抗癌经历,鼓励其他患者。可以说她是现实版的马小远,但上传第一期vlog之后,松饼君收到的却是大量的质疑、谩骂和侮辱。
“头发这么多根本不可能是癌症”、“恰烂钱”、“得了癌症为什么还要健身”、“有小肚腩”、“(在美国治病)条件这么好……死就死了吧”……在这些恶意评论的人眼中,癌症患者打扮得漂漂亮亮,说话诙谐幽默,生活丰富多彩,完全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必然是“假的”。社会对癌症的刻板印象还停留在“惨”,但更可怕的是,这种不相信没有止步于震惊,而是滋长出仇恨。

癌症长期以来被污名化了。涂炯指出,即使 “谈癌色变”问题近年得到不小的改善,医护人员、病人、家属之间还是尽力避免提及“癌”字,经常用“那个”或者“肿瘤”来替代,癌症患者出院后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区邻里的排斥。癌症是肮脏、痛苦、失序、死亡、贫穷的象征,时时嘲弄着人类的无能。这种嘲弄既针对人类整体,又针对个人,它给医学进步以迎头痛击,向普通人夸耀自己随时可以夺走一切的力量。南风窗的文章《抗癌女孩死了,他们开香槟庆祝》里写道:“仇富,仇女,仇美,让松饼君成为了爆破目标。”在一个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社会,对不公的愤懑时常被转化为对他者的敌视,可怖的癌症时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是多么少而脆弱,这种恐惧却没能开启思考,反而燃为仇恨的怒火,让身患癌症的无辜之人成为他们攻击赌咒的对象。
电影里不允许“丧”,现实里打压积极乐观,癌症从来不是单纯的病变,人们所经历的疾痛是一场政治经济事件,例如癌症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不足,回到乡镇上缺乏足够的医疗支持,都与当前中国医疗资源紧张问题有关。连癌症的治疗和突破也离不开政治运动的推助。穆克吉在《众病之王》中写道:“一种疾病,要想实现在科学层面的转变,首先需要政治层面的转变。”如果“现代化学疗法之父” 西德尼·法伯缺乏政治敏锐性,没有与极具社会和政治能量的曼哈顿名流玛丽·拉斯克合作,癌症不知还需要多久才能从昏暗的地下室浮现到公众的聚光灯下。
在中国,癌症依旧是拖垮一个个家庭的大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不少。电影中韦一航一家也因其患病而陷入较为拮据的生活,母亲省吃俭用,父亲偷偷在工作之余开车赚钱,奶奶准备卖房凑钱,但电影对现实的讲述仅止于此,更深层的社会性问题在感动的泪水中烟消云散。现实中,癌症患者的患病经历却激发他们时时思考更多社会问题,他们会评价各级政府是否将中央政策落实到位、哪些药物应该列入医保报销范围,发出农村医疗资源过少、孤寡老人缺乏照料者等呼声。
《送你一朵小红花》对癌症病友群的描绘同样因为去政治性而显得单薄。根据涂炯的田野调查,尽管癌症病友群能够争取权益的空间很小,但它毕竟是一个带有政治意味的“共同体”,患者及家属经常在群里共享信息,为面临共同问题的人发声,而不仅仅像电影里那样提供情感支持。“他们的呼吁不再是个体的,而是为生病的群体,甚至包括其他弱势的人群,”涂炯写道。与《送你一朵小红花》相比,《我不是药神》里的病友群更接近于这样的“共同体”,因而也更有力度。

想要改变癌症病人的生存状况,仅仅给他们一朵小红花、叫他们自己学着乐观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解癌症患者的困境,反思以“身体”而非“人”为中心的医疗观念,同时,政府和社会应当增进公众对癌症的认知,为患者提供更多的系统性支持和制度保障,加大医疗建设投入,做好医疗资源分配。
尾声:“小红花”不是社会现实问题的解药
《送你一朵小红花》在片尾放送了一段真实影像,画面里有冒雨送餐的外卖骑手、地铁上疲惫的上班族,还有在洪水里举着家当等待救援的人,这段影像的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积极生活的我们”。将外卖员和“打工人”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以及洪灾逃难求生说成“积极生活”,再用“我们”营造虚假的同在感,实在是莫大的荒唐和讽刺。
如果《送你一朵小红花》正片对癌症患者现实困境的挖掘有限还可以解释为去政治性,那么这段片尾则完全暴露出它在政治上的傲慢。2020年,社会就外卖骑手算法围城、“打工人”失语等问题曾有大量讨论,这段影像却不禁让人怀疑那些讨论是否仅仅发生在互联网的回音室里。“小红花”精神看似昂扬向上却两脚离地,失去土壤的花朵就算再明艳,又能够灿烂多久呢?
参考资料:
《癌症患者的疾痛故事》 涂炯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0-5
《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 著 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4
《众病之王:癌症传》悉达多·穆克吉 著 李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2
《抗癌女孩死了,他们开香槟庆祝》
https://mp.weixin.qq.com/s/ItOvIGYTb1ZV3Si93lF5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