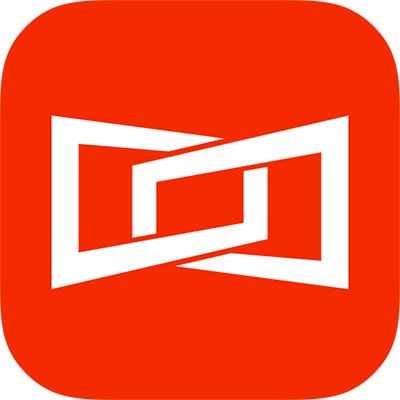文|南都观察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食用野生动物已经被千夫所指,日前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更将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无数环保人士、动物保护组织,甚至执法者付出多少努力都无法杜绝的恶习,反倒因病毒而显露出“根除”的迹象。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像穿山甲、蝙蝠这样的野生动物是病毒的宿主,那为了杜绝再次感染的风险,不如干脆把它们全数“生态杀灭”算了。2003年SARS爆发后,就有大量果子狸被杀死。江汉大学动物行为研究者萨拉·普拉托(Sara Platto)在担心,关于“穿山甲是新冠病毒源头”的猜测可能会导致这个已经濒危的动物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她强调:“问题不在于动物,而在于我们与它们接触。”

BBC纪录片《穿山甲:被捕杀最多的动物》(Pangolins: The World's Most Wanted Animal)截图。 来源:BBC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尽管自诩主宰这个星球,但现有的技术不可能消灭病毒。在生物圈中,绝大部分物种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是否与人类兼容,但病毒这个最古老的生物却是一个例外:现代社会在它的打击下十分脆弱,吊诡的是,这却正是因为我们“现代化”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高速运转的开放系统,越精密复杂就越脆弱。就像普通汽车可以适应高低不平的路,但高铁则需要分毫不差,一个小障碍可能就极其致命。现代的交通网络更是大大加剧了病毒的危险性——直到两百年前,最快的陆路传播是骑马,疫情就算爆发,也传不了多远,但现在则可以在24小时内通过密如蛛网的航班抵达全球任何一个城市。
原始社会是没有大规模传染病的,因为当时的人类迁徙不定、数量太少、居住分散,而如果一种病毒无法及时找到新宿主继续传播,它们很快就会灭绝。所以人类历史上危害猛烈的病毒,如天花、麻疹、水痘等,都是人类在农业定居之后,在和家畜的密切接触中感染上的,这已经被现代致病细菌的遗传学比较证明。实际上,现在常说的“禽流感”、“猪流感”也是这么来的:它们最初都是在养鸡场、养猪场这样禽畜密集、卫生环境堪忧的环境下出现并传染给人的。1918年曾杀死5000万人的“西班牙大流感”,现在研究大体认为其与猪流感病毒十分相似,是一种甲型流感病毒(H1N1)。
讽刺的是,正是因为旧大陆人口长期与病菌共同进化,因而他们的免疫系统强大得多。以至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对欧洲人带来的病原菌几乎毫无抵抗力,90%以上的土著由此灭绝;而黑人之所以被贩卖到美洲为奴,也正是因为他们比印第安人具有更强的免疫力,更适合作为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力。
不过,在现代的热带医学完善之前,人类所能扰动的生态系统毕竟有限,因为疟疾等热带疾病在1880年代之前几乎一再挫败了白人想在非洲、新几内亚低地等热带地区定居的企图。法国侯爵德雷伊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组织移民,结果不到3年,1000个殖民者就死了930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云南、广西等地的瘴疠,一度限制了大规模的移民。但在近一百多年来,人类几乎可以进入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而生态系统看起来却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美国疾病生态学家彼得·达扎科(Peter Daszak)曾驳斥那种“新病毒由实验室制造并泄露”的阴谋论:“这太令人羞耻了!人类似乎无法抗拒争议这些谬论。在野生动物中,病毒种类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而我们只是触及了皮毛。在这些多样的病毒中,有些病毒会感染人类,然后在感染人类的病毒中,有些会致病。”地球上像冰川、雨林等生态体系中,都有相对独立的基因系统,相互之间都缺乏抵御对方疾病的抗体,但人类打破了这些生态体系的封闭孤立,释放出了病毒,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病毒在其原本的特定生存环境下都有一个相互克制的小生态。像蝙蝠之所以成为“飞行的病毒库”,是因为它在迅速的新陈代谢之下,体温经常维持在40摄氏度上下,因而病毒不会发作,但人类却吃不消。
就此而言,近三四十年来全球各种传染病接连爆发,是生态系统遭到剧烈扰动的结果,新冠疫情是最新的一次,但却不会是最后一次。本来在一个维持平衡的生态体系中,病毒隐藏在特定的结构内,并不会自动跑出来危害人类,是人类打破了这一平衡,自食其果。在对大自然的空前破坏之下,病毒的大范围流行不是“是否”(if)的问题,而是“何时”(when)的问题。

Netflix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阻止大暴发》(Pandemic: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截图。 来源:Netflix
至今人们谈虎色变的艾滋病,现在被普遍认为是1960年代野生动物交易带来的恶果:当时非洲兴起一门利润丰厚的新生意,那就是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用于医学研究的灵长类动物。艾滋病毒(HIV)最初的传播中心是维多利亚湖西北岸,仅见于猩猩等身上,但当人类深入雨林,破坏环境,抓捕猩猩和猿猴时,它们身上所携带的艾滋病毒也就开始了全球之旅。不仅如此,艾滋病毒是一种生物安全2级的微生物,虽然高度致命,但传染性并不强,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也无法通过空气传播,在空气中暴露后只能存活几分钟,处理其血样时甚至不需要穿生化防护服。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野生动物交易,它很可能现在仍在非洲雨林的角落里。
正因此,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让它们活,也是让我们活。生态疾病学研究表明,物种多样性越高,人类感染这些病毒的几率越低,因为野生动物会对这些疾病的传播起到缓冲和稀释的作用。当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原本叮咬它们的蜱虫、伊蚊等病毒传播者,可能就转而叮咬人类,人类也就越发直接暴露在新的传染病风险面前。
记录埃博拉病毒事件的《血疫》一书在回顾这些历史时就总结道:热带雨林既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也是最大的病毒储备池,因为所有活物都携带病毒,而艾滋病、埃博拉等雨林病原体的显现,“无疑是热带生物圈遭到破坏的自然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
确实,麦克尼尔在其名著《瘟疫与人》中早就提出过一个观点:长远来看,病毒早晚都会逐渐学会与宿主共生共存,因为宿主一旦死了,它也活不了,因而最成功的、长期存活而成为流行病的菌株正是那些使人受到感染却不杀死他们的菌株——如天花和流感等。换言之,病毒毒性大,传播性弱;传播性强,毒性就会减弱。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等专家均预测,新冠病毒“有可能转成慢性的,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的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人类也是“寄生”在这个星球上。虽然在这个人类已经没有天敌、也无所畏惧的世界里,人们往往膨胀地自居为地球的主人,但疫情面前清楚地暴露出现代社会是异常脆弱的。如果我们不能像病毒那样聪明地学会共生,那么在找不到下一个宜居星球的情况下,一旦毁了地球这个宿主,我们也难逃一死。也难怪有人说,其实“人类是地球的病毒,病毒是地球的免疫系统”。
如果说这些世界末日的景象还遥不可及,那么至少经济影响是肉眼可见的——就算你不在乎野生动物的死活,至少也在意一下自己的钱袋子。这也是一种“双赢”,而事实上,也没有人类“单赢”这回事——我们要么与生态系统双赢,要么就是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