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单向空间众筹求助事件和电影《列夫·朗道:娜塔莎》(DAU. Natasha)引发的争议。
单向空间众筹求助:情怀之后,实体书店何去何从?
非典过去17年,实体书店再次因疫情进入行业的凛冬。2月24日,原本正计划15周岁生日活动的单向空间发布了一封众筹求助信,在“粮草告急”之际,希望读者能帮书店渡过难关。按照求助信中的信息,疫情蔓延以来,单向空间4家线下实体书店仅有朝阳大悦城店营业,每日售书平均不过15本,而在线直播、建群秒杀等线上促销活动也收效甚微,每次获得的收入“连值班店员一天的工资都不够”,众筹是单向空间“最后的自救”。
“求助信”很快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10万+阅读量,坂本龙一、姚晨、老狼等大V也在微博上参与转发。读者对实体书店命运的担忧和焦虑似乎短暂地使单向空间走出“孤岛”,在尚未解冻的时刻得寄一枝春芽。
“阅读是一次劈开冰海的旅途,书店是我们在寒冬中逆流而上的心灵伴侣。”在此意义上,众筹为的不只是一家销售书籍的商店,守卫“锻炼心智、存储记忆、抚慰感情的家园”才是意义所在。单向空间此举毫不意外地再次引发情怀充值的争论,对书店当前状况的描述也招来质疑。据公众号“未来可栖”,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单向空间的现金流状况不至于现在就陷入绝境,尽管书店、文字与情怀终难分割,但当情怀成为被过度依赖的营销手段,书店还能否发展出合理的经营模式就十分令人怀疑。


以情怀博取流量最后变现,并非是特属于书店的营销逻辑。去年,人人网回归、大白兔奶茶走红、周杰伦新曲《说好不哭》刷爆热搜,情怀对各个群体的精准打击从未失手。卖情怀的商业手段已是老生常谈,但每个人群都难逃脱商业的定位,所谓的“文青”正是书店情怀收割的田地。“蓝鲸财经记者工作平台”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走出孤岛”的包装下,单向空间的收费行为蒙上了一层“价值感”和“悲情色彩”,情怀充值的商业逻辑虽然老套,却总能成功唤起“自以为利他”的情绪。
单向空间此次求救的成功,也得益于与消费者关系的再塑造。去年,单向空间创始人之一吴晓波在《十三邀》与许知远对谈时说到,单向空间想要更好地发展,不应靠规模的扩大,而是着意于消费者关系的重塑。“蓝鲸”的文章认为,如果从前的许知远还被文人情结牵绊,那么当下的残酷局势则迫使单向空间向前一步,采纳吴晓波所说的“会员制”。书店产品价值的核心在于附加其上的精神符号,符号催生情感、价值的共鸣。此时,众筹救助从慷慨解囊变为一次对自我身份的体认。
不过,“求助信”引发的舆论浪潮似乎也印证了“情怀挂在嘴边的时代已经过去”的现实,至少在目前的实体书店行业如此。比起对“情怀充值”的讨伐和质疑,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注于书店的自救和转型问题。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梳理了疫情期间几家书店不同的自救方式,例如言几又联合饿了么平台,启动图书配送服务,“让精神食粮与一日三餐同样便捷”。2月28日,“言几又文化”又公布了单笔满199元赠送2枚口罩的促销活动。建投书局推出“空巢局君的生存记录”栏目,通过直播的形式向读者推荐书籍、分享读书心得,并尝试将“群星闪耀 黄金黑白”这样的展览转移至线上。
虽然已积极自救,但这两家书店现金流短缺、经营惨淡等问题依旧未得到解决。言几又集团董事长、CEO但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春节期间书店客流量、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滑80%和95%,可谓“断崖式”下跌,现金流危机短期内难以解决。建投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线上活动的确起到了与读者沟通的作用,但如何将之变现仍在探索之中,书店要恢复到正常营业水平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疫情来袭,实体书店受挫,单向空间、言几又等“网红”连锁书店依靠名人、品牌效应谋求出路,而中小型书店缺乏此类资源,处境似乎更为艰难。2月5日,中小型书店联盟“书萌”发布《疫情笼罩下的实体书店呼声 ——超千家实体书店问卷调查分析报告》,调查范围覆盖全国各省市,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参与答卷的书店大多分布在二三线城市。“报告”认为,连锁书店近年来获得了不少商业、政策红利,当下的实际情况在可控范围内,而中小型书店的情况不容乐观,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大范围的应急调整甚至闭店现象”。
报告分析指出,2013年起,实体书店行业进入复苏阶段。在“新开快开”的潮流下,许多书店将资金投入店面等硬件设备,忽视了会员系统、工作人员等软实力的发展,没有形成成功的商业模式,有“虚假繁荣”之嫌。疫情的出现中断了此前的回暖趋势,同时也暴露了实体书店近年来的问题,这是一次真实的市场检验。许多书店开始或是加速研发线上产品、开拓网络市场。然而,如何结合自身品牌特点,完成影响力变现,是书店需要潜心思考的问题。正如报告所说,实体书店要实现转型,需要将对硬件的关注转移到对技术的发展。重新找到真正的消费群体,与他们保持联系,并有效地将互联网思维融入书店经营,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实体书店才不会那么惊慌失措。
在围绕单向空间众筹求助事件的诸多讨论中,“做書”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如下疑问:如果单向空间在文化圈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许知远、《单读》以及《十三邀》等产品,何不抛下实体书店这个“沉重肉身”?而作为公共空间和文化机构,又为什么一定需要实体呢?文章作者表示,单向空间这类生存于一线城市商业中心的书店成为“象征性地标”,吸引人们朝圣打卡,不过是“刻意为之的情怀充值”。相较之下,小城市的独立书店更能保护“本地文化的灯烛”。不过,本地化社区独立书店的逐渐消失,有多少是连锁书店之过?大型书店作为“一线城市文人学者全国巡讲的分会场”而不是“本土声音的阵地”是否真的意味着浅薄?在高速流动、日趋脸谱化的现代都市里,“本土”究竟指什么?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恐怕还需要更为踏实和深入的研究。
DAU:是电影里程碑还是扭曲的社会实验?
柏林时间2月29日,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获奖名单,备受关注与争议的《列夫·朗道:娜塔莎》获得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这是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DAU系列的第12部作品,影片讲述了苏联时代一家科学研究所餐厅员工Natasha的故事。这家餐厅只有Natasha与Olga两个服务员,在终日的琐碎杂务结束后,她们喝酒聊天,谈起爱情与外遇。一天晚上,两人同一群前来庆祝放射实验成功的科研人员喝到伶仃大醉,娜塔莎与主导实验的外籍科学家Luc发生了性关系。不久后,娜塔莎被安全机构带走,遭受残酷的审讯。

“陀螺电影”柏林现场观影人陀螺凡达可用“疯狂、伟大、史无前例”形容《娜塔莎》。手持长镜头的大量使用与特写镜头的缺乏、没有表演“痕迹”的演出增强了影片的代入感与真实感,而在最后40分钟的审讯中,砸向娜塔莎的极权暴力铁拳仿佛也重重地落在了观众身上。凡达可认为,影像带来的恐惧并非源于视觉暴力,而是源自影像自身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指向了电影的制作方式——一次前所未有的疯狂实验。
DAU是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在大学时期的昵称。2005年,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沉迷于这位天才科学家的坎坷经历与古怪性格,计划为其拍摄一部传记片。在乌克兰哈尔科夫,赫尔扎诺夫斯基决心重现苏联时期的物理科学研究院。他要在21世纪打造一个关于过去的平行时空,按照1:1的比例还原当时的建筑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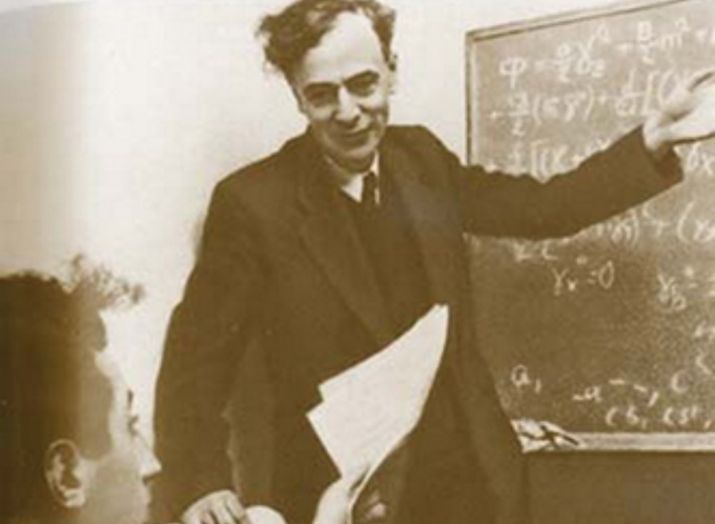
2009年,原有的电影拍摄计划被一次出格的社会实验取代。过万名演员来到DAU小镇,他们中有科学家、艺术家、清洁工、理发师,也有罪犯以及新纳粹主义者。在这里,他们被拨回1938-1968的苏联时间,一切细节随着时间流动而变化,演员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完全按照苏联的规则去生活。属于未来世界的词汇与设备一律禁止使用,赫尔扎诺夫斯基安置的大量微型摄像机无处不在地凝视着这个巨大的片场。与其说DAU是一次沉浸式的表演,不如说是一场“斯大林式楚门秀”。截至2011年,这些镜头共捕捉了700小时的影像素材,DAU系列电影就此诞生。
《娜塔莎》不是DAU与公众的第一次接触。2019年初,DAU在巴黎、柏林、伦敦举办了全沉浸式艺术体验展览。在巴黎,夏特雷剧院与城市剧院24小时开放,观众可根据期望的体验时长购买20-150欧元不等的三种入场“VISA”。体验24小时或以上的观众可根据心理测试获得属于私人的订制路线。他们在这里观看DAU影片,与神父、拉比或萨满交谈,参加科学实验。同DAU小镇生活者一样,参与者的行为都会被摄像头记录。

夏特雷剧院总监Ruth Mackenzie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说到,DAU不是电影、戏剧,也不是艺术,而是“唯一的、从未公开的体验”。这场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在三个展出城市分别打出了“平等”“自有”“博爱”的口号,《世界报》记者则用了三个截然不同的词汇形容了自己所见的DAU——出格、暴力与混乱。
此次揽获银熊奖的《娜塔莎》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女主人公Natasha赤裸地坐在椅子上,被逼将玻璃瓶插入自己的阴道。根据已观影人士的描述,该镜头保持了全片一贯的“真实性”,而这种缺乏表演的逼真感正是凡达可提到的恐惧之根源。一名拒绝为其配音的法国女演员向《世界报》表示无法认同这种拍摄行为,“这个女性确是在经受折磨,这不是演戏!”而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则回应:“我不在乎。她是一个妓女,我在一个性虐者妓院里找到她的。”
自由撰稿人Steve Rose在为《卫报》撰写一篇关于DAU的文章时采访了DAU的执行制作人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谈及上述争议性镜头,Martine表示,项目的参与者知道他们有叫停的权利,“如果她说‘我受不了了’,那么大家都会停手的。”
和Rose一样,很多人对于演出者能否在微型斯大林世界里真正“叫停”保持怀疑。在《世界报》报道的另一个案例中,一名来自纽约的表演艺术家受邀出演“控制新纳粹分子的心理学教授”,但新纳粹分子团体却控制了他,对他拳脚相加,使他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娜塔莎》中的Luc在回忆影片中的性爱场景时说,尽管DAU没有剧本,但当天许多人毫无理由地劝说自己喝酒,醒来时便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他认为这是赫尔扎诺夫斯基的安排,“他没有剧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设置好一些情况,一些足以使事情发生的倾向,这样他就可以操纵我们了。”

“控制”是DAU为人诟病的主要问题之一。赫尔扎诺夫斯基曾坦言,自己是DAU小镇的规则控制者。他是这个疯狂实验的缔造者,在微观的斯大林极权世界里,他扮演了老大哥的角色。然而,DAU里的“控制”远不止于此。Luc表示,观影或许令人不适,但他本人却享受DAU世界带来的某种突破与自我释放。比起现实世界,一些参与者在项目结束之后也更愿意回到DAU小镇去生活。
《卫报》的一篇影评指出,审问官Azhippo在折磨Natasha之余不断地询问他们是否成为“朋友”了,这并非简单的施虐,而是他们所需的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暴力与恐吓是对Natasha“里通外国”行为的修正,也是苏维埃政权对正直同志的招募,蹂躏她脸颊的皮靴勒令她参与对外国人士的监控,而不是发展一段正常的男女关系。Azhippo与Natasha之间存在一种令人惊骇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如斯大林式国家和生存在其中的人们所经历的那样,DAU王国与其参与者亦或如是。

正如《卫报》影评所说的那样,《娜塔莎》不能简单地被当作一部电影来评判,它是庞大的多媒体艺术装置的一部分,在被人们忽视的过去的15年里,其制作已然成为传奇。DAU实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叙述其意义?艺术与现实伦理道德的关系遭受了怎样的挑战?赫尔扎诺夫斯基是天才还是独裁者……诸多问题尚在争议之中。面对质疑和指控,赫尔扎诺夫斯基解释道,DAU与其说是为了重现苏联的状况,不如说是为了检测今天,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独裁者,可以是公司的独裁者、家庭的独裁者,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独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