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86年,马原发表了一篇小说,名为《虚构》。这部作品再现了马原当年秘密潜入麻风村看到的景象:在经历封锁与世隔绝的麻风村里,“我”看到麻风病人残缺的肢体、缺少五官的面孔、平静的神情以及鬼魅似的动作,这种观察本身就令“我”一次次地陷入恐惧。
对麻风病的恐惧与我们今日在瘟疫中感到的不安有些许相似。马原也在采访中谈论到了为何书写恐惧使他着迷,以及为何以文学表现恐惧是重要的。马原认为,人类自有文字有历史以来,对疾病、死亡、自然灾难和不可知的世界就存有恐惧,“我们不是今天才恐惧的,所以对麻风病的恐惧也好,对眼下新冠病毒潜伏期的不安也好,都是对不可控的、无力解析的世界的恐惧。这个恐惧的威胁一直在那。”
马原出生于辽宁锦州,17岁初中毕业下放到辽宁锦县大有农场,和其他知青一样,住土坯房,每天锄地、割苇子和修水渠。那段知青生活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回城后,马原在机械厂做过工人,后来主动申请去西藏工作,第一次申请失败,第二次终于成功。他在西藏七年,做过编辑记者,到处游走,寻找适合的故事写小说,其中就包括《冈底斯的诱惑》与《虚构》。

马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 2019年7月
日前,我们电话连线了现生活于云南南糯山的作家马原,与他聊了聊文学中的恐惧与恐惧下的文学。
“恐惧是文学最主要的魅力,恐惧是文学的动力和源泉”
界面文化:1986年你的小说《虚构》发表,这篇小说是以麻风病为主题的,那时候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以瘟疫为题材的小说?

马原:(我)对麻风病关心,一方面是我当时在西藏做记者,刚好有机会接触到麻风病隔离区——当时也叫麻风村,这是在政府力量下形成的隔离村,住的都是麻风病患者。去了麻风村以后我觉得很震撼——跟当下的瘟疫相似,麻风病是恐怖的——麻风病患者都有表面的残疾,手脚会断掉,鼻子也会烂掉,这种身体残疾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与生俱来的。
麻风病很少见,我们对陌生的东西都会有恐惧,比如说我们汉人经常说鬼,西方用另外一个词就是魔鬼,活人的恐惧点都是相似的。有两位我很喜欢的、非常好的作家,一个是格雷厄姆·格林,一个是法国人弗朗索瓦·莫利亚克,他们都写过麻风病人的故事,莫里亚克的叫《给麻风病人的吻》,格林的小说叫做《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我一直认为,《给麻风病人的吻》是全世界小说史上的一部杰作。这两部再加上加缪的《鼠疫》,在我心里都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是仅有的几部写恐惧、写瘟疫、写魔鬼写得最好的小说,所以我那时候雄心万丈,铆足了劲儿,想写一部同样出色的小说。通过一部关于麻风病的小说, 我希望能再现自己在麻风村感受到的恐惧、无所适从和陌生感等等。我想《虚构》也是我这一生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算是我的代表作。
界面文化:你在《虚构》中写出了一种对瘟疫的不安感,包括“我”不知道麻风病的潜伏期有多长,不知道与麻风病女人亲密接触的后果究竟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映射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不知道病毒的潜伏期有多长,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与感染者擦身而过。你怎么看待瘟疫或者传染病带给人的长期的不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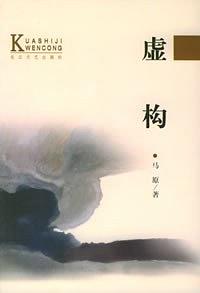
马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
马原:人类自有文字有历史以来,对疾病、死亡、自然灾难和不可知的世界都存有恐惧,我们不是今天才恐惧的,所以对麻风病的恐惧也好,对眼下新冠病毒潜伏期的不安也好,都是对不可控的、无力解析的世界的恐惧。这个恐惧的威胁一直在那。
我在家里盖书院的时候,因为自己缺少经验、从来也没有完完整整地盖过房子,所以没有在这组建筑物上做避雷针。但这件事让我心里相当紧张,因为这里每年有4个月以上的漫长雨季,雷霆闪电是家常便饭。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看过那么多被雷击中的建筑物烧毁。所以雷电像是悬在我家人和书院头上的一柄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但我知道我有生之年应该留在山上不会走了。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应该再延宕了,我上山9年了,幸运地捱过9年,我的建筑物没有被闪电击中过,但是我应该马上就去做避雷针。
我之所以把雷电这个话提出来,是想跟你说,雷电跟疾病都是同理,威胁是一直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从出生那一天,前面一定是死亡。所以死的威胁和恐惧永远存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在我们的耳边和心里。我对恐惧,尤其是许多人的恐惧特别感兴趣。恐惧是文学最主要的魅力,恐惧是文学的动力和源泉。
界面文化:我们该怎样理解“恐惧是文学是最主要的魅力”?
马原:人类恐惧很多事情,比如死亡和疾病,尤其是人类不可控的疾病,比如瘟疫,这些东西在文学中特别有活力和感染力。我个人特别看重人不能控制的那部分世界。人类有可以控制的事情,用种地来说,可控的是种子、肥料和水,另外的东西人类还是干预不了,像是火山爆发、灾难天气或者是让全世界惊恐的蝗灾、还在我们身边萦绕的疫情等等。
人跟不可控的自然的关系,这是我这一辈子最感兴趣的主题。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文学可以施展拳脚的,可能以最大限度接近真相的。这也是我对文学越来越功利化、功能化的个人内心的反叛。
我大前年写了一篇小说叫《姑娘寨》,里面就写到了一次历史上的瘟疫。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场瘟疫是一次天谴——古代一直认为瘟疫是遭天谴,人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老天爷发怒了,降瘟疫给人类。当然眼下这场瘟疫有更复杂的说法,现在都莫衷一是。但无论怎样,瘟疫都在提醒着我们,人跟自然或者说上天之间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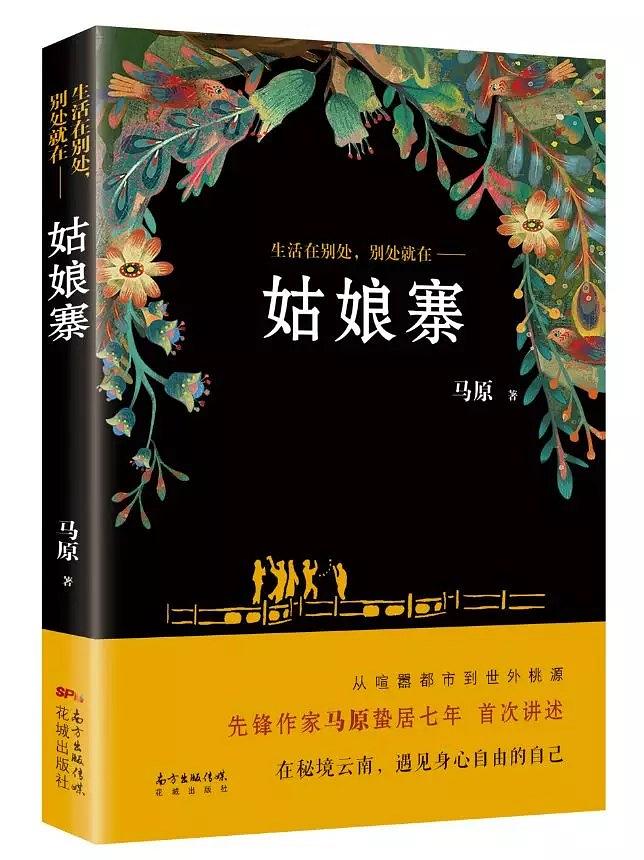
马原 著
花城出版社 2019
在这次波及上十亿人的大瘟疫之后,人类应该多讲讲人和不可控的那部分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人和瘟疫、人和死亡、人和天道等等,把文学慢慢归到原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让文学更多地诉诸人类的“干预”作为。一定要去把那些原本不可以也不可能做出准确判断的价值还给混沌本身,还给不可控、不可解析本身。
“社会学价值不是文学的首要价值,文学不是为了载道”
界面文化:刚说到这是你对于功利化文学、功能化个人的一种内心的反叛,这种反叛具体指什么?
马原: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文学,跟世界文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国家的文学一直强调文以载道——这个可能是民族传统,觉得文学背后的事情和道理特别重要。我一直不这么看,我觉得那些能恒久地、不变地给人的内心造成震撼、震动和撕裂的东西,才是文学最骨子里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现在特别喜欢讲的社会学的价值。社会学的价值在文学和小说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社会学的价值都是因时代而变的,时间过了,当时一度流行的社会学价值会变得很轻,甚至很可笑。
界面文化:所谓的文学的社会学价值是指记录时代的价值吗?
马原:社会学价值首先有意识形态价值的方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合作化”,这是苏共布尔什维克的尝试,中国也学前苏联搞过“合作化”,那时候出现了一个专门写“合作化”的重量级作家叫柳青,他写过一本《创业史》。很多年里,文学讲社会学价值的导向都影响了我们国家的文学,因为合作化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搞过合作化,60年代沿袭了这个制度,所以我们的文学要写“合作化”。然而,“合作化”是一个政府的尝试,并不具有多大的文学价值。所以从《虚构》中麻风病的话题聊起,我就愿意把我对文学的认定和我们流行的文学的价值论做一个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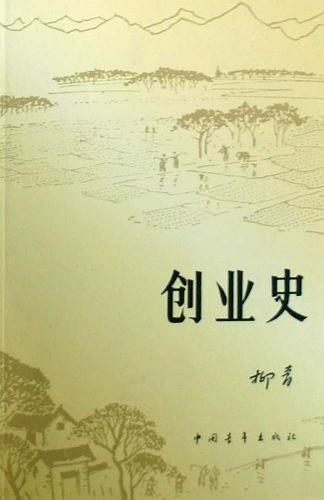
柳青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界面文化:如果说文学的社会学价值并不是文学的第一价值,那么你赞同的文学的价值在于哪方面?
马原:我一直不认为社会学价值是文学的首要价值,文学不是为了载道。文学首先是为了娱乐,文学可以给你每天重复的生活一点新鲜感和刺激。文学的第二个功能是启发和启迪,因为个人受自身生活的局限,对很多东西确实不明白,文学就像给你开一面窗一样,让你对生活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让你重新思考生活的选择,重新肯定或否定生活。
具体来说,娱乐的文学包括流行畅销书、推理悬念小说之类,现在光是《福尔摩斯》或《西游记》,就有无穷无尽的非文学版本——电影、电视或者游戏,这类娱乐文学一开始就立足于让人打发时间,带给人智力考验的愉悦。而启迪文学就比如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像《十日谈》《一千零一夜》,或者更早的《旧约》。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启迪比文学的训诫、归纳功能要重要得多。现在人们太看重归纳和训诫的作用了,好像只有能梳理大历史、能够涵盖很多人的文学才是好的、是主流的、可以得大奖的,让你升官发财耀祖光宗的。所以我个人一直特别愿意强调,让文学回到它的初始。
界面文化:所以在这场瘟疫之后,你会期待文学有一个回归——回归到文学本来的价值中去吗?你认为回归会发生吗?
马原:回归一定会发生。最近这两天一个老英雄去世——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他的作品《半夜鸡叫》塑造了一个叫“周扒皮”的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扒皮”在中国很深入人心,可是“周扒皮”只是个虚构人物。另外一些关于地主恶霸的形象塑造也是如此:有一个真人地主叫刘文彩,人们常说大地主刘文彩如何作恶的,可是刘文彩的故居我都去过,跟当地百姓聊起来,才知道刘文彩这个形象是经过“妖魔化”的,刘文彩其实是个做了特别多好事的乡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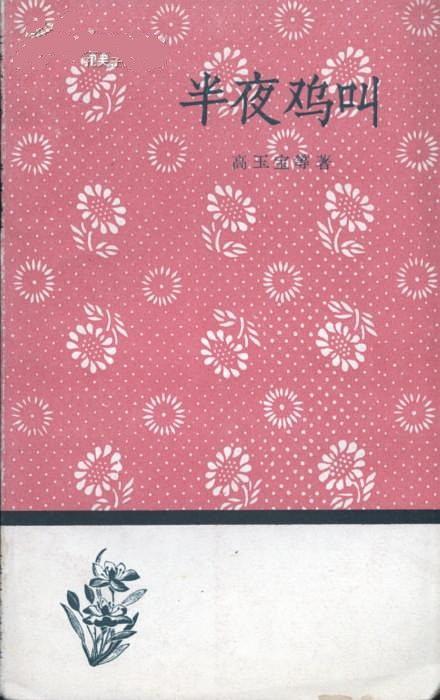
高玉宝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我的意思是,人规定了一种价值论,然后按照这种价值论做文学,这个在当时可能很火,但可能出现特别大的偏差和谬误,而时间本身慢慢还是会转回来的,人为干预、人为塑造的东西,会被时间本身纠正过来。一次上十亿人经历的大瘟疫,应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让一些东西能逐渐回归它本来的样子。
界面文化:你有没有注意到关于瘟疫的写作,包括瘟疫现场的记录或者书写瘟疫的诗歌或评论?
马原:我自己没写。我知道有一些人在写诗,诗人朋友挺多的,他们也在朋友圈发他们的诗。诗来的快,今天写,今天就可以发出来。而有一些人写诗被广泛诟病,比如说作为演员的姜昆,写一首诗,被很多人拿来和捐钱的他的同行郭德纲比。如果正好在最热闹的时候写诗,客观上变成了一种“凑热闹”,这样的文学我也不知道有多大意义。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例子,就是方方。“方方日记”变成了诸多关心疫情的老百姓每天想方设法去读的文本,它引起了公众的极大热情。原本这个内容算不上文学,但在一个好作家手里,它能够给人正面带来力量和启迪,就是好的文学。
有一点我是很肯定的,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有非常多关于这场瘟疫的叙事文本,我期待其中会有杰作出现。但我说的杰作,不是政府层面倡导的、能够获得文学奖的东西。
金钱与家庭哪个更重要?“这场瘟疫帮助我们纠偏”
界面文化:这场瘟疫中,很多人都过上了足不出户的生活,你认为这种经验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
马原:这次瘟疫导致很多人都不能出门。很多人过去总说,我每天忙、有多少天没在家里吃饭了。很多在社会上忙忙碌碌的赚钱的当官的交际的人,的确,家庭对他们早就不重要了。这个回合很多人都回到家庭,因为他们不能社交,很多人都感慨:他妈的,幸亏有这场瘟疫,要不然早就忘了家才是根本。家里有那些琐碎具体的内容,吃饭的时间吃饭,睡觉的时间睡觉,在有限的小空间里,以家庭为单位,有一点小小的娱乐,聊聊天看看电视或者看看书……你最关心的是你的家人,家人最关心的是你。
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以家庭为单位的,只有最近三四十年,大家被金钱这个魔鬼折腾得觉得家庭没那么重要了,钱才重要,欲望才重要。所以我说,在这个回合里面,人类重新体会到你生活的根基和生活的出发点,还是以家庭为主。我认为惶恐、紧张、忧心忡忡其实都是让人类重新认识到你的根基、底部的地方,你最后的归宿还是家庭。这场瘟疫帮助我们纠偏,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对生活、对劳动、对工作、对金钱,已经偏差得太多了。
界面文化:这场瘟疫对你个人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马原:没有,但是我们山也封了,山门设卡,不可以进出,外人不能进,里面不能出。我们自己家种菜。农村生活不就这样嘛,有一半食物自己种,一半去买。还好我们家不止是家,书院也在一起,过往经常有人来。我们家有两个大冰箱,冰箱有很多储存,各种各样的肉类,腊肉香肠火腿都有。我们自己还养鸡。我老婆就很开心,就说哎呀一两个月撑过去没问题,地里有青菜,冰箱里有脂肪和蛋白质。
界面文化:这次瘟疫对你的心理造成了波动吗?
马原:没,我自己的文学的一个“丰碑”就是《鼠疫》,在瘟疫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这辈子没有和瘟疫擦肩而过的幸运。这个没有办法,一个小说家可能希望经历常人不经历的事情,包括麻风病、其他的瘟疫或者坐牢。我这辈子看来坐牢没机会了,居然和瘟疫遭遇了,从经历角度说也算是一个“幸运”。
界面文化:那么这次瘟疫与你之前面对麻风病在心理体验上有何不同?
马原:麻风村是我自己去的,主动权操在我手里,可是面对瘟疫每个人都是被动的,主动和被动还是不一样的。在我内心里,我确实有这种和瘟疫遭遇的渴望。我不太怕死,因为我已经得过大病。内心对死有特别多的体悟,对死本身不恐惧。而且我是有神论者,认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