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语中的“gvul”具有多种相互关联的含义:根据上下文,它可以表示“边缘”、“边界”或“极限”。以色列的活跃人士和作家在关于该国主权边界及其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吞并和占领的争论中,都在使用这个模糊的词语,凸显出道德边界和权力限制的问题。作家菲尔·科恩·卢斯蒂格(Kfir Cohen-Lustig)在新书中,探讨了物理边界、哲学边界和社会边界,与上述争论之间的关联。在《世界创造者,符号解读者》(Makers of Worlds, Readers of Signs)中,卢斯蒂格编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文学史,探讨了全球化(狭义地被理解为,一国对外国市场开放经济边界)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作品的影响。
按照卢斯蒂格的构想,文学本身就是对“社会限制”(social limits)的一系列回应——在文学中,人们可以探讨可接受的与不可接受的,可想象的与不可想象的之间的隐喻性边界。一种黑格尔式的“社会限制”概念使卢斯蒂格提出一个简单的主张: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主导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这不仅制约着个人和集体的观点,也制约着我们心理和物理现实的审美表现。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存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即使当作品本身正在积极地挑战这些社会结构。
那些熟悉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理论、或是他著名的口号“总是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人,将很容易掌握研究文学的原理,它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形式。在研究以色列文学和巴以关系方面,《世界创造者,符号解读者》加入了杰姆逊主义,最近在学者奥德·尼尔(Oded Nir)的著作《抗争的标记:以色列小说中的集体形象》(Signatures of Struggle: The Figuration of Collectivity in Israeli Fiction)中也得到体现。卢斯蒂格的著作甚至还附有杰姆逊本人的简短序言,其中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告诉读者(更像是“告诫”),这本书“利用”文学“使真正的历史作为背景显现”。的确,卢斯蒂格对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历史非常关注,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和私有化改变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现代文学典范。最明显的是,这些过程影响了巴以争议性边界之内和之外文学产生和传播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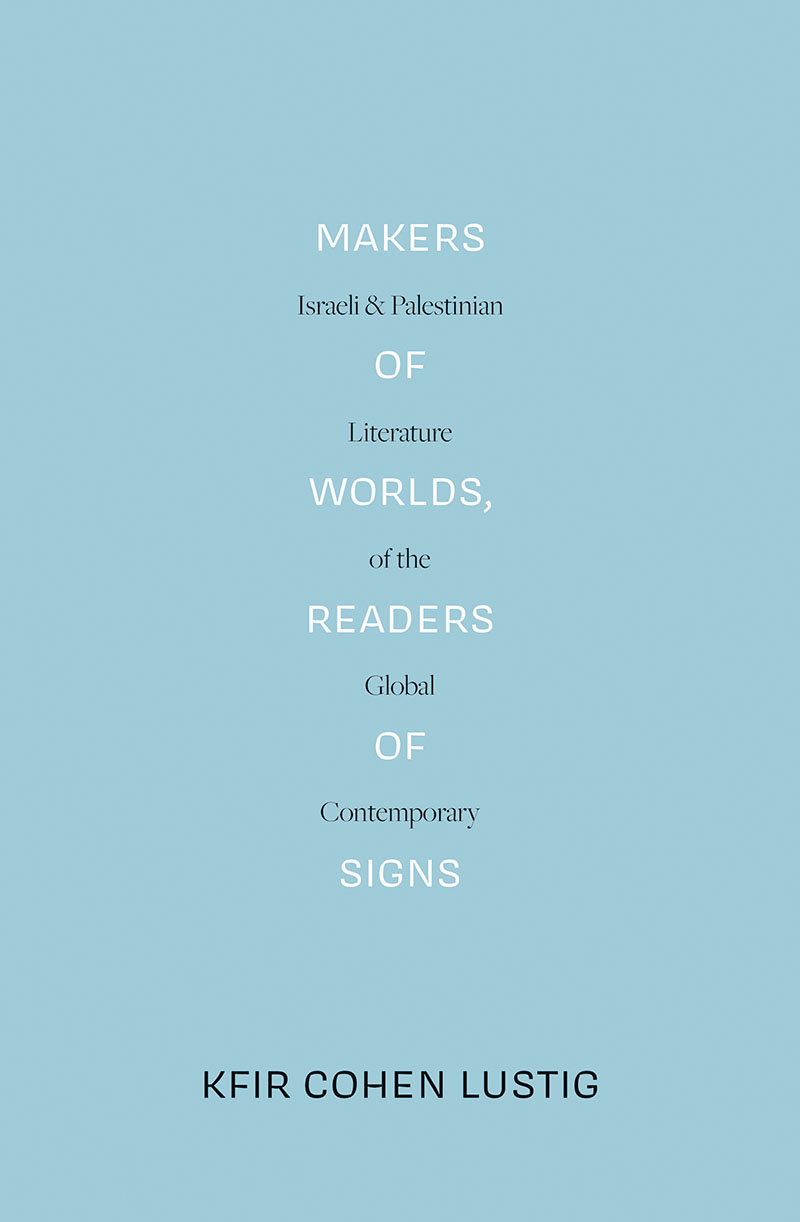
卢斯蒂格对现有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文学编史持批判态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时间顺序划分法,该划分法不关注民族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而是关注不同时期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家“审美自主”的程度。从194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左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文学反映了该两个社会中,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模糊的界限。正如卢斯蒂格所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作家有意识地参与:或通过回应建设国家的任务来“创造”他们的世界(对于以色列文学而言),或为争取民族自决而抗争(对于巴勒斯坦文学而言)。他们探讨了新的政治可能性,描绘了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角色,或以民族集体的名义在诗歌、随笔、小说和故事中表达观点。在这个时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家都很明白,文学为政治目标服务或在“创造世界”的进程中积极参与之功用。即使当他们抗议私人生活也被纳入集体生活之时(如在以色列作家Yeshayahu Koren的作品中),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们施加的限制。当他们决定接受并参与政治(如巴勒斯坦作家Sahar Khalifeh和她的同时代人所做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文学行为中认识到了必然的政治性。
在1980年代后期的以色列和1990年代中期的巴勒斯坦,人们开始重新界定划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边界。1985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经济稳定计划》,使该国经济走上了一条市场化和金融化的道路。随后,人们对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对权威和(个人)身份前所未有的文学探索。多数以色列文学评论家将这一现象视为后现代主义浪潮——由零散(个人化)的声音叙述的小说,以讽刺性的故事叙述为特征——卢斯蒂格将其解释为以色列全球化的结果。诸如奥利·卡斯特-布卢姆(Orly Castel-Bloom)和尼尔·巴哈姆(Nir Baram)等作家开始高度意识到,以色列国民与国家联系之间的松绑,从而发展出新的政治情感。他们的作品经常批判以色列的各机构,从军队到政府,但并未批判卢斯蒂格所称的任何“创造世界”的行为,转而强调个人无助和政治背叛的感受。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历史和文学走的是一条不同但大致相似的道路。 1987年爆发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The First Intifada),夺走了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约200名以色列人的生命,最终在1993年签署了《奥斯陆协议》(Oslo Peace Accords)。在后奥斯陆时代,全球资本投资网络进入了被占领的地区,主要是以外资非政府组织的形式进入。正如卢斯蒂格所说,接下来是“政治和民间领域之间象征性的分离”渗透到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艺术当中。巴勒斯坦作家仍然在政治上进行参与,但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新的资本社会的制约。阿拉伯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文学作品也加入到了巴勒斯坦的文学典范中,而巴勒斯坦文学的营销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卢斯蒂格展示了英译本巴勒斯坦作品的品牌营销如何转向了个人化特征,以强调个人和个性来替代集体性。在1989年,作家萨哈尔·哈里菲1976年的作品《野生荆棘》(Wild Thorns)的美国出版商描述该书“真实地描绘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占领,而阿达尼亚·希比(Adania Shibli)2010年的小说《触碰》(Touch)的营销词则是代表了作家本人的“独特世界”。与1980年代以来的以色列文学一样,自1990年代以来的巴勒斯坦文学也被翻译和发行,与其他(世界)“边缘”文学一样。

文学翻译在《世界创造者,符号解读者》中扮演关键角色,尽管卢斯蒂格几乎没有将其理论化。翻译研究中的当代经典著作,例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1999年的作品《文学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和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2000年的论文《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因其解释了文学作品和体裁如何从全球的“边缘”来到“中心”位置,而受到赞誉。然而它们也同样受到了批评,因为坚持称民族国家和世界之间所谓“并无区别”。卢斯蒂格的文学分析假设,我们的世界不再被整齐地划分为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资本削弱国家、并施加一种抽象等效的全球空间”。通过这一“等效”(equivalence)观念,卢斯蒂格解释了为什么过去二十年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文学作品已经类似于通常被称为的“全球小说”。由于莫雷蒂及其他人所认定的世界文学的“范畴”(事实是,当评论家进行分析时,往往只能阅读有限数量的作品),很难说是否真如卢斯蒂格所言。而在《世界创造者,符号解读者》中,卢斯蒂格本人仔细研究了十几种文学文本。在他的分析中,作品往往向读者展示的是它的独特性而不是统一性,促使他提出了问题,又仅在本书中隐晦地做答: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它是否将我们带到了我们自身经验的边界之外?正如卢斯蒂格所暗示的那样,它是否仅仅向我们证明了全球资本网络已取代民族国家?
卢斯蒂格认为,民族国家是不可逆转的弱化机制,这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严峻的难题,即关于文学与全球政治之间的关系。当代文学作品可能会受到资本跨越国界流动的影响,甚至也可能通过翻译而跨越国界,但人们(包括作家和读者)却越来越多地被禁止从一个国家迁徙至另一个国家。以巴勒斯坦为例,由于西岸和加沙各自的现行政府对其入境口岸的管控,使得过境变得难上加难。在书中卢斯蒂格提出反对,即民族主义不应是探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文学的唯一棱镜,然而民族国家仍在对广大人口施加的权力却依然令人沮丧,这超出了该研究的“边界”。不过,阅读这样一份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文学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它并不以身份认同(民族、宗教、种族或性别)为中心,而是关注了资本主义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本文作者 Danielle Drori 最近于纽约大学完成了希伯来语和比较文学的博士研究,目前任教于纽约市的不同场所,并正在撰写一本书。该书将探讨1900年代初期,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与欧洲和巴勒斯坦文学翻译之间的联系。
(翻译:西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