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年仅两岁的乔伊·格里菲斯(Joy Griffith)爬到祖父的安乐椅上看动画,而后不慎摔到了可折叠的脚架和座垫之间。脚架卡住了她的头,她开始窒息。最终被发现时她已脸色铁青,命悬一线。警察从椅子里救下她,为她实施了复苏术。急救是成功了,但她的缺氧时间已经过长,这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孩面临着永久性的脑损伤。自那以后,她成了躺在医院里的植物人。
1985年6月,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发出一项“全国消费警示”,提醒大众留意令格里菲斯受困的安乐椅型号。但该委员会尚需决定是否要求厂商改变设计,为此,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沃伦·普鲁内拉(Warren Prunella)进行了一番计算。他调查了仍在使用中的4000万张椅子,其中每一张都用了10年以上。据估计,对其实施改造每年将能挽救一条生命,鉴于委员会1980年规定了每条人命的价值是100万美元,这样改造的收益便只有1000万美元。对厂家而言完全是收不抵支。于是,同年12月,委员会决定不要求厂商更改产品设计方案。如果说,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喻的,那在当时也一样——相当不可理喻,事实上,椅子的厂家后来自愿改进了设计。
普鲁内拉的计算乃是日益依赖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里根政府使其成为了一切新的政府规制的金科玉律。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坐上了联邦规制机器的头把交椅。“经济学家相当有效率地决定着是否应该允许扶手椅碾压小孩。”本雅明·阿珀鲍姆(Binyamin Appelbaum)在新书《经济学家时段》(The Economists' Hour)中写道。“随着政府日渐依赖成本-收益分析,诸如普鲁内拉这类经济学家在事关生死的决策上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经济学成了政治生活的第一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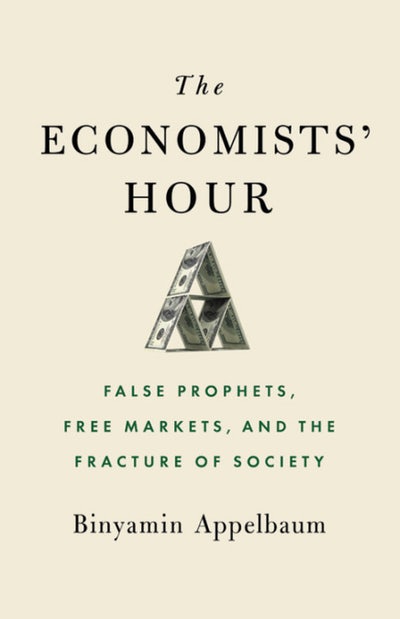
阿珀鲍姆新书的标题指的是1969年至2008年这一时期。在他看来,该时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包括减税、紧缩、弱化规制、自由贸易、货币主义、浮动汇率、宽松的反托拉斯执法、低通胀等等——几乎是经济学家们一致认同的。这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胜利的时代。阿颇鲍姆依次讨论了这些大多始于1940或1950年代的经济观念的故事,追溯了它们的创立、实施和现状。这一结构让该书读来有一种噩梦反复循环的感觉,每次重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起初,在战后经济腾飞的时代,一切都运转良好,接着你莫名其妙地就陷入了如今令人难堪的紧缩泥潭。
每个故事都开始于20世纪中叶,当时新政让经济学家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规模,政客开始求助于经济学家,以阐明其新颖而复杂的动议及向当地选民说明政策的合理性。甚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黑暗布道士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承认“讽刺的是,新政是一剂救命药”。他表示,如果没有它,他可能根本就找不到经济学家这份工作了。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后期,联邦政府中的经济学家数目从2000人迅速涨到了6000人。

新政也促使了成本-收益分析的兴起。诸如修建水坝或是兴建农村电气设施这样的大工程需要制定预算并加以约束。1939年,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提出,成本-收益分析的政治问题——即总会有人失去一些东西——根本就不是问题。理由在于,政府理论上可以从赢家那里转移一小笔钱给输家,以平衡局面:例如,若某项政策令玉米消费量下滑,政府就可以向心怀不满的农民提供救助。然而,这并没有给出政府为什么要平衡整个局面的理由,只是说这是可能的而已。阿颇鲍姆认为,如今所称的卡尔多-希克斯原则(Kaldor-Hicks principle)乃是“一种旨在照顾赢家心情的理论;而输家是否会因为拥有这些理论上的好处而安心,那是不太清楚的”。阿珀鲍姆称,该原则如今仍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核心。这种思路轻易地打发了一切政策都要面临的政治问题:如何对待输家。
自新政实施至1970年代,对企业的规制日益加强。尼克松政府设立了环境保护局(EPA)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两大机构。企业暂时处于守势,但很快就在经济学家中找到了强力的盟友,许多经济学家都以低效为由反对规制。企业开始主张,如果服从一项新的规制(比方说安全带或者控制铅含量)带来的成本超过了收益,那就不应当实行它。尼克松时代末期至今的政府都同意了这一观点。
成本-收益分析的关键,是对一条人命的货币价值进行动态测算。如果一条命算出来太贵了,那规制就是正当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应该阻止或废除规制。2004年,为放松空气污染规制,环保局悄悄地把每条人命的价值下调了8%,2008年,该局决定不根据通胀进行调整,人命价值再度缩水3%。人命价值的上下浮动看似合理,实则便于保持政治决策的不透明性。同时,它还砍掉了政治话语的灰色区域,让政治辩论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用长篇大论的数据、图表和公式把政策弄得晦涩难懂。合理的简洁性(rational simplicity)与技术官僚统治的复杂性(technocratic complexity)的联姻为累退性的政策提供了庇护,使企业获利而纳税人受损。经济学家把困扰了政治哲学家多个世纪的问题——对一个社会而言,何种程度的伤害是可以接受的——简化为了一个数学问题。

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是当代奥巴马政府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支持者,他曾表示:“美国经历了一场革命。没有擦枪走火。没有人头落地。没有上街游行。大部分人根本未曾注意。尽管如此,革命还是发生了。”
《经济学家时段》考察了新近经济史当中绝大部分广为接受、人气旺盛的道路:沃尔克的休克疗法、布雷顿森林体系被抛弃,抵押贷款的金融化,皮诺切特在智利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专制,空中客运规制的放松,等等。它们都已经被说得天花乱坠。阿珀鲍姆适时地提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政策的失败之处,譬如,美联储在1980年代面对突破天际的利率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及其乱局,就保持了铁石心肠一般的冷漠。但阿珀鲍姆的最末一章有些虎头蛇尾。他基本没有提出解决方案,只简单提了几句工会对于平衡企业权力的重要性。
但这一情况未必没有道理。阿珀鲍姆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学所造就的那个体制的产物,这位记者曾在《纽约时报》从事美联储相关的报道,他甚至在书里提出,自19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在观念的市场中已经成为了自足的垄断者,其后果可想而知:缺乏替代选项,难以打起精神来料理它那些显而易见的缺陷”。这或许可以解释书里论述不力的地方。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阿珀鲍姆也身处经济学家单一、全方位但又难以企及的意识形态所投下的巨大阴影中。不过,他的书里仍有不少真正有用的点子可资发掘。
阿珀鲍姆凸显了经济学界里高得有些奇怪的共识程度,其中一份1979年对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受访者里有98%反对控制租金,97%反对关税,95%支持浮动汇率,还有90%反对最低工资法”。他还在某处以略带顽皮的幽默提到“哪怕自然倾向于朝无序发展,他们还是对经济将迈向均衡有着一致的坚信”。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运作方式有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深信不疑。
然而糟糕的是,他们错了。纵观《经济学家时段》里列举的若干经济理论——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到亚瑟·拉斐尔(Arther Laffer)的供给侧经济学——与其他许多人类似,阿珀鲍姆也发现这些理论的预期基本都不符合现实。货币主义并没有控制住通胀,放松反垄断执法以及减少规制也没有促进创新,低税率也并没有提高企业的投资。包括令人困惑的“滞胀”(stagflation)在内的1970年代的诸多经济震荡为抛弃先前更注重再分配的经济体制提供了理由,但读者仍然十分想知道:经济学家为什么在错得这么离谱、这么频繁、这么明显,并且还损害了美国的工人群体的情况下还能大获全胜?原因很可能在于,经济学家的观点可以相当有效地让财富从下往上转移——他们一手造就了赢家,同时也在赢家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势。
这样看的话,只要你稍微留心,阿颇鲍姆的论述也可以被视作一幅宏大的阶级斗争图景,一场保守派针对新政的全面反扑,且这场反扑被一种倒退性的政治理论阴险地正当化了:经济学。或者如那位犀利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言:“所谓有说服力的经济学,通常反映的是富人们的需求。”
在结论中,阿珀鲍姆主张经济学家的时段已经结束了:如今我们有一位在涉及关税的演讲稿上批注“贸易不好”的总统。话说回来,经济学的教条并没有连贯到足以让人彻底拒斥的程度。譬如,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的吹鼓手既支持LGBTQ权利和移民,也支持世界上各种疯狂且具有压制性的右翼军人政权。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特朗普在立法上的唯一一场大胜,乃是在供给侧理论直接指导下的累退性减税,阿珀鲍姆花了一整章来考察其来龙去脉。我并不认为这个时段已经结束。这本书表明了经济学家对政府政策的重大影响,进而揭示出经济学并非抽象的、高高在上的科学,而是彻头彻尾的道德和政治科学。技术官僚和富人青睐的正是经济学所推崇的那种政治。
经济学未能回答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我们如何对待输家?——它无力回答这一问题,可以说经济学从概念上讲就催生了不平等,哪怕并非有意而只是源自袖手旁观。鉴于经济学家之间有极高程度的共识,不能指望让他们提出一个更新颖的、更有良心的答案,我们只能到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中去探索。
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下那篇乐观至极的短文《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时,他曾以为源源不断的复利将能造就一条令资本顺畅流动的大河,其深度和广度足以消除短缺,这样一来也就不再需要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认为,经济学家的重要性可能会变得跟牙医差不多。显然,事情走向了反面。经济学家如今对政府运作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如社会学家马里昂·弗瑞德(Marion Fourade)所发现的,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里是收入最高、引用最多的领域,经济学家几乎垄断了观念市场。在1950年代,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曾抱怨称自己做的工作与熟练木工无异。除非我们能回到那个年代,要不然钟摆将始终停留在阿珀鲍姆噩梦一般的“经济学家时段”里。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