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肖·马克斯(Groucho Marx)曾开玩笑说,“任何不能在床上完成的事都毫无价值。”你大概会认为他指的是睡眠和性生活。但人类——于此时或彼时——几乎在床上做过所有事。
以及,且不论我们人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床上这一事实,它们不只是突发奇想。
我在与一家床上用品公司的高管谈起床榻的历史之前,也没怎么去认真思考过它。这堆不起眼的制品里其实大有学问——它们有着7.7万年的历史。
考古学家林恩·瓦德莱(Lynn Wadley)认为,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的早期非洲祖先学会了在洞穴的地面上凿出用于睡眠的凹陷,也就是人类的第一张床。他们用能够驱虫的茅草裹住身体,以防虱子前来侵袭——虱子异常顽固,如今依旧会光临条件不太好的汽车旅馆。
我们的床榻多年以来总体上变化不大,但有一个方面例外。
今天,我们通常睡在门窗紧闭的卧室里,它们构成了终极意义上的隐私领域。除了配偶或爱人,他人一概不得入内。

但我即将出版的新书《我们在床上做些什么》(What We did in Bed)表明,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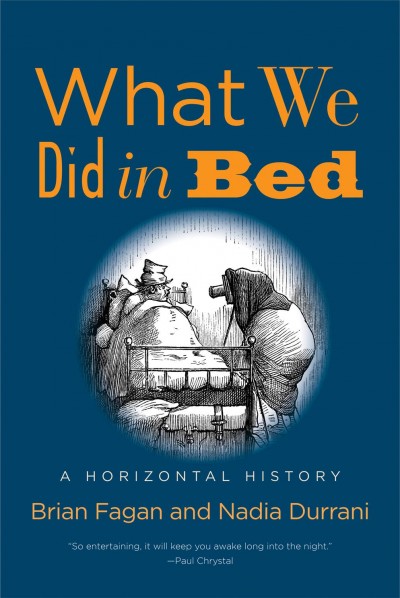
充斥着“捣蛋与胡话”的床榻
床的结构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固定的:公元前3000年的马耳他和埃及就已经在使用我们熟知的框架配床垫了,这意味着该结构的运用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
早期的埃及床基本不超出四方形的木架、床腿以及皮制或编织的床垫这些元素。靠近头部的一侧通常会设计得稍微高一点。在麻布袋或编织袋里塞入青草、干草和稻草,便制成了沿用多个世纪的简易床垫。
唯一有变化的方面是我们在床上所做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都是与家人或者朋友挤在一张床上的,没有谁对此有过疑问。
17世纪的一位日记作者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就经常与男性友人共寝,还会给他们的聊天水平打分。他的最爱之一是“愉快的克里德先生(merry Mr. Creed)”,此君带来了“美妙的相处时光”。1776年12月,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新泽西的一家客栈里同床共枕。房间里只有一扇小窗户,亚当斯不想开窗,富兰克林则执意要打开,称没有新鲜空气自己就要窒息了——亚当斯最后赢得了争执。
旅人时常会与陌生人同寝。在中国和蒙古,炕——加热过的石制床榻——最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出现在了旅店里。客人自带寝具,与同行的旅人分享一张床。
和陌生人睡一张床,有时也难免引发不快。16世纪的英国诗人安德鲁·巴克莱(Andrew Buckley)就抱怨床伴“睡相不雅且满口胡话,有时还带着一身酒气上床”。
接下来聊一聊威尔镇的大床(Great Bed of Ware),这张硕大的床属于英格兰中部小镇的一家旅馆。它于1590年完工,由装饰华丽的橡木制成,四角有立柱,尺寸相当于两张现代的双人床。据说1689年有26名屠夫和他们的妻子——整整52个人——在这张床上过了夜。

运筹帷幄之中
与挤在一张床上的平民不同,皇室成员通常一个人睡或是与配偶同寝。但其卧室却没有多少私密性可言。对皇室而言,新婚夫妇的洞房花烛夜乃是一种公共景观。皇家婚礼结束后,夫妇通常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象征性的性交。
参加完婚宴,新娘会由侍女脱下衣装并送上床。此时身着睡衣的新郎到来,有时还会带上一群乐手。床帘随后落下,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来宾们在目睹夫妇赤身裸体交欢或听见暧昧的声响之前是不会离开的。第二天早上,床单上的污渍将被公之于众,以证明新婚之夜大功告成。
此外,如果能在卧室里治理国家,谁还想去办公场所?每天早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便端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处置各种繁杂政务。爱好八卦的圣西门伯爵(Lord Saint-Simon)等廷臣侍立在旁,看着国王草拟法令以及与高官进行磋商。

从公共到私人
19世纪以降,床榻和卧室逐渐变为了私人领域。工业革命期间迅猛的城市化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城市里,样式紧凑的小楼房是主流,其房间狭小,各有特定的功能,其中一间就专门用于睡眠。
另一个原因在于宗教。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虔诚的时代,英国国教在1830年代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信条高度强调婚姻、贞洁、家庭和亲子之间的纽带,和陌生人或朋友共用一床被子不再符合清规戒律了。1875年时,《建筑》杂志刊出一篇短论,文中声称将卧室用于睡眠之外的用途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不道德。
卧室成为大人和小孩的专属去处,是19世纪富裕家庭的常见做法。夫妻有时甚至都不会同睡一间卧室,两间卧室中间可能会有一扇门,各配有独立的梳妆室。
维多利亚时代的自助类书籍就主妇如何装饰卧室提出过一些建议。1888年,作家、室内装修专家简·艾伦·潘顿(Jane Ellen Panton)曾建议卧室要采用亮色,配上脸盆架和夜壶,一张“长椅”是必不可少的,妻子累了可以靠在上面休息。
技术打破房门
如今,卧室仍被视作避难处——助人从日常生活的一团糟当中恢复过来的安抚性场所。然而,移动技术已经悄然潜入了我们的被窝里。
今年初的一份调查发现,80%的青少年会把移动设备带进卧室里,近1/3的人会把它们放在枕边。
如此一来,技术让床榻又恢复到了以前的角色:一处社会化的场所——与朋友甚至是陌生人聊天——而且一聊就聊到半夜。可以想见,特朗普总统不知道蜷缩在毛毯里写了多少条推文。
然而,这些热情洋溢的“床伴”们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弊大于利的。有研究对把智能手机放在枕边的夫妇进行了调查,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电子设备令其错过了与伴侣共处的黄金时段。另一项研究指出,不将手机带进卧室的受访者报告称自己的幸福感更强且生活质量更佳,这或许是因为电子设备败坏了我们的睡眠。
回想一番,我也不太确定和喝醉的陌生人同床是否会让自己睡得更好一点,如同安德鲁·巴克莱所描绘的那样。
(作者Brian Fagan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人类学荣休教授)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