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朱洁树
“穆斯林正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才行。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去帮助穆斯林,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与他们同甘共苦,仅仅坐在家里给他们捐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正因如此,我们决定前往叙利亚,尽我们所能去帮助那里的人。”(阿扬和莱拉)
2013年10月17日,挪威籍索马里姐妹阿扬和莱拉像往常一样出门,却再也没有回家。父亲萨迪克收到她们发来的电子邮件才知道,她们已经抛弃父母和三个兄弟远走高飞,奔赴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
两姐妹的出走对萨迪克和萨拉夫妇来说如同五雷轰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乖巧懂事的女儿会筹谋出如此大胆的计划,甚至为了给叙利亚之行筹措旅费,她们还进行了信用卡套现,将公民信用挥霍一空。两姐妹的朋友、同学和老师也百思不得其解,两姐妹聪颖伶俐,本来在挪威拥有光明的未来——姐姐阿扬曾是个充满自信的女权主义者,厌恶伊斯兰教义中驯服妇女的内容,她考上了挪威最有名望的学校之一内斯布鲁高中,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外交官……
她们为何抛弃挪威的一切,走上与原本生活轨迹截然相反的道路?受到萨迪克的委托,挪威记者奥斯娜·塞厄斯塔(Asne Seierstad)深入调查,试图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
在出版《两姐妹》之前,塞厄斯塔拥有广泛的中东报道经历。她发现,两姐妹的极端化过程简直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范例:开始上《古兰经》课程后,她们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礼拜、服饰、饮食、行为举止,一切都严持戒律,完美无缺;在接触到挪威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创办的伊斯兰资讯网之后,她们找到了更多年轻的同道中人;她们的社交媒体中也充斥着关于“伊斯兰国”的激动人心的宣传材料……
诚然,“伊斯兰国”的成因和行动逻辑非常复杂,塞厄斯塔指出,“伊斯兰国”的坐大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粗暴干涉中东地区事务、导致当地的世俗派和极端主义者联手一致对外相关。然而“伊斯兰国”的信徒中还有许多像两姐妹这样年轻的“局外人”。据统计,仅在挪威,就有90多个家庭的孩子去了叙利亚。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些人的参战呢?真的是出于对穆斯林同胞的深切同情吗?从两姐妹与兄弟伊斯梅尔的聊天记录来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这两个信誓旦旦为了“帮助穆斯林”前往叙利亚的女孩,却沾沾自喜地炫耀着自己在那里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的优越待遇:“钱、医生、药品、房子、水、电,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有权得到应得的东西,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这个国家得到的钱,我们都分到了一份。”而她们在当地想要做的,似乎也只是为身为“圣战者”的丈夫生更多的孩子,培养更多下一代“圣战者”。
“所以‘伊斯兰国’的一部分逻辑是——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而至于那些参战的欧洲人,比如说两姐妹和她们的男友,他们的理由和自己的内心更相关。的确也有一部分政治性的理由,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出于冒险、爱、做正确的事情、使命感等等。”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塞厄斯塔指出,前往叙利亚的欧洲年轻人多为“社会掉队者”,或许是出于对权势的渴望,或许是出于冒险精神,他们希望在“伊斯兰国”找到自我和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尤其重要的是,受害者心态是西方国家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极端化的重要推手,事实上,这种心态我们也能在西方极端右翼分子身上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世界的极端主义“圣战”或许并非我们想象中那般与现代社会全然不相容,而是失意者的集中反抗。
这一切是谁的错呢?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两姐妹的所作所为?塞厄斯塔并没有在书中给出明确的答案。“我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打开一扇窗,但又给读者留下足够多的余地去自行理解,”她说,“我不想告诉你应该怎么想、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减少一些刻板印象了。”

阿扬和莱拉的故事:她们的极端化过程是一个教科书般的范例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找到这个话题,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
塞厄斯塔:其实是两姐妹的父亲先联系到我的出版社。在女孩们离开之后,她们的父母非常震惊。父亲追了过去,但女孩们不想回家。那位父亲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故事警告其他人,特别是警告其他父母。女孩们在生活中的改变其实都是思想变化的信号——极端化的信号比比皆是——所以他希望有人能够就此写一本书,毕竟他女儿的极端化过程简直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范例:衣着越来越保守、祷告时间越来越长……他联系了我的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又找到了我。
我一开始并不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我觉得其中可能会有很多利益冲突——也许我会找到一些他不喜欢的材料或不希望放进书中的内容。但之后我们还是达成了共识:我先开始动笔,看看我们最后能得出什么结论。
界面文化:这是一部调查报道作品,然而本书的两位主角拒绝讲述自己的故事。写这本书最有挑战的地方在哪里,你是如何克服的?
塞厄斯塔:最有挑战的地方正在于此:她们并不配合。你的书是关于两姐妹的,但她们的声音在哪里?

当我开始着手做调查的时候意识到——你在书中也会发现——萨迪克并不总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他捏造了很多东西。当然,这些我在书中都指出来了,但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他告诉我,女孩们自发去了叙利亚,但很快她们就想回家了,然后她们被绑架了——这完全不是事实。但当时我以为这个信息是可靠的,谁不会那么觉得呢——少女们走上探险之旅,然后意识到,“哦不,这是地狱,我想回家”——正常人都会这么理解吧。所以当他告诉我,女孩们逃离了丈夫,藏了起来,他正在设法营救她们,我相信了他的话。我开始展开调查,期待着等她们回来以后,再采访她们。
所以,一开始我采访她们的同学、朋友、老师、亲人,是为了在采访她们本人之前收集素材。然后我开始觉得不对劲,因为她们的兄弟给我看了他们之间两年半里的聊天记录,我发现,她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计划要回家,也根本不知道她们的父亲在设法营救她们。
萨迪克描述的大多数事情都只存在于他自己的脑海中。这完全改变了我的写作走向。我当面质疑了萨迪克,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之间毫无交流,因为我觉得他的话完全没有可信度,他也觉得很生气,觉得我不该这么斥责他。我当时想,行吧,那我就先做其他调查。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和解了,并且一同完成了这本书。

两姐妹与兄弟的聊天记录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能听到她们声音的唯一途径。我没法和她们直接交流,而我认为,她们跟兄弟的这种交流,也许会比跟我交流的内容更加可信。虽然在聊天记录里还是会夹杂很多政治宣传的语言,但她们看上去是真心相信这些,而且她们也会流露出有趣的一面,比如问兄弟,“你剪头发了吗?”“你学习得如何?”“考试成绩怎样?”你能意识到,两姐妹还是原来的两姐妹,只不过她们身体中的一个部分被扯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界面文化:《两姐妹》仿佛悬疑小说一样令人手不释卷,书中的很多描述异常生动,你是如何找到那么多丰富的细节并还原场景的,就好像你在场一样?
塞厄斯塔:幸运的是,她们留下了很多东西。她们应该从来没想过会有记者去翻看她们的东西。萨迪克邀请我去他们家时,给我了一大箱纸张和信件。作为一名记者,我很清楚自己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宝矿。箱子里有很多东西:信件、《可兰经》的课堂笔记、地址列表。阿扬在伊斯兰讯息网非常活跃,她负责招募新人,所以她有很多人的联系方式,包括姓名、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我联系了每一个人。我联系了她们所有的同学、Facebook好友和Twitter好友——虽然她们已经不再使用Facebook,但她们的账户还在。
大多数人出于恐惧完全没有理睬我,但总有那么1%的人是愿意说话的。那些接受采访的人都很了解两姐妹,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还原她们走向叙利亚的整个过程。我在书里没有写太多她们在叙利亚的经历,在她们去叙利亚后,我基本上只能通过她们和父母、兄弟的聊天记录来了解她们的经历了。
界面文化:两姐妹现在怎样了?
塞厄斯塔:两姐妹一直待到“伊斯兰国”山穷水尽之日。最后一场激战发生在今年3月23日,在叙利亚一个叫作巴古斯(Baghouz)的村子里。在战局尘埃落定之前,她们在一个个村落之间辗转,为难民开放的通道一直都存在,但她们从未选择逃离。她们待过的每一个村子都被炸毁了,她们的丈夫也都死了,但她们选择和孩子一起留守。阿扬有两个女儿,莱拉有一个女儿。战争结束后,她们落入了库尔德人之手,被安置在一个战俘营里。从3月至今,她们一直在那里。
她们现在实际上处于一个动弹不得的尴尬境地。“伊斯兰国”一共有7.3万妇女儿童。其中大多数是本地人,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战俘营因此分为两个,一个是本地人的战俘营,另一个是国际战俘营,收容了大概1.2万来自挪威、瑞典、丹麦、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中东国家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希望遣返这些人,在欧洲,这成了一个大难题。她们是挪威公民,我们是否应该带她们回家,然后审判她们?鉴于当下欧洲的氛围,没有人想这么做,因为没有哪个政党会不顾民意——民意是“这些人是恐怖分子”。所以我们现在是不人道的那一方(笑)。不过所幸她们还活着,她们打电话回家报过平安。
她们绝对是值得面对面聊聊的人。我确定这会非常有意思。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得到这个机会。
二代移民极端化的原因:受害者心态、身份危机和对权势的渴望
界面文化:在我看来,伊斯兰二代移民的极端化背后是某种意义上的身份危机。你对此怎么看?
塞厄斯塔: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大概也是我最害怕出错的一点。身为一个在挪威出生长大的白人,我不知道种族主义是怎么回事,我没法感知,作为一个有着深色皮肤的索马里人,在挪威长大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针对索马里人,有很多刻板印象——它们当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比如说他们很懒、不愿意工作等等。
我认为两姐妹在生活中真正遇到的种族歧视并没有那么多,但我们没法控制她们遭遇他人的目光时的想法。即使别人可能并无恶意,但她们的感受也许是不同的。我在伊斯兰资讯网听很多女孩讲过,“在挪威,我早上乘公交车或火车的时候,人们会盯着我的头巾看。”我不禁会想,当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其他乘客是否也会偷偷瞄我?有些时候,我认为这种感觉有些夸大了——但这一点我永远没法确定。
我认为,很多情况下是受害者心态造成了极端化——我是一个受害者,周围的人都在反对我。你可以看到极端右翼恐怖分子也具有类似的心态,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穆斯林在侵占我们的国家!他们生很多很多的孩子,蓝眼睛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是一种非常危险、也无助于解决问题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认为言语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很多人仅仅因为网络言论就被极端化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许并没有什么让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理由。我们需要谨慎思考什么言论可以传播、什么争议可以讨论。作为一个生活在挪威或丹麦的年轻穆斯林,总是听到那些关于伊斯兰、穆斯林的争论也会不好受吧,特别是当你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
当然,大多数第二代穆斯林移民的表现很好。在挪威,大学是免费的,任何成绩优异的学生都能去上医学院、法学院、工程学院。即使你的成绩稍微逊色一些,你也可以找到合适的领域学习。如果你只是在为自己的深色皮肤焦虑……好吧,这个社会确实要为这样的问题负责,但你也要为自己负责。欧洲现在是个充满多元文化的地方,在我小的时候,1970年代,挪威只有很少的移民。第一批索马里移民是在1980年代来到挪威的,所以外来移民对我们来说也还是一件新鲜事。不像法国和英国那些有殖民史的国家,对外来移民司空见惯。
界面文化:我很好奇,两姐妹的兄弟伊斯梅尔怎么样了?他就像是两姐妹的反面。
塞厄斯塔:很有趣的是,当你和他交流时,他的表现100%就是一个挪威年轻人,虽然他也有着深色的皮肤和索马里的文化背景,但这就是他身上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了。他的价值观、 人生目标、放松的心态、口音,完全就是挪威人的样子。他遵守规则,对远离索马里战区、生活在奥斯陆心存感激。他还在上学,目前过得还不错。当然,他一度对自己的姐妹生死未卜充满担忧。如今他们恢复了联系,他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她们的代言人。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又恢复了联系,他一度赌气声称要和两姐妹断绝联系,因为她们把他的生活全毁了。
界面文化:在穆斯林年轻人的极端化中是否有性别因素,是否女孩子更容易受极端思想影响呢?
塞厄斯塔:前往叙利亚的人中,85%是男孩,15%是女孩,但这个比例也已经相当高了。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穆斯林女孩离家参战。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女孩也有更多机会计划行程、招募同伴、购买机票。即使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依然生活在压抑的环境里,但她们也有了旅行的自由。

界面文化:阿扬和莱拉一开始说她们想要“帮助穆斯林”,但当她们真的在叙利亚落脚后,又开始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不用工作就有钱拿”。伊斯兰国的许多其他女人也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似乎在她们前往叙利亚的辩解中也有一种隐秘的对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渴望,圣战似乎不仅只是一场抵抗现代社会的宗教运动,而是对当下世界秩序和地区阶级的报复。
奥斯娜·塞厄斯塔:你说得真好,你可以直接在文章里写下来了,这个分析很有见地。
我完全认同你的感受。我认为你所说的“辩解”(justification)是个很恰当的词。“我们要去帮助穆斯林。”这是她们告诉父母的答案,但当我为了写这本书,而去阅读她们的网络订阅材料时,我发现她们的关注点丝毫不在这里。她们并不关心如何帮助他人,她们也没有真的帮助任何人。她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
在挪威,她们生活在一个被富人围绕的贫穷社区,这很难让人能有什么优越感。她们倒买倒卖手机,通过金融诈骗获得了很多钱,所以当她们来到叙利亚,就成了“上流阶级”的一份子。那些从欧洲来的人通常被视为“上流阶级”,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能分配到最好的房子,拥有奴隶、清洁女佣和许多其他的优待。圣战当然有很多方面,其核心是宗教,但一些欧洲人从中挑选了他们想要的部分来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南。
界面文化:挪威的社会机制中是否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了穆斯林年轻人的极端化?比如说书中提到索马里母亲都很担心福利机构会以虐待儿童为由抢走自己的孩子,这可能是一种文化冲突吗?
塞厄斯塔:我认为我们不能把极端化归咎于福利系统。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责备的,那就是挪威当局没有强制那些母亲学习挪威的语言、融入挪威社会。在挪威,我们非常重视虐待儿童的问题,如果有关于虐童的报告,当局有权利带走孩子。这会影响到索马里社区,正是因为一些索马里父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保护儿童,家长打孩子是违法的,即使你是一个移民也是如此。
界面文化:叙利亚危机造成了大量叙利亚移民,在近些年造成了欧盟内部的分裂,比如说英国脱欧。在你看来,欧洲的未来将如何?
塞厄斯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只看到种族和移民问题,也要看到阶级问题。欧盟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在欧洲,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群体,他们过得还不错,但底层的数量也在扩大,这造成了分裂——那些拥有很多的人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底层人群害怕移民,是因为害怕他们会抢走自己的工作,至于上层阶级——那些去牛津剑桥上学的人——多元文化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威胁,而是有趣的外国餐厅、有趣的新同事,或者环球旅行。所以我认为指责“那些愤怒的脱欧人”是有点不公平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被社会抛弃的落后人士。
我们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解决阶级和金钱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将矛头对准移民,因为这样就会让欧洲变成种族主义的温床。让我们开阔思维,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社会融入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对英国这样阶级森严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西方媒体书写中东问题:超越刻板印象的关键是让读者自己思考
界面文化:你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报道过俄罗斯、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多场冲突,写过关于塞尔维亚、巴格达和车臣地区的书。你是如何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家、以外来者的身份融入当地社区的?
塞厄斯塔:你需要耐心和投入。我认为耐心是最主要的特质,你需要有好奇心,但你也需要能够安静地倾听、观察,而不仅仅只是拿着麦克风去问问题。你需要在当地多走多看,耐心等待。
陌生感不仅在国外会有,对我来说,在挪威拜访伊斯兰资讯网俱乐部、参加他们的会议就是踏入一个陌生领地了——我以前甚至都不知道挪威还有这样的组织。这也是为什么挪威读者(也许还有丹麦读者)都很震惊:“这个真的是在奥斯陆发生的吗?”我们仿佛生活在平行世界里,大多数人对此毫无感知。
这本书连续两年在挪威是销量冠军,因为人们急切地想知道在自己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我的丹麦编辑在读完书后向我感叹:“我是两个青春期男孩的妈妈,我都不知道他们平时在做什么。如果他们陷入了类似的境地,我可能要过很久才会发现。”我认为对于很多父母来说,这本书既让他们震惊,也让他们警醒。

界面文化:鉴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截然不同,你是否会担心自己在书写中东故事的时候无法完全理解那个世界?
塞厄斯塔:当然,我们需要一直保持谦卑。我在《两姐妹》的后记里也写道,这本书只能给你关于两姐妹生活的匆匆一瞥。完整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完全的中立客观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保持诚实的态度很重要。这本书的书名是《两姐妹》,不是《中东通史》,所以这本书可以是其他中东题材书籍的补充,如果这本书是一些人阅读的第一本关于中东的书,我希望它能启发他们去读更多的材料,加深对中东的理解。我费了很大的心思以很短的篇目讲述了叙利亚的历史,这样,即使你此前对叙利亚一无所知,也能毫无理解障碍。
当然,我还采用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其中一位是做恐怖主义研究的,另一位是做亚洲研究的,还有一位是伊斯兰学的专家。他们一起帮我审阅了本书手稿,修正错误,指出描述失衡的地方。
所有的因素相互缠绕,造就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有很多内部敌人——是的,他们对抗西方,但他们也对抗什叶派穆斯林、库尔德人等不同的部族。他们渴望建立国家,获得权力。单单认为这是一个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世界的故事就太片面了,当然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对于两姐妹来说,如果我们去看她们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会发现,她们并不是非常在意政治。有些人认为,这些人会变得极端化是因为来自西方的攻击,但我们要注意到,有些时候这只是他们的自我辩白。我认为极端化的因素也有非常存在主义的一面,特别是对那两姐妹来说。她们像是在寻找生命意义、为某些超越生命的更宏大的东西去奋斗,对她们来说,这样的选择是值得的。
界面文化:我们要如何理解“伊斯兰国”的迅速扩张呢?这是9/11造成的,还是整个西方的排外心理造成的?
塞厄斯塔:请记住,“伊斯兰国”已经覆灭了。是的,的确有9/11的因素在,“伊斯兰国”脱胎于基地组织,是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之后出现的。美国进攻伊拉克激怒了整个地区的人,因为那场战争的起因实在是站不住脚的,充满了谎言和误解。当美军占领伊拉克,伊拉克政府和军队中的所有人都失去了工作,这些都是世俗化的人,和极端主义毫无关系。他们非常愤怒,转向地下活动去攻击美国人,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开始和曾经的敌人——极端主义者取得了联系。换做是战前,萨达姆政府中的官员和基地组织成员是绝对不可能结成联盟的,而这是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既掌握萨达姆政府的技能、军队力量,又和自杀式武器及极端主义者联系起来。
随着“阿拉伯之春”,他们得到机会进入叙利亚,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伊拉克——他们希望伊拉克和叙利亚能成为一个国家,他们渴望权力和复仇。所以,“伊斯兰国”的崛起和西方国家贸然干涉中东事务、强行推行政策有关:西方试图在中东推行民主价值观,我们认为这仿佛是一件包装精美的、可随手赠予的礼物,但它在那里行不通。
所以“伊斯兰国”的一部分逻辑是这个——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而至于那些参战的欧洲人,比如说两姐妹和她们的男友,他们的理由和自己的内心更相关。其中有一部分政治性的理由,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出于冒险、爱、做正确的事情、使命感等等。60%加入“伊斯兰国”的年轻男人有犯罪记录——可能不是什么重罪,就是小偷小摸——这些人可能是街头混混,是落后者,是欧洲社会的失败者。所以“伊斯兰国”有几股不同的力量,除了真心想建设“伊斯兰国”的人之外,还有那些无父无母、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有趣的是,前往叙利亚的女孩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伊斯兰国”不断扩展,直到2015年,所有人都意识到无法再坐视不管了,于是俄罗斯、美国、欧洲和当地的军事力量纷纷介入……
界面文化:企鹅兰登书屋日前出版了《我们土地上的女性:阿拉伯女性报道的阿拉伯世界新闻选》。《纽约时报》评价称这是一本“激动人心、引人深思、文笔斐然的新闻集,它重新书写了外国记者陈旧的报道规则,驱散了哪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你作为一位外国记者,如何看待西方媒体不断加深针对阿拉伯和中东世界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的问题?
塞厄斯塔:我认为西方媒体已经出现了改变。不是说那些刻板印象已经不存在了,但问题是,刻板印象从来不会凭空出现。中东女人非常顺从,中东男人很有权势——是的,这些是刻板印象,但它描述的也是部分真实的。爱德华·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的概念,指出西方在神秘化东方,但这更多发生在过去——将中东和阿拉伯人想象成充满异域风情的、不理性的。在以前,他们的形象是诱人的,但当下的刻板印象更多是,“他们是危险的、可怖的、有威胁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打开一扇窗,但又给读者留下足够多的余地去自行理解。前两天在书店做活动,有一位读者问我如何评价两姐妹,我说,我很高兴你在读了书之后还会向我问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的立场没有在书中显现出来。这是我希望达到的写作目标。我不想告诉你应该怎么想、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减少一些刻板印象了。
我也认为这两姐妹是超越任何刻板印象的,她们其实比她们自己承认的更像挪威人。当她们开始争取信仰权利的时候,她们抗争,写请愿信,收集人们的签名,给校长写信。那位校长后来告诉我,虽然她不支持她们的做法,但对她们的行为印象深刻——她们充分利用了民主制度中的所有工具来为自己争取进入一个在我们认为非常具有压迫性的制度里的权利。她们意志坚定,其中一个女孩还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在书里,她们自己就打破了刻板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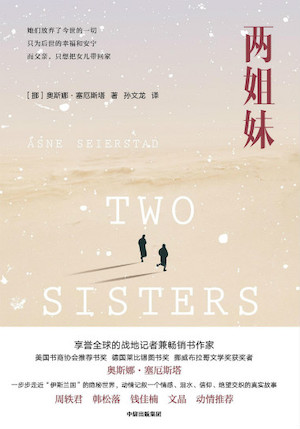
【挪】奥斯娜·塞厄斯塔 著 孙文龙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