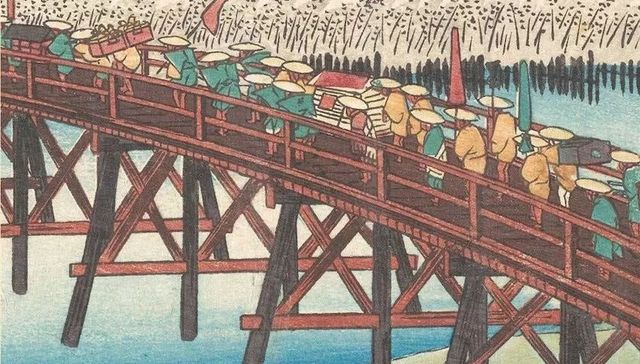撰文:吕利 | 经济观察报书评
在曾于1858到1864年间任英国驻日公使的阿礼国看来,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停留在中世纪的国度。幕府和大名共治的局面有如金雀花时代的英格兰,统而不治的天皇则是墨洛温末期被宫相架空的法兰克君主,即便失去了作为职业军人的战斗力,武士作为特权阶层仍高举平民之上,这样的社会形态不但支撑了德川政权两个半世纪的统治,甚至自马可波罗的时代以来便没有任何改变。
从表面上看,北岛正元在《江户时代》中传达的信息与阿礼国的观察不乏相通之处:他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把江户时代定性为“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并用德川政权对社会力量的压制与农民和市民群体的反抗编织了一条讲述江户时代260年历史的线索。但只要翻开本书便不难发现,《江户时代》所要讲述的江户时代并不是一个如阿礼国描述的那般停滞的历史阶段。在日本历史上,江户时代不但见证了近代化以前速度最快的城市化与农业扩张,也经历了识字率和商业流通的快速增长,还孕育了喧嚣躁动的大众文化,只要看到光琳的屏风、芭蕉的赠答与北斋的锦绘,现代人便能感受到江户时代鲜活的脉搏。虽然没能凭内在演化突破自身作为传统社会的壁垒,但江户时代的诸多要素仍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并在明治维新以后自然地接续到了近代日本的社会与国家形态当中。
分封乎?集权乎?日本特色的专制主义
在21世纪的今天,称江户时代为“封建社会”的提法已在日本近世史学界的语汇中逐渐式微,《江户时代》一书中以阶级斗争为唯一线索的论述受制于本书出版(1958年)时学界的认识,在视角和史料选取上也难免局限。但就认识江户时代的出发点而论,北岛正元在书中采取的路径并无过时之处:日本历史进入江户时代的过程也是专制主义在列岛社会得到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由16世纪末短暂的丰臣政权开启,最终于17世纪藉德川政权之手得以完成。
如果阿礼国不是在江户幕府统治末期的19世纪,而是在西方人第一次登陆日本的16世纪中叶接触当时的列岛社会,他所能见证的“封建”性恐怕会超过他的想象。在丰臣政权登场之前,日本历史正处在所谓“中世”末期,原本为日本提供政治向心力的庄园制度和室町幕府的武家政权在15世纪后半叶的内战和政变中走向崩溃,日本社会进入了军事化与政治权力分化程度空前高涨的“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日本各地的统治权虽落入地域性武士领主——大名手中,但大多数大名在领地内只能对众多规模更小的武士团(“国众”)进行间接统治。而在这些勉强可以用武士间的主从关系加以笼络的势力之外,地方社会还存在大量持有自卫武装和传统特权的村落、神社与佛寺,大名往往难以建立排他的财税与司法权力。

在这一环境下,丰臣秀吉在1590年左右基本消灭了日本国内的敌对势力,掌握了全国的霸权。作为步卒出身的武将,丰臣秀吉在列岛社会的传统政治秩序中并无统治全国的身份基础,也曾明确表露过进军亚洲大陆的野心。无论出于维护对内统治还是进行国际战争的需要,秀吉都决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彻底的集权化改革。
丰臣政权的改革无意在原则上否定各地大名的独立性,也不寻求建立统一的财政国家,其重点在于要求各地领主以维护秩序的名义着手取缔农村社会用于自力救济的武装,并派遣行政官僚进行自上而下的检地,以在全国大名的领地内确立标准化的财税制度。这一遗产在德川家康于1600年夺取全国霸权之后也得到了继承。但在表面的安定化之下,17世纪德川政权的早期统治者仍需面对巨大的风险。
虽然秀吉对全国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强有力的重组,但由于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令大量装备火绳枪的军制和更先进的要塞技术在全国普及,这种重组并不意味着日本社会自中世末期以来的军事化程度降低了。如果把1600年之后不久日本社会的军事化状况编成一张供需关系图,可以说随着国际战争和国内慢性动乱的平息,日本社会对武力的需求已经大大下降,但供给在17世纪初并没有得到与需求下降相应的调整。夭折的“火药时代”就此从一台鼓动集权的机器演变成对新任统治者的严重威胁:日本前近代史上最后两场大规模战役都发生在江户幕府草创的17世纪上半叶,而两场战役中挑战德川权威的武装力量正是由依托火绳枪和日式要塞组织有效抵抗的无主武士与受其领导的百姓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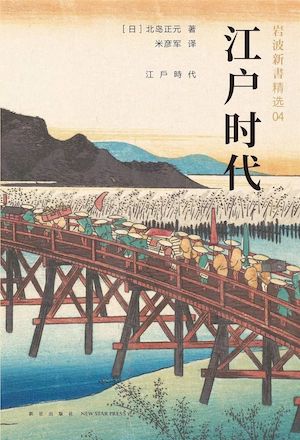
(日) 北岛正元 / 著 米彦军 /译
新星出版社 2019年4月
面对武力失控的风险,江户幕府的早期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对高效军政体制的追求,转而建立一种追求社会控制、避免大规模失序的内向型霸权体系。在对外政策上,德川政权彻底放弃了丰臣秀吉的扩张主义路线,甚至对海外通交严加管制,最大限度地降低日本与东亚-西太平洋世界的联系,明确了日本国的边界;在对内政策上,德川政权则延续丰臣政权的作风,在幕府直辖领和与幕府关系密切的大名领地上执行严格的兵农分离制度,并将武士与领地的军事与工商业资源向领主所在的城池集中(“一国一城”)。到17世纪后半叶为止,以身份制度和锁国体制为标志的江户时代社会已基本形成,日本历史正式从“中世”进入了“近世”阶段。
王霸之道:僭主政治的政治经济学
在江户时代26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幕府和诸藩的行政机构以极为精简的规模(大坂两奉行所以总计约300人的规模治理了50万以上的都市和城郊人口,而代管约10万石幕府直辖领的甲府代官所只有约十余名官吏)有效地维持了财税与治安体制的运转。但在政治体制上,德川政权终江户一代皆无意且无力动摇中世以来武家社会的分封制秩序,而是选择用强势的主从关系将武家社会的实际权力集中到将军的所在地——江户而非天皇所在的京都,并对直属幕府的家臣和分治各地的诸藩加以钳制。这一思路在同时代的儒学者之间引发了漫长的“王霸之道”论争,也令近世日本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与近代世界分道扬镳,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僭主政治(tyranny)。
在江户时代最能体现幕藩体制权力关系也最具独创性的制度设计是大名的参勤交代。早在武家政权诞生之前的平安时代,与来自中央的实权人物结成主从关系的地方武士定期前往主君的官衙与府邸充当宿卫便是武家社会的重要习俗,后来的镰仓与室町幕府也概莫能外。始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23-1651年在位)任内的参勤交代制度继承了这一基本逻辑,但与之前强调主从之间的个人关系、只要求武士本人携带少量武装随从短期赴任的制度不同,参勤交代制度下的近世大名原则上以一年或数年为单位在江户的藩邸与领地的居城间交替居住,还需在途中携带准军事化的随从队伍“大名行列”,以和平方式对幕府履行相当于战时标准的军事动员义务。这一制度代进一步对中世末期军事化程度过高的状况进行了整顿与规范,而由于迁居江户占用了大量的领地治理时间,大名往往需要在江户藩邸与领国设置两套班底,令大名与领国地方社会的关系变弱,从而切断了中世领主制的存在根基。近世大名就此成为一种可被幕府增减封地、迁移乃至撤销的身份。
正是在武家社会的权力与财力空前集中于德川一极的背景下,位于关东平原滨海低湿地带的江户在短短一个世纪里从一处不适合大量人口居住的地方据点崛起为世界第一的大都市,吸引各地的财政收入和不纳入农业范畴的手工制品从日本全国向江户集中。而崛起于丰臣时代的大坂则作为濑户内海和日本海沿岸各领地的物资和财富集散中心成为“天下的厨房”,不但在规模上迅速超过了历史更为悠久的大城市京都,还在大坂湾周边的兵库等地孕育了一批经营经济作物和工商业、与城市商业活动关系密切的乡村集镇。
进入18世纪,日本列岛的人口已从17世纪初的约1000万以上增长到3000万,水田面积也经历了类似比率的高速膨胀,这一势头虽然在之后一百年里显著放缓,但经济活动的结构性优化仍在不断推进。由“消费革命”刺激农民加大劳动力投入以扩大生产的“勤勉革命”已然展开,即便史料表明江户时代的官僚存在压榨农民收入剩余、限制农民消费的倾向,但生产者脱离对生活和生产安定化的追求、开始产生改善生活水准和扩大储蓄-再投资的偏好。虽然在《江户时代》里,北岛正元赞扬了务实主义的大坂并批评了消费主义的江户,但在推动江户时代日本经济运转的机制之内,两座城市无疑代表了同等重要的两股力量。
与农业经济稳健的增长相比,江户时代的财税制度似乎仍停留在实物税(糙米)的阶段。但由于丰臣秀吉检地以来的标准化改革在全国建立了单一的税制(“年贡”)、统一的度量衡和同质化的土地课税标准,江户时代的年贡米也在经济活动中呈现出货币化的色彩。尤其是在物资流通的枢纽大坂,相对稳定的政治和信用预期(以及相对短缺的货币供给)催生了早期的期货市场,令教科书式的封建农业税成为一种早熟的金融交易品。正因如此,当19世纪后半叶明治国家着手废除幕藩体制、建立现代化财税制度时,旧有的幕藩收入和与之绑定的武士秩禄得以迅速转换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公债,在江户时代和近代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架设了又一座制度性桥梁。
边缘-中心:幕末维新的原动力
在经济史上,江户时代与明治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已颇为显著,但在政治史上,江户时代与明治时代间的断裂却难以否认。随着1868年的戊辰战争尘埃落定,自1853年黑船事件开始的幕末政局最终导向了武力倒幕的结局,德川政权长达260年的实际统治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落幕了。
在明治维新的阴影之下,幕府在江户时代后期对锁国政策的坚持常被视为令日本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症结,但在18世纪末的田沼时代(1767-1786),作为将军近臣把持幕政的田沼意次也曾推行重视工商业的政策,并对兰学和主张开拓北方边境、积极应对俄罗斯威胁的海防论怀有兴趣,而在黑船事件后,幕府也频繁派员出海斡旋,在关东地区进行初步的工业化建设,并放宽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兵农分离政策,将部分农民纳入基层武装力量。
即便幕府在施政中展示了或许令其他东亚政府难以企及的灵活性,但在阿礼国和萨道义等西方外交官看来,幕末日本的内政局势仍决定了幕府的统治地位存在根本的暧昧与薄弱之处。问题不在于德川不够先进,也不在于德川保留了封建制,而在于即便德川仍在日本享有表面上的相对优势,那些原本居于边缘的势力早已今非昔比。
在北岛正元看来,18世纪末期“边缘”力量在日本的崛起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在地理上,幕藩体制下逐渐成熟的全国市场开始渗透地方经济,促使仅凭农业税无法维持财政健康的地方领主也开始追求类似田沼意次政策的重商主义专卖制,开发可作为特产品的经济作物与手工制品。作为结果,距离大坂-江户经济轴心较远的萨摩、长州(西日本)和会津(东日本)较早恢复了经济实力,也在1860年代政治争端的两侧分别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社会层面,18世纪以来以江户、大坂和京都为中心的都市化为知识与人物的跨地域跨阶层流动提供了平台,虽然没能孕育出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场域”,但依旧催生了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尤其是在18、19世纪之交的田沼时代与化政时代(1804-1830),国学者中有商人家庭出身的本居宣长、从藩士家庭出走的平田笃胤,兰学者中则有医师出身的杉田玄白与足轻(下级步卒)家庭出身的平贺源内,至于凭尊王思想接近京都公卿高山彦九郎和在幕府支持下探索鄂霍次克海的间宫林藏也都是关东的豪农之子。而在后来深刻影响了幕末政局的边缘诸藩,本应在传统政治秩序中位于中下层的武士也通过私塾、结党等横向纽带增强了话语权,在明治维新前后争得了与出身不成比例的显著地位,甚至成为明治国家的舵手。
在讲述到近世日本迎来西方列强挑战前夕的1830年代后,《江户时代》的叙事便宣告结束。但即便在1868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向萨长列藩主导的新政府军投降之后,江户时代仍以一种灵活的形式在明治国家的体制内外得以延续。在体制内,幕府解体后留下的大量旧幕臣凭借在近代化改革和地方治理中积累的经验,再度被吸纳到维新后的近代化官僚体系内,在军、政、经系统拥显著的存在感;而在体制外,福地源一郎(《东京日日新闻》)、栗本锄云(《报知新闻》)等旧幕臣也利用江户(东京)发达的出版行业与充足的读者群建立了日本最早的本土新闻行业,与自由民权运动和条约改正运动联合起来,成为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方针的批判者。“反动派”的豹变在今人看来或许充满了讽刺意味,但江户时代正是以这样的方式适应了近代文明的规则,融入了日本历史的下一场轮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