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傅尔得
作为刚刚开幕的“2019大理国际影会”其中的一个展览部分,《Hai,Dozo!日本影像新世代联展》展出了八位代表日本新世代中坚力量摄影师的作品:小原一真、岩根爱 、千贺健史、细仓真弓、三保谷将史、横山隆平、内仓真一郎、长谷良树,意在以这些年轻摄影师的多样性创作,呈现日本最当下的影像风貌,也呈现一个他们所成长、思考并理解的日本。

作为亚洲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刚从“平成”进入到“令和”纪元的日本,正面临着它的新时代。而处在更替之交的新世代影像艺术家们,正以挑战性的崭新影像语言,在表达着自身处境的同时,展示着对当前时代的回应。
上一个世代的日本摄影师们,以“战后日本摄影”、“vivo团体”、“挑衅团体”、“街头影像”等关键词,集体式地进入了国际视野,而日本也因其强大而悠久的摄影文化,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受到了以纽约现代美术馆和伦敦泰特美术馆等为代表的来自当代艺术权力中心的关注与收藏。
新一代的日本摄影师们,在一个经济自1990年便开始持续衰退的社会中成长,伴随他们成长的,是一个人口逐渐减少且迅速老龄化的日本社会,由此不断加剧的劳动力缺乏等问题,并未能让他们像祖父辈一样进入终身雇用的集体安全中,反而,在物价下跌、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社会不断攀升的贫困率和自杀率中,他们进入了未来暗淡的零工经济时代,进入了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而日益挤压并取代人类工作的时代,由此,在时时刻刻与缺乏机会的挫折感的抗争中,他们日益降低了对未来的期许。


日本的影像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而现实的成长环境,无疑造就了新世代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日本年轻世代来讲,上一代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他们真实的处境究竟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又如何看待世界?他们还关心自身的历史吗?而面对这一世代的现实和困境,他们又怎样处置内心的情绪呢,是焦虑悲观抑或是积极抗争?

展览以八位摄影师的创作,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与上一代摄影师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战后时代的摄影师们,在日本战败的社会氛围下成长,他们熟悉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爆炸,熟悉日本无条件投降,也了解麦克阿瑟成立的“联合国盟军驻日总司令部”管理下的日本,更熟知在进行“东京审判”时,日本天皇在向全国人民发布的《人间宣言》中,对天皇在神道思想中的神性地位进行了撤销。
所有这一切,都让前辈摄影师们,在一个压抑的战后日本时代成长,在一个战前日本的所有价值观被全盘否定的不信任与不安的环境中成长。他们肩负了太多的政治、社会责任,战争留下的物质与精神创伤成为其创作的重要主题。虽然,前辈摄影师们前赴后继地对早在其前一辈的摄影师们,无论在创作手法还是在对媒介的认识上,都进行了挑衅,但是,他们依旧被笼罩在一个漫长的“战后”氛围中。而作为艺术中心的西方,当他们将日本作为东方摄影的代表纳入其研究体系的时候,也依旧会为其贴上“战后”的标签。

但是,新世代的摄影师们,处在一个远离战争结束的年代,处在世界正在发生极速变化的时代,迅猛发展的科技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生态,让人们的生活、思考及价值观等发生着剧烈的震动,日本的年轻人加入了互联网的国际社群,分享者更广阔的时代情绪,他们不再肩负前辈摄影师们对于战后时代的沉重氛围,而是以解放的、先锋性的多样化概念,自由地进行个人化的表达。新世代的摄影师们,不仅观看方式变得更为多元,而且对摄影媒介本身进行了挑战。
于前辈摄影师而言,新世代所做的,正是挑衅之挑衅。他们的创作与自我延展,得到了广泛的肯定。此次参展的摄影师,他们在日本新世代摄影师中极具代表性,如获得2019年第44届木村伊兵卫摄影奖的岩根爱;如早在2011年就入选了荷兰摄影博物馆的同名杂志《FOAM》天才新人奖的细仓真弓;如三保谷将史,其作品正展览于阿尔勒,他是当下日本很多策展人和杂志编辑眼中的重要新星;如横山隆平,他以自己的语言,延续了为外界所著称的日本街头摄影的传统,他的作品也曾在濑户内海国际写真祭展出。

此次参展的八位日本摄影师,都深入研究了某一项主题,用他们各自的影像语言,从色彩、身体、物件、信仰、身份、社会自杀症候、日美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核弹试验等历史进行追问等方面,直面其群体的精神内核和外部的社会情绪。
Q & A:
千贺健史:担心《自杀潮》会形成“维特效应”
千贺健史(在2018年受邀参加荷兰Breda摄影节,其作品被印作摄影节画册的封面,此外,其制作的摄影书《自杀潮 (The Suicide Boom) 》入围了2019年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作者书奖,另外一本摄影书《压抑之声(Suppressed Voice)》也入围了2019年卡塞尔摄影样书奖。)
1774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书中的男主角维特因为爱而不得,最后选择了自杀。这部小说在当时形成了现象级的阅读热潮,由此也引发了青少年模仿性的自杀潮。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 Phillips在1974年提出了“维特效应”的概念,意指在媒体报道某自杀事件后,公众参照其知名的自杀方式或知名人物的自杀行为,所进行的模仿。
作品:《自杀潮》




Q:你为什么会有拍摄《自杀潮》系列的想法?你拍摄这个系列的前提预设是什么?
千贺健史:2015年,我的朋友自杀了。在那之后,我就对开始自杀这个项目开始感兴趣并进行研究。但是仅聚焦在我的朋友,这个项目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我不想让它成为一个简单的自杀故事。因此,在2018年,策展人后藤由美建议我为荷兰的布雷达摄影节(Breda Photo)做一个关于自杀的项目。那一年Breda摄影节的主题是“超越无限(To Infinity And Beyond)”,就是那种“限制”促使我更新了这个项目。
Q:通过这个系列的拍摄,你在对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杀现象的理解上有什么变化?
千贺健史:我明白他们自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霸凌”、“贫困”、“心碎”、“责任”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现实中,我们虽不能简单地说出“理由”,但人们就是会去自杀了。相反,这使得人们很难理解自杀的问题。
Q:你认为目前日本社会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与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等有什么关系吗?
千贺健史:在日本,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基于日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我认为人们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朋友和社会,对他们所经历和承受的情绪等,都没有意识到或不了解。
Q:能说说这个系列的拍摄过程吗?你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着手和呈现?你似乎做了很多的功课,如对自杀地点、档案资料、旧报纸、以及那些正经历自杀危机的人等等,都进行了田野调查。你一开始都是以哪几条线来开展这个系列的?
千贺健史:起初,我从研究和拍摄我朋友的自杀故事开始,我对他的父母和一些朋友进行了采访,此外,我还追踪了他的死亡之旅。在这过程中,我还分析了自己的自杀欲望是怎么产生的,以及是什么影响了我。那次旅行之后,我调查了过去及历史上很多引起人们模仿的自杀案例。因此,我去了那些事故发生的地方,去了乡村博物馆,到乡村办公室进行相关询问,还去了国家图书馆,甚至还在拍卖会上买了过去的旧资料。我还采访了那些对有自杀欲望进行支持的人,采访那些有自杀欲望的人,以及那些曾多次试图自杀的人。基于这些认识,我向各方就内容进行了证实,并写了一篇约四万字的文章,内容是关于“那些灌输给人们的自杀选择”的概念,是在这些文字的基础上,我才开始展开拍摄。而且,我专注于不把照片拍得太漂亮,也不在于要创造一个隐喻性的形象,但与此同时,我老老实实地拍摄了在我自己内心中所产生的自杀感觉,我用这些感觉来讲述我朋友自杀的故事,以及对触发人们自杀想法的无形原因等进行分析。
Q:你的拍摄聚焦于哪种类型的自杀者?你是否接触过试图自杀或找寻各种方法自杀的人?如果有的话,他们是否出现在你的照片中了呢?你有一些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千贺健史:那些不知不觉地试图要自杀的人,那些克服了自杀欲望的人,那些帮助别人自杀的人,那些在家人自杀后受到影响的人,那些阻止了家人自杀的人,那些说自己想死只是开玩笑但其实非常严肃认真对待此事的人,等等,他们都在我的照片中。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比如在拍摄之初,我拍了一张一只手在堆积木的图片。与这位拍摄对象的交流,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对我说,“当我发现我认识的人自杀时,我觉得自己似乎也被允许自杀了。”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一年前就着迷于她熟知朋友的去世,尽管她不记得在那之前或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最后,她还是上吊了。虽然,她因为被室友及时发现而幸存下来,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都被自己上吊时摔下起的声音、被抬上担架过程中的声音,以及被抬到救护车里的强烈记忆所影响。她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经历了很多挣扎。有一天,我在不知道这些的前提情况下,向她寻求拍摄方面的帮助,我问她是否可以拍她在玩堆积木游戏的样子。我本意是想用堆叠积木来隐喻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因为人们有时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就崩溃了,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拼命地生活。当她告诉我,她在过去的一年里是如何极度害怕一种类似于对积木倒塌的声音时,我便跟她说,可以不用配合我的拍摄,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极限,但她还是想要尝试一下。因此,每当她在叠加积木时快要崩溃时,她便会重新调整一下它们的平衡,从而就可以继续向上堆叠。
Q:日本有很多著名的自杀地点,比如青木原等,你认为这些自杀地点为什么那么有名?
千贺健史:最近,位于日本东京都葛饰区新小岩一丁目的新小岩站,成了一个新的著名自杀地点。媒体上充满了关于在火车到达前自杀者跳下去的消息,这引发了模仿式自杀。当下的日本,在互联网上,对于失去生活希望的人来说,“让我们在新小岩见面”这句话,变成了一种流行病。日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流行话语,意思是,我也很快就会死了,所以,你也不要怕会死。这句话常常是人们出于善意而同情他人的感受,但这往往会导致对方自杀。这样,当人们死在一个著名的地点时,会有一种归属的团结感,给他们一种自己并不孤独的感觉。由此,日常的流行和对话,其实让我们创造了一个个关于自杀地点的神话,使得当人们想象自杀时,会无意识地回忆起发生过的那些故事以及地点。我曾写过关于青木原的文章。在松本清张1959年出版的小说《波之塔(Tower of Waves)》中,有一个角色在青木原森林内自杀。由于1960年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并搬上银幕,因此,“青木原=自杀”的认知度便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那之后,每年都在青木原发现30到50具尸体,其实已经有很多年,每年都有超过100多具尸体在那里被发现了。而2000年以后,大规模的搜寻尸体行动停止了,是因为政府警政部门发现了太多的尸体,而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却只会导致更多的人选择在那里自杀。即便如此,2011年,仍有121名计划自杀的人因被发现后而自杀未遂,所以很明显,这不再是一种时尚,而已成为一种常态。
Q:你认为耸人听闻的社会自杀事件和名人自杀等,会产生社会的模仿效应吗?
千贺健史:是的,这些会产生典型的维特效应,让那些企图自杀者,会采取同样的行为。他们认为,自己会在死后的世界遇到那些著名的自杀者。但是,这其实让那些被同样问题困扰的人,得不到正确的方式去进行解决。如果媒体做的自杀报道被看作是一则美丽动容的故事,这只会让人们也想要采取这样的方法,也得到那些所谓的“美丽”。
Q:在拍摄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你对这一现象的担心的是什么?
千贺健史:当我开始和一个想要自杀的人预约拍摄时,同时也跟我的朋友们谈论了这个项目。后来,其中一个朋友告诉我,在那之后他曾动过自杀的念头。其实,在日本,人们一般不会与别人谈论自己想要自杀的想法,主要因为担心当谈论这类严重的问题时,会被人回避,也担心会让别人为他们担心太多,这在日本社会是一种禁忌,会让我们认为不应该与别人谈论自杀倾向,等等。然而,朋友告诉我的这件事情,让我了解到“自杀”其实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基本上避免将拍摄对象作为带有“自杀欲望”的象征,还有,我不会把画面弄得太漂亮,因为,我总是担心漂亮的照片会让人们引发自杀的欲望。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认为最大的困扰在于,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形成“维特效应”。
Q:在拍摄过程中,你如何看待摄影这种叙事方式?
千贺健史:我认为摄影是最灵活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之一,因此,在处理微妙问题的影像时,会有一种危险,而我希望的就是避免这种微妙的影像对观者造成误导的可能性。因此,我也相应采用一些文本来进行支撑。
Q:你如何看待日本社会的自杀潮,你希望通过创作向社会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态度?
千贺健史:我认为自杀潮不是在有自杀欲望的人群中产生的,而是产生在我们的社会中。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的日常用语、态度和行为等,是产生自杀意识的一部分。同样,即使我们不理解人们想要自杀的原因,但我们还是应该要积极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谈。我认为,他们基本上其实并不想死,而只是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他们若不知道怎样使自己脱离苦楚,就没法得到安慰从而好起来。
Q:在这个项目的长期创作过程中,你曾与那么多与自杀有关的人、事、物等进行长期的接触,这些曾影响过你产生自杀倾向吗?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克服的呢?
千贺健史:的确,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有时会想到自杀。但是,在那些时候,我都会试着去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是什么影响了我”等等问题,之后我明白,我只是在逃避每一个艰难的处境,想象着死后的一切。但死后的一切,真的存在吗?通过类似这样的自我问答,我常常会渐渐冷静下来。
内仓真一郎:“照片力”有压倒一切的力量
内仓真一郎(在2018年陆续荣获了“2018 Canon写真新世纪优秀赏”及“7th EMON AWARD Grand Prix大奖”两个重要奖项,并在2018年10月展览于东京都写真美术馆。)
作品:《十一月之星》《收藏品》




Q:可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吗?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要把摄影当成自己的职业的?你的生活经历又如何为你的创作提供了动力?
内仓真一郎:我是作为照相馆经营者的后代出生的。从小,我便一直看着父亲拍照的样子长大。从18岁开始,我进入摄影学校学习。之后在东京以摄影师工作为生,同时一边进行自己的创作,这样的日子经历了十年,直到之后我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九州东南部的宫崎县。 现在,我就在宫崎县生活、创作。对摄影的动力,来自于我内心的追求。从小,我的内心其实就有着一些自卑感,那种感觉在我成为大人之后也并没有消失,直到现在,我仍然有这样的感觉。但那股感觉,却化作了我摄影创作的动力,因此,在创作时,我会感到自己在创造充满了强大生命力的作品。
Q:你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呈现和反映了你所生活的地方?当你进入摄影领域时,你的日本背景扮演了什么角色?上一代的日本摄影师和当前的摄影环境对你有什么影响?
内仓真一郎:我觉得自己的作品跟我所住地方的连结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乡村,日常的生活都更值得关注,都同样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之前,我大多是在东京的街头拍照,但我并不认为那算是我的日本背景,在我看来,背景更多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那里有无限的世界,我认为那很美。我很喜欢日本的一些前辈摄影师,如土门拳、东松照明、细江英公、森山大道、奈良原一高这五位,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开始研究并学习他们。他们的作品很棒,简单来说,这些前辈摄影师们可以仅仅凭借“照片力”就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现代日本的摄影潮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以照片来表达的方式变得少了,但是,我就想继续创作能以直接的“照片力”来发挥影响力的作品。
Q:你最初是如何看待摄影这种媒介的,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图片在社交媒体上前所未有地使用的时代,你如何看待当前环境下摄影语言?
内仓真一郎:照片有各种各样的作用,它是一个反应自我的媒介。现在的世界,社交网站上正在使用大量的照片,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因此交换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正因为这样的时代,成为摄影家必须以压倒性的实力才可以。
Q:在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的过程中,你认为最重要与之斗争的事情是什么?你认为摄影是一种怎样的叙事形式?
内仓真一郎:其实还好,我每日需要斗争的,就是将那些突然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想法抓住。往往,每当我有一个想法时,便会立刻掏出口袋里的记事本,将其记上,写下一些提示信息,之后便开始着手拍摄。就叙事形式来讲,我认为在当今时代,摄影是一种具有拯救大众表达般功能的大众叙事形式。
Q:我们都知道,日本因为有着一个非常广泛和成熟的出版市场,其摄影的出版在世界上一直有着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认为哪一种是更好地展示作品的方式,展览抑或是摄影书?能谈谈你的拍摄项目中编辑照片的标准吗?
内仓真一郎:两者都是重要的表现方式,我认为展示是摄影的本质。你既可以从印刷出来的原作中,看到影像的精彩,也能以摄影书的形式看到编排、拍摄的思路,两者都很重要。就我自己的创作而言,我会更偏向于选择带有生命和死亡意蕴的照片,我一直都以摄影来在对生、死这样宏大的主题,因此,我的编辑思路也按照这个思考在进行。
横山隆平:摄影有如醉汉诗人的诗,虽无聊却美丽
横山隆平(以自己的语言,延续了为外界所著称的日本街头摄影的传统,其作品也曾受邀参加日本濑户内国际写真祭。)
作品:《城市与物件》




Q: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要把摄影当成自己的职业的?你的生活经历又如何为你的创作提供了动力?
横山隆平: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迄今为止,我的摄影创作,其实受到了我所接触到的多样文化的影响,如小说、音乐、电影、街头文化等等,特别是边缘群体创造出来的东西,我深受这些影响,由此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摄影创作的道路。
Q:你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你的摄影领域?你的日本背景扮演了什么角色?
横山隆平:从20岁开始,我就一直住在东京。在那期间,关于“城市是什么”的问题,便一直是我的创作主题。此外,东京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事件等,都成了我的创作背景。
Q:你最初是如何看待摄影这种媒介的?又是如何看待当前环境下摄影语言?
横山隆平: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反,作为一位影像创作者,我认为摄影是单纯的光的化学问题。如何将光的作用本身与现在相联系,以及如何将其数字化后使之再富有生命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我所考虑的基本课题。
Q:在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的过程中,你认为最重要与之斗争的事情是什么?你认为摄影是一种怎样的叙事形式?
横山隆平:我认为,最重要的,大概在于需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物质的最终存在方式,需要思考影像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方式。如果要谈叙事的话,我认为摄影有如醉汉诗人所写的东西般,内容都是一些虽无聊却又美丽的日常故事。
Q:展览抑或是摄影书,你认为哪一种是更好地展示作品的方式?能谈谈你的拍摄项目中编辑照片的标准吗?
横山隆平:其实我认为展览和摄影书都是重要的展示形式,没有优劣之分。如果谈及我的编辑标准,我会更注重三点:光线、印刷之美,以及照片本身的存在形式。
其他摄影师作品欣赏:
岩根爱(2019年第44届木村伊兵卫摄影奖获得者)
作品:《KIPUKA》



小原一真 (曾个展于阿尔勒摄影节、巴黎摄影博览会,以及日本的IMA画廊,此外,其摄影书《沉默的历史》入围了巴黎摄影博览会与光圈基金会的摄影书奖,阿尔勒摄影节作者摄影书奖、卡塞尔摄影书奖年度最佳摄影书等。)
作品:《比基尼日记》


细仓真弓 (在2011年入选荷兰摄影博物馆出版的同名杂志《FOAM》的“Talent”天才新人奖。自2002年至今,她每年都受邀参加荷兰阿姆斯特丹的UNSEEN摄影节。)
作品:《Jubi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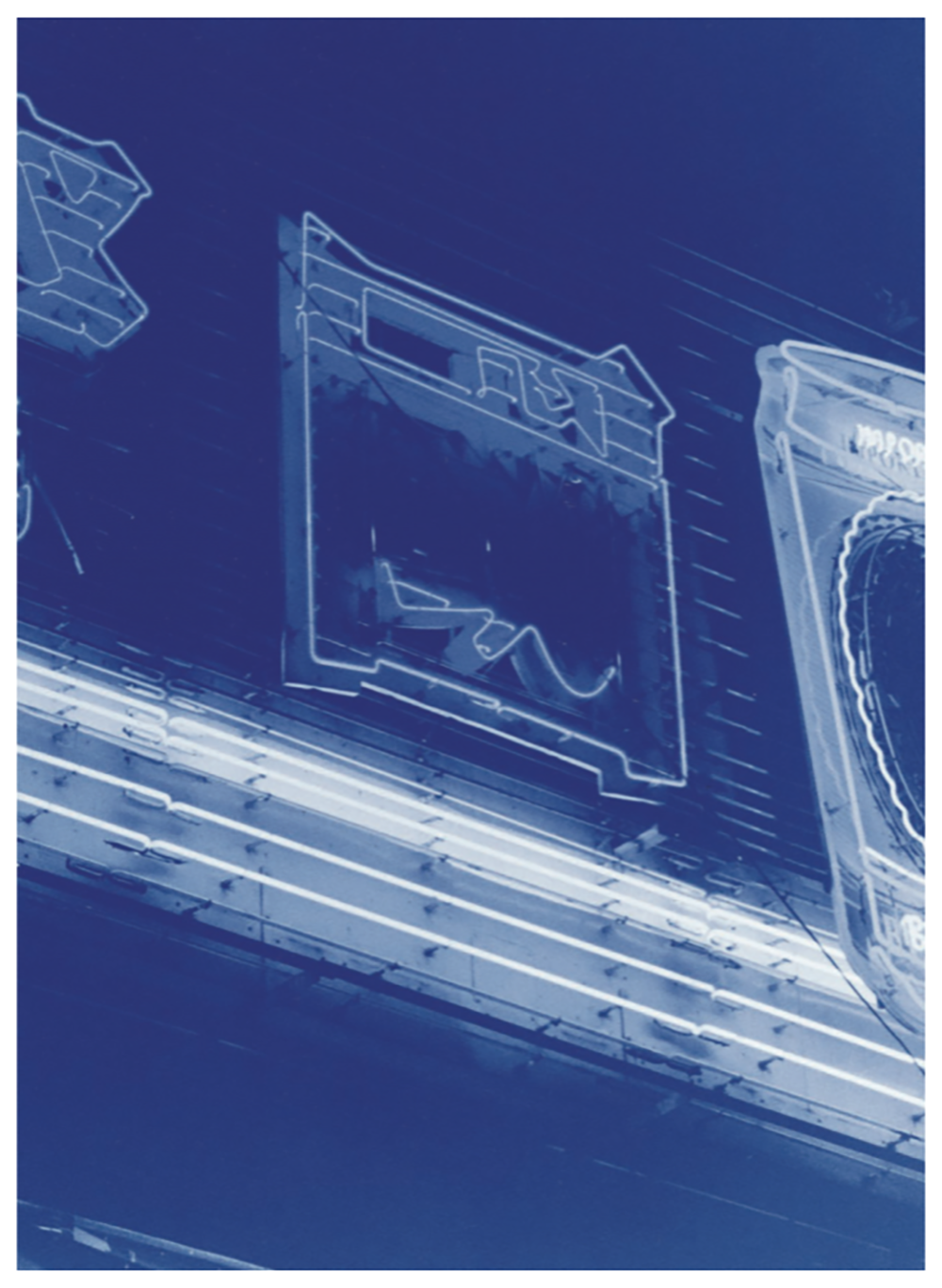

三保谷将史(善于从日常生活的体验中感知其根源,其作品正展览于法国阿尔勒,近两年其受邀参加欧洲和日本的多个摄影展,成为当下日本很多策展人和杂志编辑眼中的重要新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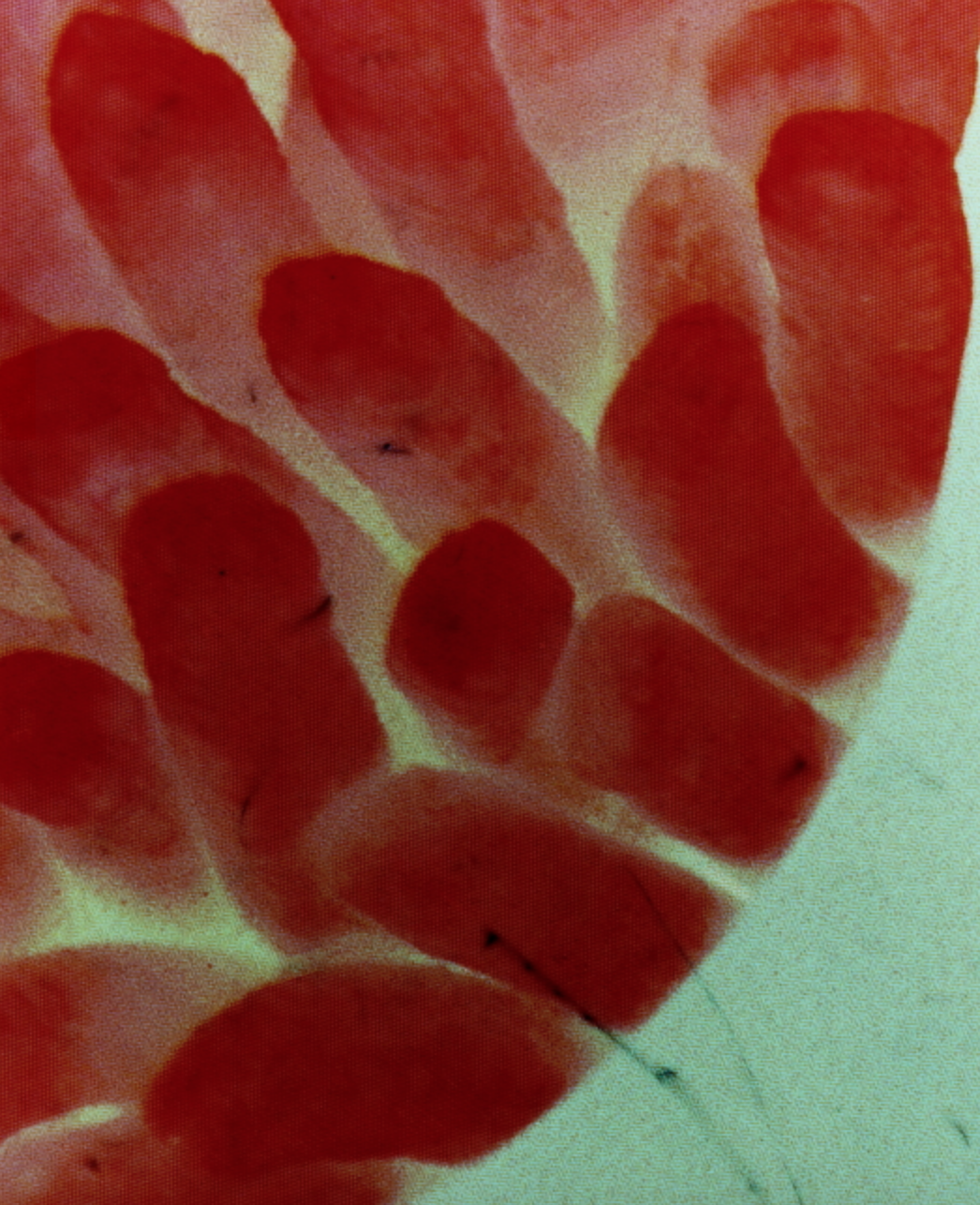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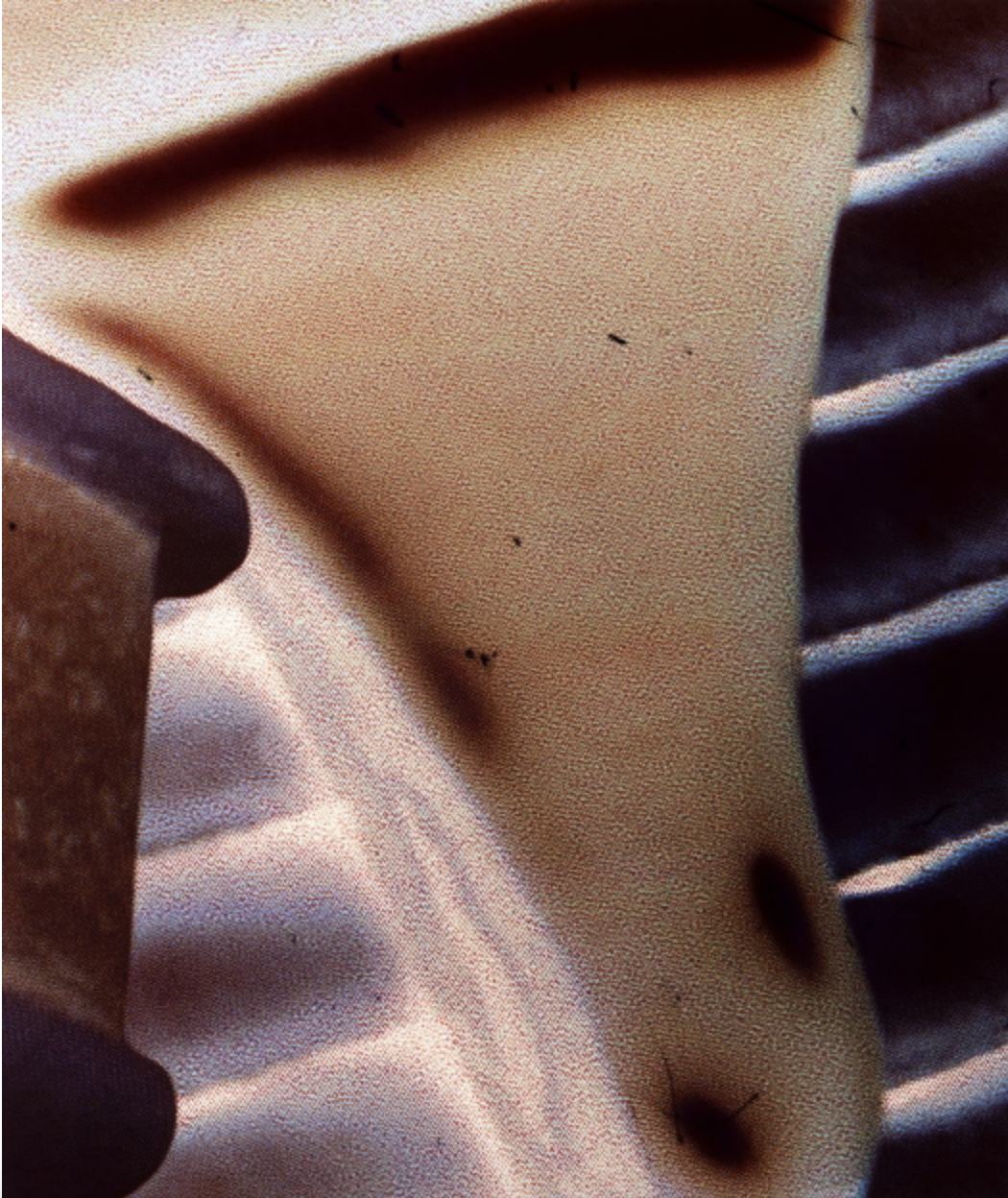
长谷良树 (获得2018年的LensCulture新锐摄影奖)
作品:《181度》


傅尔得,策展人,作家。著有《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肌理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