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吕迅·东方历史评论
近五年来,国际学界陆续出版了几本有关二战后中美关系的新书,以下几本大体折射出两国发展曲折的历程,解释了在历史的分水岭上他们是如何站到了对方的彼岸。
中国、美国在七十年前关系发生逆转,曾经有过长达22年的敌对时期,我们往往将之划归为国际冷战的一个方面。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以德意日投降而告终,但是并没有能够妥善修复当时国际社会分裂的局面,美苏各自主导的国际秩序相互碰撞,但是又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维持着恐怖平衡的状态,因此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正面的战争,但是在板块的联接处则冲突不断,这就是所谓的“冷战”。三十年前,柏林墙倒了,铁幕拉开了,但是当时主导着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依旧存在,影响至今。
如果选择一本书来了解冷战的开端,《美国与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美国与中国》不是费正清(John Fairbank)早年的那本,而是由《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2016年出版的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一书。这本书摘取了二百四十年中,作者认为印象最为深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光影片段加以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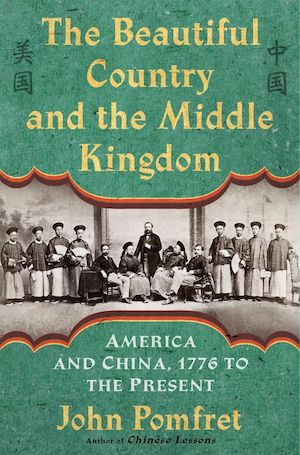
这本书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传统白人主流历史叙述的质疑和反思。作者潘文不同意冷战始于1946年或1947年的传统说法,他就以1945年卷入中国内战的伯奇(John Birch)上尉为冷战牺牲第一人。从论述二战中后期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使华开始,潘文突破了传统以美国军方资料为基础的“史迪威—白修德—塔奇曼范式”(Stilwell-White-Tuchman paradigm),而采纳了修正史学派陶涵(Jay Taylor)、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米德(Rana Mitter)等的观点,否定史迪威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外交能力。史迪威是二战时美国派到中缅印战区来的美军统帅,但实际上他能指挥的美国人很少,主要是指挥中国人并控制美国租借物资的发放。他对1942年中国赴缅远征军的失利和伤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数度紧张,史迪威最终不得不被美国政府撤换。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是了解二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一把钥匙。蒋史矛盾既不单纯,也不孤立,是与中国战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尴尬地位紧密联系的;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独体现在二战时期,而且自然扩展到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使华、国共谈判以及冷战初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史迪威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曾三度来华。他有着突出的语言能力,专门在北京学习过中文,能讲汉语官话,1926-1929年在马歇尔的直接统帅下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营长及参谋,属于美国的“中国通”。
难能可贵的是,潘文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些所谓“中国通”的种族主义思想。他引用陈光甫的一篇文章,批评史迪威口口声声说热爱中国百姓,其实爱的只是“顺从讨好他的中国人”:这些“中国通”是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来华的,他们已经习惯了二十世纪初在华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优越感。潘文也揶揄另一位“中国通”——谢伟思(John Service)的爱中国,只不过是背着自己的美国老婆,又爱上了一位中国女演员。他还找到了谢伟思未版的回忆录,并引用了谢伟思反省自己的话:认为美国人能够改变中国的想法,“是有一粒自大的种子(在作祟)吗?或许吧”。

当然,潘文这种观光导览式的写法,也是有利有弊的。优势在于作者以其带入式笔法,引导读者的情绪随着情节的变化而跌宕起伏;缺点也很明显,这种浮光掠影的方式忽略了各种细节,很难深入细致地探讨某一问题,可能会用情绪化的论断来代替周密的论证。例如,他否定了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一切功绩,包括在印度训练中国远征军的成绩。在否定史迪威的同时,潘文毫无保留地称颂另一位美国将军——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这样,魏德迈所犯的一些过错当然也没有被提及。同样的瑕疵也见于潘文对赫尔利的论述。他认定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的表现一无是处,当谈及赫尔利与驻华使馆其他官员之间的意见分歧时,却莫衷一是。在论及马歇尔使华的问题上,作者没有深挖,一带而过,但他点明了史迪威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为其调停带来了不良影响,承认马歇尔使华注定会失败。
我们再来看《外交关系》(Foreign Affair)主编丹尼尔·柯兹-菲兰(Daniel Kurtz-Phelan)去年出版的 "The China Mission: George Marshall’s Unfinished War, 1945-1947"(《中国使命:马歇尔未竟的战争,1945-1947》)。这可能是英语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本专门写马歇尔使华的书。他的可取之处在于查阅了马歇尔图书馆里收藏的以往未加利用的马歇尔夫人凯特琳及其助手的私人文件,去塑造了一个更加生活化的人。然而,如果你认为这本书与三十年前的马歇尔传记(Pogue著,Viking版)相比有什么创新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作为国务院的前职员,柯兹-菲兰的论调相当官方:中国的问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行,这不是马歇尔的错,他尽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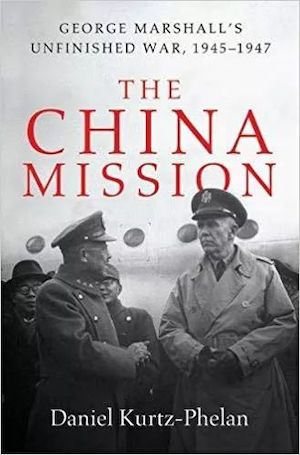
柯兹-菲兰同样也利用了蒋介石日记,但是往往在于论证蒋的固执以及马歇尔的辛劳。如果说蒋日记也算新材料的话,那么作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则了无新意,甚至对于共产党方面就没有参考什么资料,未有如同潘文那样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收集利用。比如柯兹-菲兰先是用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的话来证明中共与莫斯科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往来,借以讽刺蒋介石的猜疑,然后又表示马歇尔非常敏锐地洞察了莫斯科在东北对中共的援助,来表明冷战已经开始,最后又以马歇尔用自己的飞机运送周恩来并没有把周遗漏的情报交给国民党一事为例,说明马歇尔忠实而公正的人格。就像陶涵给蒋介石立传一样,柯兹-菲兰笔下的马歇尔是一个完人——就连他发怒的样子都是可爱的,值得为他的每一个失误辩护。这本书就和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一样混乱。
中国在柯兹-菲兰笔下就是个倒霉的所在。他介绍马歇尔太太旅居重庆的经历时是这样写的:“凯特琳一样地可怜。她觉得重庆糟糕透了,人多拥挤以致她很少出门,她出门的时候也是目视前方,避免眼神接触,因为车窗外面贴的都是人脸”。她是真的不喜欢中国,因此给家里写信说:“我走进洗手间,望着窗户外的中国人,我就萌生出一个愿望——把华盛顿所有高官和他们的太太们都派到这里来,然后我为她们挥手道别‘你能和你夫君一起去中国真是多么了不起啊’”。马歇尔本人对国民政府的评价不高:“我不知道委员长的智囊们都有谁,不管是谁,他们都是最差劲的,毫无建树,只会为国家带来麻烦”。用作者的话说,马歇尔觉得1946年的中国就像1941年的日本。
作者全部论述的核心就是蒋介石辜负了美国人的慷慨,而且他的傲慢招惹了俄国人。当时整个美国好像都认为马歇尔的天才圣手能够为中国拨乱反正,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做不到,而马歇尔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柯兹-菲兰摆出一副和谢伟思、马歇尔一样的“中国通”面孔,他应该深深赞同当时马歇尔的提议,即国共双方都后退一步而把控制权交给美国人,他甚至觉得应该用菲律宾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他赞美马歇尔曾在菲律宾服役,却没有提到马歇尔在那里镇压过菲律宾人的独立运动。柯兹-菲兰说对了一件事,那就是1946年5月马歇尔已经在慎重考虑自己的退路——回国就任国务卿,然后中国任务的失败导致他把目光投向欧洲而促成了马歇尔计划。和他的太太一样,马歇尔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中国任务,也不在乎中国人,他在乎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名誉。按照作者对马歇尔上庐山时情景的记叙,当他坐着八抬大轿惬意地享受牯岭清风的时候,一定也觉得那些停下休息、正脱掉上衣拧出汗水来的轿夫们有碍观瞻。
接下来要谈的是一本写1949年的书:"A Force So Swift: 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迅雷之势:毛泽东、杜鲁门与1949现代中国的诞生》)。作者佩雷诺(Kevin Peraino)是《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的主任记者。这本2017年的新书可读性非常强,文笔优美,形象生动。佩雷诺从他对居住在北京已经八十多岁的陈勇(音)进行采访写起,画面一下子拉回到七十年前的那个秋日夜晚,耄耋老者变回了十六岁的提灯少年——陈参加了开国大典后的庆祝游行。可惜的是,在之后的篇幅里,作者没有再提过陈勇,而是从1948年底的华盛顿开始了他的故事。借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佩雷诺穿插介绍了几个与中美关系有关的主要人物至此的人生,包括宋美龄、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杜鲁门连任和蒋介石下台的强烈对比之下,1949年拉开了帷幕。他特别强调了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外交能力不足,借用其助手腊斯克(Dean Rusk)的话说,艾奇逊是大西洋人,“完全忽略了世界上的褐色、黑色和黄色人种”。作者明确指出艾奇逊依赖凯南(George Kennan)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来制定对华政策。众所周知,凯南是苏联问题专家,是冷战政策的美国设计师,但凯南原本特长是在欧洲,因此他和国务卿都认为中国不重要。“我们还没有真的准备好去领导世界、拯救他人”,凯南很自然地说道,“我们还得先拯救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凯南要急切主张出台一部白皮书来为美国对华政策辩解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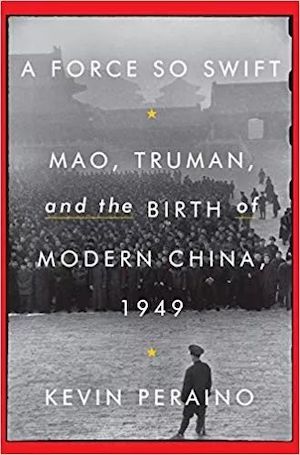
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提到戴维斯(John P. Davies, Jr.)是凯南政策计划室的主要智囊。戴维斯这个人很有意思,以往似乎没有什么关注。他和谢伟思一样出生在四川,属于国务院的“中国通”,但他比谢伟思要世故老练得多。1938年他就与史迪威和周恩来在汉口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二战期间投靠史迪威,挂名在美国驻华使馆,帮这位不善交际的美国将军打点与华盛顿、延安以及在重庆的各方面关系。他利用在开罗会议期间接触到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机会,经由总统的挚友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直达天听,建议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这就是后来的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这个人曾因为在一次由印度到重庆的飞机失事事故中展现出的卓越领导才能,而被授予自由奖章。后来史迪威被罗斯福召回,戴维斯自己去了一趟延安,然后就主动要求发配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在那里,他成为凯南的心腹和有关中国的情报来源。当马歇尔1947年回国就任国务卿的时候,就命令凯南组建政策计划室以提供咨询。戴维斯也就很自然地继续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关注香港科技大学常成教授今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朝鲜战争的新书《被绑架的战争》(The Hijacked War),对戴维斯的作用有新的论述。
我也不知道佩雷诺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宋美龄。可能是从性别的角度出发,他安排宋美龄以夺目的姿态在全书中率先亮相,但随后又多次描写她企图以自己的魅力征服昂格鲁撒克逊的男人们,还写到了她的病、她的梦魇以及她那只被蒋介石枪杀的猫。以往我们认为蒋宋之间并非政治婚姻,夫妻间的感情很好,尤其是读过蒋日记之后,更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蒋每每提及“美妹”都是心怀感激。可是从宋美龄多次长期滞美的经历来看,可能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毫无疑问,宋美龄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佩雷诺利用了宋美龄在美国与蒋介石联络的电报记录,透露出她旅美期间仍然试图积极影响蒋的内外政策。在上海易手之后,宋美龄曾劝蒋介石切断海底电缆线,断绝上海与美国的联系,建议伪造人民币来制造金融混乱,甚至还要派特工潜入华北和华东,给留在那里的外国人制造麻烦,以嫁祸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虽与宋美龄不和,但遇事也还要跑到宋的寓所,首先征询她的意见。
作者研究了艾奇逊的中国观,发现艾奇逊和马歇尔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蒋介石政府粗鄙无能,而且美国自二战后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加以援助,都被这个政府给滥用了——他称蒋为反动派。艾奇逊其实坚信: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是个相对较弱的角色,不会具有实在的攻击能力,他那句著名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还说不出下一步有何举措,需要看看灾难的尘埃落定之后还剩下什么”。当然,艾奇逊也不关心什么能留下。他无所谓,反正“中国像现在这样动荡不安都有一百年了”,一个农业国拥有如此庞大(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他甚至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辩称,把中国丢给斯大林只不过会增加苏联的负担。艾奇逊当时关心的是能否通过增加美国对华非战略品出口的数量来拉拢中国的新政权。他在白皮书发表之后,又让杜鲁门声明:“美国并无从福摩萨攫取特殊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或者把福摩萨从中国分割出去”。只不过在正式发布的时候,后半截话被删掉了。正如专栏作家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1949年所写的那样:“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是阴沟死水上漂着的一块碎木板”。
作为自然和历史的分水岭,全书把这一年的6月30日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毛泽东在这一天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方针,尘埃终于全部落定了。之后,凯南和艾奇逊开始制定遏制战略,即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实行围堵,最为重要的是,提高日本在战后东亚的地位。作者还提及了苏联在这一年试爆了原子弹。我们从冷战的要件来看,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其实对于中美关系来说,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那就是美国自1944年至此对中国国内政治的介入和干涉。
这本书还补充介绍了一些美国在华暗战的活动——秘密情报工作。作者利用了国务院所属情报机构(OPC)特工考克斯(Alfred T. Cox)的私人文件。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威斯纳(Frank Wisner)是美国中央情报局(OSS-CIA)的骨干,他直接向艾奇逊和凯南汇报工作。据说威斯纳听取了“飞虎队”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的建议,在1949年为中国地方实力人物直接送去资金援助。10月,考克斯就和同事罗肖尔特(Malcolm Rosholt)一起把两大筐的港币现钞押送到白崇禧在昆明的办公室。同样,他们也资助了云南的卢汉。
对于1949年末的中苏谈判,作者参考了毛泽东和斯大林12月16日的部分谈话内容,但是并没有注意到有关中苏条约的问题。谈及毛泽东对苏联的接待和冷遇不满时,突然说他想弄一个新的条约出来,显得十分突兀。佩雷诺认为斯大林相信美国不会干涉台湾因此积极支持毛泽东收复台湾,并且指出斯大林希望中共收复台湾能够起到孤立杜鲁门和艾奇逊的作用,这是没有根据的。随后又说毛泽东担心朝鲜战争会招致美国干涉,因此很不愿意支持金日成。事实上恰恰相反,毛泽东并没有那样的担心,而且对金日成非常支持,只不过金日成没有告诉他时间表。同样值得商榷的是,这本书暗示蒋介石早在1949年上半年就决定以台湾为自己的避难所了。
其实,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2016年出版的"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蒋介石、美国与台湾形塑》)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和记者的非虚构性写作不同,这是一本严谨的史学著作(部分内容也出现在林2017年的中文本《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一书)。基于蒋介石日记,林孝庭提出国民政府最终迁台完全出乎蒋的预料。因为迟至1949年12月,蒋介石还打算以云南作为他拒守的基地,孰料卢汉临阵倒戈。而美国政府在此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书中透露卢汉曾经多次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互通款曲,表示愿意在美国庇护下独立,该意愿遭到拒绝后才毅然投诚共产党。从此蒋氏父子逃往台湾,台湾在经历了短期回归之后又再度与大陆隔绝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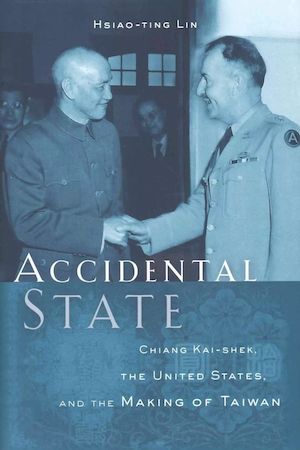
对于冷战初期美国对中国南方边疆的政策,林的研究可谓独到。他认为以驻华使领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自1947年下半年开始积极支持中国边疆实力派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分离出去。根据林孝庭的考察,美国国务院早在1947年5月(“二二八”事件之后的两三个月)就准备介入台湾事务,并且在1949年初至1950年6月一直反对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准备以孙立人取而代之。根据蒋日记,宋美龄在1949年10月5日密函蒋介石表示国务院中的“一些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在挑拨孙立人与蒋的关系,蒋对此深信不疑。就在杜鲁门发表不干涉声明的1950年1月5日,孙立人秘密告诉一位美国驻台北武官:蒋听到了一些孙计划发动政变的传闻,他向蒋表示这完全是谣言并要求澈查。蒋介石最后委任孙为陆军总司令,但却毫无实权,仅仅负责一些军事训练项目(1955年,孙立人因郭廷亮案被蒋介石革职软禁)。蒋其时陷入了一种孤立境地,几乎无人可以信任。杜鲁门和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的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会像在大陆时一样土崩瓦解。
书中还指出美国对台独主义运动的支持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分裂和不成熟。从1947年“二二八”事件到1949年蒋介石政府辗转迁台,台独运动以之为契机,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并且在东京、香港和台北都找到了美国军方和外交界的同情者。而美国政界也同样将其视为一股潜在势力而加以利用。国务院和国防部希望由吴国桢和孙立人出面,将这些人和其他台籍精英统领起来组成新的台湾地方政府,还专门任命了驻台北副领事欧斯本(David L. Osborn)代表美国与这些台独运动领袖联络,并提供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内的某些身份加以掩护。于是,艾奇逊一面宣布了他不干涉台湾问题的立场,一面又通过驻台的使领官员保持与台独势力的联系。
以上四本书大体折射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曲折的历程,解释了在历史的分水岭上他们是如何站到了对方的彼岸。像罗斯福、马歇尔、杜鲁门那样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不过是会犯错误的凡人,而带有种族主义思想隐患的“中国通”们可能对中国一窍不通。从柯兹-菲兰的新书看来,七十年中美之间思想的鸿沟并没有被双方的巨额贸易填平,甚至可能反而愈来愈深,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