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自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上海南京路的“四大”百货商店——先施(1917)、永安(1918)、新新(1926)、大新百货公司(1936)依次开张,它们以争奇斗艳般的手段,在橱窗里撒起雪花,让美女在现场制作香皂,将南京路变成了上海的“百货公司路”,也让传统店铺诸如澡堂、旅馆、日用品商店等默默退出。
在去年出版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连玲玲提出,上海百货公司通过橱窗和营销催生了一种“欲望的民主化”,这意味着百货公司虽然主要向中产阶级以上销售产品,但也会邀请更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群加入,将消费欲望向下渗透。而“欲望的民主化”的手段既包括设立廉价部门和大减价活动,也包括在顶楼设置票价低廉的游戏场。
1992年,正在读硕士研究生的连玲玲为了查阅百货公司的资料第一次从台湾来到上海,此后她又多次来上海,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近日,她再度来沪,并重访了南京路——现在的南京路与她印象中的景象已然不同,新建筑盖起来,原先的历史建筑成为了被遮蔽的前景,这让她觉得有些难受。也是以此次来访为契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与连玲玲在复宣酒店的咖啡厅里进行了一场与“欲望民主化”、百货公司的影响、女性消费与女职员有关的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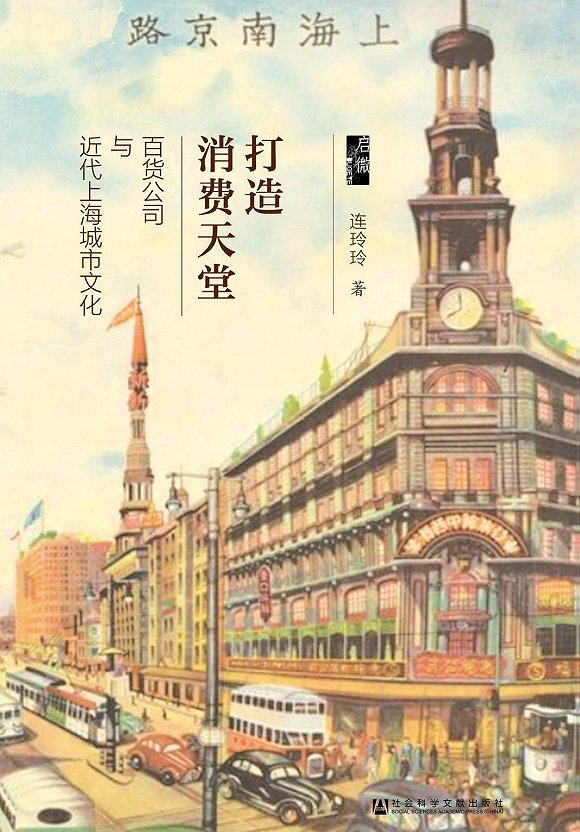
连玲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6月
“欲望的民主化”:消费欲望不仅限于某个阶层,而是可以在不同的阶层间传播开来
界面文化:你的专业研究背景是妇女史研究,那么是如何开始做百货公司的研究的?

连玲玲: 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百货公司的论文。当时其实还很少人研究百货公司,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出了一批关于百货公司的史料,我的老师说你可以做这个题目,所以我就来到上海看这批材料,那时是1992年,我算是很早来上海看资料的研究生。当时我的论文是以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新式企业怎么在中国出现,怎么生根发展,后来又是怎么应对政治上的变化的。后来我去美国读博士,也没想到什么关于这个题目的新的研究方向,就放下它去做妇女史了。等到我博士念完回到台湾中研院工作,我有一批同事读过许多消费文化的理论及历史的研究资料;特别是明清方向的同事,他们注意到了明清时期消费的蓬勃状况,他们也将16世纪到17世纪晚明时期看做中国第一次消费革命,事实上这个消费的趋势是一直延续下来的。然后我就想起之前做的百货公司是可以从另外的消费文化的角度继续做下去的。
界面文化:书中讲到了“欲望的民主化”这个概念,讲的是即使消费不起百货公司商品的阶层也可以借助百货公司的橱窗和百货公司整个营造的氛围来感受消费的欲望,“欲望的民主化”是书中讲百货公司影响的核心概念吗?
连玲玲:这的确是我书中的一个重要的观点。百货公司这样的场域好像只为了有钱人而来,好像只有在里面消费的起的人才会受到百货公司的影响,其实百货公司不只是为了购物的人,它的建筑、橱窗和文化意象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都是影响,欲望的民主化的意思是消费欲望不仅限于某个阶层,而是可以在不同的阶层间传播开来。
界面文化:对于今天的南京路来说,“欲望的民主化”这点仍然适用吗?
连玲玲: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我们看到的南京路的东西还是很贵。那天我去买衣服,花了好多钱(笑)。可是在南京路走来走去各种人都有,外地人也很多,外地人可能难得来一次上海,可能存了好久的钱,或者是带着孩子或者自己过来,上海的消费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现代的象征,也代表一种未来富裕的向往,这还是带着欲望的民主化的作用。
界面文化:像书中讲到的百货公司的廉价部门和季末年末打折,是否也都属于“欲望的民主化”的策略的一部分?
连玲玲:欲望的民主化有好几种层面,刚我讲的是一个层面,还有一种是公司从经营角度,刻意地希望可以扩大有钱人的市场之外的市场,当然目标市场不可能是真的很穷苦的人,但像是先施公司的“一元商店”——那种店全场可能就只有两种商品的价钱是五毛一块,但对小市民来讲是可以消费得起的;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买最高档的,但用廉价的价格也买到了先施公司的东西,可以讲“这是先施公司的”,管它是公司还是商店,它就是先施的,这会造成欲望在更大群的消费者中传播开来。
另外,我在整本书中花了最多的力气来讲屋顶游戏场。百货公司设置屋顶游戏场,本来是想要创造一个文人可以休憩的地方,让百货公司可以看起来高雅一些,但不想要太多经济负担,所以收很便宜的门票,两毛三毛一张,但也因为门票收得太便宜,所以吸引了一批跟他的商店完全不一样的人。结果形成了两个市场,对公司的经营来说,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问题。百货公司为了要开拓市场、制造欲望的民主化,结果反而造成了公司经营的市场模糊,甚至与社会对百货公司的感观也形成了冲突。

界面文化:这里的“跟社会对百货公司的感观造成冲突”,是说屋顶游戏场让百货公司看起来不高级吗?
连玲玲:譬如说,有太多的烟赌娼的事情发生,或者一天到晚有人在那边吵架打架,或者是骗人事件。这整个观感跟楼下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以至于在1946年有人开始举报永安的屋顶游戏场天韵楼有不法和色情的事情。那么永安公司的想法就是要清掉这些摊贩,但是这不是赶走一个两个人,而是赶走很多靠这个生活的家庭,那时正是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兴起的时候,整个社会经济状况都很混乱,在这个情境下,导致了更多来的矛盾,以至于市政府、社会局和警察局要干预这个事情,永安公司的改造到最后也都没有成功。所以欲望的民主化,对公司来讲,开始的构想和后来走的路是不同的。
界面文化:当代商场也会宣称自己不仅是购物的场所,也是集消费、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目的地,你认为现在商场里的休闲娱乐可以算作当年那些屋顶游戏场的当代版本吗?
连玲玲:这要看休闲娱乐的是什么了。当时的游戏场是个场子,你买一张票可以进去看所有的表演,比如京剧、评弹、滑稽戏和其他地方戏,也可以玩游戏机,或者看哈哈镜——我们现在看很好笑,但当时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很新鲜有趣的玩意。现在在上海消费的场所,不管怎么样,还是基本的门槛,不会像当时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跟那时的游戏场是不太一样的。上海百货公司的游戏场影响到后来的台湾地区,因为有一些上海的企业家后来去了台湾,在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有百货公司出现;上海的百货公司变成了他们的model;他们把上海百货公司的雏形搬到了台湾,这样的百货公司里也有屋顶游戏场。我在所里报告我的题目的时候,一些比我年长的同仁,就回忆道,比如在高雄的大统百货也有那种屋顶游戏场,也是很便宜就可以去,虽然游戏的项目不太一样了。这样的游戏场现在我比较少看到,更多的是美食街。
界面文化:你会去上海一些新的百货商场吗?比如比较起来算是新兴的商圈五角场(就在采访地附近)?你会认为这样的商圈比起南京路来会缺少上海特色吗?
连玲玲:有时间会逛一下。一个社区的兴起,需要有各种生活机能,才能让人集中,百货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的感觉因为相似的东西太多以至于就没有特色。南京路之所以在当时特别,就是中华一条街,它当然不是最漂亮的,霞飞路更漂亮,但讲夜上海、讲上海繁华,若不提南京路是无法想像的。现在上海商业发展的轨迹和100年前很不一样了,这也会让我们重新反思究竟什么是上海。当然,你也可以说上海不是固定的,上海之所以迷人就是因为它又洋又华,不中不西的混杂性,而且,城市是有机的、是有生命的、会发展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更注意的是那是个什么样的上海,而不是把过去的上海固定化为“上海特色”。
百货公司的场景:让一部分人致富,让一部分人感受到被剥夺
界面文化:你刚说到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百货公司的消费文化都是一种影响,那么对不喜欢的这种影响的人来说,这种欲望的民主化会不会反而刺激到他们呢?
连玲玲:当然会,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的左翼文人面对上海的繁华,看到的更多的是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有一批人由于上海致富,可是也有一批人由于上海的富裕而被剥夺。百货公司正是这种让一部分人致富,让一部分人感受到被剥夺的场景,所以上海一些左翼文人的确对百货公司有一些批评,报纸上也会有人投诉说百货公司只代表着上海繁华的幻象而不是实际。对于中下阶层小老百姓来说,百货公司完全是高不可攀的。譬如说有名的作家刘呐鸥,蛮早就注意到百货公司的这个方面,他1927年写的一篇小说,在描述百货公司的时候,就充满左派的对阶级对立矛盾的控诉(记者注:此处指刘呐鸥短篇小说《流》,书写了玻璃橱窗内外的不同世界)。百货公司从公司角度来说是全球化的产物,日本文人描写百货店的文学文本也对中国的知识界有一些影响。
界面文化:美国历史学学者卢汉超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里写到了上海里弄里的小商店,提到上海那个时期的普通里弄百姓可能不会去百货商场,而是在里弄商店里完成吃喝住行的必需消费,你是怎么看待他的这种研究与观点的?也就是说,上海摩登与普通市民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可以接触得到,还是基本没什么关系?
连玲玲:的确有可能会这样,有的市井小民是从来不出远门的,所有生活衣食住行所需就在隔壁,买东西也不需要进入到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之中。当然有人从来没去过百货公司,或者去娱乐也都是去江北的娱乐场,那种露天的、不用买票、只要给点赏钱的杂耍和戏剧表演。但是难道都是这样吗?黄包车夫够穷了,可是他会载着太太小姐走过这些百货公司,这难道对他没有一点影响吗?百货公司的影响不仅仅是购物方面的,而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南京路这条路给人的印象不是因为人们进去买东西而形成的,而是一种社会影响。我认为就算不逛百货公司,他们也不会自外于霓虹灯的现代性影响。里弄当然非常贴近老百姓,它的影响跟百货公司散发出的现代性和视觉冲击不同。还有,关于屋顶游戏场的消费数据有一个统计,它的客人多半都是小市民,所以说小市民不见得完全不可能接近百货公司。(记者注:《打造消费天堂》一书中提到,天韵楼门票相对低廉,分为盘梯和电梯两种,价格分别为1角和2角,直到30年代票价涨成3角。对比当时知识青年每月生活预算50元,以及工人阶级平均年收入416元来看,这一价位的游戏场门票消费者还算负担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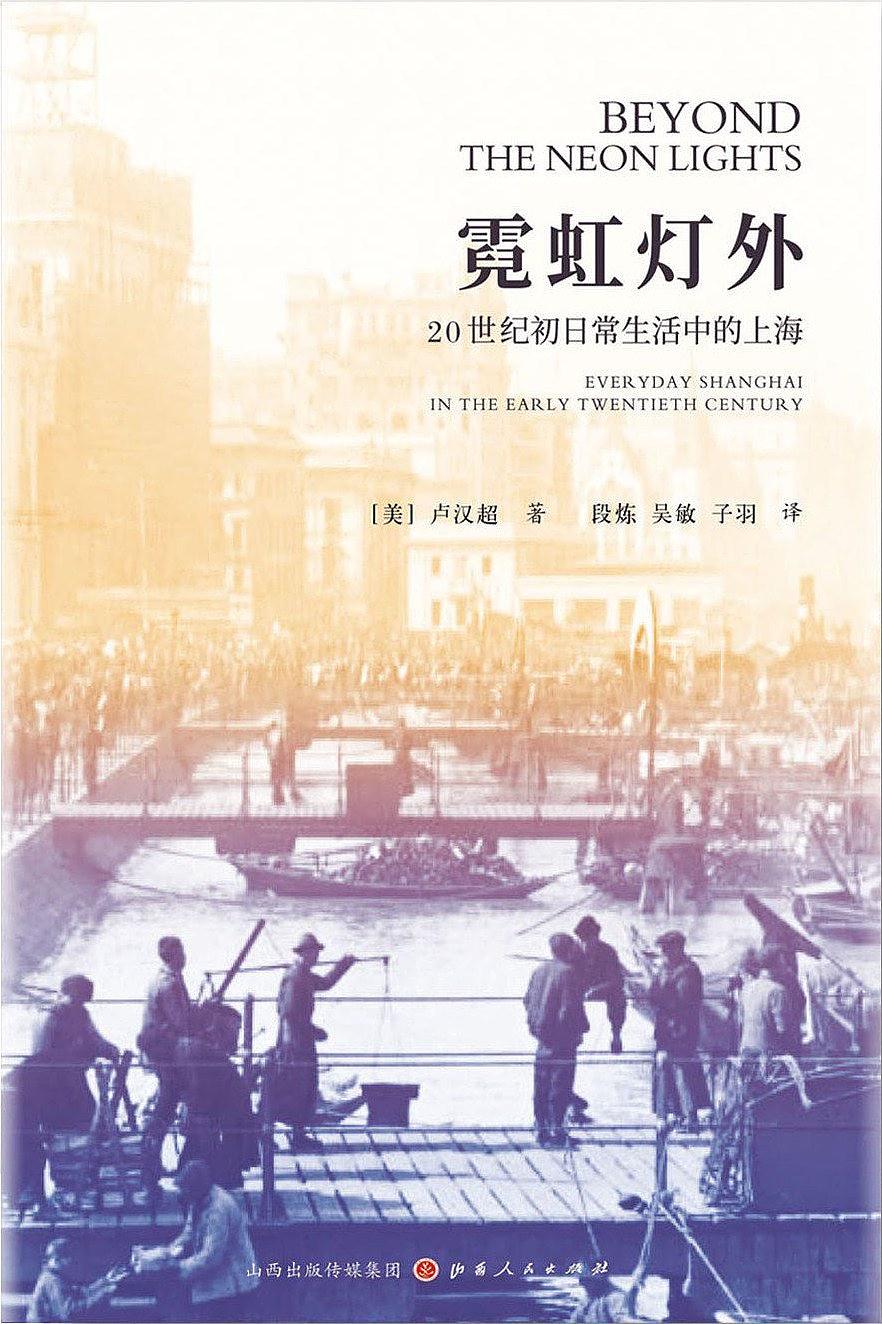
[美]卢汉超 著 段炼 等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界面文化:刚才你讲到,百货公司的屋顶游戏场里有滑稽戏、哈哈镜这些有搞笑效果的娱乐项目,也提到了百货公司的娱乐休闲性质,那么对百货公司来说,娱乐或者说搞笑的功能是不是重要的?就像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教授雷勤风(Christopher Rea)在《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里讲的,通常被认为充满苦难与眼泪的近代中国其实是有许多笑声的,而笑声也可以透露出一些正统的、严肃的观念之外的戏谑和嘲讽之声。
连玲玲:那一本书讲到了很多种类的笑声,其中有一种笑声因为有讽刺性,对现有体制构成了嘲弄和挑战。百货公司是一个充满笑声的场所,屋顶游戏场也会有滑稽性和喜剧电影,但那一种充满笑声是比较多是对现实生活压力的解消,而不是对国家政府的挑战,我没有看到直接讲滑稽戏的材料,可是在屋顶游戏场会发行一种《游戏场报》,这种报纸发行的时候会有一些对军阀政治的嘲讽,那时中国正在军阀混战时期。
界面文化:所以这个《游戏场报》的编者是专门聘请的文人,而不是商场内部员工兼职编写的?
连玲玲:公司每个部门都有部长,游戏场的主任是公司的员工,这个主任会另外请文人来办报纸,文人负责写稿拉稿,这种报纸是很便宜的,如果你去游戏场,可能就是送给你当成节目单来看,这种报纸不是想要盈利的,只是因为光是节目单不好玩,文人为报纸写东西可以拿到稿酬,有时稿酬就是游戏场月票,这也是促进游戏场发展的一种方式。这种报纸和《永安月刊》的编辑就不同了,《永安月刊》的编辑群是公司里的广告部,两份刊物的走向和编辑方针有一些不同。

雷勤风 著 许晖林 译
麦田出版 2018年6月
百货公司的性别结构:男性是权力位阶的上层,女性在下层
界面文化:你的专业是妇女史研究,你认为女性的消费在近代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连玲玲:我在书中讲到了两个角度,一个叫做女性消费,一个叫做消费女性,女性作为消费者一般会被强调或者过度强调,每次讲到百货公司就一定是一堆女人在里面抢东西、买买买这种状况,但是女性消费者,为什么都是女性被贴上消费者的标签。好像男性都是从事生产,女性都是从事消费。其实从晚清梁启超在讲女性角色时,就给女性贴上了消费的标签,他把人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生利者,一种叫做分利者,在他的分析里,大部分的女人都被归为分利者。所以在晚清大思想家观察里,中国社会问题就是太少人生产,太多人消费,因为不是所有的男人都生产,但是大部分的女人都消费。国货运动也一样,一定是讲男人是国货的生产者,女人被动员作为国货的消费者,从这个方面来说,女性不断地被贴上消费者的标签。
可是女性会跳出来表达自己的消费的正当性,来讲她们是在为家庭消费而不是为自己消费,所以女性消费需要重新附着在传统的女性角色上,也就是回归于家庭之中。我书里写到永安公司老板的女儿结婚的时候办嫁妆,不断地强调着,她是一个人操办嫁妆的,不管是新家的布置,还是床单和家具的选择,都是一人办的,老公什么事都不管,这都是在表达消费的正当性。因为女人如果为了自己买东西好像很自私,但如果是家庭主妇的角色,就有了消费的正当性。所以虽然都是女人在买东西,可是她在为谁买东西?买的可能是丈夫和小孩的东西。
界面文化:消费女性的部分是什么意思?
连玲玲:这部分是从女店职员的角度来说的,在当时,女性刚刚踏入公共领域,她们那时候工作不是好好做事、拿薪水那这么简单,她们的存在也容易被放大,女店员跟男性顾客接触的场景在当时还是作为一个奇观存在的,也会有男性焦虑女性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可是在百货公司里,女性员工只占到百分之十。的确有公司利用女性职员卖东西,制造话题性,给女职员取了一堆的外号,什么西施、皇后等等绰号,其实都在物化女性。书中的例子是卖钢笔的康克令小姐,不管哪个女孩子上了这个柜台,都是康克令小姐,大家不会记得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叫康克令小姐,也就是说她的身份跟商品紧紧结合在一起。

界面文化:是不是就像现在的车模和车的关系?
连玲玲:可是你们会说宝马小姐吗?不会吧。当时会这么说。我后来去澳大利亚访问了以前新新公司的老板,当年他是少东家,我访问他的时候已经八十几岁了。他们公司有一种热水瓶叫水仙花,他们有一个水仙花皇后,专门负责卖热水瓶。访问的时候他还很得意地讲,这是他们很好的一个招牌,没有人记得水仙花皇后叫什么,只记得她叫水仙花皇后,这就很清楚地展示了女性被商品化的过程。
界面文化:如果一个商场是有性别属性的,那你认为它会是阴性或者女性的吗?
连玲玲:我必须说百货公司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好像看起来非常女性化,它的橱窗和商品,女店员和女顾客,都好像非常女性化,但如果拉高层次来讲,百货公司的经营者叫的出名字的没有一个是女性,这些男性其实是整个百货公司权力位阶的上层,而这些女性是在下层,在百货公司权力结构里男性居于上位,但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女性,好像这里是女人的世界,事实上百货公司的权力来自管理阶层和资本家,这还是一个男权的世界。
界面文化:那人们看到的这个景象——百货公司是女店员和女消费者的世界,难道是一种构建出来的幻象吗?
连玲玲:不能说是幻象,她们就实实在在地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女店员看起来被剥削和物化,但是她们并不是默不作声的,《申报》做过女店员的座谈会,找了女店员来讲自己的生活,从来不会有人自我介绍我是康克令小姐,她们一定会讲自己的名字,也一定会介绍自己的工作,比方说她是怎么卖面包的。卖面包这件事很简单,她就只需要坐在柜台那边,有人要买面包,她从柜台里把面包拿出来给客人,甚至收钱都不是自己收。但她要强调卖面包不是简单的事情,讲得好像煞有介事,很专业一样,女店员需要把自己职业的一面表达出来,所以她在主张自己的职业认同而不是女性认同,因为只有主张职业认同,才能表示出她不是靠美色和性别来做这份工作,这跟小报里对店员的描述什么皇后、西施之类的完全不同。这是表达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还是很微弱,女店员人数不多,且受制于表达的通道。《申报》也好《大晚报》也好,做女店员的专访也是因为好奇,这种的表达通道还是有限,她们还是面对着持续的物化。但我们现在只能透过媒体的再现,我没有找到女店员自述和日记,虽然她们都是中学程度,都是可以自己写的。
界面文化:她们的声音总是要通过各种媒体来表达,历史学家要如何借助这些媒体了解女店员比较确切的状况?
连玲玲:有趣的是,这些女店员后来也在后来不同的时代接受访问。1960年文革年代,这个访问的目的是要斗资本家,女店员要说资本家多坏多坏,让她们穿着高跟鞋站在生产台上面,对她们如何剥削。1980年代,这些女店员又接受采访,回忆1930年代公司店员的情况,觉得穿着高跟鞋卖东西“神气得来”,因为1980年代已经是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的经济阶段,要从1930年代的基础开始回顾。所以即便我们可以找到女店员的口述,但她们不同时代的口述都有不同的说法。作为历史学者我们需要透过这些眼镜来观看,没有办法把眼镜拿掉,但也要察觉到眼镜的存在,透过更多不同的材料的排比,慢慢地抽丝剥茧看到女店员真正的状况。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