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编剧帮 随芳芳
周振天是国家一级编剧,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的他,四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创作一线,带来了《蓝鲸紧急出动》《蓝色国门》《潮起潮落》《舰在亚丁湾》等引人入胜的军事故事。除了军旅题材,他创作的作品还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例如《玉碎》里的玉器古玩文化、《神医喜来乐》中的中医药文化、《闯天下》里的杂技江湖等。在第五期训练营现场,他以《影视剧本选题的定位、开掘与叙事策略》为主题,为大家分享创作经验。

切入点:不能正着写
写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拍电影还是拍电视剧?从哪切入?从哪开掘?怎么开篇?这些问题大家都会遇到。首先要找到切入角度。
切入点太重要了,切入点好是步步顺,切入点不好步步不顺,甚至影响你的命运。我有一个朋友写八大山人,问我怎么改剧本,我说你千万别正着写。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亡国公子,非常痛恨清政府,坚决不留辫子,宁可剃发出家,然后他一边念佛一边画画,成了中国画的开山鼻祖。他画的鱼和鹰很多都是翻白眼,他的态度就是我不正眼看你,不和当政者合作。那个时候清政府已经是一个正宗王朝了,你写他和当朝不合作,能在主流媒体播吗?离开政治的环境就行,你写一个落魄公子发愤图强变成艺术家的励志故事就是可以的。

举一个例子,电影《老少爷们上法场》讲的是天津火烧望海楼的故事。在同治年间,中国人烧了法国的望海楼,还杀了传教士,英国派出军舰停在渡口,要求清政府交出犯人,但没有人承认,就有人给曾国藩出主意,用二百两银子买一条人命。以前有一个京剧叫《火烧望海楼》,它的角度是中国人民对洋人的侵略义愤填膺,充分表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这个戏现在就不能演了。当时我就想必须找到什么时候讲都没有问题的角度。
我从《沽水旧闻》看到,当时买了13个人,他们在上法场之前说“我们是为大清朝去死的”,最后他们都穿着戏装,扮成张飞、赵云、窦尔敦等古代好汉,沿街百姓给他们喝酒,敲锣打鼓送上法场。这一瞬间给我留下很强的印象,很悲怆。我就写了这十几个人出于什么心态去死,有的是为了拿钱给父亲买棺材,有的是想得道升天,还有一个是为了改变出身,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参加科考。这个故事你要写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现在怎么写,怎么演?写成出于什么心态去死,这个角度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的生命力和观赏性。

再举一个《小站风云》的例子,天津有个地方叫小站,是袁世凯练兵的地方,北洋时代那些赫赫有名的领袖和军阀全是小站练兵出来的。直接写小站练兵我不敢写,因为北洋军阀是近代史中最黑暗的,办的都是卖国求荣的事,虽然小站练兵在军制学上很有意义,但直接写央视不会播。但是他们提的条件很诱惑,一千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从小站稻切入,把小站练兵包装在一个近代史故事里,两个种稻大户家的年轻人,从小家族间有竞争,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两个人一直在对抗和较劲,通过他们参军把小站练兵带出来,讲述两个年轻人走了不一样的道路的故事,这个戏央视八套就播了。
风格:用喜感包装深刻话题
落笔之前你还要思考要用什么风格写,有的故事只能写正剧,有的故事就不能写正剧。电视是大众媒体,即便你写的是黑暗的时代、深刻的话题,也要给一个轻松的色彩。比如一个苦药片,制药厂都知道外边要包一个漂亮的糖衣。如果一开始就说这个选题很深刻,一拉这个架子观众就不爱看了,大家累了一天了,晚上回家还要看你说教,即便写深刻的话题,也要给观众一个可以接受的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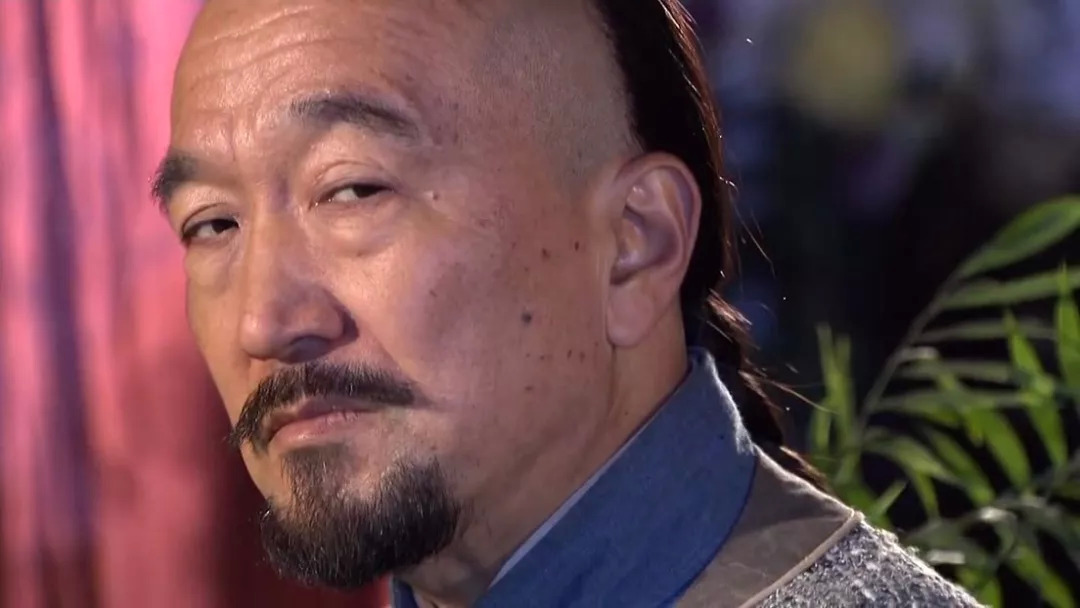
写剧本的时候,如果能有喜感就就往喜感写,我写《神医喜来乐》就是用喜剧包装一个深刻的东西,我觉得比板起脸来,一本正经讲中医和太医之间的斗争要好玩,观众神经放松下来了,一点也不妨碍你写深刻的东西。
如果主人公写成喜剧人物,能把你的故事传达出来,你就按照喜剧来写,如果主人公不能喜剧,周围人也要有点喜感,或者他跟他周围人的关系也要有点喜感,要是没有喜感观众看起来就累。中国京剧里生旦净末丑总有一个丑,这个丑是五大行内的分工,这是一个规律,也是艺术本身的东西,一定要有让观众提神的戏,让观众觉得有意思,当观众走出剧场和关了电视机再想,这个戏是很扎心的,写出这样的东西就是编剧的本事。
叙事策略:虚构的能力
编剧核心就是“编”,你要是不会就不要干这行了,“编”就是无中生有,以小见大。说白了我们拿什么换稿酬?如果剧本是水裆尿裤的,都是说闲话,这个剧本就没戏。人家现在都不傻,有一个编剧班子看剧本,首先第一关责任编辑在看。责任编辑说每集没有五六块硬梆梆的肉疙瘩这个戏就不行,这是我们本行最实在的,你拿什么填充几十集的故事,靠上楼梯、吃饭、进门、脱鞋、挂衣服、寒暄根本撑不了的,怎么办?你必须要在字里行间里和戏剧人物的关系里都设计好了,把戏抠出来,这个抠就是虚构能力的重要性。

歌剧《洪湖赤卫队》一个小时,它就是一个小时的情节,当时让我写三十集电视剧,我说你扯吧?电视剧最后播出是28集,这就得虚构,有的靠细节,有的是延展。我反复看歌剧的片段,唱“月儿弯弯照楼台”的时候有女儿在楼上磕瓜子往下看,我就写了他女儿和女婿的戏;我去了衡水后知道当地的胡匪很厉害,加了一条胡匪的线索。
一个小时的故事情节唱一个小时足够了,但是作为一个长篇电视剧必须增加一到两条副线,别怕观众看不明白,现在观众很聪明,你就把观众造晕,你的戏必须冲突性很强,让观众期待看。当然《简爱》这种故事是另一种东西,要看演员的表演,还有家庭伦理那种细腻的东西。像《洪湖赤卫队》这样大叙事、大背景的东西还是要把几条线同时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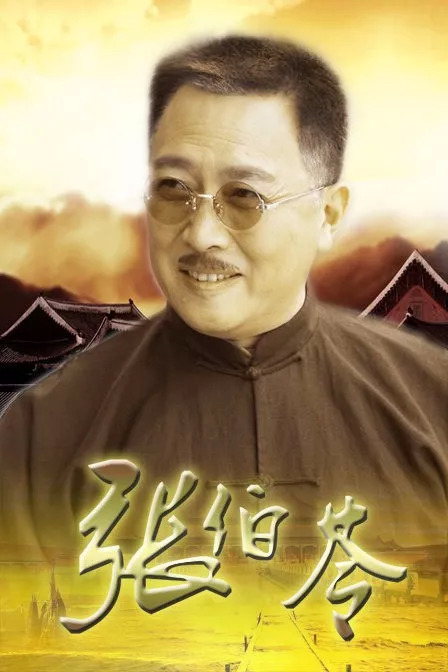
我再举一个例子《张伯苓》,张伯苓是周恩来、曹禺的恩师,在南开大学培养了五六十个国家院士。我从历史中看到的就是张伯苓怎么办大学、怎么筹资,我们要善于遵从历史,从了解张伯苓历史的专家嘴里,从历史缝隙里把戏扩展。有一场戏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把南开大学炸平了,当时张伯苓在南京开会,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半个月没出来,要变成戏,必须要给他一个外力让他出来,要是写他经过半个月思考重新振作起来,这有啥看头?
我虚构了一个小男孩,前面做了一个铺垫,他妈妈对他说:“孩子,你看到了吗?这是南开大学校长,将来你长大了,妈妈把你送那儿上学。”当张伯苓把自己关起来后,这个小男孩来敲门,对他说,我将来去你那上学行吗?张伯苓愣了一下说,南开大学没了。
小孩就掏出几个硬币给他,说我捐点钱,你再建一个行不行,张伯苓接过钱眼泪都快出来了。这场戏是我编的,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有形的南开炸了,但是无形的南开还在,师生还在,这是真事。作为编剧,我们要找到他从低沉和崩溃转到振奋的那个过程,他未必有这个事,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想通的,但是我们得把他合理化,我们千方百计要找到让人物内心世界外化出来的东西,从历史人物的经历中去抠戏,去找到足以让观众信服他从低谷、崩溃又重新振作起来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