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扬-维尔纳·米勒
翻译:陶小路
人们都在说,自由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它正受到人数不断增加的民粹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的左右夹击。人们说,中间立场无法维系。但是,如果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中间立场受到动摇而濒于崩溃,那么为什么很少有人援引以赛亚·伯林、小亚瑟·施莱辛格、卡尔·波普尔和雷蒙·阿隆这样的伟大的“开放社会”的捍卫者的思想?我们会以为,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会让这些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参与”现在的讨论。但是,虽然他们没有被遗忘,但在当代政治辩论中,你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名字。不过去年(指2017年)有一个奇怪的例外,爱尔兰的财政部长对伯林称赞有加,因为伯林帮助他应对“人们针对公司税收政策提出的要求”(考虑到这位部长给出的古怪的理由,这件事倒是几乎验证了我说的“你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名字”这点)。这当然不是将伯林的思想用于抵抗民粹主义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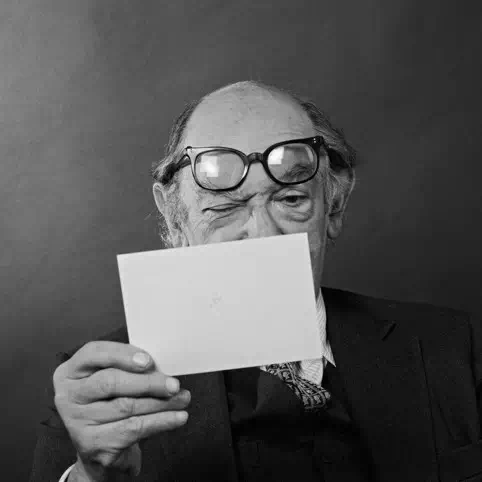
在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能从“冷战自由主义”中借鉴的思想资源有很多。这些思想家经过惨痛的教训之后认识到,这个世界并非注定地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他们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认真地去思考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受到的批判和挑战。但是,施莱辛格在他出版于1949年、颇有影响力的《关键中心》(Vital Center)一书中所概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想,更不是在极左和极右之间简单地找一个中间点。这些思想家试图在20世纪的历史环境中去设想一种有原则性的自由政治。这种有原则性的自由政治与今天那些迷失方向的中间派试图先发制人地采用民粹主义手段截然不同——例如,希拉里呼吁欧洲停止对难民的援助,因为在她看来,移民问题只会对民粹主义者有利。她的潜在想法似乎是,可以通过模仿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来击败他们。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则不那么认为。
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于当下的对话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政治思想各自的宏大叙事之间的冲突(即使冷战不仅仅与政治思想有关)。伯林和阿隆提出过一个广为人知的论断:20世纪的极权主义的乌托邦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民粹主义者没有类似的乌托邦计划,他们不像许多共产主义者那样相信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民粹主义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学说,无论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或者“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宣称自己在政治上的竞争者们腐败、“不老实”,否认竞争者的合法性。
伯林和阿隆的批评在这里不适用,因为民粹主义者不需要去吸引知识分子或者提出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宏大的思想观念。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不是去期望一个完美的未来,而是去想象一个属于同质的、纯粹的“人民”的,只在幻想中存在的过去。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将所有政治问题都归结为归属问题:他们暗示不认同自己对“人民”这个概念的理解的那些公民根本不属于人民;如果某些公民对民粹主义者提出批评,那么这些人很快就会被谴责为叛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án)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同时会攻击“自由派精英”和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

特朗普则宣称反对者是“叛国”、“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在华沙发表的演讲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否对我们的价值观有信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们?”,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冷战处于最紧张时期的发言,但他紧接着又说的一句话才更能说明他的真实想法:“我们对我们的公民是否足够尊重,可以守护好我们的边界?”他描绘出这样一幅世界图景,中东恐怖分子和来自拉丁美洲的人们(虽然成为美国公民,但可能是内敌)一直对真正的美国人构成威胁。

面对极权主义而非民粹主义的威胁,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总是强调多元主义。他们所说的多元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利益的多元化(20世纪中期对民主制度的辩护的基础便是这个意义上的多元主义,民主制度可以让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可以和平地竞争),还包括了人类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作为民主社会特征的“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小亚瑟·施莱辛格语)。如伯林和波普尔这样的思想家强调,一个国家如果要去实现一个以某一套价值观作为基础的乌托邦蓝图,个人权利必然会受到侵害,因为不同的个体所接受的价值观各不相同,而且这些价值观之间往往是不相容的。这种有原则性的多元主义呼吁尊重个人和群体的多样性,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民粹主义者提出的那种单一的“人民”的概念是多么危险。
如施莱辛格这样的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也试图构想出一种“具有战斗力的信仰”来捍卫“关键中间立场”。他们让自己投入到一场有关思想的斗争中,他们认为这种斗争会产生一个附带作用,那就是他们的理想会变得更加清晰。正如伯林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总是对自己说,在一个耶稣会士和一个怀有善意、但是头脑混乱的人之间,我会更欣赏前者。至少前者知道自己在争取和反对什么,而且让自己的斗争武器保持锋利。”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伯林又劝告人们要保持温和,并警告道,对某个政治“信念”做出回应,不一定要通过某种“反对信念”,因为那样做就相当于认为一种狂热思想只能被另一种狂热思想击败。

这两种自由主义立场——渴望通过进行一场“有益的论战”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一种自觉的对温和立场的支持——目前都遇到了问题。由于民粹主义没有一套逻辑连贯的信条,因此也就无从设想一套施莱辛格式的“反对信念”;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应该能弄清楚自己的立场是怎样的,不需要敌人来帮助自己明确立场。另外,只有当你可以合理地论述两个极端同样危险的情况下,中间派或温和立场才会对人有吸引力。右翼民粹主义和在我们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左翼民粹主义之间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两个极端的对称关系。人们可能不同意美国的桑德斯支持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追随者的政策主张,但是这些人都不反对多元主义。他们可能认为应该“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而战”,但是他们并不会把“血统纯粹的人民”这样一种概念作为自己政治行动的基础。(这并不是说任何地方的左翼力量都没有那种内在的反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委内瑞拉灾难性的“21世纪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人们几乎忘记了当施莱辛格为中间立场辩护时,他也在支持非共产主义的、非斯大林主义的左翼(施莱辛格称之为“自由左翼”),而不是在左右翼中间寻找容身之处,或者主张一种精心设计下的左右共存。伯林和波普尔则实际上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对于一个良善社会来说,福利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施莱辛格反对“不负责任的富豪统治的暴政”,并呼吁采取民主手段对经济进行控制。这种立场使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与哈耶克这样的人物区分开来,后者公开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是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的重要精神导师。
如果对温和中间立场的支持是基于某种让人难以信任的“中间主义”,而非基于原则,那么这种支持也就不值得称赞。民粹主义者反对“全球主义”和“开放边界”。但是又有谁真正主张完全开放的边界?即使在今天的学术界,主张实现真正的全球正义和人们的自由流动也是少数派。当波普尔为“开放社会”辩护时,他反对的是教条上的不宽容以及思维上的部落主义;这是个认识论上的观点,而不是关于移民政策的观点:他希望人们有开放的思想,不是主张自由出入的领土。(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倾向于接纳难民,他们所主张的也是自由主义,一种更早些时候从宽宏大度意义上讲的自由主义。)
在所有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伯林似乎是最能认同民粹主义就民族认同议题进行的文化战争的一位。毕竟,伯林终其一生都认同犹太复国主义,对民族主义有着极大的同情。他总是强调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使用“意识受到伤害之状态”这样的说法来解释自18世纪以来的许多意识形态驱动的过激行为。他是在描述一种不被认可的感觉,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重视的遭际,因为达不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所假定的标准而产生的感受。在这个“乡下人的悲歌”【这个说法来自2016年出版的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一书——译者注】的时代,伯林对政治不满的心理来源的敏感可能特别有价值。
在当代民粹主义评论中,人们像是条件反射性地经常使用诸如“愤怒”和“怨恨”之类的词语,但是这种置身事外的“诊断意见”有一种俯视众生的优越感。这样一些表达还有可能将情感因素完全与理性剥离,从而让严肃的辩论无从进行;而事实上,情感与理性从来都不可分隔。毕竟,人们的愤怒情绪背后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主要通过心理视角来看待他们的不满情绪,我们就不太可能去直接问他们这些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些原因是怎么来的。另一个危险就是过度的同理心,特别是在没有与“人民”有过实际接触的情况下。直接去了解人们的生活经历是一回事;完全把煽动民意者(无论这些人是政治家还是脱口秀名嘴)对这种经历的描述当真则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在努力去理解一件事情时,我们可能会变得过于善解人意【伯林称其为“设身处地地体认”(Einfühlen),一种去认同他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过程】,会导致“全部理解就是全部原谅”的问题。那些声称完全理解所谓“普通民众”的意愿的人们【德国人有时称这些人为“民粹主义同情者”(Populismusversteher)】所作出的种种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会持续非常久。许多人会直接认为民粹主义者揭示了我们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或早或晚,其他政治力量也会将这些似是而非的“真相”作为自己开展政治行动的基础,例如,据说工薪阶层就是厌恶外国人和移民。
今天的自由主义在去努力重新确立其价值的过程中,必须不能仅仅是一种条件反射性的反特朗普主义,也不能是基于对左、右翼民粹主义存在对等关系这个错误假设之上的,对中间立场的辩护。本着伯林和其他冷战时期知识分子倡导的自我批判精神,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原则是怎样的,放弃1989年之后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抱有的幻想:历史进步是必然的。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在民主程序之下的冲突的合法性。用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认为冲突是对自由的保障。但除了已有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间立场意味着稍稍考虑到左右两边的主张——还需要运用想象力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定义冲突,同时忠于施莱辛格所谓的“人道尊严之精神”。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全灵学院院士,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高级访问院士,并在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以院士身份进行博士后研究,是欧洲年轻一代思想家中影响较大也较为活跃的翘楚人物。著有《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宪政爱国主义》、《什么是民粹主义?》等。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2018年11月26日“NYR Daily”栏目,《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