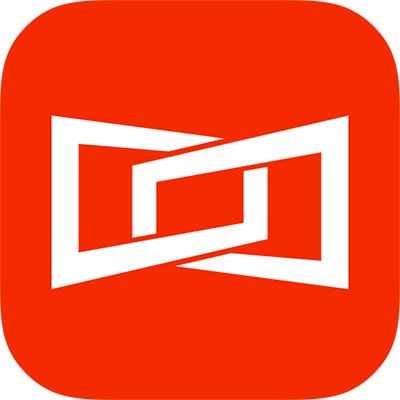袁香芹,南都观察“未来的事”特约体验官
出了沧州高铁站,我钻进了一辆开往客运站的公交车,想往投币箱里塞钱,发现钱的入口被一个红色的卡子挡住了。“不要钱,直接坐。”司机说。
“为什么不要钱呢?”我问。
“从11月15日到第二年3月15日,全城所有公交车都不要钱。”车开动了,发动机的声音有些大,司机很专注,我没有再问下去。
答案是从大巴车上的一个老爷爷那儿听到的。大巴车往河间开,中途经过西蔡村村口,我会在那儿下车,再有大约5公里的路程,到村里去参加一个关于“农村垃圾分类”的经验分享和培训会。
老爷爷说:“这是第三年了,年年都是这个时间段,公交车都不收钱,就是让这些人少开私家车,治理雾霾,减少污染。这就是咱们国家的优越性。现在沧州好多公交车都是用电的,便宜又环保。”
到村子里时已经入夜,很明显能闻到空气中因为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硫的味道。户外很冷,我裹了一顶包住半个脑袋的厚帽子,依然很冷。借着村民屋子里透出来的光,能看到正在排气的烟囱。
屋子里暖和了一些,村子里全都是大平房,屋顶得有三米高,所以即使烧了暖气,屋里也不是特别暖和。我和另外两个一起前来学习的人睡在老乡家的一个大炕上。我想象中的大炕会像“睡在炉子上”一样的热,但现实里,仅仅只是不冷而已。
早上发现老乡家炉子里的火已经熄了,暖气管还有些余温。出门去院子另一角的旱厕,旱厕由红砖和石棉瓦简易搭建,没有门,和室外无异。室外零下五六度,我滋了泡尿,顿时云山雾绕。村里大多数烟囱都暂时休息了,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味道弱了很多。
大约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到了培训的现场——村委的一个大会议室里。路上能看到零星的一些垃圾,烟盒、零食袋之类的。
会议室的桌凳像高中教室的布局一样排列,坐了四十来个人,除了主办方以及邀请来分享的专家、实践者,还有从山东、甘肃等农村来学习经验的村支书和同事,从高校来的老师和学生,做环保的NGO从业者,想在垃圾分类领域把公司做上市并“超越马云”的创业者……以及我,单纯想看看农村的垃圾分类到底能做成什么样。
上午的分享讲了很多垃圾分类的历史,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实践,有的挺有意思,大部分都挺无聊。但为了写一篇稿子交差完成工作,我还是认认真真记了笔记。
我最期待的环节其实是看村子里到底是怎么做垃圾分类的。到了下午两点,开始了。
在这个华北平原的村子里,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收垃圾啦收垃圾啦,大家把分好类的垃圾提出来分类投放……收垃圾啦收垃圾啦,大家把分好类的垃圾提出来分类投放……
环卫工人驾着一辆装了四个垃圾桶的三轮车出现了,三轮车的设计很适合装垃圾桶,后厢的底架很低,放上垃圾桶之后,桶的最高处刚好比绝大多数成年人胸口的位置略低,往里倒垃圾时不会很吃力。
可是并没有人来“投放”垃圾。大部分村民家的大门都紧闭着,但是有的门口放着两个垃圾桶,一个用来装“厨余垃圾”,一个装“其他垃圾”。环卫工人就把两个小桶里的垃圾分别倒进不同的大桶,有时候装厨余垃圾的桶里会有一些塑料袋,他会把塑料袋挑出来,扔到装其他垃圾的大桶里。

▲ 一场众人围观的“垃圾分类回收”过程。 南都观察
三轮车沿着村里的路往前开,停停走走,再次停下来时,环卫工人把村民装厨余垃圾的桶清空了,站在一边的村民请他再等等,拿着空桶又回家装了满满一桶菜梆子,这样反复装了两次,一共倒了三桶。
再往前,有个垃圾桶被狗扒翻了,小土狗把头钻进桶里翻东西,垃圾被翻得四散,有的被风吹远。赶走小狗,环卫工人揽起地上的大部分垃圾,连着小桶里的一起清理走了。
除了两个桶之外,有的村民门口还放着一个瓷盆,里面装着煤灰,但是环卫工人并没有管它。
“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处理煤灰,它很重,倒的时候灰很大。”这次培训会的组织者陈立雯说。煤灰既不属于可以用来堆肥的“厨余垃圾”,也没有必要像“其他垃圾”那样被运走填埋。
在另一家门口,陈立雯赶在环卫工人之前先去看了看桶里装的东西,她要检查这家人这次把垃圾分好类没有。“这家人之前一直分不好,有时候厨余垃圾里还有塑料那些东西。要提醒他们很多次。”她说。这次分得很好。
但路上还是能看到零星的垃圾,也有那种直接丢在小路路口的装满垃圾的塑料袋。陈立雯说,这些需要整体打扫才行,环卫工人目前在做的是将村民分好类的垃圾分别回收,以便处理。

▲ 不听劝的部分村民,依然留了些垃圾在桶外。 南都观察
环卫工人每天都会来收垃圾,一般从下午两点忙到四点,有时候垃圾多,结束的时间会晚点。以穿过村里的主干道为界,村子被分为两个区域,每天清理一个区域,每家人的垃圾都能在两天内被处理掉。
2017年6月,陈立雯开始在多个村庄里做垃圾分类,是公益组织“零废弃村落”的发起人。在西蔡村,经过一些前期准备——比如给村民发桶(两个垃圾桶,分别用来装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村民沟通等——垃圾分类于10月28日正式启动。在这之前,她已经在河北涞水南峪村、浙江金华马宅村实践过垃圾分类,有了一些经验。其实她还是西蔡村的村民,这次是直接“在家办公”。
虽然每家人都发了两个桶,装厨余垃圾的那一只还专门配了个盖子,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关住臭味,但村里用“特供桶”的并不普遍,更常见的反而是用过的油漆桶、旧水桶等。发的新桶干净又结实,村民直接用来装水或者其他东西了。
走到村旁一个大姓家族的坟地,还是能看到里面四散的零零散散的垃圾,陈立雯说那是过去几年积累的旧账,他们已经清理过一次了,这已经算比较干净了。
坟地不远处有户人家,灰墙上用白色的油漆工整的写着“此房后严禁倒任何垃圾”,“提升大气质量,保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我以为是村里或者乡上的宣传部门专门刷的环保标语,结果被告知这些标语都是这家人自己刷的,过去很多村民都往他家附近的空地扔垃圾,他们深受其扰。

▲ 村民自制的“提升大气质量,保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 南都观察
村子的边缘有一处空地,一半露天,一半搭了防雨棚,露天的区域堆了八堆已经发黑的厨余垃圾,它们是西蔡村自10月28日正式启动垃圾分类以来的成果,在这里完成自然堆肥之后,可以直接以有机肥料的形式回到土地。空地上还铺了一层砖,没有糊水泥,因为都是厨余垃圾和秸秆、菜梆等,堆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废液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可以直接下渗。而且土地没有做硬化,将来如果要更改堆肥的地点,直接撤走那一层砖就行。

▲ 村旁用于堆肥的空地,冬天少雨,直接堆在了雨棚外。 南都观察
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只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其他垃圾”会去到哪里呢?
得到的回答是,在过去的农村,因为生产、生活几乎全都可以不靠外部资源,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比如秋天的收获也包括了开春耕种时的种子,养猪既为了过年也为了有机肥,所以不会专门去买种子、化肥、农药等,也就不会产生不可降解的垃圾。包装复杂的商品也没有全面进入农村,所以基本上可以实现“垃圾不出村”。
但现在,过去传统的农业系统的知识体系无法解决新的塑料垃圾的问题,加上施用化肥,也不再依赖“农家肥”或者堆肥了,“垃圾围村”的现象开始全面突显。有的地区的垃圾越堆越多,有的则进入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进入填埋场或者焚烧厂。但农村垃圾有一个特点,可自然降解的垃圾其实特别多,它们本来完全可以留在本村并且被妥善解决,只是由于没有做好源头的分类,和塑料等垃圾混在了一起,变成了新的麻烦。
于是农村的垃圾也不得不一股脑地进入整个本就混乱的垃圾处理系统,当它们进入县一级的填埋场、焚烧厂,迅速增加的垃圾量会给这些原本为城市设计的处理终端带来巨大压力,有的地区的垃圾处理量甚至会猛增三倍,处理能力远远不够。而且没有做好“干湿分类”的垃圾进入焚烧厂之后,湿度一旦过大,在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危害巨大的二恶英。
所以“零废弃村落”的目标之一就是“垃圾不出村”,起码不让那些可堆肥、可降解的垃圾出村。至于更精细的垃圾分类,比如再细分为纸张、塑料、金属等等,因为终端处理系统仍不完善,当下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垃圾分类的困境——终端不完善,即使居民们在前端做好了分类,最后绝大多数垃圾还是进了填埋场或者焚烧厂。对资源和热情的双重浪费。
这似乎成了做“垃圾分类”工作的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整个回收系统将解决途径过多关注在“填埋”“焚烧”这样看似“眼不见心不烦”的方式上,而忽略了在源头的减量和前端的分类上。
于是投放更多的大垃圾桶——不管怎么样,先收起来再说。
但投放过多的垃圾桶反而不利于垃圾的分类回收,因为居民普遍还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缺乏监督甚至惩罚,投放数量再多、颜色再丰富多彩的垃圾桶也无济于事。垃圾分类需要的恰恰是更少的大垃圾桶——不能再提供24小时随时都能投放垃圾的生活环境,因为这样不利于观察居民分类投放的情况。要么在他们来扔垃圾的当时就提醒,要么在合适的时间去敲门沟通。所以每家人需要至少两个桶,需要他们自己分类,在固定的时间段里投放垃圾。只有看到每家每户的分类情况,及时提醒,分类工作才会做得更好。

▲ “零废弃村落”发给村民的两个桶,“厨余垃圾”桶还配有盖子,用于防臭、挡狗。 南都观察
两个桶、两种分类也有利于简化居民的分类——先把厨余分出来,干湿分类,就已经很好了,在后续的人工或者机器分类过程中,没有混合厨余垃圾的“其他垃圾”会被更高效的处理好。在农村,村民们很清楚哪些垃圾是可以用来堆肥的,学习得很快,西蔡村只用不到一个月,就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明白了垃圾分类的要求。
在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有关于垃圾分类的立法,结合长期的公民环境教育,以及“按重量收取回收费用”等经济调控手段,厨余垃圾在最初就被“挑选”出来,其他各种可再利用的垃圾也可以被有针对性的回收处理,最终进入焚烧厂的只有很少一部分。
“可回收”“可降解”标志也常常带有欺骗,比如可回收的一次性纸杯,被用于各种公共赛事和场合,但它是由纸和薄膜组成,必须经过专门的拆分之后,才能进入回收系统。而我们常常把用过的一次性纸杯扔进垃圾筐,和其他各种垃圾混合在一起,从源头上阻断了它进入回收系统的机会。比如“可生物降解”的饭盒,实验者将其埋入土中,到所谓的“降解周期”之后再挖出来,发现它只是解体了,并没有被降解,它的降解需要进入到工业化的处理设施中。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这些看似“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问题,贴上好看的标签仅仅只是缓解了部分人的焦虑和愧意,它们依然在环境中慢慢积累,没有被消化掉。
因为太过关注村里的垃圾,走路都在低头观察,我还在地上捡了一块钱。除了捡钱不交公,这次我还犯了一个错,一直把卫生纸往“厨余垃圾”的桶里扔,到最后一刻,快出村时,我才偶然听到,用过的卫生纸应该扔在“其他垃圾”里。

▲ 地上捡到一块钱,抻一抻,压一压,回城之后好坐公交。 袁香芹
我羞愧极了,感觉对不起村旁那几堆正在成熟的堆肥。随后我坐着大巴车回到了熟悉的城里,这里有更多的垃圾桶,此前的我不用考虑该把用过的饮料瓶和卫生纸扔在哪个垃圾桶里,因为它们最后反正都会混在一起,去到同一个目的地。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这样了。我又回到了北京,发现北京在这方面连河北的一个农村都比不上。
*本文为南都观察在“农村垃圾分类经验和教训分享会”上的部分学习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