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思航
拉斯·冯·提尔是电影节的常客,也是影迷们心目中的异类。他的每一次出现,几乎必将伴随着一个大新闻。
有时候,这个大新闻不仅仅只是关乎他的电影,也可能包括他那不同寻常的举动。2011年,拉斯·冯·提尔因其关于纳粹与犹太人的不当言论,而遭到了戛纳的长期“封杀”。

然而,在时隔七年之后,他又带着自己的新作《此房是我造》回到了戛纳。无论是他重返戛纳本身,还是他这部不负众望的新作,都在电影界刮起了一阵旋风。何谓“不负众望”?这当然是指,《此房是我造》依然继承了着冯·提尔式的超重口味,甚至更胜一筹。
但是,如果仅仅是重口味,那么这也不过只是一部B级片罢了。拉斯·冯·提尔之所以能够位列世界艺术电影大师之林,就是因为他将这些“反人类”的内容,框在复杂而精巧的结构之中,并通过这样的作品,来体认这个星球上最深重的罪孽。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杰克(马特·狄龙饰)是一位患有强迫症的工程师,但他同时也是“登峰造极”的变态杀人狂。起初,他驾车在路上遇到一位因为汽车报废,被困公路的女人(乌玛·瑟曼饰)。

在帮她求助修理工的路程中,杰克逐渐因为她烦人、毒舌的碎碎念而失去耐心,用千斤顶将其杀死。后来,他迷上了杀人,并将每一次杀人当作完成一场艺术品,他屠杀受害者、玩弄尸体的手段也越来越变态、残暴,他的强迫症也似乎被渐渐治好了……

这篇文章将分析这部影片独特的叙事结构。事实上,《此房是我造》的形式,是与内容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影片的形式甚至决定了它的高度。
在这部影片中,拉斯·冯·提尔采取了一种复合式的叙事结构。同时,它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几乎是曝露在外的。
首先,我们从《此房是我造》的片名中,就可以找到这一结构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此房是我造》的英文原名是“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意为“杰克所造的房子”。它来源于一首英国民谣《这是杰克造的那所房子》(This Is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以下是这首民谣的前三句:
意为:“这是杰克造的那所房子;这是放在杰克造的那所房子里的麦芽;这是吃掉放在杰克造的那所房子里的麦芽的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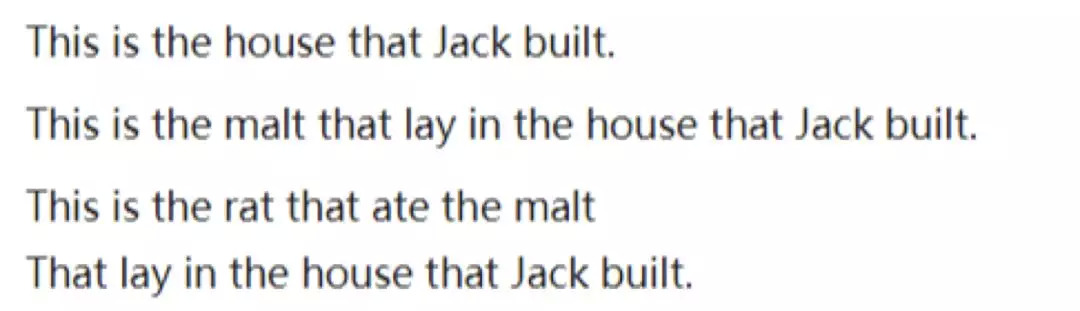
这首民谣通过套层结构的从句,将不同的信息组合在一起。其实它所讲的并不是杰克的房子的故事,而是这些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第三句中,“老鼠”的元素与“杰克”的元素之间的联结,已经非常脆弱了。随着从句不断叠加,新元素与老元素之间的联结,将变得越来越薄弱。
拉斯·冯·提尔在他的长片处女作《犯罪元素》中,就已经用到了这首民谣。而在《此房是我造》这部以此为名的影片中,他更是直接采用了这首民谣的叙事方法。

杰克有一个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目标——造房子。他用我们看来非常牵强的方式:教堂建筑与艺术的材料,将建筑与杀人联系在一起。而后,他又通过“诗歌”、“政治”等借口,开展他的残酷屠杀。
这些借口,与不同元素之间的连接,随着影片的发展,就变得像那首民谣中的从句引导词“that”那样,变得越来越脆弱、没有意义。我们知道杰克想要造一座房子,但我们并不知晓这一目标的来龙去脉。我们看到他不断地杀人,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如何遇上、选中这些受害者的。
从某种角度来看,他部分地继承了这首传统民谣的手法,但是,这部影片看起来并不像民谣那样简易、散乱。这是因为,他还从另一个地方偷了师:毫无疑问,那就是但丁的《神曲》。

无论是从始至终与杰克对话的“维吉尔”(在《神曲》中,维吉尔正是但丁的引路人),还是戏仿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名作《但丁的渡舟》的油画般的镜头,都对这部经典作品进行了明确的指涉。
《神曲》的叙事结构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其一就是元叙事。除了《神曲》故事的主线之外,还穿插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其他故事,每个故事都包含着它们自己特定的文本系统。
而在《此房是我造》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大量的元叙事、元影像。我们可以看到拉斯·冯·提尔其他影片的重返,可以看到著名巴赫演奏家格伦·古尔德弹奏钢琴的影像,可以看到对威廉·布莱克的诗歌《老虎》与《羔羊》的重新解读。

《神曲》的第二个特点,是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交错。我们看到但丁游历三界的时间主线,被划分明确的空间场景所斩断。这些不同的空间是彼此独立的,我们甚至可以在某个空间中,看到不同时间线索的并置。
虽然电影与文学不同,本身就自然而然地携带着这种叙事效果。但在《此房是我造》末尾的地狱段落中,我们看到杰克在相同的银幕空间中,凝望着他童年记忆中的刈麦场景,这直接回应了《神曲》中的时空效果。

《神曲》叙事结构的这些特征,在原作中同化了刹那与永恒,使人类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共存。但在《此房是我造》中,由于民谣结构的存在,它们反而加深了我们的绝望感。
如果说,拉斯·冯·提尔在民谣结构中,安放的是实质性元素的话,那么他利用《神曲》结构中安放的就是类似于联结物、从句引导词的元素。
如此说来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继续分析我们在阐述民谣形式时提到的例子。随着影片的发展,所谓艺术与谋杀之间的关系,显得越来越薄弱,但他仍旧采用着《神曲》式的元叙事,将那些外在于影片的元素,一股脑地插入其中。

于是,原本只是显得有些稀薄、无意义的联结,忽然显得荒诞、可笑起来。拉斯·冯·提尔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将稀松平常的英国民谣,与贡献卓著的文学经典融合在一起。
其中最令人惊异的一点在于,如果我们要用“荒诞可笑”来描述这两者中的一种,大多数人无疑会选择前者。而在《此房是我造》中,《神曲》的结构特征,反而是创造荒诞效果的部分。
在他那些象征意味浓厚的重口味段落中,“建房子”或许已经成为宗教、政治、战争、艺术乃至人类人道主义目标的隐喻。
但是,《此房是我造》最为“重口味”的,或许是他这种颠覆经典的叙事结构。它暗示着人类将永远迂回、永远离题;永远隔着一层玻璃,无法接触眼前的彼岸;永远会在通往希望的陡崖上坠落,堕入最深的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