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金宇澄参加上海作协举办的一个青年创作班,与许多青年作家一起前往宁波的山间采风。创作班要求参与者在结束时各交一篇小说,一帮只顾着爬山喝酒的年轻人半焦虑半无所谓地谈起孙甘露早就写好了、谁谁又写了一篇还不错的小说云云。金宇澄原本毫无头绪心事重重,直到有天听别人开玩笑地说到棺材,他突然灵光乍现,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三点一气呵成地写出了被创作班老师评价为“创作班最好的小说之一”的《风中鸟》。
那灵感一瞬点中的是金宇澄记忆中的少年时代,文思就此淙淙而出。1969年,17岁的金宇澄“知青下乡”远赴黑龙江农场务农,直到1977年才回到上海。在黑龙江,他做过一段时间木匠,见惯了有人死后木匠加班赶做棺材的场面,小说里记录的正是他见证的一段往事:一个濒死的病人被意外抢救回来,棺材用不着了,搁在木匠房门口风吹雨打日渐残破,但农场上的老人都在暗自盯着这口棺材,因为“谁先死谁就能用这口棺材”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金宇澄甚至还看到过一个老人半夜里蹲在棺材附近。在小说的结尾,有两个人都处在弥留之际,但医生发现谁都死不了。棺材的归属悬而未决,故事却结束了。
由世纪文景出版的金宇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方岛》《轻寒》《碗》在上海书展正式亮相,其中《方岛》一书收录了上述这个故事。作为文景艺文季的首场活动,金宇澄与专栏作者顾文豪做客浦东新区陆家嘴图书馆,以“如何书写记忆”为题展开对谈。金宇澄打开记忆的阀门,与听众分享了三本新书背后更多他曾经经历过的故事。
同许多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人一样,金宇澄见证了时代拨弄下的人生百态,他认为在这样的大时代中当事人是痛苦的,但对于从事文学的人来说也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们能把知道的东西写下来。他坦言年轻时的经历对自己的创作有巨大影响,甚至认为作家的最大动力就是他的少年时代。金宇澄鼓励有志于从事写作的年轻人从非虚构写作开始,发掘身边的故事,沉下心来获取滋养。

“东北版的金宇澄”:作家的最大动力就是他的少年时代
金宇澄透露,因为写作中运用了大量东北方言,早年程德培先生曾误认为他是地道的东北人,在1980年代末二人见面时,这个误会才解开。对东北的人与事如此活灵活现的描述,来自金宇澄的血肉经验,他在对谈现场与观众分享了一个他记录在《碗》中的亲历事件。在黑龙江农场,一位粤籍老人临死前心心念念想喝故乡的甘蔗水,“我”骑着马,冒着风雪为他送去一碗白糖勾兑的糖水。糖水甫一送到,老人就过世了。走出医院时,“我”发现马儿脱了缰早已跑远,雪一直下。这个故事一直在金宇澄的心中盘桓,他又将这种对人生无常的无力感付诸笔端。金宇澄认为,文字记录的其实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它不会产生效益,但文学的功能就像是玻璃罩一样,成为一种时间容器,保存这些珍贵片段。

在黑龙江的知青生活为日后的金宇澄带来了无尽的写作灵感。“一个作者没有更多的可能性,给作者的最大的动力就是他的少年时代,他绕不出去这一块,绕出去这一块的都是他陌生的。你必须写你最熟悉的东西才能跟别人有分别,因为是你自己得到的经验。”他说。
金宇澄称,“暧昧”是他写作的永恒主题,即人与人的关系“不应该把它写得特别明白”,应该有所保留。在他看来,这吻合了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们在生活中接受的信息量极大,见多识广,已不再像上一辈读者那样需要详尽得面面俱到的故事了,“现在你越写得详细,(读者)可能越早会判断到它有问题,因为(读者)有经验”。
另一方面,这种“暧昧”还来自金宇澄在写作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动荡年代、我们上一辈的(故事),在我的几本书里都有。这个事情是人算不如天算,你进入到一定的深度,就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相信,没法计划自己能做什么事。在大时代里面,只有我们创作文学的人能得到一些好处,能够把知道的这些东西写出来,除此之外,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事。”
农场的生活艰苦酷烈,与笔友的通信令金宇澄得到外界的些许信息,获得片刻的慰藉。其中一位笔友曾告诉他:“你的信写得挺好的,你可以写小说。”这成了他动笔写作的最初动力。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宇澄的东北经验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故乡上海的怀恋,并在日后促使他用《繁花》记录下自己记忆中的上海。
注重细节:小说的语言是第一位的,内容次之
和《方岛》《碗》不同,《轻寒》是一个关于抗战时期江南水乡的故事。顾文豪介绍称,《方岛》《碗》中收录的故事有许多片段曾在金宇澄的散文作品中出现过,而《轻寒》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作品,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电影的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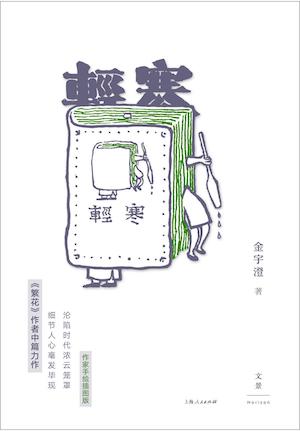
金宇澄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8
金宇澄回应表示,《轻寒》是他于1991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一个四万多字的中篇,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像电影但却很难被拍成电影的故事。为了写好这个故事,金宇澄仔细地研究了江南地区风土人情的方方面面,并融入了从父亲那里听说的、在抗战时期曾经发生在老家吴江的前尘往事。在他看来,小说中用种种细节勾连起的故事不似一般小说或电影那般大开大合清晰明了,但用细节给予读者无穷的回味正是他最喜欢的写作手法,因此无论是《轻寒》还是后来的《繁花》,都没有什么大框架或史诗色彩,而是题材比较小的、接近平民百姓的内容。
对细节的把握和语言的运用息息相关。金宇澄认为,小说最关键的要素就是语言,“语言是第一位的,不是内容——内容你要等差不多读完才知道好不好,哪怕这个小说不好,但是语言好的话,也是合适的。”
金宇澄继而对1990年代起小说影视化改编热潮对小说写作的影响表示忧虑。他认为,由于影视剧本强调故事情节而非语言,导致目前的一些小说家不重视修辞,只关注故事本身,“但我个人认为影视(改编)是非常次要的一个要求,小说一定要有自己的要求。”
“我们现在流行的语言方式就是更加专注使用一种流畅的、浅显的、明快的语言,但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他笑称,《繁花》之所以写得那么繁琐,是因为他在动笔之前读到一个汉学家说自己现在翻译中国小说不用查字典,受到了很大刺激。“我在写《繁花》的时候,尤其是修订它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谁要翻译我的这个小说,我要他/她把中国字典翻烂!”
青年写作:年轻人可以从寻找上一辈人的故事开始
对谈结束后,金宇澄就听众提问做出回应。在被问及当下年轻人应该如何在平淡的生活中挖掘写作素材时,金宇澄再度强调了从自身经验出发写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写作需要持之以恒的积淀,如果年轻人的积淀还不够,可以从非虚构写作开始,深入调查某一事件,从中发现人间社会的复杂性。
他认为年轻写作者可以先从观察、思考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做起,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也能够诞生非常好的作品。他举例称,沈从文在上海的两年多时间里十分不喜那里的大都市氛围,于是回到北京后写出了激动人心的《边城》。“年轻人实际上唯一缺少了一点怀旧,但怀旧不构成写作的全部。这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逐渐了解的过程,但是很多人有表达能力,或者突然找到了什么(素材),会非常好地表达出来。”
金宇澄的另外一个建议是,找到上一辈人去了解他们的故事。“这一代年轻人,因为是独生子女,从小就被父母笼罩,根本不会关心父辈的事情。不像我这一代人,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我,但是我始终关注父母的情况。这一代年轻人的朋友都是和他们差不多的人,但其实父辈是你打开写作之门最好的钥匙。”金宇澄回忆道,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印象最深的熟人就是他朋友的长辈,是他们令他感受到了旧上海的得体和余裕,“到朋友家去,他的妈妈或者外婆会把我当成男人,给你泡茶,给你抽烟,烟灰缸和热毛巾递过来,坐下来陪你聊天。虽然说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现在这种场景是找不到了。”
“高尔基曾说过一句话:‘我的信仰是从皮肉上熬出来的。’我在想,我也是这样吧,写作和你的生活经验非常有关系。面对社会种种的问题,可能只有写作才能够得到某种解脱。一个不写作的人,把故事告诉作家朋友,这个是最好的。这本身都是一些人生的碎片,但是你仔细看,它们都有光彩。”金宇澄说。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