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题为《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的文章在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里广泛传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章说的是深圳市宝安区一个名叫“华联城市全景”的高档小区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今年6月,为了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优先保障优抚对象和残疾人住房需求的政策,该小区打算将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中的24套配租给登记在册的优抚和残疾人家庭。7月16日,宝安区住建局公示了最终的配租方案,将有41户符合标准的家庭来认租这24套房源,其中17户的备注信息中显示“精神类残疾”,残障等级从一级到四级不等,最终的看房日期定在7月18日。此消息一经传开,就在业主中间炸开了锅。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向住建局提出抗议,并在小区门口拉起横幅抗议,条幅上书:“保障了他们的住房权,谁来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一位ID为“张玉华”的业主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一则“求助帖”被截图并大量转载,在帖子里,他(她)自称是一个“走投无路、急需帮助的有产者”,自己所在的高档小区“房价7万5,现在住进了17个精神病患者”。“张玉华”表示,小区内都是商品房,只有两栋楼用围墙与小区隔开,是政府搞的公租房,之前业主们听说这个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现在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安排进了17户精神残障人士。他(她)认为,政府此举损害了“靠自己辛苦工作买房的业主”的利益,也无法保障小区里孩子的安全,并强调,业主们的抗议不是在制造“阶级矛盾”,制造阶级矛盾的是地方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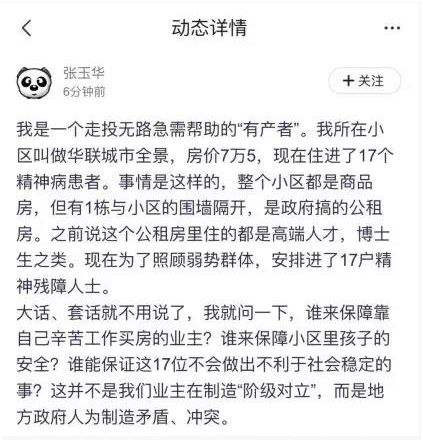
最终,住建局临时取消了原定于7月18日的看房安排。此外,由于《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一文将这17户家庭的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前14位以及儿童的残疾等级等)全部泄露了出来,许多原本符合配租条件的家庭也决定放弃选房。后来,通过媒体报道,许多人才得知,这17户“精神类残疾”家庭中有15户是自闭症儿童家庭,孩子年龄大多在6-12岁之间。
这一细节导致该事件在网络上进一步发酵。在公众的想象中,自闭症儿童是智商超群或者有着特殊艺术天赋的“折翼天使”,与“会发疯伤人的精神病人”这一刻板印象反差极大,舆论纷纷转向指责小区业主自私、缺乏同情心。有业主表示,他们一开始并不清楚可能入住的“精神类残疾人士”是自闭症患者;但也有人认为,业主们的集体反对行为与精神残疾的类别无关,实际上是担心开放给弱势群体的公租房会影响这一高档小区的房价。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讨论的,不是对于自闭症或其他精神疾病(残疾)公众教育缺乏的问题,而是作为一起封闭小区业主的“维权事件”,它究竟反映了今天中国城市中产对生活怎样的想象与恐惧。一方面,是对家——以及作为家的延伸的封闭小区——的想象,将之想象为一个可以提供物质享受、标识社会地位、体现阶级审美的“私人天堂”,家是避风港,是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最后的圣土;另一方面,对家的美好想象也伴随着对家以外的世界的恐惧、厌恶和回避,包括工作、公共生活,也包括千千万万的“他者”。因此,占有的另一面是驱逐,享受的另一面是忍耐,悉心呵护的另一面是漠不关心,甚至是随意践踏。这一墙内墙外、公私之间的严重割裂,造就了今天中国都市生活的独特景观,也形塑了雄心勃勃又焦虑不安的中国中产。
封闭小区的空间政治:“安全”的本质是阶级区隔?
根据业主的描述,华联城市全景花园小区(以下简称“全景花园”)是一个高档商品房小区,那么这两栋公租房和小区里的商品房又是什么关系呢?长期关注特殊需要儿童的公众号“大米和小米”通过调查发现,全景花园是一个旧改项目,在商品房之外,该项目还配建公共租赁住房374套,已分配出去350套,剩余24套,集中在两栋楼里。这两栋楼与小区主体的商品房之间用一道围墙隔开,并单独管理,与小区主体的公共面积是一条内部道路,而公租房的住户如果想要进入小区花园,则需要从小区外面或者地下车库绕行。
“大米与小米”援引《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作为商品住宅配建的保障房,像全景花园里的两栋楼这样被墙隔开、独门独栋的“特殊待遇”,在深圳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但2017年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深圳市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配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住户可与商品房业主共享小区配套设施,并执行统一的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开发商不得在人才/保障性住房与商品住房之间涉及围墙,也不得有其他类似的歧视性措施。
全景花园的情况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商品房的开发商和业主几乎是在封闭小区的内部又建起了一个封闭小区。封闭小区(gated community)的话题曾在2016年引发热议,当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逐步打开封闭小区”作为政策导向出现在政府文件中,触碰到了许多封闭小区业主的神经。
两年过去了,兴建封闭小区的步伐似乎并没有放缓,更不要说打开已建成的封闭小区,关于封闭小区的争论似乎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深圳全景花园事件中,舆论似乎更倾向于关注对自闭症的污名和歧视问题,而忽略了这其实是发生在中国式封闭小区中的一次典型的“业主维权”事件。
所谓的封闭小区就是“有出入门禁的住宅区”,小区里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其实是私有性质的,只有业主可以进入和使用。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和发展经济学教授伟仕达(Christopher Webster)认为,封闭小区不仅是一种带有明确排他性的空间形式,它还意味着一种与政府主导的城市治理模式不同的,以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主之间的契约为主导的模式,契约包括一个通用的行为准则(类似“业主公约”),它规定了业主对小区管理所负有的集体责任,这就为业主在封闭小区内行使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提供了依据。

封闭小区在20世纪末从北美兴起,很快被复制到全球各地。早在21世纪初,封闭小区就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领域内的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学界对这种新兴的空间现象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这是后现代城市空间碎片化的典型表征,它源于对城市基础设施网络排他的使用权,并最终导致社会内部的分崩离析;另一些人则认为,封闭小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构筑起了一个“俱乐部领域”(club realm),其中共享的集体消费品(介于公有物和私有物之间)——即封闭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是作为房子的搭卖品(tie-in)提供给消费者的,因此,封闭小区可以被视为一种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因为这里的公共服务是由市场定价的。
在中国,尽管从空间形式的角度上看,四合院和单位大院都可以算是封闭小区,但作为一种城市治理模式的封闭小区则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房所有权和城市治理改革才开始出现的。由于人们的支付能力(收入)、社会阶层和消费需求的日益分化,在中国的城市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也从地方政府和国有单位,逐渐转移到了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手中。因此,在2016年关于封闭小区的讨论甚嚣尘上之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土木建筑学院教授赵燕菁曾为《澎湃新闻·市政厅》撰文称,围墙的本质是公共服务的落差,只要存在公共服务的落差,就必然存在围墙,只是有些围墙有形,有些则无形。
然而,这种论调未免将“围墙”太过自然化、中立化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围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不仅是收入和偏好差异的一种自然结果,它还是中产阶级小心经营的一种空间政治。人类学家张骊在对昆明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提出了“阶级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class)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封闭小区在城市中产身份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张骊认为,商品房与封闭小区内的私人生活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使他们所追求的空间上的私密、文化上的区隔和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生活方式得以着陆。
同时,这一空间政治还包括着对中产以下阶级的排斥和驱逐。许多研究都显示,封闭小区的业主对所谓“安全”的理解,不仅仅是远离犯罪,而是一种清晰的社会边界,一种稳定而同质化的人口构成。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教授鲍存彪在对上海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发现,封闭小区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他者化”(moral othering),通过将他们刻画为“不文明的、肮脏的和危险的”,来强化一种“道德空间秩序”。

在全景花园的例子中,这种“道德空间秩序”展露无遗。业主“张玉华”在“求助帖”中提到,最初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小区的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因此并没有业主抗议,而在听说将有“17户精神残障人士”入住的时候,业主们纷纷沉不住气了。换言之,公租房分为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类,前者针对的是城市引进的高端人才,后者则针对的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封闭小区里的中产业主们可以接纳前者却一定要赶走后者,理由是“孩子的安全”、“社会的稳定”。这其中当然有社会大环境污名化“精神残疾人士”、将其粗暴地想象成行为不受控制、有暴力倾向的“疯子”的因素,但正如上文所言,所谓的“安全”并不是一个犯罪统计学意义上的客观指标,它其实更接近于一种主观感受,而这种“安全感”所依赖的是一个阶级同质化、不存在“偏离”(deviances)的环境。
进一步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士提供保障性住房,对于城市整体的治安和稳定来说是好是坏,无需赘言。最近半年多来,接二连三发生的报复社会性质的暴力事件(而且这些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孩子)足以说明,这些因生计无着而绝望愤怒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边缘人群,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远比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要危险得多。请注意,这里我们讨论的对象并不是个体,也不是个案,我们讨论的是一种贫富差异、阶级区隔的现实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一种保障制度对这一潜在风险的控制作用。而对于封闭小区的业主来说,他们想要“安全”,却不希望“安全阀”装在自己眼皮底下,这再次说明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安全”,而是“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所谓“社会的稳定”无关,甚至与“社会”无关,它清晰无疑地建立在一种隔离之上——仿佛任何人和事,只要在小区围墙之外,在中产活动、消费的商业空间之外,就不可能威胁到他们,也因此与他们无关。
居室的幻境:捍卫家园是改造社会的前提还是阻碍?
但围墙真的能挡住危险吗?
围墙当然不能替城市中产抵挡外界的危险,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墙内建筑起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核心是“家”,封闭小区可以看做是“家”的延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关于美国底层住房问题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中,有一段对“家”的意义的阐述,应该会让很多中国人产生强烈共鸣。他说,“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他还援引了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明,对家的关心和捍卫,是普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托克维尔说,“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物,谈何容易?但如果说要在他家门口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似乎也符合张骊提出的中国新兴中产的三个关键词:业主身份、消费事件和针对私有财产的维权行动(homeownership status,consumer practice,and property-based activism)。张骊认为,中国的新兴中产正在经历一种“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一方面,他们追求私密、安稳、舒适的家庭生活,试图用围墙和其他手段将家与外界隔绝开来,营造一个“私人天堂”;另一方面,面对和地方政府、地产商、物业公司的种种纠纷,他们又不得不走出去,捍卫自己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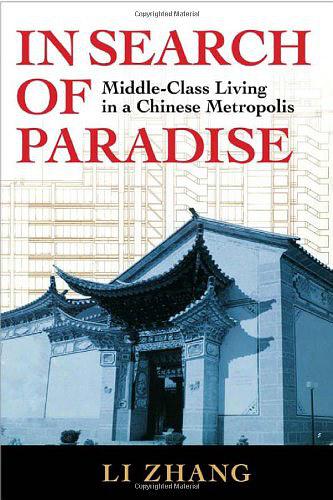
张骊 著
由于向内营造私人天堂和向外维权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矛盾和张力,这一“双向运动”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既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言,激发由小家而大家、由家而国的连锁反应,让捍卫家园成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初衷和起点,最终培育出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公民社会的土壤;同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彻底割裂公和私,甚至制造一种不断损人利己、最终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例如,在全景花园事件中,中产业主越是想把所谓的“危险”赶到墙外,墙外就越危险,就需要更高的墙来保证墙内的安全,最终家从乌托邦变成了异托邦,它成了外部环境的反面和补偿,成了城市中的一块飞地。
正如人类学家项飙在为《扫地出门》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谈到的,“家天堂”的意识背后是一种诡异的“双重异化”,“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去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居住空间——变成了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另一方面,“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成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从而“把家提到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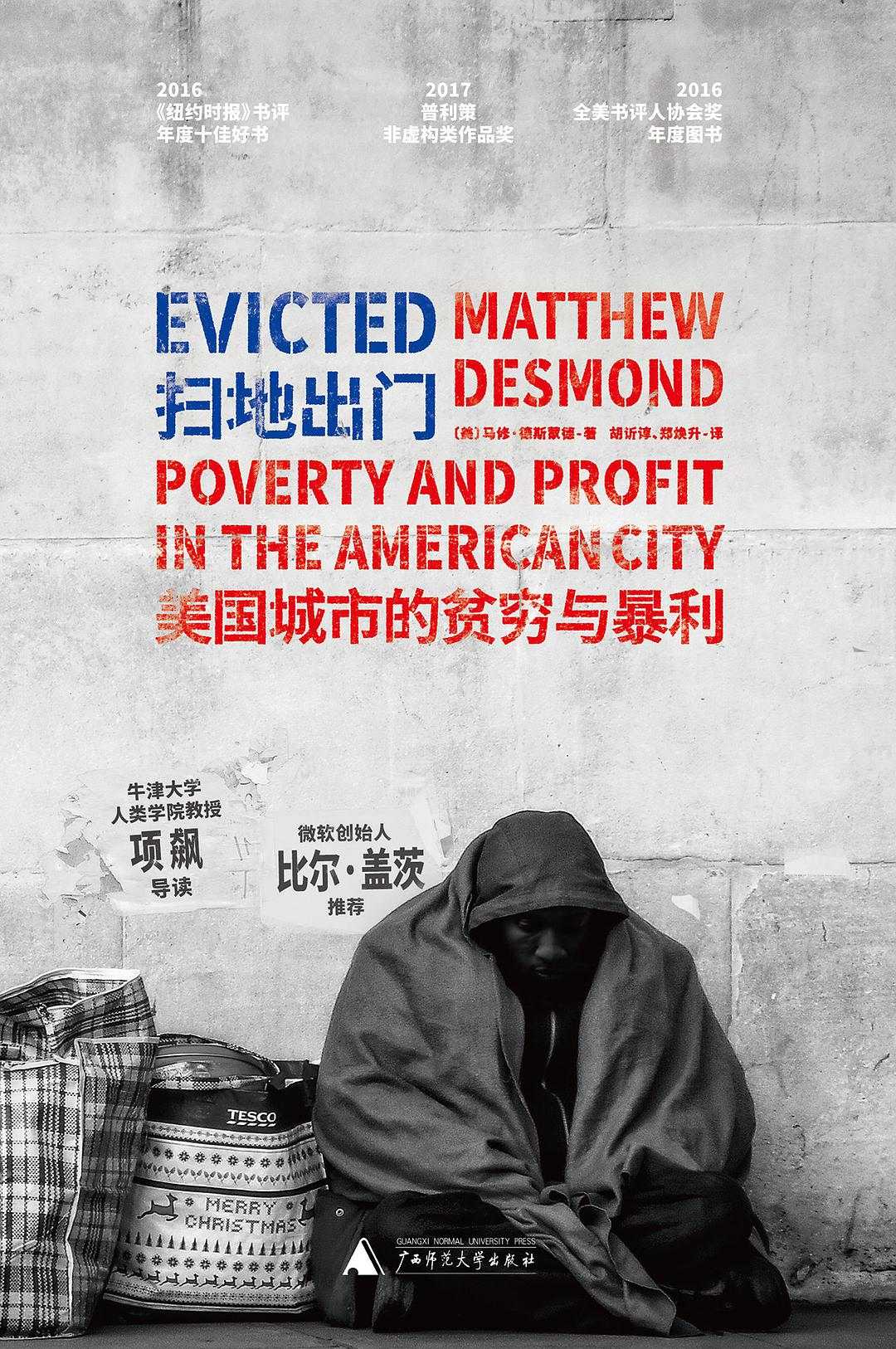
马修·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 郑焕升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项飙认为,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家神圣化,也就是把家和社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才把家绝对化成一个私人祭坛”。他也指出了一种恶性循环,可以看做是前文提到的那种恶性循环的一个推而广之的版本,即“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何人相遇交流)则成了折磨和负担”。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在“拱廊计划”中提出了“居室的幻境”这一概念。他谈到,正因为人们在办公室不得不面对现实,才需要在居室通过幻觉来获得滋养。在今天的中国,“家”这一“人之为人的基本需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幻境,或是本雅明所说的“个人生活的虚拟框架”。人们逐渐背离了个人生活的真实框架(即劳动和一种有益的公共生活),不再期待通过工作创造价值、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改造社会,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虚拟框架”的建设、享受和维护中去。更进一步说,在为这一“私人天堂”、“虚拟框架”添砖加瓦的过程中,我们在工作中更深地异化,甚至不惜破坏社会公义,与威胁、侵蚀着我们家园的力量同流合污。这大概是每一个自豪的“有产者”在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道德困境:是不是只有通过更加无所忌惮地竞争、掠夺、驱逐、践踏墙外的世界和墙外的人,我们才有资格在墙内获得片刻安全和体面的幻觉;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我们被墙内的幻境深深地催眠,信以为真,才能说服自己,去承受墙外的全部乌糟和不堪,在其中摸爬滚打、分个胜负?
但这幻境是多么脆弱啊,墙外的世界正在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暴力形式冲击、挤压着这个幻境,就算是再建起更多的墙、无数的墙,在封闭小区里再圈出一个封闭小区,在已经升级的消费水平上再次升级,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孩子就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了吗?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