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白先勇还记得9岁那年他初次到南京路时的情形。在《上海童年》中,他回忆道,“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色彩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
白先勇见到的是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南京路,而在此前的二十年间,上海的先施(1917)、永安(1918)、新新(1926)、大新百货公司(1936)就已经相继开张,它们不仅将南京路变成了上海的“百货公司路”,让传统店铺诸如澡堂、旅馆、日用品商店等默默退出;也以争奇斗艳般的手段,在橱窗里撒起雪花,让美女现场制作香皂——“逛马路”这件事已经充满着趣味。

研究百货公司的学者菊池敏夫认为,百货公司从兴起到运营,目标群体都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那么,在这幅上海百货奇观里,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群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或者说,如果人们买不起百货公司的商品,他们还会去逛街吗?针对这一问题,在最近出版的《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连玲玲提出,百货公司的确鼓励了更多顾客进入消费市场,这也使得不同阶层的消费欲望会互相渗透,显得并不那么“阶级分明”。而美国历史学家卢汉超在《霓虹灯外: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里这么写道,上海的里弄居民——他们主要由公司职员和工人构成,并不需要置身于南京路上,只在家门口,就可以满足衣食住行。 这似乎是由霓虹灯分割开来的这座大都市的两面:百货商场免费对所有人开放,邀请更多人想象更高级的消费,而里弄居民其实仍旧足不出户并怡然自得。

橱窗购物:催生“欲望的民主化”
连玲玲在《打造消费天堂》里指出,上海百货公司并不拒绝中产以下的顾客,百货商场的广告宣称“为所有的人提供所有的物品”。不仅如此,百货公司本身也已经融入了城市景观。以橱窗来说,早在30年代,百货商场就已经出现了情境式的布置:永安公司在中秋节时的橱窗里安置着一轮巨大的明月,身边有一名古装的宫女,借用的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圣诞节前夕的永安会在橱窗摆放一个白发白须的圣诞老人,旁边陈列儿童玩具;在冬季,百货公司还会把橱窗布置成雪景,用机器源源不断地由棉絮抛洒出雪花,同时摆放冬季用品。过路的人们不需进店,就可以知道商店内所推销的商品,甚至在商店结束营业之后,自带电灯照明的橱窗仍然向路人源源不断地贩卖着诱惑。

连玲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6月
百货公司不仅设置了富有趣味的橱窗,还推出了许多奇观式的展销活动,吸引消费者前来观看。例如中国国货公司在儿童节布置的儿童游乐市,将两位小女孩任命为市长、副市长,还在“市内”命名了中山大道、国货大道,以及图书馆、动物园和市长办公室,基本展现了一个现代都市的微缩全景。再有,永安公司的香皂制造表演,让两位年轻女职员操作机器,将碎皂片和香精搅拌均匀……在人们面前再现香皂制作的过程。在这样的新鲜的刺激之下,逛街这一行为本身成了本地人一项颇具娱乐性的消闲活动。而对于外地游客来说,百货公司也成为了游览上海的必游景点。在1920年代,浙江省和广东省师范学校学生的毕业旅行已经把百货公司列为参观景点之一,30年代出版的《上海游览指南》也将南京路的百货公司列为推荐观览的地标,即使没有时间购物,也应当选择一家“以观一斑”。


连玲玲认为,百货公司通过橱窗和营销活动催生了一种“欲望的民主化”,这意味着百货公司虽然主要向中产阶级以上销售产品,但也会邀请更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群加入,将消费欲望向下渗透——但在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上世纪上半叶,“欲望的民主化”能否实现问题重重。上世纪20年代《申报》上的一篇评论将这种差距归结为城乡的差异,设想假如把这样的百货商场搬到内地城镇,乡民一定是不敢进去的,“……来往顾客多系高等人民,唯其如此,故其陈设不为过分,反觉为不可少者。设移该店于内地小城或乡镇上,乡民见之,只有立于门外瞻观,何敢入内购物。”再者,百货公司的橱窗邀请路人参与观看,也招致了遮掩社会贫富差距的批评。甚至有人著文斥责,百货公司那些装饰华丽的橱窗会使人们忽略“流浪儿童的丑态”、“脚尖边的倒路尸”,忘记“这大都市中还有着无数愁苦的脸相”。
大降价和游戏场:住持和尚都想一探究竟
在明显的贫富差距背景之下,百货公司如何放下高不可攀的身段,真正邀请更多顾客进入消费?它们找到了降价促销的方法。最早,惠罗公司推出了一元部门,随后永安、新新也设置了廉价场来吸引顾客。这些公司在减价期间设立低价商品,减价期结束就撤掉。
菊池敏夫在《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里描述了南京路百货公司大减价的情景,“一到大减价的时候,南京路的上空便飘扬着无数百货公司‘原价打折 、在库一扫大减价’、‘买国货’等标语旗帜……这边的百货公司如果喊‘大减价’的话,那边的百货公司就说‘大廉价’。”一年里,虽然名目各不相同,但总会有4-5次大降价活动。后来,大新公司将廉价部门作为常设部门,置于地下一楼,进门的顾客必须每人购买一张4毛钱的门票,还可以购买地下商店的广式点心、茶和咖啡,还有便宜的意大利香肠。先施公司也在法租界专门开辟了一元商店,全场只销售五角和一元商品。
在连玲玲看来,廉价部门的常态化是百货公司试图吸引不同阶层顾客的体现。借由廉价部门,百货公司一方面可以清仓过季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低收入顾客得以消费价格档次较高的产品,从而使得低收入者模仿高收入者消费,拥戴在高收入阶层已经过时的“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菊池敏夫与连玲玲的看法并不相同。菊池敏夫认为,大降价和常设廉价部门只是为了巩固和扩大中产消费者,由于当时的经济波动,他们并不能保持稳定的购买力,所以降价行为是百货公司与这一阶层人群之间互相扶持的表现,换言之,与收入更低者关系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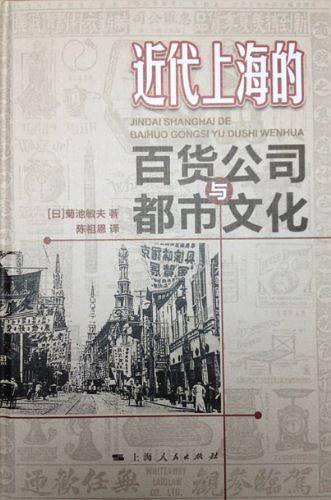
菊池敏夫 著 陈祖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廉价部门显然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据当时《妇女杂志》记载,连三昧寺的住持和尚看到国货公司的低价商品,也都想要入内一探究竟。林徽音也曾写道,上海附近江浙地区的人也会愿意趁百货公司降价的时候,乘火车前来采购大批商品。只是,连玲玲指出,这种廉价部门虽然欢迎更多人来,但它们所处的位置还是揭示了百货公司的消费分层:大新公司的廉价部门设置于地下一层,与光鲜亮丽的上层商场不同,地下一层难免潮湿、闷热,顾客购物区须与收货、包裹、开箱、散仓、机房等设施共处;并且,这里连自动扶梯都没有,顾客必须步行抵达。这里与上面的楼层明显是两个世界。
除了开设在“地下”的廉价部门,百货公司还在各自的屋顶开设了门票低廉的游戏场,游戏场里有花园、凉亭和高塔,即使是工人也可以乘坐电梯上去游玩。1922年,永安公司屋顶的天韵楼里不仅有地方戏曲演出,也会投映活动影戏,即后来的电影,此外还有各种魔术、口技、武术表演。天韵楼门票相对低廉,分为盘梯和电梯两种,价格分别为1角和2角,直到30年代票价涨成3角。对比当时知识青年每月生活预算50元,以及工人阶级平均年收入416元来看,这一价位的游戏场门票消费者还算负担得起。所以,在30年代,来往天韵楼的顾客平日里有六千人之多,周末甚至会达到九千人。

与廉价部门相似,顶楼游戏场与百货公司在接待不同阶层的顾客方面也是有所区隔的。永安专门为前往天韵楼的顾客设立了入口,使他们不需要经过百货公司就可以乘梯直达。进入30年代,天韵楼彻底从文人雅集场所变成了大众游乐场,这引起了一些文人的不满。曹聚仁就曾将当时的天韵楼讽刺地比喻成“人间伊甸园”,意在将在其中游戏的男女比喻成裸体的亚当和夏娃,将他们的互相追逐形容为“吃禁果”。也有文人注意到了等待拉客的妓女和在人堆里来往的女招待,指责她们又“卖笑”又“出卖贞操”。有些时候,一些文人也会对这些女性流露出同情,认为她们来自底层、为了家庭自我牺牲,是“值得敬佩的生活的战士”。

里弄居民:业余裁缝成千上万,购物中心就在拐角
百货公司通过橱窗、廉价部门还有游戏场邀请收入不高的工人、小职员进入,而在这些场所也不可避免地将他们与中上层消费隔离了开来,因为他们的加入会“影响”中上层的体验——有人认为,更多市民加入游戏场会使其“格调”变低。那么在霓虹灯外,这些被“隔离”的上海人有自己的生活园地吗?衣食住行又是如何解决的?
卢汉超在《霓虹灯外》里是这么写的,以公司职员和工人为主的大多数上海人,住在狭窄的弄堂里二或三层砖石建成的成排的房子中,他们的生活与其说是都市的,不如说是乡村式的,“新的一天伴随着两轮粪车沿着弄堂滚动的隆隆声开始了……紧接着就是每天令人讨厌的生煤炉的活儿……”他还写道,“里弄生活的混杂,不仅表现在居民身份的形形色色,还表现在人们将居住和各种商业活动融为一体。”所以,弄堂里不仅有工厂、学堂,也有自己的商店,人们的生活与里弄交融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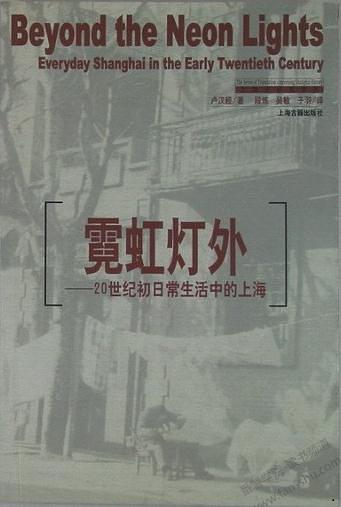
卢汉超 著 段炼 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12月
在穿衣方面,卢汉超发现,上海大多数生活在里弄的居民,是与商场消费无缘的。他们平时不会去商场购置衣物,也不会去高级时装店比如培罗蒙、鸿翔等等定制西服,原因很简单,因为价钱太高、消费不起。他们会去家门口里弄拐角的裁缝店定制,或者直接买布回家自己缝制。而具体到实际生活中,家庭裁缝的职责就落到了妇女的头上,所以妇女的裁缝本领就成了婚配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卢汉超写道,一般来说她们会裁剪衣服,还会编织绒线,就算最手拙的,也至少会缝制内衣。就连鲁迅儿子的衣服也大多是由许广平缝制的,虽然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这类知识女性不擅长做针线活。
更有意思的是,家庭妇女自己制作衣服也讲究时尚。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旗袍流行的款式每年都有变化,在这种风尚不断更新的冲击之下,业余裁缝为了紧跟风潮,也会去布店比较布匹的颜色、质地和价格,还会查阅时尚杂志,或者通过好莱坞影片来想象西方的服装样式。因此,卢汉超说,上海这座时尚之都的服装革新,不能仅仅归功于城市里一些著名时装店的专业设计师,还应当归功于坐落在偏僻小弄堂里的众多小店中的裁缝,以及上海普通家庭里成千上万的业余裁缝。
衣服自己做,小菜也要自己烧。里弄居民去不起拥有外国侍者的百货公司高级餐厅,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小菜市场。上海既有设计出来的宁兴菜市场,也有从人口稠密的地方自然生长出来的小菜场,这个菜场通常会占据马路的一部分,菜贩在竹片搭建棚屋里摆摊。卢汉超描写道,每天清晨,人们每天都能去离家不远的菜场买菜,还会彼此问候,“小菜买好了吗?”小菜场也让餐桌上的上海家常菜变得种类丰富,他们的菜单里不仅有上海的本帮八宝辣酱、肉丝豆腐羹,还有模仿西餐的菜式,比如用番茄、白菜、土豆、胡萝卜加牛肉熬制成的罗宋汤。
卢汉超在书中提到,里弄居民更不会去南京路买东西,因为他们的购物中心就位于他们生活街道的拐角。以位于南京路和霞飞路之间的宝裕里为例,这里有烟纸店、大饼店、火腿店、煤球店、裁缝店、饭馆和布店,还有诊所、学校和袜厂——在这里,“只有5%的居民在南京路和霞飞路购买大部分的物品。”如果想要获得更多选择,人们会去地区性的购物中心,这样的地方距离每个居民区的步行距离是10-15分钟,比如静安寺、曹家渡、徐家汇等等。“尽管上海人把南京路看作市中心,但很少有人觉得有常去那里的必要,”卢汉超说。而问题在于,如果平民只是偶尔去南京路,主要购物消费都不在百货公司,那么百货公司的“欲望民主化”和现代性想象,可能真的与他们相距甚远。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