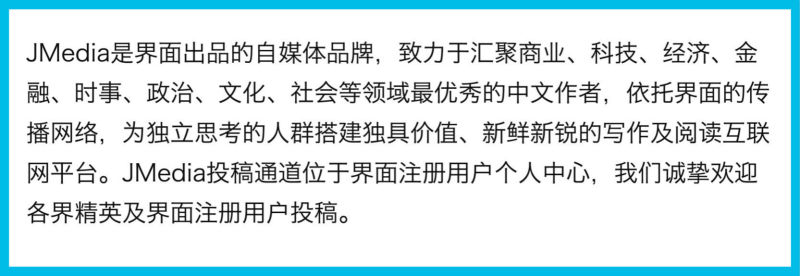1960年,大胖子希区柯克导演的psycho上映,这部电影中文一般译为《惊魂记》或《精神病患者》,一个青年同时扮演他自己和自己既爱又恨的母亲,时时刻刻自我否定:在这一时刻,他是自己,下一瞬间,他是厌弃爱子,用爱作为武器管控下辈精神和肉体的骄横母亲,在无数个独立的时间节点,他和内心的另一个“我”都是对方的分身,都在挣脱……
1997年七月一日,维多利亚湾,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先生在瓢泼大雨中努力站稳,象征英国绅士风范纹丝不乱的套装被暴雨全身浇透,黯淡的目光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缓缓降下,紫荆花旗升起取而代之。一个时代结束了,一起结束的除了日不落的帝国梦,还有彭定康幼女的香港模特梦;历史,总是吊诡的将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交互书写。
香港,盎格鲁撒克逊,潮汕文化,资本主义发展了一百多年的体制精髓和华人社会相切,排斥,交融,弹丸之地最终演变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货柜港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之珠”。他和马华衍生出的新加坡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不同:香港,英文书写文书,但全体居民过所有的农历节日,连佛诞都过;与此同时,与一河之隔的广阔大陆母亲不同,他讲究契约,法制,民主……所有这些矛盾体成就了香港之所以是香港。
155年英国殖民地历史,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国共拉锯的缓冲带,香港的每一步命运都和战争捆绑在一起,这个城市,见惯了悲欢离合,兴衰交替,所以处乱不惊;也正是因为兴亡交替,世无永恒,他讲究效率和回报,实用主义盛行,而要文明的生产,交换,便需要依赖有效司法,便捷交通,尊重契约,这一切社会的断面都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河里与由人情维系的大陆渐行渐远。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诞生有闲,作为口岸又有人口流动更替的现实基础,香港,在潮汕文化之上渐渐演进出俗文化,以粤语歌曲为发轫,民间小调经过现代艺人填词,或者直接改编经贸多有往来的日本歌曲,经过工业化的运作,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占据世界华人市场,和香港的武侠小说,黑帮电影成为华人精神产品的标杆。香港高度的流动性将这些文化带进了东南亚,洛杉矶,温哥华,“有华人处必有金庸”成为文化昌盛的注脚。
提及香港文化,自然绕不过武侠电影,胡金铨,张彻二位如果说是开山鼻祖,那么程小东徐克则将其发扬光大,香港的命数在于:他来源于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原本有可能偏安一隅,固步自封,但战争打开了香港和香港人的眼界,举凡香港文化史上的巨星都身份可疑,颠沛流离:金庸来自江浙,徐克来自越南,杜可风来自法国,王家卫则逃难来自素以精细和国际化著称的上海,所有这些元素造就,香港,讲粤语,但绝对不是广东,讲英文,但绝不是不列颠,更不是英语文化圈的印度,澳洲,香港的魅力就在于他什么都沾一点,但永远只是香港。
经济腾飞,社会转型,光怪陆离的生存乱象,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会为俗文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也诞生了以“明星效应”为基础的香港电影文化,从邵氏分离出的嘉禾以及后来的新艺城,美亚,寰亚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了电影的类型和风格,也捧出闪耀世界的巨星。
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俗文化因为成功的市场运作和票房考量,每每套了一个轻松的商业外套,但仔细探究,都可在大文化圈上寻根:志怪小说和民间传说对应以林正英为代表的鬼片,方言劝世小说为原色加上李碧华蔡澜的现代推演对应以《胭脂扣》为代表的奇情和风月,潮汕宗族文化对应以《英雄本色》为代表的黑帮电影,可以说,香港电影花虽繁茂,但根却稳稳扎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上。
香港的俗文化,是只能在香港土壤诞生的文化,歌唱演艺,电影,小报,统统接市民文化的地气,但其运作过程,统统以体系化的现代公司介入,邵氏,亚视,无线,TVB,嘉禾,银河映像,更不论《东周刊》《苹果日报》这样热火朝天的的市井八卦。
正如香港兴于人口流动,繁衍出各色市井文化,“九七回归”,亚洲金融风暴,本港经济低迷,人口外流,大陆逐步开放,经济日渐强势,欧美电影在港台逐渐放开配额限制占据主流院线,特别是港人对自我身份的迷失,让曾经在世界影坛和文化史上焕发奇光异彩,将华人文化推出国门的香港电影在90年代中期日渐式微,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焦虑感占据700万港人曾经意气风发的心,用一个片名来反应这一时期港人的心态,那就是《去年烟花特别多》,这一刻的香港人,又站在了他们的先辈曾经对抗葡萄牙人,英国人这些外来洪荒的风口浪尖上,是走,还是留?是消极对抗,还是积极融入,华灯初上的夜晚,每个港人望着这个世界第一的天际线和维多利亚湾的天星小轮都会追问自己。
2003年对香港电影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SARS事件让香港成为重灾区,受到世界瞩目,张国荣梅艳芳两位殿堂级巨星相继离世,除北京政府与港府签订合约加紧双方合作,港片再无能力吸引外部投资,港片华丽转身的时刻终于到来:众多香港电影人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北上,依靠政策利好和大陆合作,瓜分庞大的内地市场,代价是放下身段,剥离香港电影人独特的光环,放逐在大陆资本大潮中接受检验;要么则是继续留港,在艰难时世中孤芳自赏,坚持自我,这意味着对14亿人口巨大市场的放弃,偶有中间道路:以方令正罗卓瑶夫妇为代表的电影人移民海外,直接息影,以吴宇森周润发李连杰成龙为代表的电影人在摇摆时刻意欲进军美国电影市场,以西方资本重现当日辉煌,无一例外铩羽而归。
如果用一部电影可以概括香港电影和香港俗文化,《无间道》是不二之选。刘伟强麦兆辉庄文强三人组的黄金搭档拍摄的《无间道》三部曲是香港电影的挽歌,正式宣告“香港电影”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落幕。《无间道》三部曲既是挽歌,也是宣言:三部曲之三上映年份恰好定在2003年,可谓意味深长,这一年正是香港电影北上元年,第三部的演职员名单里赫然出现陈道明胡军这样的大陆一线明星,这是香港电影真正落幕的纪念时刻,从这一刻起,所谓香港电影业已不复存在,之后的彭浩翔杜汶泽等等只是:“香港人拍的电影”。
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类香港电影传奇般的故事:一个人双手互搏,与自己过招,挣脱自己,意味着涅槃,迷失自己,意味着失败和癫狂。但,人,这样一个沉重的肉身,真的可以挣脱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