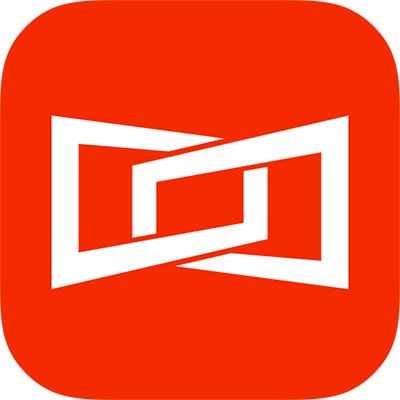作者 | 李思琪
设计 | 托马斯
很多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突破体制,再次服从体制,最终成为体制。
1988年底,还没来宋庄的唐建英,用一张床单包着自己的画,找到还没有去美国的宋伟。唐建英当时还不是艺术家,而宋伟已经属于中国最早一批有钱人,当时还是长城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馆里的工作人员对唐建英说,“稍等,那是我们的大老板。”唐建英板着一张脸,直接坐了下来,工作人员没敢坐。宋伟来了,让唐建英解释解释作品,唐建英拒绝了,“宋先生,画就是让人看的。”
宋伟盯着唐建英,唐建英没有躲,也丝毫不吝于表现他的杀伤力。
直到宋伟盯不住了,却也不回避,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往天上一扔,呢子大衣一甩,洒一身水,一拍桌子站起来,“哐!哐!哐!”比划着弹了一曲贝多芬。停下来后,闭上眼睛说,“有钱人,不是没有痛苦。”
“宋先生,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唐建英开始把画收起来准备走,工作人员出来送他,宋伟拉着长音喊了一声“好走——”。
唐建英一听,停下了,回头一指宋伟,“十年后,我让你来找我!”

唐建英的23岁,是在石家庄的钢铁厂度过。那是在圆明园画家村还没有形成的1986年,中国的美术界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85美术新潮”。
钢铁厂没有学历门槛,也不用考试,但进去了要做重体力活。唐建英开始体会到工人的命运,那种在大时代面前的无力感。
他一边与钢铁厂的危险相处,一边听到同龄人聊梵高、聊莫奈、聊印象派和野兽派。和朋友们一起去写生次数多了,他跟着画了自己的第一张画。朋友说,“你能画画,你用色感觉很好。”
对唐建英来说,“从小就没得到过肯定和表扬,这是第一次别人给我点赞,我在青春期,有着那种骄傲劲。那时候真是充满热血,充满对知识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
那个时候,他看着自己的一屋子画,听着音乐,喝着茶水,或者喝着酒,眼泪就会掉下来了。“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总有一天我要征服他们。”
唐建英在钢铁厂的危险果然来了,他的脚被砸骨折了,没法继续工作,他北上来到了圆明园画家村。把唐建英带来的是他的两个学生,他们本来想考北大,但又喜欢美术,和唐建英一起待久了,逐渐被他影响了,没有考。
就是在这期间,他与宋伟有了那一次“眼神对峙”和“十年约定”。
同一时期的北京,大约是在1988年,大街上多了一景——快餐车,宋伟把它称作“长城快餐车”。当时,进口车、私家车还不常见,宋伟每天开着这辆高大、封闭的雪佛莱卖羊肉串,一块五一串。
他说自己当时有3辆快餐车,每辆车每天大约卖掉上千个羊肉串,2000多块钱。也就是说,在“万元户”是“阔气”标志且极度稀缺的时候,宋伟已经是百万元户了。
在艺术批评家廖雯的记忆里,1989年春节期间,中国美术馆院里院外,忽然进进出出一些长头发、大靴子、“绿林”模样、表情激昂的人群,美术馆仿佛被“占领”了。那是在这里参加“89现代艺术展”的“前卫”艺术家,中间“混”着一个人,矮个方脸,黑色绒领棉大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干部”包,他就是宋伟。
筹委会没有预料到,这次“89现代艺术展”成了“中国80年代十年现代艺术的一个句号”。办展之前,策展人高名潞表示:“以前是政治上不可抗拒的原因办不了展览,那实在是无奈。但如果这次因为经济原因使展览不能开展,我将宣布永远退出美术界。”
那一年,北京市平均月工资是170元,宋伟为展览提供了赞助费5万元,还向栗宪庭表示,他打算用10万元买10件展览上的作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当代艺术。在齐中华拍摄的纪录片《宋伟》中,高名潞说,当他通知筹委会这个消息时,大家都喊“‘个体户’万岁!”
前来参展的艺术家王广义,在之后的一天下午,神秘兮兮地把另一位策展人栗宪庭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一共十沓——宋伟果然买了他的作品。
王广义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当天晚上,栗宪庭一行十几个人来到一个湖南馆子,共花了200多元。
宋伟正式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位收藏家,在此之后新的10年里,他消失了。按照自己的说法,1991年10月4日,他去了美国,这个日子对他来说很重要。那一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久被抓,紧接着宋伟所有的钱被充公。
他怕了。

1989年夏天,在圆明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唐建英撑不住了,他跑回石家庄,“就想回家吃碗炸酱面”。1990年,唐建英的“画家”身份首次为人知晓。他在石家庄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展《唐建英》,创立了“无光画派”。
河北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费正也来参观了画展,给了唐建英很高的评价,后来还经常建议他,“你不要只在河北,这里太压抑了,你应该去德国。”
90年代初,正是圆明园画家村最风雨飘摇的时候,也是中国艺术家刚刚开始在世界上展露头角的时候。圆明园艺术家方力钧在1992年“脱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新艺术展”上,一个澳大利亚人花4500美元买走了方力钧几幅素描。此后,方力钧再也没为卖画发过愁。
1993年,徐冰、方力钧等中国艺术家在威尼斯双年展上集体亮相,沾了“第三世界”的光,光头形象让方力钧成为展览上最惹人注目的中国画家之一。同年,他的作品《第二组No.2》(《打哈欠》)被《时代周刊》用作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内容的一期封面。画面中的人物光着头,张着大嘴,面目扭曲,像是在打哈欠,又像在呐喊。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把这种风格称为“玩世现实主义”,这类作品泼皮、戏谑、富有痞气。在很多人看来,与王朔的文学作品相似。几乎同时期,解构政治符号的“政治波普”风格、批判“消费主义”的“艳俗艺术”也出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在20世纪末叶迎来了在国际上的大爆炸。
1993年,没有工作的艺术家们本就被视为社会上不务正业的异类,再加上当时几起艺术家与公安部门的冲突闹得满城风雨,遣散圆明园画家村的消息不断传出。
那年岁末,方力钧等人开始商量着离开圆明园,在张惠平一位叫靳国旺的学生推荐下,他们来到了北京市最东边的宋庄。1994年,第一批圆明园艺术家在宋庄开始买房,圆明园画家村失去了“定海神针”,最终于1995年10月解散。
1994年,宋庄小堡村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刘炜买了两个院子,把其中一个送给了栗宪庭。当时的价格是5000元,栗宪庭称之为“刘炜的厚谊”。同样来自圆明园画家村的岳敏君第一次去小堡村时,赶上六级的大风,飞沙走石,尘土飞扬,到处堆有垃圾,房子大都破败不堪。
这些画家们当时实在没地方去了,小堡村也由此成为最早的画家村,现在被称为“核心区域”。“核心区域”中最核心的小堡商业广场向东8公里,就跨出北京属于了燕郊镇。
在作家陈湘鹏的描述中,“京榆旧线一个小路口的蓝色路牌上写着北京界,前面是河北燕郊,身后就是北京通州。燕郊行宫东大街上的满树霓虹灯,有心使北京难堪,它们携道路两侧的高层住宅区,热闹地围着北京的难民们:欢迎来到河北。艺术家们决定保住北京的文化身份,没有再跨过这几公里。”
在20年前,另一位作家马越,却一不小心就跨过了这8公里。1997年11月,他第一次去宋庄,打算跟着香港回归的步伐,自己也回归到圆明园流浪艺术家的阵营。当时的930路分成了区间车、城建新村线和燕郊线,车子开动,他才发现乘错了车,最终在高速上一路经过了宋庄灰蒙蒙的村庄,来到了燕郊酒厂,“那种心理,也挺有意思。”
在世纪末富起来的,不只有艺术家。有一位在外资画廊做画框的木匠,工作久了认识了不少画家,创造了一桩生意——做艺术年鉴。当时还很少有人做艺术年鉴,他靠把版面卖给艺术家,一下发了财,收藏了很多名家的画,最终在宋庄建立了自己的画廊和艺术网站。
做完个展后的唐建英,感觉到石家庄“盛不下自己”,带着画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几位雕塑系一年级的学生在打乒乓球,一看就是初学者。唐建英走过去说,“帮我看看画吧?”
“等会,打球呢。”等学生们打累了,擦擦汗,“把画拿来看看吧。”
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在这几个学生的帮助下,唐建英的作品在油画系的朝戈、毛焰等人之间传看。愿意帮助唐建英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再回到石家庄后,他有一次跟着在北京开公司的发小来到宋庄,看到了宋庄一些靠卖画致富的画家,感受到了贫富的两极,他坐不住了。
2000年,唐建英38岁,离婚来到宋庄。他在宋庄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被称为“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后者看了他的画说,“画的不错”。唐建英更坚定了,他要留下来。
来宋庄后的一次饭局上,他见到一个人很眼熟,但那个人一直在躲着他的眼神。唐建英问,“您是姓宋吗?”对方摇摇头。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在卖画,过去问,“宋先生,您开个价吧。”宋伟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宋伟,开价300元。
后来,唐建英又给宋伟买了不少衣服,宋伟穿到外边总说,“这衣服,建英给的!”

2000年的宋庄,还只有七八十个画家。路上还没有路灯,整个小堡村只有一家饭店,叫“四合饭店”,大家去的时候经常是AA制。
很多艺术家在刚来的时候经历过偷房东的面、捡早市之后的白菜帮、白水煮面的日子。在许多晚辈的想象里,这样“穷且志坚”的经历被浪漫化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自我沉醉。
唐建英却摇摇头,“贫穷是很可怕的事。”
他这次来北京后,画的第一幅画是抽象化的“天安门”。在黑色的画布上,几抹红白相间的线条。那之后不久,他开始了最有代表性的《规矩》系列和《网》系列创作。
《规矩》系列中,他画了许多瞪着惊恐大眼的男人,脸上还有伤口,穿着灰白色的囚服。他想表现出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集体无意识,“他们都想做一个个规矩的人,这里有驯服的结果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教化作用。”
这些作品不“玩世”、不“波普”、不“艳俗”,不同于宋庄最主流的绘画风格。如果说宋庄是一个江湖,他把自己比作装疯卖傻却武功高强的“老顽童”周伯通。
在宋庄,第一个买唐建英作品的人是从圆明园来的画家高惠君。高惠君在一次展览上向唐建英询价,唐建英开价100美金,但他想了解一下自己画的走向。高惠君说,跟你说实话,我买。唐建英说,真是你买的话,给500人民币就行了,但是你画这么好,怎么买我的?高惠君的理由是,我想吃点辣的。
宋庄的艺术村落慢慢聚集,在酝酿了四五年后,艺术市场又一次的涨潮在2005年前后来临了,这一次的购买主角中,多了一部分中国的收藏家和投机者。唐建英的工作室来了一帮人,一放就是40多万现金。
他的脑子一下就懵了,又要强装镇定,“让我捋一下,这画有点大,让我考虑考虑。”
2005年的第一届宋庄艺术节是一个分水岭,很多艺术家的作品被全部打包买走了。其中最受收藏家欢迎的,仍然是那些“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和“艳俗艺术”作品。
这一次富起来的人,比90年代多得多。曾有一位艺术家,常把其他成名艺术家的形象与其常用视觉符号结合在一起,画在一幅画上。有一次卖画的时候,他没有开价,问顾客,你觉得值多少钱?顾客说,500。他说不行,500太低了,你给800。
为了这次的艺术节,组委会开始征集宋庄的logo。最初收到的300多个作品都不满意,于是又找了很多专业院校和专业专家组织设计。最后,栗宪庭定稿了艺术家杨洮的设计,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杨洮是宋庄当地艺术家。
有关这个logo诞生过程的报道并不多,还曾被错误地记录为,“栗宪庭找了村里几个艺术家,采用上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流行的错体字,把’宋’和’庄’两个字结合起来。”
在设计的过程中,杨洮以致敬中国艺术家徐冰作品“天书”的方式,把“宋”的最后一笔捺改成横,造出的新字里有“宋”、有“庄”、有人才的“才”、主人的“主”。设计完成后,由政府买下,杨洮拿到了1.5万元的费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个记者问杨洮,“你把那一撇改成一横,就值这么多钱?”杨洮一听有点烦,“你改改试试。这一横是多少年的审美和判断力的积累,很多东西都在里边,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跟这些人没法说。”
同样由杨洮为这次艺术节设计的,还有至今仍矗立在被称为小堡村“长安街”的徐宋路南端的“大牌楼”。那是他的不锈钢雕塑作品。原本是仿照凯旋门设计,又因为这里是画家村,就做成了画框的样子。
杨洮将这件作品命名为“宋庄之窗”,窗子上签了他的名字。从2011、2012年前后,大牌楼被整个覆盖住了,年复一年,有时是标语,有时是活动海报,雕塑上的纹饰不再被看到。
在2008年的报道里,这座“宋庄之窗”被称为“大铁门”,并且被认为非常关键。因为在它建立起来后,徐宋路上的饭馆越来越多,使宋庄镇原本唯一的饭馆“四合饭店”关张了。不过,杨洮并不知道自己的“大铁门”有这样的影响,虽然他2000年就来了宋庄,但只去过四合饭店两次。
如今“大铁门”所处的位置的确很关键,就连最具宋庄特色的大标语牌也在这座牌楼的对面——“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杨洮的作品也在那一次艺术节上被艺术策展人程昕东全部买走了。程昕东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法国的第一人,早在1996年就在法兰西画廊策划了《四点交汇:张晓刚、方力钧、顾德新、张培力展》。
杨洮那一批作品是把文革时期的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剧照与体育运动项目结合起来,因为文革与奥运都是运动,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他想以此构成一种反讽。
一系列的成绩让杨洮获得了宋庄镇2009年文化创业产业学术贡献奖,当时只有四人获奖,栗宪庭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最终,杨洮没有用任何一种神话式的说辞来总结这次涨潮,而是说“有些东西没有跟好那个节奏”。
“是作品上没跟上那种走向吗?”
“不是,是在社交上。我的作品也属于有点个人符号,但是我们很多艺术家不太会沟通,会比别人慢一拍。”

更多的艺术家开始买房了,唐建英却没赶上。他曾申请过一个东区的房子,25万。他去请农民吃饭,吃完后放了一条熊猫烟,对方剔着牙说,“谢谢啊”。再听说消息时,地已经分完了,没有给唐建英留。这位艺术家想去要个说法,有人劝他,“你请吃饭了?我们都给红包了,给两三万的都有,人家谁还没吃过饭啊。”
工作室的租金价格也在疯长。唐建英在宋庄路附近租过一个工作室,400平米,一年3万。住了三年后,房东提出让唐建英先搬出去一段时间,等他重新装修一下再回来。装修是为了把这一大间工作室分隔成三小间,每一小间的租金一年就是3万。
2004年,一个农家小院每年的租金是五六千元,2008年是一万五六千元。2007年底,小堡村的总产值6亿元,上缴国家利税2000多万元。宋庄西部区域高端商品房价格接近万元,与宋庄紧邻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房价从2000元飙涨至五六千元。
2005年艺术节前夕,小堡村宣布在村北拿出400亩地兴建艺术园区时,提供给画家建工作室的土地价格是10万元/亩,4年之后也涨了两倍。
时任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甚至画好了更宏伟的蓝图:2006年~2020年,宋庄镇将腾出大约4万亩集体建设用地,按照10万元一亩的价格,这就是一笔40亿元的收入。按照当地通常出租给艺术家建工作室的价格,将有120亿元的收入,平均到宋庄镇5.6万农业人口中,将给每个人带来7万元到30万元的收入。
然而,一切想象在2008年戛然而止。唐建英的一个31万元的单子被取消了,当时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人们说是金融危机,但他觉得“怕什么,老子来的时候就是金融危机。”
唐建英养的藏獒黑子才到他家一年,在此后的11年里,唐建英为了照顾黑子,从没有离开宋庄超过一周。正如艺术市场的一波浪潮终会过去一样,藏獒的价格也在达到至高点后突然落下了,从十几万掉到了几十元。
2009年,小堡环岛拆掉了工业感十足的雕塑,请艺术家方力钧来设计新的雕塑——形如一座倒扣的喇叭,从底座到顶端依次使用土、砖、瓷、铁、铜、银、金七种材料。
大家叫它“大喇叭”、“大锥子”、“金字塔”、“七色环”,或者直接称其为“雕塑”、“环岛”。一块不大的牌子上标明了它叫“土生金”,设计者方力钧在牌子上解释了它寓意的“等级观念”:材料的自上而下排序是人们习惯的排列。虽然雕塑所选材料出自自然,人们还是将其区分为高下等级,乐此不疲。
很多人注意到,金属在阳光下泛着不同颜色的光泽,而最底层的泥土屡屡受到雨水的侵蚀,也最少被人注意到。
没办法,人是社会性动物,其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等级观念。
2005-2008年的潮涨潮落中,宋伟再一次消失了。这一次不是他又离开,而是人们把他遗忘。宋伟很少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有关文献里,因为当越来越多的收藏家给艺术市场真金实银的推动时,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地给艺术家“开条子”。
最早是在1997年,他在栗宪庭家听大家聊天,说到没钱办展览的时候,宋伟忽然说:“老栗你现在做展览还没有钱吗?我给你开个条子。”于是拿过笔纸,写道:“请给栗宪庭展览经费一个亿!宋伟。”栗宪庭和妻子廖雯开始感觉到宋伟的异样。
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宋伟不断地给他看好的艺术家开条子,有的五千,有的一万,有的一百万。他先后被诊断为躁狂症、精神分裂症,也一直在河北省第三精神病院、北京通州精神病院、回龙观精神病院、宋庄敬老院、顺义精神病院等地辗转。
他从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至于开的那些“条子”,他曾说“它是精神鼓励,相当一个、一个、一个……相当于解放前皇帝给的镇金。”
妻子和宋伟离婚了,后来又有女艺术家来和他同居。在这期间,宋伟陆续把早期收藏的画作卖出去,等画卖完了,同居的女艺术家也走了。
2013年,网上开始传一张照片,一位皮肤黝黑的光头男子坐在路边,光着膀子,身上还有点伤。中国第一位当代艺术收藏家宋伟,开始了他在宋庄的流浪。

如果艺术家不出门,潮落之后的宋庄就和任何一个农村看上去无异。
1993年出生的艺术家向帅在2013年来到宋庄,和老师住在村里,“我师母在望京带孩子,不过来,于是我们两个男的,还有一条公狗,在一个两亩地的院子里,天天工作、画画。我早晨出去买个菜,村里那些老太太聚着聊天,七八十岁的老头骑个三轮车,骑贼慢,你去买个菜回来,感觉他才往前骑了一点点。见过最年轻的人,是村口一个卖豆浆的、40来岁的大姨。这就是生活,节奏好慢好慢。”
1992年出生的木石在2017年来到宋庄,一年后,终于在宋庄认识了第一位90后。对方感到很惊讶,问他,这里的年轻人确实很少,但真的有这么夸张吗?木石解释说,没有在美院学过美术,在这没有同学的圈子,所以真的有这么夸张。
木石从不说自己画的是“国画”,而说是“水墨”。他使用毛笔和宣纸,因为这是他最熟悉的工具和材料,但真正想创作的却是更具先锋性的当代艺术。他把老家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形容为“五四运动的风没有吹到的地方”,这个小县城里很多人会画画,但画一些娇艳富贵的牡丹或是一幅客厅摆的山水画,就已经是所谓的艺术。
无论对人还是对艺术,家乡都无法包容个性的存在。
不过,就在他来到宋庄的年景里,宋庄所特有的独立性和创造力也正在消失。这一现象是从2012年后变得明显的,那一年国家画院的院长来到宋庄,找栗宪庭陪他吃饭,饭桌上,领导们说,“要把国家画院的大旗插在宋庄。”
栗宪庭的心一下子凉了,民间宋庄的生态终于还是遭到了“入侵”。
2013年,方力钧被聘为国家画院当代部主任。连宋庄路和徐宋路交叉点的商店老板都发现,他来宋庄7年之后,虽然整体形势日渐在萧条,但为国画家服务的刻章店却越来越多,从一家增加到了二三十家。
木石第一次来宋庄的时候,先去找了和他是老乡的艺术家陈震生。陈震生建议他,如果想来宋庄,不要像很多人一样只呆一两年就走,画画很难短期内获得高收入,这一点要做好心理准备。于是木石就来了,和很多留下来的艺术家一样,画画并不是他的唯一收入,凭着以前开书店的经验,他至少能靠卖书生活下来。
很快,他发现了真正难以解决的困难。传统艺术的圈子喜欢标榜师承出身,当代艺术需要符合某个时期的特定潮流,他有时候会学习所喜欢的国画家的风格,有时也和当代艺术家们交流,但很难说,他到底属于哪一派。
一边是难以看清的宋庄形势,一边是强烈的好胜心,他陷入了新的困境。“我决定要从事艺术的时候,是从传统意义上的体制里出来了,但现在又进了另一个体制。可是其实我也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体制,我在宋庄也只是一种边缘的状态。”
木石来到宋庄的半年后,有一次经过“土生金”,发现它的北面有一个入口。里边很脏,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进去了。楼梯有三圈,顶上有一个很小的平台,周围是几个三角形的窗户。
在小堡村,那是一个制高点。由它向南北和东西方向延伸出去的徐宋路和潞苑北大街,是小堡村最宽阔的两条路,周围都是标志性建筑,但在“土生金”的小窗户里向外望的时候,木石找不到方向了。
一位曾建议他专注于传统艺术的朋友,相隔一年再见时告诉木石,“你现在这样真好,我三年前被国画界泰斗的一句话给害了,他说,’行,不错,能出来,你不比他们差。’”
唐建英在这几年也认识了一些青年艺术家,这些年轻人经常会邀请唐建英来看看自己的画,给些指点。他去看了,有时候看得心疼,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条件。
有一次,他面对一对年轻夫妻,很多话实在没法说,只能问他们这是哪买的沙发。年轻夫妻说不是买的,是捡的,唐建英说,“这就对了,不要买,不要花钱……贫穷是很可怕的事。”

按照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大约10年一次繁荣的规律来看,下一次的繁荣马上就要来了。
很多艺术家希望,不要再错过这一次的浪潮。他们等着、等着,还没等到任何艺术市场繁荣的迹象,却在2017年冬天得到与之相反的消息——通州区被指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
如今从小堡商业广场向南8公里,就是正在建设的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比艺术家们更敏锐地捕捉到形势变化的是当地村民,因为“要拆迁了”。4月28日,艺术家张海涛在2001年花3.5万元买的房子,被房东强行闯入。房东解释说,去年,他在微信上看到国家要对农村土地“确权”(农村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消息,要对农村宅基地和农房所有权进行登记造册,他心里一顿,觉得形势不妙。“国家不出台这个政策,我也不会想要。要确权那是国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房屋产权矛盾在宋庄一直存在,在整个北京周边也一直存在,但这一次的争夺却格外引人注意。如果这次的拆迁风波继续扩大,受到波及的不仅仅是当地的买房的艺术家和房东,还有更多未立稳脚跟的青年艺术家、背井离乡的外来务工人员、卖不出画只好在当地转行的画家和所有打算借宋庄招牌发展文化产业的人。
2018年5月1日早晨五六点,宋庄镇的某一村口聚集了两三百人,成了临时“劳务市场”。他们等着被不断到来的私家车带到北京的各个工地,男人一天少则挣230,多则挣280,女人一天只有150左右,甚至有时候还没拿到工资,就被包工头强行打发走了。
一天10个小时体力活后回来,还不知道明天的工作在哪里。这一天,由于是法定节假日劳动节,来“趴活”的人更多,包工头给的工资就会更低。
面对一波一波前来询问的媒体,他们已经有了最基本的防备。第一反应是,“你能不能给我拍张照呀?”紧接着就问,“我们不会被赶走吧?”这个可是谁也不能保证的,这些务工人员中没有曾经的艺术家。
在宋庄有人数超过1万人的艺术家,以及更多无法计数的艺术相关从业者中,很大一部分人以难以被人察觉的方式生活着。
有的画家开起小饭馆,饭馆里放满了卖不出去的作品,养活自己的同时,没少接纳吃不起饭的艺术家。有的画家转行送外卖,成为了少数能感知宋庄淡季、旺季的人:3月~6月、9月~次年1月是淡季,每天从早上10点熬到晚上12点,只能接20多单,其中大多是送往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寒暑假是旺季,因为会有很多学生来参加各个画室的集训。不论淡季还是旺季,这位画家外卖员很少看到画家订外卖。
来到宋庄11年的策展人吴幼明说,不要问艺术家“为什么不成功”,就像不要问一个人“为什么没有活过100岁”一样,宋庄的成功艺术家(仅只经济上的成功)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了,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宋庄不断地分裂,分裂为一个个圈子、一个个阶层,没有谁能充当“最了解宋庄”的人。但就在我以为宋庄的集体记忆正在消失,那些曾经有影响力的人正在被更年轻一代所忘记的时候,杨洮提醒我,“崔健说过一句话,’只要天安门上还是那张像,我们就都是一代人。’”
就是这一代人,在一些已经记不清日子的夜晚,把尼采的酒神精神诠释得极为恣意。尼采所谓的酒神状态中,通过类似酒精之类的麻醉剂或其他使人迷醉的状态,人们暂时忘却自我,达到一种自弃的状态,从而与世界意志融合,使人们领悟到生命永恒轮回的真谛。酒神状态是人们原始生命力的张扬,是生命本能的热烈的释放。
女艺术家李亚松喝到兴致正好,一字一顿地讲,“艺术,就是灵魂,从肉体,抽离出去的产物。”对面另一位艺术家一拍桌子,“是肉体从灵魂抽离出去的产物!”
唐建英喝多了,在只有9张桌子的小饺子馆里,把身子往前探了一点——三十年前与宋伟对峙的眼神似乎又出现了——“我要小声地给你们朗诵一首尼采的诗。’人生乃是一面镜子。在镜子里认识自己,我要称之为头等大事。哪怕随后就离开人世。’”
90后艺术家木石喝醉了,从小堡商业广场沿着徐宋路一路向南走,“谁说我还没成功,我成功了,我就是成功了。我不再是小县城里一个月领600块钱的临时工。我以前的那个单位,在一条小胡同的尽头,胡同有几百米长,只有两米左右宽,就像被规定好的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头。我现在能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了,我想让家人知道我现在过得很好,但一想到更多的时候是靠卖书而不是靠卖画,我真不愿意这样。”
午夜的宋庄,只有洒水车不断地从他身边经过。“想想以前刚来那会,总想着出人头地,还想着成为下一个方力钧、岳敏君。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说着这些话,他走出了写着“中国·宋庄”的大牌楼。
牌楼上的“SONGZHUANG CHINA”已经掉了几个字母,没有人去修。
三声原创内容 转载请联系授权